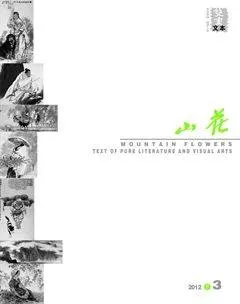试论元杂剧《连环计》与明传奇《连环记》人物之异同
在风起云涌、变化频仍的三国时期,诞生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难免附会人们的想象,以满足世人的英雄情结和猎奇心理,于是便衍生出许多历史中本不存在或是经过大量夸张渲染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载体,如在元杂剧中,三国故事便是主要题材之一,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都大量入戏。吕布虽然在三国历史上的作用不如曹操、刘备等人重要,在戏剧中的分量却丝毫也不逊色,因为他的事迹天然符合了人们对于英雄美人类型故事的心理期待。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便是将人们耳熟能详的吕布戏貂蝉的故事敷衍为王允运智除董卓。而明代戏曲家王济更在前代戏曲创作基础上将小说创作的成就融入其中,创作出传奇《连环记》。二者在内容主题上有相同亦有相异,但同多于异;在人物塑造上则异多于同,打上了创作者鲜明的时代烙印。
郭英德先生曾将元杂剧《连环计》归入“情节戏”,谓其“情节多曲折变化,在情节中刻画人物,富于动作性,是所谓‘戏包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传奇《连环记》则有融人物戏、情节戏、武戏三者为一体的倾向,既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描写了曲折生动的情节,还充满热闹的武打场面。与杂剧相比,传奇人物形象要丰满许多。
反面人物中,董卓可为代表。无论是在杂剧还是在传奇中,董卓无疑都是一个典型的乱臣贼子形象。杂剧第一折,人物出场时的宾白:“官封九锡位三公,走追奔马显英雄,文武官员闻我怕,某中心不老汉朝中”,“某每回临朝,将我这腰间的剑锋露四指,雪刃吓文武群臣,人人失色”,[哪咤令]曲后复云:“某家看来,朝里朝外,除我一人,再有谁敢和我做对手,我就着他立生祸殃,身家也不保,九族不留。” 这些道白赤裸裸地将董卓残忍霸道的性格和想要唯我独尊的擅权野心表露无遗。他能够感觉到王允的威胁并派人跟踪提防,突然造访吴子兰,说明他也有些心计,只因称帝心切,且又贪恋美色,才失了防备。如第一折中突然造访,本可识破王允,却被认可他夺位的一番言语糊弄,相信了王允。在传奇中,对董卓的刻画更复杂一些。第三出《观灯》中董卓上场的宾白“洛阳眼底无天子,金坞行中多玉人”,恰是对他贪权、贪色的准确概括。传奇中的董卓较杂剧更为狡诈。在杂剧中,他几乎是被人奉承、提篡位之事就言听计从,甚至对王允也失去应有的警惕。但在传奇中,他始终不完全信任王允,如第十九出《回军》中对王允送紫金冠给吕布的动机表示怀疑,断言“那王司徒乃奸诈之人”。再如,第二十六出《掷戟》中,与吕布发生冲突后他对李儒说:“去问王允这老儿,说貂蝉送与我,就说送与我;说送与吕布,就说送与吕布。一个人送得来不明不白,使我父子在家拈酸吃醋,是何道理?”并质问貂蝉道:“为何的,低头倒在人怀里?”、“全不顾纲常是与非”,这显然更符合情理。杂剧中这一段落却没有表现出他的任何怀疑,见到吕布便直接发生冲突。
吕布在杂剧中算是中间人物,但在传奇中作者则更倾向于将他塑造成反面人物。杂剧中将他安排成与貂蝉原为夫妻,因战乱失散,表现出他颇重感情的一面。与貂蝉重逢在王允家时做“哭科”,云:“貂蝉,兀的不想杀我也。”被王允撞破时连忙说“不干他事”,怕怪罪貂蝉,哀求道:“老丞相可怎生可怜见,着俺夫妇团圆呵,吕布至死也不忘大恩也。”这一番话出自一个骁勇善战的七尺男儿之口,足见他对貂蝉的情深。他虽然勇武,“虎牢一战兮众皆靡”,但缺乏谋略,意气用事,容易冲动。他对王允与貂蝉没有任何怀疑戒惧之心,当然这与貂蝉是他的妻子有关,但还是少了一些思考判断。传奇中,情节的增添让人物更加丰满。一方面,通过更多细节突出吕布的勇武;另一方面,在第十九出《回军》中,他兵败之后谎称得胜而归,董卓说了他几句,他还“发恼使性”,不仅说明其虚荣心很重,而且还容易被激怒、被利用,为后来的反目埋下伏笔。同时,作者还增加了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两个弱点:贪财、好色。杂剧中只简单提及的丁建阳认吕布为养子事被敷衍为《说布》和《刺父》两出戏,表现出他目光短浅、贪图名利,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当董卓遣李肃送礼给他,他便改口称:“吾闻太师奸恶,与丁建阳引兵来此征讨,他原来是个好人”,“太师汪洋度量,敢不敬从所招”,很痛快地答应为虎作伥,正如李肃所料“利动他心便着迷”,这是贪财一面。与此同时,传奇改变了貂蝉与吕布的夫妻身份,从而使吕布与董卓反目成仇,只缘于一个“色”字,便如王允所说“观此二人(吕布与董卓)皆溺于酒色”,这为美人离间提供了可能。此外,传奇作者改变了吕布有勇无谋的一面,曹操献剑他起疑心,成亲一事他问完王允,仍不相信,复问貂蝉,当二者说法一致,他却是“只恨我关上来迟了”,“早知道相见难为情思也,何似当初不见高”,竟说出“你好生服侍太师去罢”这样的话,直到貂蝉以死相逼,才表明要娶她的决心。这样的吕布显然比杂剧中更有心计,同时也更自私怯懦,人物形象更复杂,也更负面。基于这样的性格,离间他与董卓,使其甘冒风险、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更困难,也使王允的智慧与貂蝉的牺牲越发得到彰显。
王允在杂剧中应该算正面人物的代表,但也有不完善之处。在杂剧中他虽然是“一点丹衷似石铁坚”,但同时还有“加官赐赏”、成就功名的想法,一开始也不愿独自承担皇帝意旨:“董卓权重势大,老夫有何才能,可请众官来商议,共灭此贼方可”,连环计也并非他个人谋划,有太白金星暗示和蔡邕指引。同时,他还有浓厚的封建道德伦理意识,不仅自己做出掩在湖山石边偷看偷听之事,当听得貂3Vq88Uy29l2CdfawuLjgEw==蝉烧香祷告内容时,唱道:“我则道他为疾病,却原来耽闺怨,方信道色胆从来大如天”,“我见他泪痕儿界破残妆面,我可甚治家能治国,敬愚不敬贤,顾后不顾前”。佯装撞破二人相认,冲上去斥责道:“你畅好是私情的忒自专”,“你这个贱媳妇无断送”,“你走将来卖俏行奸”。也许由于元代是中原文化的断层期,儒家思想淡出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起码不为蒙元统治阶级所认可执行,所以下层汉族文人才会在作品中表现出儒家的道德说教,如男女之大防等,以示对蒙元统治的不屑和反抗。应该承认,我们今天看到的元杂剧,除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之外的这些本子,都是经过明人整理的,多少会有一些改动,带有明人的痕迹。但就这部剧而言,与臧懋循的《元曲选》相较,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更多带有剧团演出本的特点,文字相对粗糙,曲子无论从完整性,还是字句提炼用韵,都远不及臧本,宾白也更粗俗,更口语化,演出的程式化也更鲜明(如某人前去某地必说一句“……走一遭去”,到达时必说“可早来到也”等),这些都跟《元刊杂剧三十种》有相近之处,而与臧本有很大不同。因此可以推断赵琦美所校息机子本中的这部剧还是相对忠实地保留了元杂剧的风貌的。
在杂剧中,王允对待貂蝉的态度并不像一个父亲对待女儿,而如同对待自己的一件附属物品,对她缺乏应有的爱惜和尊重。他在不知内情时斥责貂蝉:“你怎生道‘夫妻每早早的团圆’?哪个是你丈夫?从实的说,若不说,令人准备着大棒子者。”后来设计宴请吕布“捉奸”时骂貂蝉:“你这个贱媳妇无断送”,骂两人“卖俏行奸”。貂蝉向他诉说了拜月祷告原委后,他唱道:“谁承望,俺家里搜寻出这美女连环。到来日开筵,我脂粉内暗暗的藏着征战。我施计谋,他怎脱免?”王允心怀家国乾坤、社稷江山,却未充分考虑貂蝉的感受,只把她当做一个可使连环计的美女诱饵。他虽允诺“我着你夫妻美满,永远团圆”,但是有先决条件的,不过也是诱使貂蝉从命的饵料罢了。不仅如此,还搬出一堆冠冕堂皇的道理说教:“春秋之间有鱄诸之妻替夫主成其大名,公孙胜妻举夫应梦,乃得世代光辉”,“你如今替你父亲掌此一计……儿也,休顾那胖董卓一时春点污,博一个救君王万代姓名香”。刚才还在训斥貂蝉“耽闺怨”,与吕布“私情忒自专”,现在却连他那套封建道德伦理都不要了,只因为能成全他的计谋,能让他“忠心得意专”。这有似威逼加利诱的态度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起码不像一个情义兼备的男人所为。
在传奇中,王允则完全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正面典型。程朱理学虽然在明代一直被统治阶级所提倡,但从明中期开始,随着经济领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文艺上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文艺是未受封建‘闻见道理’污染的纯洁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