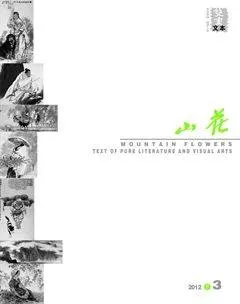余华和海勒的黑色幽默比较研究
余华小说中呈现了很多黑色幽默的因子,本文以《兄弟》和黑色幽默代表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探讨黑色幽默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以及余华对黑色幽默的运用呈现出来的同质性及不同于西方的特质。
余华和海勒创作的相似背景
一、相似的时代环境
黑色幽默小说的产生与60年代密切相关。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持续不断的动荡及新科技的发展使海勒经历了沉寂、愤怒、文化喧嚣的时代。有评论家把50年代到70年代称为“美国历史上的荒诞时期”[1]。海勒参加了“二战”,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带有颠覆美国政治的意义。相似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革”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余华说,《兄弟》要写这样两个时代,“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2]。可见,无论西方的“二战”还是中国的“文革”、市场经济,都给人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似且严酷的政治气候加深了两位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黑色幽默”成为余华对抗外部世界的方式。
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黑色幽默文学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弗洛伊德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其影响颇深。黑色幽默作家极端地审视现实,面对世界的混乱觉得无可奈何,只有“通过一种病态、自嘲、可笑的幽默手法来排除他们心中的不满、愤怒和绝望”[3]。于是蕴涵虚无、异化与荒诞色彩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成了他们创作的基础。
黑色幽默对中国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作家自觉地将西方黑色幽默与中国当代的历史、现实相结合,余华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存在主义哲学直接影响了二者创作的相似性,他们都用当代人充满疑虑、揶揄和冷峻的目光审视现实。
《兄弟》表现出的与西方黑色幽默的同质性
《第二十二条军规》包括军规在内的所有令人发笑的情节都造成了对理性的怀疑和挑战。《兄弟》中李光头带着宋钢骨灰上太空的细节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宇宙中人类的生存注定孤独。下面就来具体分析《兄弟》表现出的与西方黑色幽默的同质性。
一、以荒诞应对荒诞的主人公
黑色幽默作家紧紧扎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的荒诞想象适应了荒诞的现实。这深深影响了余华的创作,他曾说:“有时候荒诞比真实更加接近真实。”[4]他通过荒诞来写现实,当主人公既无法与现实正面对峙,又无法质疑世界的秩序时,只好选择以荒诞应对荒诞。
当尤索林一丝不挂地面对授勋的将军时,他的玩世不恭使死亡、战争这样严肃的主题失去了传统的意义。李光头和尤索林一样荒诞至极。他从屁股大王到破烂大王,再到刘镇的GDP,其成长之路充满了反叛,生存在李光头身上成了一场闹剧。他的生活逐渐走向荒诞,而荒诞最大的表征就是文本中狂欢化的叙述。
作为福利局局长的李光头带领手下的瞎子、瘸子组织成一支奇特的队伍向林红求爱的场面何其荒诞,以致守门的老头说了一句幽默的话:“我还以为是毛主席来了。”[2]李光头致富后,无数想争财产的女人抱着孩子在他公司门口哭诉,最后在法庭上演闹剧;从全国各地来的记者对李光头进行采访,李光头声泪俱下地哭诉自己的童年史、爱情史和创业史。这里余华笔下的人物将自己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发泄到对生活极不严肃的态度上,令人哭笑不得,同时对他们的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这是他小说中黑色幽默的典型意义。刘镇公然买卖人造处女膜为处美人大赛做准备的情节令读者捧腹大笑,然而笑后又引发思考,当今社会似曾相识的各种选美大赛中众多黑幕比起文中的叙述有过之而无不及。
余华曾说:“我觉得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荒诞,从压抑禁欲到纵欲乱性,从政治癫狂到经济混乱。”[5]他的小说将现实中的荒诞变为小说中的荒诞,呈现给我们一个光怪陆离、丑态百出的荒诞世界。宋钢的死亡、李光头逃到外星球上,这和尤索林最后逃到中立国瑞典一样,这种暂时逃离此在的方式对主人公而言是一种救赎吗?此处的苦难难道真的可以在彼在的空间中得以化解吗?黑色幽默影响下的余华在荒诞和反叛的形式下埋藏了深刻的内涵,他赋予主人公以荒诞应对荒诞、以荒诞的内容撕碎社会生活脆弱的命脉,给人无尽思考。
二、人物在多重异化下无处遁逃
心理学家斯金纳曾说,“20世纪有以下两种荒唐的现象:一是机器看来愈来愈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是生命有机体越来越像机器”[6]。黑色幽默热衷于表现科技给人带来的精神压迫。科技使战争无所不用其极,尤索林忍无可忍后的逃离是否能够彻底摆脱困境呢?我们不得而知。《兄弟》中的人物更多处于政治、经济、科技多重异化下无处逃遁的状态。
荒诞根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对人的制约和异化。余拔牙收钱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拔掉一颗革命的牙,要付一角革命的钱。”[2]李光头跟刘新闻说检验时,“一个春风吹,一个战鼓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这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春风吹,战鼓擂”等伟人严肃的政治辞令和个体为了收费、炫耀性经历等充满戏谑色彩的话语之间形成隔阂和尴尬,让人在这种张力中看到人性的异化和现实的荒诞。
经济成为异化人的又一工具。人在市场经济的挣扎中身不由己,宋钢卖兰花的羞涩如同《一地鸡毛》中帮卖鸭子同学收账时小林的心态,足见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被商品经济颠覆后的异化心理。在林红人生轨迹的转变中弥漫着经济作用下人性的沉沦。
科技正在将人类异化。现代医学的进步如处女膜修复手术使人类的道德观、两性观在不断异化。李光头举办处美人大赛,最后获得冠军的是一个妈妈,评委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这就是绝妙的讽刺。
宋钢的卧轨自杀导致林红逃离现实半年后成为红灯区的林姐。李光头走向孤独和虚无,他带着兄弟的骨灰逃离地球和尤索林逃到瑞典一样,表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荒谬及其对个体造成的无法摆脱的困境。这里,命运的无序与残酷不仅让主人公在劫难逃,更重要的是,死亡、堕落、逃离的介入使主人公有了无人告之对错并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的暂时救赎,这便构成了文本黑色幽默的底色。
三、以幽默稀释苦难
黑色幽默小说善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强烈的反差中形成悖论的审美效果。
柏格森曾说过:“人一旦成为生活的旁观者,那么,生活的许多场面都变得滑稽可笑。”[7]这令黑色幽默小说的主人公学会不动声地色面对生活的残忍并发出笑声。这种幽默影响了余华,他用幽默表现“文革”的荒谬并稀释成长中的苦难。宋凡平胳膊脱臼还告诉儿子们“我让他休息几天”,并教儿子们如何让胳膊休息,从而将脱臼的苦难事实变得趣味无穷。他告诉儿子浮肿就是“光吃不干活,就长胖了”,这里隐含了叙述者悲天悯人的叙述态度,让读者在嬉笑之余产生对社会的忧虑和思考。
《兄弟》中诸多人物和海勒笔下的丹尼卡医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丹尼卡是一个活生生的军医,但没有人相信他活着,“他在阴影里徒劳无益地徘徊着,活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8]《兄弟》中明明是活人,余华却当成鬼魂来叙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宋凡平“看到厕所里空无一人,只有跷起的两条腿,他吓得大叫一声。这一声撞见了鬼似的惊叫,把李光头全神贯注的父亲吓得魂飞魄散”。[2]
“他的继父站在那里惊魂未定,他觉得自己只是眨了一下眼睛,那两条跷起的腿一下子就没了……他心想难道大白天还有鬼?”[2]
孙伟的母亲“深更半夜像个鬼魂似的悄无声息地走来走去,常常把我们刘镇的群众吓得喊爹叫妈,差一点灵魂出窍”。[2]
李光头找的六个合伙人“聚在一起时不像是活生生的人了,他们像六个鬼一样冷冷清清地坐在一起,铁匠铺到了晚上也像墓穴一样悄无声息”。
海勒笔下西方的“幽灵”到了余华笔下被置换为“鬼”。“文革”的禁欲在小说中被夸大,人物畸形发展,使读者在笑中深感沉重。孙伟母亲像个鬼魂一样半夜游走,这里充满了戏谑和夸张。我们知道戏谑的特点是对本应引起同情的事物进行略带恶意的夸张,或进行不带感情的直接描写,以带来幽默的效果。这里余华不仅没同情,还反其道而行之,这既是对“文革”失控年代的反讽,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苦难血腥的味道。李光头的六个合伙人由最初满怀希望到最后像鬼一样冷清地坐在一起,事态朝着读者和六个合伙人预期之外的方向发展,把共同致富的美好外套揭去,暴露出合伙人虚伪和怀疑的本质。这种对立,在“像六个鬼一样”的叙述中显现出幽默,用幽默稀释了怀疑,带来的是对信任和价值的颠覆。余华小说黑色幽默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和人类生存的悲哀。
余华黑色幽默的本土化特色
中西方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渊源和作家素养的不同决定了余华的“黑色幽默”和海勒的“黑色幽默”并不全然一致,余华在汲取黑色幽默时更有本土化的特色。
一、存在脉脉温情
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代表的黑色幽默小说在处理现实的重大突破时是反道德和反人伦的,以此凸显现代生活的杂乱甚至错位。丹尼卡妻子收到的慰问信和抚恤金使她相信丈夫阵亡,知道丈夫没死后也带着孩子搬了家。这些事件因被夸张到闹剧的地步,让人在笑声中体会无法言说的悲凉。
与海勒不同,余华在《兄弟》中表现了很多家庭间的脉脉温情。李兰在上海治病时收到宋凡平的信就是她全部的慰藉。宋钢跟周游走时带走了自己和林红的合影。林红虽然背叛了丈夫,但面对宋钢的死,她说“无论我做过什么,我一生爱过的人只有你一个”。小关剪刀和妻子虽然嘴上相互对骂,但仍关爱对方。文本中很多夫妻都表现了患难见真情,支持这些个体存在的勇气无一例外地都是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家庭内的爱和温暖。
二、城乡文化的冲突和对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格局明显,这与西方黑色幽默产生的后工业背景不同,因此中国的黑色幽默作品常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作为特点,这是西方黑色幽默所没有的。
《兄弟》中城乡文化明显的冲突和对立表现在宋钢、小关剪刀这些带着浓厚乡土文化气息的人在城市中的艰难求生上。小关剪刀说:“要是早知道自己出来是这个模样,我当初肯定不会出来。”宋钢也喃喃自语:“我要是知道这样,也不会出来了。”小关剪刀当初不听父亲的劝阻,宋钢不听林红的阻挠,不顾一切地去城市闯荡,他们作为乡村文化的代表符号在城市中痛苦挣扎的生存状况表现了两种文化不仅难以兼容,而且更多的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尖锐对立和冲突。
三、更多价值的追问——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审视与反思
余华的黑色幽默与海勒所代表的具有彻底虚无主义、怀疑一切理性和价值、否定一切并旨在揭露世界无序性本质的黑色幽默不同。余华小说中即使人被异化,仍有更多价值追问,表达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审视与反思。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人物早就习惯了生活和意识的混乱,并将混乱视为生活的本质,以荒诞代替生命的终极意义;而《兄弟》在荒诞中直面存在,探索人性和生命的价值,进行积极的人文关怀。余华将人物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的辛酸苦辣表现得淋漓尽致。宋钢和父亲都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执著。宋凡平为了兑现承诺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下,宋钢为了让林红过上好日子外出,因亲情和爱情的双重背叛导致其从精神到肉体都走向死亡。两代人的命运都被卷入一个不可逃避的怪圈中,最终都无法摆脱轮回的宿命。这里表达了余华对生存和发展的审视,对整个人类未来的担忧。
余华说他没有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到海勒的黑色幽默和其整体氛围的影响。他说:“我想有朝一日‘幽默’会成为我的一种理想。”[9]他在《兄弟》中一改前期创作中与世界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受黑色幽默的影响,与历史和现实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余华的黑色幽默呈现出本土化的形态,这也表明人们对黑色幽默这一应对世界的方式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余华用他独特的黑色幽默告诉我们,人应寻求一种可以诗意栖居的生存境界,开辟一种精神生态的资源,这有助于人走出当下的生态和生存的双重困境。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研究生创新基金课题重点项目支持成果。
参考文献:
[1]郭昌榆.论黑色幽默小说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哲学蕴含[J].成都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