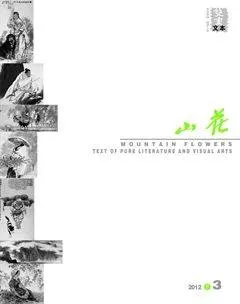印象石门坎
夜宿石门坎
到达石门坎时是下午四点过了快五点钟,天色很暗,细雨中的群山云雾翻滚,空气中有高原独特的清冽味道,感觉气温比威宁还低。
一下车我忍不住缩了缩脖子,说声好冷。刚要进到乡政府,一眼望见一幢气势不凡的石房子鹤立于周遭,大家的脚步都不由得同时转了向。
房子的外观虽不复杂,却是纯粹的英式建筑,不知道采用的是哪种石头作建材,看上去是深沉的灰黑色,据说一丝不苟的英国人建房时,完全按照从英国带来的模型操作,建成后的房屋跟模型不差分毫,连石头的数量都是相等的。
参观过后,认为保护得还算不错,就是有些沉闷。原以为是大名鼎鼎的柏格理牧师的住宅,后来才知道在建这幢房屋时,柏格理早已去世。根据墙上的文字说明,该房建于一九三七年,让人叹息的是当初设计和建造这所房子的高志华牧师还没来得及入住,便被土匪杀害了。这似乎给这所房子莫名的忧郁找到了最好注释,望着门前松树上的老鸹窝,我不禁想起狄更斯笔下大卫·科波菲尔家的老房子——“鸦巢”,相似的意境,相似的美丽,相似的阴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房子仿佛天生就带着一种宿命的色彩,让后来瞻仰它的人不胜欷歔和惆怅。
天黑得很快,因为农业厅的人要搞调研,我们只好抓紧时间跟乡政府的人做些交流,本来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祖基(音同)村,了解后才知道,因为天气恶劣再加交通不便,我们根本到不了祖基村,让我们好一阵遗憾。就我们这个小集体的大多数来说,一心想去祖基村跟风景什么的没关系,主要是听说那里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为百分之百,想看看那里的人究竟什么样?为什么人最穷却最诚信?
趁别人搞调查,我仔细研究墙上的石门文化保护遗址的示意图,发现这里的旅游资源很丰富。
之前,因为要来这里,也曾做了些功课,知道威宁大山深处的石门坎之所以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因为一个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曾在这里发起过一场社会改良运动以及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所产生的社会感召力。
到了此地,才知道不光小小的石门坎驰名中外,这里的人也见识多多,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乡里的老秘书张国辉。张国辉是个六十开外的苗族老人,看上去很像一部电影里的印第安人,据说他的父亲便是柏格理的学生,目前,他是石门坎文化的活字典。
可能是跟很多高端文化人打过交道的缘故,他比乡里的另外两个干部更懂得活跃气氛,吃饭时,他讲了一个笑话,说柏格理的孙女曾来这里扫墓,当时她只有三十二岁,因为她的头发跟眉毛都呈极淡的金色,被高原的阳光一照,显得白发苍苍,一个六十来岁的当地人望着她感叹:怕有八十了吧?真不容易!这么大年纪还能跑到我们这个山沟里来参观!这个笑话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家一扫先前的拘谨,变得随意起来,虽然外面雾雨重重,屋里却是暖意融融。
吃完饭踏着泥泞往住宿处走,感觉乡里的街道还没形成统一的格局,每家每户的房子好像散落在坡上的积木,各自为政,显得有些凌乱,由于电力不足,灯光有些发暗,抬头往黑黝黝的山下望,山谷中的几点灯火在密雾中更显萧索,高原夜晚的风像刀子似的往人身上割,竖起衣领时,几分羁旅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入住的旅店据称在当地条件最好,其最有力的依据是在屋内有一个男女共用的厕所,(似乎其他旅店的厕所都在露天坝,考虑到晚上起夜要冒着寒冷出门,这的确是个够舒服的旅店)旅店的主人是本地的老师,是个热情洋溢问一答十的人,同时也是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开旅店是他的第二职业。据老板本人吹嘘,他的小店住过许多名人和学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沈从文的孙女,这位沈女士对石门坎情有独钟,一来就待十天半月,还把送我们来的张秘书(张国辉老人)弄到北京去见了很多的世面。当我们问住一晚要多少钱时,他眯着眼睛说,十块钱!政府带来的人哪敢多收?说得我们都笑起来。
看我们进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离开火炉弯腰去拿暖瓶倒水洗脸,因为她转身太快,我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只看到一截小蛮腰。等她站起来后老板介绍说她也是旅店的客人,是今年才来的特岗教师,在比这里条件更艰苦的村寨教书,今天是到乡里来签合同的。所谓特岗教师,就是先试教三年,三年后双方合作愉快,便可成为正式教师。看她长得眉目清秀,我们问她是哪族人?她说是回族,家就在不远的中水。问她来这里工作习不习惯,她有点腼腆地说,不习惯,最主要是教学方面跟原来老的教学方法有分歧,所以工作压力有点大。值得欣慰的是,她用新方法教的学生进步也很大。问有没有辍学的女孩子,她说有,为此她也很苦恼,有个辍学的学生家她都走访了七八次,可每次都被家长不高兴地礼送出门。另外她班上(好像是一二年级,因为还在学拼音)有一个女学生注册年龄是十三岁,她自己估计是十五岁,结果还没等她考证清楚这个学生的真实年龄,这个女学生就出嫁了。看得出,小姑娘很有敬业精神,从她的身上,我们依稀感受到柏格理在此的流风余韵,但她的无奈也是现实的,因为没人能给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她的苦恼。
因为第二天小姑娘还要起早回村里上课,所以大家都休息得早。可是最好的旅店没有带给我最好的睡眠,整个晚上我床头的房门都在跟我作对,它总是自作主张让我们的房屋敞开胸怀,同时让我的床处于穿堂风的风口上,再加缺水,此地的卫生普遍不尽如人意,床上被褥气味不佳,以至于我一晚上都在开自己的批判会:那么多阳春白雪之流在这里都住得下,你一个下里巴人有甚忍不了的?可是不管我如何高标准严要求地苛责自己,我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终于明白,专家学者不是谁都能做的,总是要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能做方能达到那样的高度。霎时间,又想到柏格理和他的同人,一百年前,这里的条件不知比今天恶劣多少倍,他们却能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在这里生活,须得有怎样的爱心和毅力才能度过那样艰苦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他们来自物质文明极为发达的地方……这样长长地想下去,直到老板十岁的儿子起来上学时,我有些迷糊了,因为门响时我好像跟他一路出了门,走过英国人的石房子时,我在随风轻诉的松林中看到有修道士的长袍掠过,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睡着了……
天亮才见杜鹃花
倏忽醒来,有狗在叫。
起来时,旅店唯一的服务员苗族姑娘小兰已把洋芋烤在火炉上,是这里最好的油沙地出产的新洋芋,撕皮后蘸上特色辣椒面吃别有风味。这是当地的常规早餐,倒也省时省事。
出门时,看到雨停了,气温仍然很低,借用一位武侠小说家的表述:冷,冷风,冷风吹。我倒不认为这位小说家是在玩文字,因为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反复出现的就是这三个词。
远远近近曲折无常的山脊上白雾茫茫,形成很磅礴的雾潮,雾潮呈上升状,据说这是天气转晴的征兆,但愿如此。
整个乡镇仿佛都还在睡梦中,似乎早起的人只有读书娃和鸦鹊,再就是我们一行四人。站在乡政府的门前俯瞰油画般的山谷,一大群鸦鹊喳喳叫着在山谷里飞上飞下,为了这种羽毛黑白相间的鸟我们昨天曾争论过,原因是它既像喜鹊又像乌鸦,请教人后我差一点就给当地人递佩服书,因为它就叫鸦鹊,于是乎,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
山上山下转过后,才知道当年英国人买下的所谓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其实占地很大,(似乎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牛皮故事的影子)至今陡峭的山坡上还残存着当年的许多建筑,在保存较完整的长房子徘徊了一阵,接下来看到的修道室,足球场,游泳池以及柏格理从英国带来的那棵巨大的无名树,在带给我们无尽苍桑感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几分曾经的西方色彩。
在柏格理的墓边,我们意外发现两朵杜鹃,玫瑰色的花朵和经霜后已然变得橘红橙黄的橡树叶交相辉映,使得墓地周围色彩缤纷。面对那两朵霜后的杜鹃,我突然想到说书人的口头禅: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关于柏格理对此地的影响和他的个人魅力,我无意重复,来自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学者们早有煌煌专著,我关心的是那些在时间的尘埃中渐被湮没的生活小事。
参观时,我一直留意柏格理的日记多次提到的“五镑小屋”,关于“五镑小屋”的名称来历,我还没找到依据,估计跟当时的造价有关。它是柏格理和他的夫人在此地的家。遗憾的是从头到尾,我没听见有人提起过它,也没有遗址什么的供人凭吊。
从有关文章我们知道,五镑小屋不仅仅是柏格理的私人住地,它也是当地的医疗中心,每每礼拜后,有教众络绎不绝地来这儿求医寻药,柏格理夫人埃玛便是当仁不让的白衣天使,这个白衣天使给人治病的细节耐人寻味,据说,她给病人拿药时,药粉可以包在纸里,可药水怎么办?最后她想到把药水倒在鸡蛋壳里,可见在这世上,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物质贫乏更能刺激人的想象力。
尽管医疗条件极差,他们的半拉子医术还是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尤其是为当地人接种牛痘,对当地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福音。当他们怀揣闪闪发亮的医用小刀,满腔热忱给人接种时,那种笃定的神情好像他们无所不能。殊不知他们也有搞不定的时候。文明如柏格理,也对当地苗族人的一些土单方感到纳闷。
在柏格理传奇的一生中,马是他传教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看他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在骑马翻山越岭,从某种意义上说,马也是他最忠实的朋友,所以,当他的马生病时,他焦虑万分,面对在痛苦中煎熬的坐骑,他束手无策,最后一个当地的苗族朋友把他的马治好了,所采用的方法奇之又奇。
根据马生病的症状,苗族朋友说,这马得的是腹绞痛,必须吸入旧衣服燃烧时冒出的烟方能治好,据此,他们扯了一些碎布燃起青烟,放近马的鼻子,起初马有些不习惯,可最后,它竟熟练地吞云吐雾起来,好似一个老烟鬼碰到古巴雪茄,而后,它开始排出大量的水,最后迅速恢复健康开始吃草。这事千真万确,柏格理在日记中写得明明白白。
说到治马病,当地还有一种方法,说人的脂肪也能给马治病。在二十世纪初,威宁昭通一带的人对一顶戴了二十年的旧帽子看得很重,有经验的养马人会出大价钱买回去以备不时之需,据说马生病时,用那油腻腻的帽子盛水饮马,马病顿时痊愈。
联想到历史上此地产贡马,这不奇怪,在长期的养殖实践中,我们的先辈肯定总结出不少实用性很强的独特经验,只是不知道这些民间方法现在还有没有用?
(关于这一点,我好不容易在通往昭通的小路上碰到一个牵马人,便急不可待向他咨询,结果他摇头说不知道,问马病了怎么办?他说找兽医。问兽医怎么办?他说打针。)
爱情一九一三
离柏格理修建的游泳池不远,有一道天然的石门,石门下便是柏格理带人用原始工具凿开的山路,当年这条山路是通往昭通的交通要道,也是石门坎与外界联络的唯一通道,(以后又修了通彝良等地的小道)自从有了这条通道,石门坎跟世界的距离变得很近,基督教的教义在这里深入人心。一时间,西风东渐,大山深处人人仰望耶和华,旷野和干旱之地,呈现出无比的欢欣,仿佛玫瑰花开,沙漠有河。
可是在一片颂歌声中,也有不和谐,因为基督教在带给人们文明的同时,也把他们严格的礼教带给一方水土,从某种意义上说,扼杀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关于这对恋人,严谨的柏格理用了西方的爱情经典来形容他们——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在一九一三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1月15日,有两个苗族年轻人,就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互陷入热恋之中,那位姑娘大约十九岁,已经同另一个寨子中的某人订了婚约,而她的情人则已成了家,爱的激情使他们发狂,然而他们也意识到两人必须分手,不久前的他们双双外出,把自己各拴在一条长绳子的一端,绳子被抛挂在一根悬在峡谷的树枝上,他们侧站在树干下的一块石头上,共同跳了下去,随后就悬了起来,绳索吊在树上,两具尸体各在一端,真是近乎狂热的恋情。
这个故事很惨烈,可是作为主的爱心大使,柏格理在日记中的语气却出人意料的冷漠,他在客观冷静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真是近乎狂热的恋情”。显然,他对这对恋人的做法不以为然。
从古至今,苗人的爱情总是与热烈、奔放、自由这些迷人的字眼连在一起,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遗憾的是他们的某些风俗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冲突,从柏格理的日记中,我们经常看到烧宿寨房的记载,所谓宿寨房,是苗族人谈恋爱的场所,也是苗人的公共娱乐场所,可能在教会人士看来,烧了宿寨房,人们自然就会聚集到教堂,聆听主的声音。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事物的两面性。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恐惧使得这两个年轻人做出这种极端的选择?
不管怎样,有一点毫无疑义,那就是这两个年轻人曾经或一直是基督徒,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他们的心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压力。
想来,他们也曾尽量遵守教徒的规矩,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可是在一九一二年那个秋天,他们在某个山间小路或是某个美丽的村庄遭遇爱情时,他们那与生俱来的热烈情感便狂放起来,一切都变得不可掌控,结果不言而喻,他们的不伦之恋被人们唾骂,令教会失望,让他们心目中的王痛心疾首。在这个东方国度的偏僻一隅,“红字”的阴影一如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让人由不得想深入下去。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当四乡八寨的人涌入石门坎的教堂时,或许他们没能参加礼拜,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教堂后面的橡树林中相见相拥,没想到,教堂里响彻云霄的祈祷竟让他们产生了必死的决心。
于是,他们相约来到一处悬崖上,这里有姿态最美的树,有经霜后最红的叶。从崖上斜逸而出的一棵橡树在冷风中轻摇,好像是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让他们感到些许温暖,也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几分留恋。可是,那只是片刻的犹豫,男孩子最终毅然决然把绳子的一端系到自己的脖子上,同时,将另一端灵活地摔过树枝,让女孩子在另一头系好,当一切停当后,他们相互寻找对方的眼睛,寻找最后的温情。
一只雄鹰从远处飞来,它带来的气流让崖上的红叶纷纷下坠,男孩子伸出一只手,接住了一片美丽的红叶,然后他温柔地把它放进女孩的手里,刹那间,女孩的眼睛放出万般柔情,与此同时,他们一起纵身跳下,瞬时两人高悬于峡谷之上,夕阳的光辉令各在一端的身影变得永恒,而他们中间的那棵橡树顿时变成象征他们爱情的连理枝。
这个惊心动魄的场景最终定格在人们的脑子里,扑灭了人们眼中的狂热,我想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认为他们应该去天堂,因为能为爱情付出这种惨烈代价的人不多,凡在阳世受过此种痛苦的人不应该去地狱……
站在险峻的石门坎上遥看对面峡谷上五彩斑斓的丛林,我的思绪万千,似乎对面崖上的每棵橡树都是当年爱情的见证,因为风过处,我听到一声声叹息从那里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