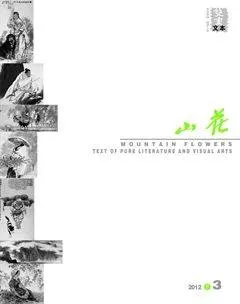那些人
就这么生活着,年岁增长了,记忆的河道里,曾经相识和相交的人,在不知名的时刻,像宽广的夜色下的波光,闪亮着,或湮没了。
《红楼梦》里,贾雨村和古董行做贸易的旧识冷子兴风尘偶遇,坐在村肆中沽饮。谁人背后不说人呢,两人谈起了贾府上下的一干人等。昔人此类的议论,常常会追溯到“天机”,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是和“天”相连的;在对“天”的仰视和探察里,天下万物都有了各自的前因后果,所有的纷繁,都有了内在的秩序。不似我们,自觉被各种道理全副武装了,或者被庞杂陆离的生活打磨到百炼成精了,其实离那本来明朗的“天机”,是越来越远的。那一天,郊外的闲谈漫饮间,贾雨村听冷子兴说起了宝玉种种古怪的行迹,感慨道,天地之间有两种气,一种是清明灵秀的正气,另一种是残忍乖僻的邪气,两气相逢,两不相下,“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世间的男女,偶秉此气而生,“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
隔着时光和人群,这样的感慨,会偶尔地浮在“万万人中”的我心里。我要说的那些人,也就这样带着岁月的暖意,常被我记挂着。
那时我20多岁,在一道幽暗的走廊尽头,一间堆满了零乱的稿纸的办公室里做个小编辑。别人看我,是个面色苍白的寡言的女子,偶一言语,就暴露了不谙世事的局促。在我自己,却是装满了与日常无关的思想和感触,它们庞大地压迫着人,让日子在真实和虚幻中摇摆。时常地,挤在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心思恍惚起来,便想:这就是我的日子吗?随后,就有说不出的荒凉和迷茫。
一个下午,一个清癯的、目光炯炯、卷发稍长的男人到机关办事,经过我的办公室,便折进来闲谈。我不清楚看人说话的道理,有人跟我谈文学、文化了,就像闷罐开了个口子,记不得混淆拉杂地说了些什么。正说到心事浩茫连广宇时,他忽然问我,调进机关没有,评了职称没有?我几乎一惊,从云层落下,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长期借调、身份不明之人,平日在走道上遇见厅长,恨不能躲进墙角的。然后他说,要不,到我们研究所来吧,我们那里有编制。
于是,我就到了艺术研究所,这个大家自嘲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重新坐在一间木格窗下的堆满了稿纸的办公室里。但重要的,是见到了那些人。
那个男人,是研究所的谢主任,我的新办公室里,靠墙立着他收藏的一具2米多高的傩面王,每天瞪着面盆大小的两只眼睛,从远古穿云拨雾,目光如炬地瞪视我们。后来关于他,我知道了一些故事。他家里收藏的乐器,可以配备一个弦乐队,这些乐器,几乎件件到他手中就可成曲,当然,最熟谙的是小提琴,不仅会拉,还能制作。他做提琴的手艺在坊间也或有耳闻,从选料、定型、刨背板,到线锯锯音孔、黏合低音梁、制作琴头、装弦轴和音柱、磨合马子,整整40多道工序,一道也不能怠慢。他的收藏,无关利润和市场,全凭兴致。后来他当了厅长,有一次带团去维也纳演出,在一个旧货市场里淘到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斯氏据说是迄今最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生活在十七八世纪。当代某位著名的大提琴家,被人问及谁人堪比斯氏,他回答说,要等待另一个斯特拉迪瓦里出现,就像等待另一个莫扎特。斯特拉迪瓦里一生共制作了千余件弦乐器,流传至今的也不过六百件,这无价之宝,竟在二百多年后,被谢主任迢迢万里地前去找到,不得不说他和提琴的因缘,幽微且深长。
每逢春节单位里的联欢会,他必西装革履,玉树临风地立在简陋的场地上,为我们拉奏一曲。对小提琴的所有描述中,有一个中国的词语最是贴切,几乎无可替代,那就是“如泣如诉”。在他如泣如诉的提琴声中,我们喝茶、嗑瓜子的声音自觉地收敛了,一曲结束,他额头的卷发和手臂微微一扬,我们脸上浮着的都是肃穆。
他家的房子不大,被铺天盖地的书籍和他驳杂的收藏占据,有的地方出入和转身也困难了,而他还收集流浪狗。其中的一只冬夜里难产,他整夜蹲守在旁侧为它接生,自己汗流浃背,保了母子平安。第二天在办公室,听他带着感情说起来,我仿佛在听另一个人的故事,因为他日常的言谈,往往是理性得如同高堂悬镜,不知在多少年前就照得一切分明了的。他的举止言行,也似乎有条不紊地参照着圣人的遗训,君子不器,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云云,总之,他是一个拥有如书上所言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人,给难产的狗接生这样的事情,竟不似他所为。
他的故事里,有一桩,多年后回想仍然让人愁伤,那是他年少时候的故事。那时候,因为父亲做过旧军医,他们姐弟过早地背起黑色的十字架,在运动的风雨里四散、漂泊。他被独自遣发到一个叫水田的地方,那里的云雾山上有一个寨子,寨中有一个知青点,其实,也就是一间牛圈和孑然一身的他。白天,他跟着别人种包谷,夜晚,他在牛圈里点一盏小油灯读书。每天早晨起来,他洗冷水浴,锻炼筋骨体魄。日子长长,未来如坠云雾,最难耐的是孤独,但是,他随身带着一把提琴,它是他的朋友和亲人,寂寞时拉着它,内心的困顿便轻缓了下去。终于有一天,他替自己拿定了主意,打好背包下山,去修湘黔铁路,背包里,裹着他的提琴。
那个天地苍苍一无所依的少年,行走在乱石和荆棘间的山道上,背着一把提琴,去找他的将来,他的背影,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艺术研究所侧身于一栋陈旧的办公楼底层,楼上还有诸家单位。木楼梯红漆斑驳,踩上去吱吱的或砰砰的响。过道是狭窄的,地面甚至有了坑洼,游着泥土的潮气。楼前不大的坪地边,是临街的一排门面,门面迎着的,就是人流和车流了,也同样不舍昼夜地流淌。那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国家正经历着沧桑巨变,一个人也是如此。我们坐在窗边埋头稿纸,心里却是尘埃纷纷的,外面的生活和它的躁动,像挡不住的市声,终究蔓延到每个人的日子里。谢主任仿佛一个大力水手,奋力摇着橹,期望我们都乘着这叶从旧年月里驶来的方舟,齐心协力划到艺术的彼岸去,一个也不落下。他是善于做管理的,给我们都设定了一个预期值,谁可以做傩文化专家,谁可以做苗族舞蹈专家,谁可以做民族器乐专家,谁可以做民间戏曲专家,谁可以杂学庞收成大家。他无法许给财富和权利,因此有时候,他也是在跟风车战斗。
每一天,为保护资料而立起的铁门哐当打开了,我们还是坐在自己的桌子边,度着自己的日子。太阳升高了,大街上的喧声,开始是扯不断理还乱,后来就沸沸扬扬。
在这些辨不出来历的声音中,有一个声音,却可以穿墙而来,直入人心脾,那是隔壁的姚老师在接电话。喂,这里是艺术研究所,请问您哪位?姚老师的京韵念白,是不分戏内戏外的,“喂”念做“外——”,先就有一唱三叹之感;“哪”念做“馁”,电话线那头纵然有千万里之遥,也被这一个字拉近来,近到就在她并拢的膝前坐下,看她的右手轻轻放在左手上,削肩直直的,巧笑倩兮,跟你说着人生如戏,那戏里的家常。
初次听到这一声“喂”,我是一惊的。我这样寻常孩子中的一个,在那个年代精细到几近严苛的艺术标准面前,就像一个自然生长的野孩子,后来又去读了中文系,满脑子的萨特卡夫卡,难以理解一个人是由于怎样的机缘,进了艺术的门槛,又经数度春秋的训练和淘汰,将自己打磨成一个举手投足都艺术化了的人。见到姚老师,我也同样是吃惊。她那时年逾半百,俨然一位卸了妆的青衣,有着笑盈盈的水一般流转的眼波,无论任何时候,她说话,是清音悦耳的,她走路,是莲步姗姗的,假设她还有嗔恼或愤懑,那也化为了戏中的台词,受了诗意的润泽,早削减了火气。那一回,我们全所去遵义春游,经费有限,书记所长都随大家坐火车硬座。几个小时的行程里,我们吃零食,打扑克,大声说笑,稍矜持一些的,也就是坐而论道,不时起了争执,嗓音粗大起来。只有姚老师,肩头围一袭披肩,脖颈优雅而挺直,静静地在窗边读一本小说,偶尔因我们的一句话笑起来,那笑也是风日妍静的,绝不会失了章法。
姚老师对于我,一直是一个谜。她独自住在研究所转角处的一间房子里,我只进去过一次,床单光整得没有一丝褶皱,屋里有一种淡淡的沁香。有时一连几日不见她,那是她到贵州各地去做田野调查,因为她是《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的编辑部主任。多年后,我读到一则他人写下的小资料,回忆姚老师为了得到关于布依戏的第一手资料,身背干粮,一手提马灯,一手攥着防身用的打狗棍,徒步于荒山大菁、丛林沟壑,在南盘江两岸的布依山寨出入,她还去了黔西南册享县最边远,最艰苦的板街、板其、板坝三乡。有一次山间迷路,只好几个人在荒岗燃起篝火,靠在一起听山风呼啸,野犬哀呜,直到天明……
就让姚老师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吧。去年,河滨公园的樱花开了,游人群中,一眼看见一个风姿楚楚的老太太走过来,与满眼的樱花和阳光分外和谐,让周围刻意装扮的年轻女人们失色。已经记不清多少年不见了,我迎上去,心底有什么阵阵地往上涌。姚老师说,她已近80岁了,但我不相信。世上有一种人,可以把自己塑成雕塑,立在别人心里,风声雨味也不能侵蚀,她就是这样的。
研究所里的黄姐,跟姚老师刚好是另一路活法。
她曾是70年代省歌舞团的台柱之一。她们那一批舞蹈演员,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属国色天香,因每一个都从千万人中挑选而来。当她们三五成群地走在灰色的街面上,会洗亮了多少人的眼睛,落入多少人的梦里。人常说,人间莫大的悲哀,一是英雄落幕,二是美人迟暮,辉煌过后的凋落,比波澜不兴更加的在夜深人静时啃噬人的心肠,其中的况味,也非我这等常人可解。但是,黄姐却轻松地过了这个关隘,因为她从演员转向研究,跑遍了贵州的山旮旯,写出了《舞蹈与族群》这样的专著,她的心里有一张旋转的彩色的地图,那是贵州各地各民族舞蹈的图景,只要她打开话匣子,一时半刻是无法收束的。
你听她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地说她的舞蹈,会想起佛法的修行中,有一关是弃小我向大我。如果这“大我”,对于黄姐就是舞蹈,难怪她这样一脉天然的风范,仿佛她前生就是搞舞蹈的,三生三世也不渝。
依我们现在对这生活的识别,黄姐早就是“富婆”了。她家的大房子,进去转一圈也记不住到底有几间,她家的保姆,说起话来眉目生动,似乎也是舞蹈出身的。但是,黄姐给我最多的印象,倒是她经常从乡下回到所里,背包里装着摄像机,脸庞上有两团风吹日晒的腮红,脚下的鞋子黏着泥土,有一次好像鞋跟也崴掉了,走路高低不平。你问候她,她根本无心闲白,她有一脑子的所见所闻所感要告诉你,语速提得很快,不然就跟不上她的心速。而且,黄姐从来不说自己的美,在她那里,美是很小的东西,假如还需要时间、精力、时尚来修饰,那她就更是弃之不论了。只是有一次,我坐在她身后开会,一抬头,阳光透过窗棂斜进来,照着她的后颈窝,我发现黄姐是百里挑一的美人,肌肤有瓷器的光泽,身型,也是古瓶的线条。
艺术这个事情,格外地讲究火候,既仰仗天分,又是一部心法。若要用一句话来说黄姐,我想,她是由舞而巫的人。“巫”这个字,很了得,上通天,下通地,中间是人生百态,人情之常,未必有几人能担得起这个字。前些时候,又跟黄姐坐在一起开会了,其中一个男编导,俊朗帅气,像谢晋电影里的男主角,他私下嘀咕了一句:我就不会即兴舞。黄姐接口道:那是因为你的面具太多,你把它一层层地撕掉,你就会跳了。我在一旁听着,心里天高地阔,黄姐,是有一个大我的,因为大,所以驰骋往来,简单而自在。
研究所里最像艺术家的,要算刘老师。他就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直鼻深目,发丝飘逸,笑起来,糅合了孩子的童真和智者的深奥。有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问他,比如人为什么有命运?贵州的民族艺术跟其他地方相比到底有什么?他几乎都是笑而不答,让我怀疑自己的问题可笑,然后,真心惭愧自己的可笑。但是,他经常跟谢主任争吵,是那种有模有样的真吵,两人都红了脸,曲指扣着桌面,完全无视我们在一旁观看,他们争吵的问题,其实也类似我的提问。他一定在心里,和我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可我一点也不埋怨。因为别人告诉我,他经常围一面塑胶的围裙,双手握着一把大锅铲,在寺庙前砖砌的炉台前熬粥,为了舍粥给众人。
皇甫老师是研究傩面具的,他的学问我不懂,只是以为做学问的都该是他的样子:手指间的烟缕袅袅地升起来,罩住他深沉的、忧思的眼睛;由于长期伏案,他的肩背微佝着,面色也苍黄。在我们眼里,学问,使他成为一个脱略的高人。不过,有一次闲谈,不知谁逼着大家讲一讲一生遇见的最美的女人,他受逼不过,也说了一个故事。那是他有一次在苏州出差,住在一家小旅店里,晨起到巷陌中吃早点,看见一个女人,一手拎豆浆,一手牵孩子,从他面前走过。她,就是他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皇甫老师记忆里的那条苏州小巷,不知是否还在。我们城市里所有的旧楼都拆掉了,它们承载过的岁月,也如浮尘,飘荡在各人的回忆里……每次经过闹市区,隔着车窗,看见那栋灰白色的、带拱梁门廊的房子,我就会奇怪它怎么依旧立在那里,落在四周高大的、散发金属光泽的楼群间,落魄而寂寞。我似乎在等着它被拆掉,因为这是早晚的事实,也更映衬了那些记忆,年久愈醇,是无人能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