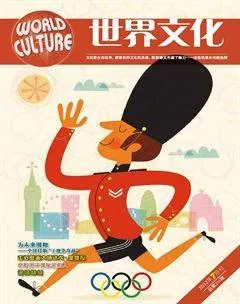狄思累利的“青年英格兰”之梦
2012-12-29 00:00:00赵国柱
世界文化 2012年7期

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伦三岛,活跃着一位擅长文墨的政治明星。他两度受命组阁,主政期间多所建树,为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大英帝国带来无上荣光。随着帝国的扩张,他的声名远播海外。即使是在东方的华夏大地,论及他的文字也不时见诸报端。据学者考证,清末时由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和《画图新闻》最早发表专文,高度评价他的政治生涯,称其为“一时豪杰”;对其文学成就虽着墨不多,但也赞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每出一编,读者俱叹为奇才”。这位被时人誉为“豪杰”和“奇才”的大人物就是英国历任首相中唯一的小说家本杰明·狄思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
狄思累利出生在伦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3岁时皈依英国国教成为基督徒。1821年,他在父亲建议下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实习生。但他对法律兴趣不大,转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824年,他写了一部讽刺社会现实的短篇小说。该小说并未得到出版商的青睐,狄思累利在失望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之后,他又化名“时髦者”发表了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1826)。小说抨击了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在伦敦社会引发热议,作者的身份也很快被媒体披露出来,为此狄思累利受到评论界的严厉指责。这一时期,他还与人合作投资了南美矿业股份和《代议报》,结果蒙受巨额损失。此后他长期深陷债务之中,直到1852年担任内阁财政大臣时才得以解脱。
在经受连番挫败后,狄思累利极度抑郁,几近精神崩溃。1830至1831年,他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和近东的一些国家。对他来说,这次旅行意义重大。他不仅恢复了健康与活力,而且认识到只有投身政治斗争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回国后,狄思累利搬到了伦敦西区,开始出入豪华府邸,走访政界名流。但他的从政之路并不顺利。1832至1835年,他先后四次竞选议员,均以失败告终。同一时期,他创作了包括《年轻的公爵》(1831)《康塔里尼·弗莱明》(1832)《奥尔罗伊》(1833)《亨里埃塔·坦普尔》(1836)和《威尼西娅》(1837)等多部描写上流社会风尚的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
1837年,狄思累利成功当选保守党议员,从此青云直上。1848至1880年,他担任议会保守党领袖。其间,他曾三次出任财政大臣,两度担任首相,最终登上权力巅峰。在任期间,他对内积极推动议会和政府改革,对外致力于巩固和扩大英国的海外利益,被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
狄思累利在从政之余并未忽视文学创作。他最好的小说当推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康宁思比》(1844)《西比尔》(1845)及《坦克雷德》(1847)。有论者指出,狄思累利作为小说家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用小说书写了历史。他的三部曲在许多方面回应并创造性地发现了在工业大潮冲击下英国社会经历的变化,较早地对工业革命中的进步观念及其背后的功利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三部曲出版后畅销一时,狄思累利由此跻身19世纪英国最杰出小说家之列。狄思累利晚年还创作了小说《洛萨尔》(1870)《恩迪米昂》(1880)及残卷《弗肯尼特》(1881)。
“青年英格兰运动”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是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内的一个政治团体。该团体以狄思累利为核心,主要由几名青年贵族组成。他们反对时任保守党领袖兼内阁首相罗伯特·皮尔的政治路线,名噪一时。狄思累利为扩大政治影响,决定采用小说这种既符合时代精神,又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其所在团体的政见。“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就此应运而生。
由于狄思累利在英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且其作品中富含浓郁的政治气息,后世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政治生涯。他的三部曲多被看作是包裹着故事外衣的政治宣言,而不是描绘生活的现实图画,长期以来一直被排斥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之外。目前,评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狄思累利开创了政治小说的传统,他将意识形态与娱乐相结合,为正在经历变革的传统社会创造了一种政治话语。有学者将三部曲中丰富的政治语言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将狄思累利的政治思想命名为“社会托利主义”,把其特征归纳为:捍卫王权和国教的尊严、弘扬民族传统、恢复社会团结。
实际上,三部曲并非只是政治宣言那样简单。它们虽然产生于政治斗争的氛围之中,但其本身却表现出超越政治语境的文学和社会价值。值得首肯的是小说的文风。三部曲之所以深受读者好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中使用了许多模棱两可的语言,这种介于认真和反讽之间的文风使小说充满张力。英国著名评论家莱斯利·斯蒂芬(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之父)对狄思累利的作品有如下评论:
其哲学理论可以是真正的信仰,或只是一点虚张声势,或是对朋友甚至自己的戏拟。其华丽的段落,可能是有意的过分着色,或代表了他的真切的品位。其铺陈恰到好处,既可以说是讽刺家故意采取的荒诞笔法,也可说其中的荒诞是他看到的人皆有之的常情。不幸的评论家犹如《威尼斯商人》中的求爱者,无论作何选择,都不免碰壁。
其次,三部曲是19世纪英国小说中较早带着问题意识探讨工业革命的历史小说,清晰地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的复杂体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狄思累利在三部曲中揭露了功利主义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
《康宁思比》以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贵族青年秉承传统的骑士精神,吸纳新兴工业阶级的进步理想,逐渐转变为政坛精英的成长历程,体现了狄思累利对处于贵族与资产阶级权力更迭时期英国政局的独特思考。《西比尔》以一个出身贫苦工人家庭的年轻女子的恋爱经历为线索,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贫富分化的严重危机,以及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指出社会的分裂源于弥漫于英国社会的功利主义。《坦克雷德》则通过一个贵族青年坚定的圣地之旅,冀望通过融合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为功利主义笼罩下的英国社会寻求一剂精神良药。在狄思累利看来,要想解决英国的社会积弊,只能走“精英治世”之路,即国家必须由集想象力和责任感于一身的政治精英来统治。
显然,狄思累利的“精英治世”思想是以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理论为基础的。卡莱尔认为,世界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伟人的历史。伟人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应该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在《康宁思比》中,狄思累利成功地刻画了新时代众望所归的领袖犹太人西多尼亚。西多尼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清晰的历史视野。他不仅能充分地认识到工业革命中的进步力量,而且还能从精神和文化的高度超越盛行于英国政商两界的功利主义。他看到了英国各阶级之间存在的严重对立,指出英国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精神品格正在衰亡。若要拯救英国,就必须恢复“英雄崇拜”的社会意识,使民众找回崇高感和热情,走出趋利避祸、趋乐避苦的功利魔咒。狄思累利在小说结束时借西多尼亚之口表达了对主人公康宁思比等青年贵族的期待,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伟大职责,致力于消除社会对立,使英国重新成为一个和谐的国家。
三部曲的创作时间正逢英国历史上的“饥饿的四十年代”。当时的英国社会危机四伏,有关阶级斗争的讨论不绝于耳。与《康宁思比》偏重描写上层社会的沙龙政治不同,《西比尔》将关注的视角转向英国的整个社会,突出了贫富对立和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全景式描写,其中年轻女矿工劳役的情景最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英国未来的母亲们赤裸着上半身,穿着粗布裤子的双腿之间拴着一条皮带,上面系着一根铁链,借此拉着一桶桶煤块。每天要这样爬行12小时——有时甚至是16小时——的竟是一个个英国姑娘!而且,她们爬行的是崎岖而又黑暗的道路,上面还布满着坑坑洼洼。
狄思累利在《西比尔》中并置了大量的贫富生活场景。他往往先描写一个富人的生活场景,随即就对穷人的生活进行刻画,有时干脆将贫富状况并置于同一个场景。通过一系列鲜明对比,狄思累利特意安排主人公艾格蒙特与社会主义者墨利讨论英国现状。稚气未脱的艾格蒙特认为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是古往今来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墨利对此进行了反驳,一针见血地指出,女王统治着“穷人”和“富人”两个民族。他们之间没有交流和同情,互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情感,其教养、饮食习惯、习俗及所遵循的法律也不尽相同,似乎居住在不同的社会,甚至是不同的星球上。狄思累利通过“两个民族”这一生动的比喻警示世人,英国的繁荣昌盛只是虚有其表而已,日趋严重的贫富两级分化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安定。
“青年英格兰”三部曲成功地传达了狄思累利的政治思想,为当时英国存在的严重危机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作为小说,三部曲的成功并不完全在于政治思想本身,而在于狄思累利能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让其思想为故事增添色彩,在保持小说文学性的同时,令读者深刻地感受到思想的力量。他对历史巨变时期人们渴求精神指引的敏锐把握,以及在现实与想象之间保持的适度平衡,足以使其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中占有颇为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