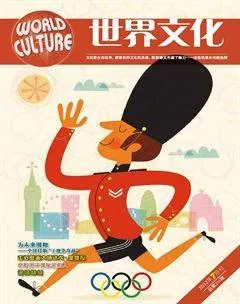漫话胡须
2012-12-29 00:00:00
世界文化 2012年7期





人类最早在什么时候开始剃须的呢?根据考古发现,答案是在两万年前左右,人们发现了那时刮脸用的石制刀片。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刮脸的历史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作为人体身上的体毛,头发可以保护脆弱的头顶,汗毛可以保护毛孔,眉毛可以防止汗水流入眼睛,那么胡须究竟有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呢?尽管绞尽脑汁,科学家们还是找不到证据为胡须“歌功颂德”。相反,近来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发现,胡须具有吸附有害物质的特性:人体呼吸排出的有害气体、大气中的多种金属微粒、香烟中的一些致癌物质,均可以被胡须吸附。那么我们不要留胡须就是了!事情没这么简单,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因为胡须引发的大战。事情是这样的:法国卡佩王朝的路易七世有次把胡须剃掉了,王后艾莉诺,阿基坦公爵的女儿,对此大为不满。愤怒的她在没离婚的情况下就改嫁给大胡子的安茹伯爵,即后来的英王亨利二世。作为嫁妆,阿基坦落入到亨利之手。因此这块土地成为英法两国激烈争夺的地方,这也是后来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由此看来,胡须还真不是件小事。
宗教下的胡须
胡须在宗教活动中是一种信仰的标志,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许多关于胡须的记述。例如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就曾有这样的记载:为了侮辱犹太人,与之为敌的阿莫尼特人剃掉大卫王使者一半的胡须。和其他东方民族一样,胡须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是力量的化身,是神所赐予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根据犹太经师的传统规则,犹太男子必须留须,胡须不能用剪刀修剪,而是用火烧掉。《旧约》认为刮光脸的男子与异教徒外表上相似,因而刮脸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拿破仑三世的一字须这种宗教文化下,如果一陌生女子触摸到一男子的胡须,这将是对他造成的最大的几乎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伊斯兰教中,同样有着蓄留胡须的规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男性穆斯林都是留有胡须的。在伊朗刮光脸是西方人的化身,同时也是堕落的标志。在沙特阿拉伯,所有男子都必须蓄留胡须。在阿拉伯国家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一个没有胡子的男人等于一只没有尾巴的猫。”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例外,那就是在朝圣之旅结束前不久。到那时所有的朝圣者听从号召,将胡须剃掉,剃光所有的体毛,以此表达对真主安拉的绝对恭顺。
在基督教中,人们对于是否可以蓄须并没有达成一致,至少是在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如此。耶稣使徒的画像和雕像表明他们都留有胡须,许多德高望重的修士和苦行僧日积月累地甚至终生蓄留胡须。民间很快就将这些僧侣那仙风道骨般的胡须与神圣相提并论。对此,托莱多主教极为讽刺地评论道:“如果胡须能使人成为圣者的话,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山羊更神圣的了。”在中世纪德国广为流传的谚语这样说:“胡子长不见得有大智慧。”
在随后的基督教发展历史中,罗马教士的脸部变得越来越光净了。由禁欲男性组成的教会将胡须看成是贵族、骑士和农民的世俗取向,同时胡须也是性欲的象征。为了同世俗社会划出一条界限,1119年的图卢兹宗教会议规定:“如果神甫同非教徒一样任其须发生长的话,将被逐出教会。”格里高利九世在其颁布的教规法典中写道:“如果教士不遵守这些规定,主祭可以强行将其胡须剃掉。”然而,同样是信奉基督的东正教却不认同天主教的这种做法。在东正教中,所有的教士和修士必须留有胡须,以此保持同上帝和耶稣形象的一致。这种形象的原始画面来自维罗妮卡汗巾和都灵耶稣的裹尸布,这两件圣物表明耶稣是留有胡须的。所以胡须也就成为区分天主教与东正教以及其它传统教派的标志性特征。
世俗下的胡须
世俗生活下的胡须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古埃及只有法老才可以蓄留胡须,因为它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因而其它阶层的人都必须剃光胡须。如果法老的胡须(是在下颌而非络腮胡)不够长的话还可以用假胡须粘到下颌。甚至连埃及女法老也会“长”胡须,以显示她们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同为地中海世界的古希腊人、罗马人也接受了埃及人的这种做法。在古希腊,只有老者和武士才可以蓄胡须,因为胡须代表着年长、智慧和威严。所以为古希腊哲学家而雕刻的画像表明他们都留有胡须。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最老的、最有威望的神才会有胡须,例如天神宙斯、海神波塞冬和冥王哈德斯,而年轻的奥林匹斯神大都是嘴角光光的。此外胡须还有一种特别的作用,它是隔代的标志,在处于父权制下的雅典社会中,正式剃须的青年男子就成为受人尊重的成员。古罗马人似乎十分讨厌胡须,这可能与日耳曼人有关,这群北方的敌人蓄着蓬乱的大胡子。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作家甚至将这群野蛮人与动物相提并论。野蛮人(Barbaren)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中的胡须(Bart)这个词。同样伦巴底人(Langobarden)可以溯源到“胡须很长的人”(Langb?rtigen)。后来随着古罗马皇帝哈德良蓄起了小胡子,胡须才在古罗马复兴,这可以从那时保存下来的雕像和硬币得到印证。
古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在废墟之上纷纷建立了封建国家。由此对于胡须的崇拜重新在欧洲流行起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留胡子是件很平常的事。这种情况直到近代结束前都没有改变,中世纪的查理曼、“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德国宰相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留有不同样式的胡须。到了近代胡须有了新的含义。在1830和1848年欧洲革命中,起义者们纷纷留起了络腮胡。由此胡须代替服装成为革命分子的明显标志。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胡志明、卡斯特罗,在这些左派革命家们的胡须中体现的是那种具有反抗意味的政治审美意识。胡须完全属于左派的外表形象。为此,德国的保守派在攻击和谩骂中甚至将胡须贬称为“民主主义者之胡”。
和胡须过不去的还有俄国的彼得大帝。这位一心想把俄罗斯引向现代化道路的统治者,从欧洲考察归来后就在俄国掀起了一场剃须运动。彼得将大胡子视为俄罗斯保守的标志,誓与胡子为敌的他在国内开征胡须税。较高等级的人缴纳100卢布,农民则缴纳1戈比。即便如此,蓄着大胡子的贵族比比皆是。气急败坏的沙皇甚至亲自动手,剪去他们的胡子。同胡子作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并不仅仅是彼得,还有“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及其将军们。土耳其革命成功后,凯末尔于1923年当选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此后他在国内推行现代化的改革,其中就包括世俗化的内容。通过立法,土耳其禁止所有的公职人员和大学生蓄留络腮胡。
到了现代,统治者们对于胡须的热情急剧下降。他们剃光了过去象征着权力与智慧的胡须,转而依靠那洁白无瑕的牙齿和貌似乐观的假笑,以期获得民众青睐。昔日革命左派对于胡须的嗜好不复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们脸上得到确认。现在,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已经没有了对胡须的爱好,这是因为蓄胡不仅对身体健康不利,而且还会使男子看起来显老。此外,刮光脸部可以更精确地显示面部表情,这被认为是一种坦诚的表现。进入21世纪后,人们似乎不再对胡须抱有好感。总之,胡须样式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趋向,更同政治密不可分。一部胡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的政治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