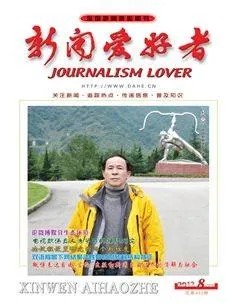西方修辞与传播视域下的受众研究
【摘要】受众是西方修辞与传播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也是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受众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点不尽相同,多模态媒介的推广给受众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西方的受众研究成果丰富,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等多方面均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受众;受众研究;修辞学;传播
受众研究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我国的修辞学传统对于受众的研究“向来不够重视”[1]172,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是一张白纸”[2]139。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市场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而受众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信息的主动消费者、选择者、主导者和制造者。在一定意义上,传媒研究“一直是受众研究”[3]447,传媒经济“从本质而言就是受众经济”[4]109。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受众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重要和意义深远的领域”[1]179。本文主要从西方修辞与传播的角度探讨受众研究的成果与思路,并对国内的受众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受众及其概念的变迁
受众即英语中的audience,源自希腊语,意为“倾听”。古典修辞学时期,主要指集中在某一地点的演讲听众和观众,后来概念逐渐扩大,也将读者包含在内。随着现代修辞学与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大,受众的含义越来越广,不仅可以指出席大型集会的听众,也可以指演讲人、作者、出版物的听读者,还可以指通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媒介接收特定信息的群体,甚至可以指特定信息所针对的“幻想群体”[1]174。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时期的信息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推广和应用,传统定义中的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和获取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使用者,甚至是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受众不仅包括与信息传播者对应的信息接受者,也包括信息传播者本人,对于信息传播者而言,受众不仅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信息的接受者不仅接受信息,可能也参与信息的使用与制造,并有可能也转化为信息的传播者。正如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界限,“受众一词所指的对象正在消解”[5]127。
西方传统的受众研究
传统的受众研究。受众研究在西方的研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不过古典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主要指演讲的听众与观众。为了论述方便,传统的受众研究大体可以分古典修辞学时期和近代修辞学时期。
古典修辞学时期,柏拉图非常强调听众的作用,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强调了理解听众的本质对于演讲的重要性。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古典修辞学家都认识到了听众在雄辩与劝说中的作用,例如早期的诡辩家高尔吉亚认为,词汇的声音,如果用技巧精心设计,可以俘虏听众[1]311。尤为重要的是,作为欧洲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修辞学著作,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汲取了古希腊修辞理论与实践的精华,对受众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6]亚氏对于青年、老年、壮年、贵族、富人以及当权者等群体的性格,以及愤怒、友爱、恐惧、嫉妒、怜悯、镇定等十六种情感做了详细的分析,是西方文明史中最早也最全面的关于受众的描写,是古典修辞学时期受众研究最为经典的成果。
近代修辞学时期对受众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18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修辞学家坎贝尔牧师。他认为修辞即能动地改变观众的过程,其目的是“启迪理解、满足想象、触动情感、影响意志”[7]1。受到当时功能心理学影响,坎贝尔关注大脑如何发生作用,把古典修辞学的知识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创建了以理解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修辞学,提出了“听众中心论”,为当代的受众研究铺设了道路。
现代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修辞学几乎变成了辞格的研究,修辞学传统陷入空前的低谷,成了一门“垂死的学科”[8]907。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写作与言语交际学兴趣的增加,修辞学悄然发生变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人们更多地使用“写作”、“文章学”或“交际学”等取代“修辞学”,在当时“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西方修辞学以新的面孔重新开始了新的复兴,受众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并得到快速发展。
其一,文章学或写作领域。19世纪末,美国大学开设了写作课之后,写作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现实—传统派、过程派等写作理论流派,学者们探讨了写作过程中受众的影响,他们认为,对于受众的意识和理解能够提高文章的质量,提醒作者与受众交流。当代西方修辞学家韦恩·布斯就讲,写作犹如演讲,必须考虑接受者、场景以及预期的回应。其二,新修辞学运动。从20世纪早期的言语交际热到五六十年代新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言语交际学、文章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将受众研究与当代哲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说写者转向听读者,强调受众在言语交际、论辩效果以及知识建构中的作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佩雷尔曼和泰特卡。两人认为,论辩的目的就是赢得听众的支持,听众的信奉既是论辩的目标又是论辩的起点,他们区分了普遍受众与特定受众,对于论辩过程中受众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此外,新修辞学运动的领袖博克也对传统中的受众的被动地位进行了质疑。博克的观点拓展了受众研究的思路,使受众研究变得愈加复杂化与多元化。其三,读者反应批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阐释学、俄国形式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文论开始把研究中心从作者转移到读者之上,尝试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研究方法,强调读者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作用,试图在对读者接受过程的研究中,把握艺术经验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规定性,由此沟通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之后,后现代主义更是采用独特的视角,打破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界限,对传统的受众观进行了颠覆。
当前大众传播阶段的受众研究
传播学与修辞学同根同源,但由于修辞学自遭受柏拉图贬低以来名声一直欠佳,源于古典修辞学演讲传统的言语交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之后另立门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传播学处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语义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神经病学等多学科接口,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进行研究。传播学虽然与修辞学分而治之、各自表述,但两者研究内容基本相同,两者均涵盖了人类交际的各个方面,均处于多种学科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视域下的受众研究与当今修辞学视野下的受众研究完全是一脉相承,毫无二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媒介与传播市场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播领域开始进一步对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受众研究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而且成了修辞与写作、阅读理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交际研究、论辩、戏剧、电影、电视、广告、新闻、宗教、政治、教育、表演、营销等不同学术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在当今时代,受众研究涉及的对象包含各种口头语与书面语、语言与非语言、音频与视频、真实与虚拟等多媒介、多模态的信息形式。受众研究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涵盖了主题、创造、策略、论辩、布局、推理、情景、风格、伦理、态度、美学、效果、媒介、权力、意识形态等等。
与传统的受众研究相比,当代的受众研究主要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强调了受众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二是强调了受众作为消费者、使用者或创造者的不同角色;三是受众研究的思路、方法、内容等呈现多元化态势。在西方近年影响比较大的如麦奎尔关于受众的综合研究[9],福斯在论述其“邀请修辞”理论时对受众内涵的研究[10]41,奥特和麦可对受众研究方法的研究[11]29-293,艾德勒和罗德·曼对受众类型、受众参与、受众预期、受众目的、受众投入、调查手段等问题的研究[12]330-337,罗斯维尔对受众分类与受众组成的分析[13]345-349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受众研究学说众多,特点各异,相互之间既有借鉴,又有差异,而且新的观点学说仍在不断的更新之中。
西方受众研究的启示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在受众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我国关于受众的研究仍然有不少可改进余地和发展空间。
第一,关于受众研究的认识。大多数受众研究基本出于商业目的,更多地考虑的是收视率、市场占有率等市场因素,对于在文化背景下受众本质的深入考察成果较少。受众的多维研究有利于揭示修辞与传播活动背后的态度与行为,揭示修辞与传播实践中的权力关系,揭示修辞与传播活动的本质与动机。第二,关于受众研究的目标。受众研究大多较为空泛,或者视野比较狭窄,缺乏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代表性成果。开展中西文化背景下修辞与传播活动中受众的研究,对于理解中西修辞与传播的特点,改善我国的对外宣传话语,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关于受众研究的方法。国外成熟的受众研究一般均有较为严谨科学、合理有序的方案设计和较为系统、较为客观的数据处理方法和信度效度分析。相比而言,国内的类似研究设计较为简单,数量较为有限,研究结果主观性较强。第四,关于受众的内涵研究。国内的受众研究相对较为空泛,受众内涵需要进一步细化,如年龄、性别、人数、时间、场合、地域、专业、目的、教育程度、价值取向、经济地位、文化差异、社团情况、调查方式等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受众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媒介背景下受众的作用完全不同,如演讲中的受众与听证会的受众;而且相同情境下同一受众的身份也会发生变化,沦为或自甘沦为“非受众”[14]149,受众与语境的契合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关于受众与媒介的结合。当代大众传播的重要特征就是信息传递的媒介发生了质的变化,语言与非语言、真实与虚拟等多模态情景下的受众研究成果较为少见。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更使得受众研究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重大课题。受众作为一个共同的话题和发展平台,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进行对话,对于新时期新媒介多模态背景下的修辞传播理论与实践而言,不仅前景广阔,而且意义深远。
[本文为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No.200801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温科学.中西比较修辞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刘燕南.《受众分析》:解读与思考[J].现代传播,2006,(1):137-139.
[3]Palvik,John V.,and Shawn McIntosh.Converging Media[M].3r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4]李惊雷.传媒经济的受众主体初探[J].国外社会科学,2011,(3):109-113.
[5]Biocca,F.A.“The breakdown of the canonical audience”[A].Ed.J.Anderson.Communication Yearbook[C]11:127—32.Newbury Park,CA:Sage,1988.
[6]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7]Campbell,George.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Ed.Lloyd Bitzer.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3.
[8]Bizzell,Patricia,and Bruce Herzberg.Rhetorical Tradition: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C].2nd ed.Boston:Bedford Books of St.Martin’s Press,2001.
[9]McQuail,Dennis.Audience Analysi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
[10]Foss,Sonja K.,and Karen A.Foss.Inviting Transformation[M].2nd ed.Long Grove:Waveland,2003.
[11]Ott,Brian,L.,and Robert L.Mack.Critical Media Studies:An Introduction[M].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
[12]Adler,Ronald B.,and George Rodman.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M].11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3]Rothwell,J.Dan.In the Company of Others: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M].4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4]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联书店,2004.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编校: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