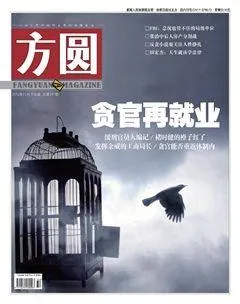田宏杰:天生就该学法律
【√】年轻的田宏杰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缜密的逻辑思维、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天生应该去学法律
她是首位连续被破格晋升的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最年轻的女性学科带头人,她还是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她就是田宏杰,一个将法律视如挚爱的天秤座女人。
“天秤座的人生来就带有一种使命感,他们心里有一杆在不停地衡量着各种事物的秤,只要遇到不公就会想要去改变。”田宏杰说,法律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与她的天秤性格不谋而合,转学法律满足了她所有的追求和理想,也让她的生命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迄今为止,田宏杰已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3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6部,主编、参与撰写学术著作近60部,12项科研成果14次荣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2002年经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田宏杰是一位颇具法学天赋的学者,但获得菲尔兹奖才是她最初的梦想。
兴趣悄然而至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我们那个年代高考的主‘旋律’,除了那些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同学,只有少数理科不太行的同学才会去选择读文科。”田宏杰是典型的好学生,从小到大,她的各门功课都是年级第一、第二,于她而言,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不过就是课程表上的一个个待学的科目,她不讨厌任何一门功课,但她从来没有真正去考虑过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数学是母亲帮她选择的专业,姐姐读的是化学专业,母亲希望她们姐妹能在理工科领域有所建树,成为学术界的“大小威廉姆斯”。
然而,尽管是母命,但田宏杰的心里却没有滋生出任何叛逆的情绪。“我喜欢寻求挑战,喜欢那种经过几个小时演算后终于找到答案时的兴奋,学数学恰好可以带给我这种刺激感。”就这样,田宏杰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旅程,过上了天天与数字、符号、草稿纸打交道的生活。
她本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像大学系主任新生致辞中所说的那样,终生与数字相伴,未曾想大四的换寝经历却为她人生的一次重要转型埋下伏笔。
“女生在理工科里一直都是稀有动物,当时川大数学系的97名学生中只有7名是女生,而每个寝室的容量是6人,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女生会被分去与其他专业的同学混住。女孩子的依赖感都很强,分到其他寝室就像是被孤立了一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成为‘第7人’。我们就搞了个‘轮换制’,每个学期换一个人‘被孤立’。” 作为7个人里的小妹妹,田宏杰成为最后一个被交流的对象,而她搬去的恰恰是法学院的寝室。
“学法律的女孩子跟学数学的女孩子相比要活泼很多,几个女孩子整天唧唧喳喳的很是欢乐。”田宏杰告诉《方圆》记者,搬到法学院的寝室后,摆龙门阵(重庆方言,聊天的意思)代替了厚厚的演算纸,成为每晚的必备活动。
“晚上卧谈的时候,她们几个就会拿一些稀奇古怪的案例出来讨论,有时还争论得不可开交。”这是田宏杰与法律的初次邂逅,这些案例中有人情冷暖,有世态炎凉,她第一次发现法律竟是如此的强大,可以定纷止争,可以惩恶扬善。
“也许是天秤座的本性使然,我看不惯一切不公,而法律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去改变这一切。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像是在解一道数学难题,紧张而又刺激。”于是,田宏杰开始留意起这个叫法律的东西。
除了爱抱不平的个性,法律对逻辑思维的要求也深深吸引了田宏杰。“那时我还是个门外汉,对法律一窍不通,但我发现她们争论的双方常常是在相同的前提之下得出迥然相异的结论,而且还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就笑言,如果换我来学法律,我肯定年年都拿一等奖学金。”年轻的田宏杰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缜密的逻辑思维、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天生应该去学法律。
打心底里热爱的事
尽管如此,本科毕业之后田宏杰却没有立刻投入法律的怀抱,而是选择了一份与数学专业相关的工作。“我那时像学数学专业的人一样报考了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但统招研究生的指标只有两个,而我是第三名,正好这时又有工作的机会,所以就放弃了定向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去工作了。虽然自己对法律比较感兴趣,但始终没有把它放到议事日程之上。”
由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工作后的田宏杰非常清闲,每天工作之余的“任务”就是跟同事们在办公室里比赛打俄罗斯方块,一“打”就是一年。
“后来有一天,一个同学跟我打电话聊天,她向我抱怨每天加班的辛苦,但我却羡慕不已,她每天都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充实自己的生活。而我,工作量非常小,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打方块、比得分、编写游戏程序,循环往复。”田宏杰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了无生机,虽然工作待遇优厚,但她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
一番思量之后,她决定转学法律。
“真正接触法律之后我才发现,法律的内涵很丰富,它不仅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还凝聚了公平、人性以及做人的智慧等等。而这一切,正是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东西。”田宏杰告诉《方圆》记者,她很感恩,因为她在有生之年找到了自己最喜爱的东西,而这份爱可以让她义无反顾地将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
“许多人穷尽一生心血,有可能都无法找到自己所热衷的事业,而我不仅找到了,而且还能有机会去从事,我很幸运。因为大学毕业后的那段工作经历,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要重新扬帆起航,我只能是拼尽全力。”于是田宏杰开始“偷”时间,其他人的一天是24个小时,但她的一天却是26甚至是28个小时。
“从1994年到2003年,我只看过一场电影,平均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教室、图书馆以及电脑桌前度过,写论文写得特别畅快时,几天几夜都不会合眼。”为了不耽误一分一秒,田宏杰会在冰箱里备上几十包泡面、几十袋榨菜、几十根火腿肠。饿了,就烧一壶开水,泡一碗面,蹲到垃圾桶旁去吃,然后一股脑地扔到垃圾桶里,再继续回到电脑桌前工作。
“这样可以省去收拾碗筷的时间。”田宏杰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经常以泡面为食,田宏杰的脸上长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痘痘。感觉到发痒,她就用手直接去挠,破皮流血了,她就随手找张纸巾擦一下,接着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对一个人来讲,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正是对法律的这份热爱让她十数年如一日,始终与电脑为友,与法律文献为伴。
于是,在正式与法律接触的第7个年头,即博士毕业后一年,她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第9个年头,破格晋升为教授;第10个年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田宏杰用10年的时间走完了许多法律人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才能走完的路。
“我喜欢这里,但却不得不走”
2004年,田宏杰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这个让她终生留恋的学校。“我喜欢法大的老师,喜欢法大的每一个学生,直到现在我依旧很怀念那段时光。”她用怀念来形容,是因为早在2006年3月她就已经离开法大,选择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当时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急缺刑法学老师,王利明老师希望能挑选一批有激情、有实力的青年教师,为刑法学专业注入源头活水。”人民大学是田宏杰的母校,母校当时的困境让她很是牵挂。一番抉择后,她决定离开法大。
然而,虽然田宏杰只在法大待了三年,但她却与法大的学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为了挽留田宏杰,法大的学生们发起了签名挽留活动,看着那一条条、一封封表达同学们心愿的短信、电子邮件,田宏杰不禁泪流满面。
徐显明校长的亲自挽留、高浣月副校长和曲新久老师的真诚交谈,同样令田宏杰感动不已,终生怀想。“多么好的学生,多么好的领导,多么好的学校!我真是割舍不了。但是,我的母校需要我回去,而没有母校的培养,就不会有我的法律人生。人,不能忘记养育之恩。”
法律人最重要的是担当
决定做好了,但那些曾与田宏杰朝夕相处过的学生却令田宏杰难以割舍,她决定兼顾法大与人大两所学校的教学任务,义务将其在法大的剩余课时讲完。
那时的中国政法大学本科部在昌平校区,那段时间,田宏杰每周有3天要往返于海淀和昌平两地,“包油”也“包人”。
“政法大学当年的刑法课程设置与其他学校不同,课时要比其他学校少一学期。作为法学主干课程,在规定的课时内很难把内容讲透彻,我就在周末给学生加课,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一个班,十二点半到下午五点一个班,晚上六点到十点一个班,后半学期几乎周周如此。” 田宏杰告诉记者,只要还有一个学生的眼神里有求知的渴望,她就会讲下去,即使自己早已疲惫不堪。“法律人最重要的是担当,是社会责任,教书育人就是我的社会责任。”
这样密集的安排让田宏杰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去吃饭,法大的学生们就悄悄地买了营养快线、核桃露等放到讲桌上,让田宏杰在喝水的同时补充些能量。
法大实行选课制,田宏杰的敬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选她课的学生,但教室的容量有限,不断有学生通过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问她,“老师您可不可以再扩容啊?您知道吗,每次有您课的时候,我们不到早晨6点就在教学楼外排队,楼门一开,五分钟之内座位就会被占满,我们都非常想听您讲课。”
这个学生的话让田宏杰很感动,“其实,上大课很累,即使有话筒,也得经常扯着嗓子大声喊,否则,最后几排学生还是听不清。但教书育人是老师最大的担当,学生的肯定是我最大的荣幸。既然学生们有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我就应该尽我所能去满足他们。”
一直到现在,只要法大同学们邀请作讲座,田宏杰都会尽量争取到场。“法大本科部地处昌平,学生会的各种论坛、讲座完全由学生策划、组织,非常不容易,而举办水准都很高。能给学生们一定支持,在我非常快乐,更何况,在法大工作的几年,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
田宏杰的“法大情结”并非仅仅缘于此,她始终认为教书育人是老师的责任,没有任何门第之分,只要学生渴求获取知识,她就不会拒绝。
“我们这个社会不乏有才华的人,但越来越缺少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而这一点对法律人来讲更为重要。”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现代化研究所所长,现在的田宏杰不仅要做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还要致力于政法栋梁的培育和法治队伍的建设。自己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不难,难的是让所有的学生都有社会担当。
什么是该做的事
采访中,“法律人最重要的是担当”常常挂在田宏杰的嘴边,她曾经以为实务界理论水平不高,现实中又有许多的无可奈何,无法真正做到有所担当,所以博士毕业后她便义无反顾地做了大学老师,以为这样才能独善其身。然而,在东城区检察院的挂职经历却改变了她,也将她的“担当理论”丰富升华。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认识到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法律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法律人精研法理,而且需要法律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不仅要求法律人准确适用法律,而且要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田宏杰告诉记者,三年多检察系统的学者挂职经历,让她对司法实务和中国法治建构的实践有了深刻的切身感受。
从理论派到实践派,田宏杰彻底消除了自己作为学界中人可能因雾里看花而对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产生的误读。“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往往需要一定的实践历练方能铸就,法学家首先应当是优秀的法律家,法学教育研究只有源于实践,才能真正高于实践。”
检学共建让田宏杰受益良多,在实现研究领域突破的同时,她的研究成果与教育培训的质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高。田宏杰不仅培养打造了一支法经济学博士生科研团队,她提出的“前提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犯罪认定机制、“行政优先为原则、刑事先理为例外”的行刑衔接机制等研究成果以及信息治理理论,在丰富和超越传统理论的同时,也为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受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与好评。
“新时期的中国法学只有坚持终极现实关怀,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研究中国社会、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真’问题,法学研究成果才能谓之科学,法学专家的建言献策才能真正指导实践。唯有如此,培养出来的法学学生才能成为具有科学问题意识和突出创新能力的卓越法律人才,而不是人云亦云简单重复前人的法律工匠;法学前沿的开拓,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法治发展方向的指引,而不是对国外法学前沿的急于追赶乃至于盲目追随。这是我们中国法学学者必须负起的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