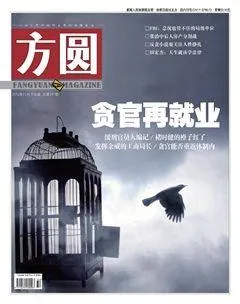身在异乡为异客
【√】从诗性和哲学的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是身在异乡,一生都在短暂的时光中漂泊
一个诗人朋友深夜打电话来说感觉自己已经病得很厉害,就像要死的样子,他描述症状时让我想起了老年的托尔斯泰——手心发凉,四肢发抖,很想哭,很想爱。放下电话我就想到了一个巨大的灵魂在不断超越自己现实定义的同时,肉体就会成为意识领域的障碍,让死亡也变得宏大而又神圣。我是一个苟活的人,整日里安身立命,懒得出门,也从不想在开阔的大地上走得更远。但是我羡慕那些行万里路者,我总觉着他们有比我更多的勇气与心力。
日前我在一所大学的文学讲座中说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人海子与他的作品。他的卧轨自杀像是给了诗人海子一枚至高的诗歌勋章。听众也像是更加迷恋于我对一个诗人死亡时刻的那些神秘与细致的分解描述,有的感情丰富敏感者还当场流下了泪水。
我也因此而动容,但还是把话题拐到了人世的温暖上,当然是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说还是好好的生活吧,用一个生者的信仰化解那些人类的巨大悲情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类似那些永恒的星球。我还说到了朦胧派的先驱诗人食指先生与他的相信未来,我先后在山东与北京见过这位先知,他集高大的孤独与一种普世的温情于一身,在山东有人背过身来问我他是不是刚从疯人院里出来不久,我说他看上去是有些憔悴,但语气铿锵充满了人性的关怀;他走路的样子是有些让人担心,但你能感受到的是他卓尔不群,两袖清风。
也许在诸多的财富中,孤独是最为珍贵的一笔,由人类的悲情造就的孤独是一种神圣的馈赠。不要死,活下去,是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对美好世界的召唤。他在百般绝望中写下:彼得堡,我还不想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死亡、诬陷、监禁、饥饿、流亡,都没能让这个灵魂的漂泊者放弃生命,尽管他因患上精神分裂,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未遂,所幸只是摔伤了胳膊,他活了下来,尽管依旧挣扎在死亡线上,却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高产期而成为世间一位不朽的诗人。
我的这位诗人朋友显然也已写出了惊世之作,他奔走天涯只是为了改善现实的境遇,然而离别自己故土的隐痛并没有阻止自己巨大的创作激情。另一个好朋友说我们只是想有个好日子可过,所以总是希望眼前能够更加敞亮些。朋友们之间总是如此,诚挚的人世温情总能带给一个异乡人内心一缕奇异的光束,哪怕让黑夜中的美梦延续的更长更美妙一些。
我是个厌恶楼宇而眷顾阳台的人,养养花,种种草,听舒缓的曲子,让一条忠诚的家狗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好人家。就有朋友直言说我这样的一个写诗的人一般死不了,他指的当然是自杀。
其实我也曾有过这种因为生而纠结才有的举动,我想过那些曼妙的事件与将肉体投奔下去的深色水域,可是正如我懒得出门,我只是庸俗地生活在一个更加庸俗的地域与人群,所幸还有人世的善举让你没完没了地去学习与工作,孤独作为一个豪华的阵容将永远排布在另一个自我之中了。
从诗性和哲学的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是身在异乡,一生都在短暂的时光中漂泊。正因如此,亲人的关怀,朋友的问候就显得特别重要。生活中,令我引以为豪的是我的朋友们,他们有的才华横溢,有的平凡如我,像一条深山里的溪流,需要安静与鼓励才得以存在与延展。我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他们从内心出发,总是说一些真挚而温和的话;而这些好听的话,我很想找个地儿记下来,时常得意地翻一翻,此时,我相信我看见了大海,并相信这就是我们内心不停涌动的温情的大海。
刘瑜
青年诗人,著有诗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