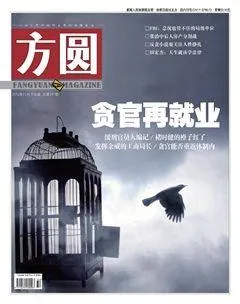贪官能否重返“体制内”
【√】资格刑通过剥夺腐败犯罪人担任公职的资格,从根本上剥夺了其再次实施腐败犯罪的能力, 进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特殊预防
“阜宁缓刑官员入编”所带来的舆论漩涡渐渐平息,但关于“贪官再就业”的话题却不应该止步于个案。民众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非议在于:贪官在任上已经“捞够了”,即使被判刑,出狱后也应该衣食无忧。凭什么还要跟我们来抢夺社会资源?
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腐败的不满、恐慌与担忧,另一方面是刑满释放的低级别职务犯罪人员面临难以再就业的窘境。也就是说,对于法律而言,必须同时解决腐败预防控制和反对就业歧视两个命题。
贪官能不能再当公务员?能不能再有事业编制?能不能重新就业、工作?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一套解决方案。对此,有人建议在刑法中引入“资格刑”的概念,也就是说,法官在对职务犯罪审判的同时宣告禁止犯罪人再次担任公职。
资格刑并非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一个刑罚分类的概念。资格刑在国内立法中一直备受争议,但却在国外刑事立法中被广泛使用。将资格刑引进到国内立法中,能不能防止“阜宁缓刑官员入编”类似的事件的再发生?会不会对出狱贪官的再就业形成一种歧视?《方圆》记者采访了吉林大学刑法学副教授李海滢。
将贪官从公职中剥离是国际惯例
《方圆》:你认为出狱后的官员能否担任公职人员,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重返“体制内”?
李海滢:当然不能。
《方圆》:据我了解,你是主张设立资格刑,将贪腐官员从公职中彻底剥离出去的支持者。
李海滢:是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腐败很严重,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这种情况下,设立一套完善的资格刑制度,可以确保刑法在腐败犯罪控制方面的功能得以更为有效的发挥。
《方圆》: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资格刑?
李海滢:腐败犯罪资格刑的设置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如奴隶制刑法中的“不齿”,秦朝的“废”、“夺爵”,汉朝的“禁锢”, 唐朝的“除免”,及至清朝末期与民国时期的“褫夺公权”,最后一点至今仍然在台湾地区刑法中被保留。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处罚并没有明确规定资格刑, 只是在第383条贪污罪、第386条受贿罪、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的司法建议,影射出了一点资格刑的韵味。
当然,也有人觉得现行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但个人觉得它的政治意味更浓,剥夺面也更宽,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与我们所提倡的资格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纵观国外立法,虽然可能翻译名称不一,例如有“禁止担任公职”、“褫夺公权”等等,但其实质都是禁止有前科的人再度担任相关公职。一般都将剥夺腐败犯罪分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公职等纳入本国刑法规范, 如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其中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立法,因为与我国同属于成文法国家,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资格刑在腐败控制方面的作用
《方圆》: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有犯罪记录的人不得被录用为公务员,这能算是资格刑的一种吗?
李海滢:《公务员法》的规定只是一种行政处理,而行政处理与刑罚处罚是有区别的,也违背了罪刑法定的精神。资格刑是与生命刑、财产刑、自由刑并列的一种刑罚。必须由刑法规定、法官宣布、被写进判决书,对腐败的预防和控制才会更加“名正言顺”。
《方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刑法学实务界曾有一批人主张出台《反贪污贿赂法》,资格刑就曾被提及应列入其中。但随着该法律的流产,将贪官从公职人员队伍中剥离的想法也没有真正实现。这是为什么?
李海滢:我们国家这几年对于刑罚方面的立法不是特别正式,1997年刑法已经连续出了八个修正案,都没有提过刑罚种类的问题,别说资格刑了。
但是,有关反腐方面的专门性立法一直都在努力中。我们也期望,能够在其中专门针对腐败犯罪,引入资格刑的概念。
《方圆》:那么,你觉得对贪腐官员从刑罚上直接明确禁止其从事公务员或者某些职位,能够在其出狱后起到哪些作用?
李海滢:我觉得有四个作用:首先, 资格刑通过剥夺腐败犯罪人担任公职的资格,从根本上剥夺了其再次实施腐败犯罪的能力, 进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特殊预防。
其次, 对腐败犯罪适用资格刑, 是对犯罪人更直接、更严厉的否定性政治评价, 可以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 增强刑罚的威慑功能, 从而强化腐败犯罪的一般预防。
再次, 腐败犯罪分子利用自身国家公职人员的资格,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 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害, 也严重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对这些犯罪人科以资格刑, 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机关威信和纯洁国家公职人员信誉。
最后, 对情节较轻的腐败犯罪, 单独适用资格刑, 有利于克服目前短期自由刑所存在的交叉感染、再社会化困难等弊端, 也符合刑罚的经济性要求。
《方圆》:具体的制度设计内容有些哪些呢?
李海滢:我觉得在刑法中可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在总则中, 系统规定资格刑的内容、适用原则、适用对象、适用模式以及执行方式等;第二层是对于情节较为严重的腐败犯罪, 明确规定应当附加适用资格刑;第三层是对于情节较轻的腐败犯罪,明确规定应当附加适用或者单独适用资格刑。
剥夺资格不等于就业歧视
《方圆》:我们发现,在“阜宁缓刑官员入编”的事例中,县政府是打了“事业编”这个擦边球,从而规避了公务员法的规定。那么,资格刑的禁止的范围应该有哪些?仅适用于公务员,还是需要涵盖事业单位、公共团体、国有企业?
李海滢:这是跟我们的体制有关系的。很多事业单位,实质上都在行使公共权力。从当前的刑事立法看, 腐败犯罪资格刑的适用对象仅限于我国国家公职人员。所以,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等都在这个范围内,这样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才有权立案查处。
《方圆》:很多反对我国引入资格刑制度的人都存在一种担忧:会不会是对于出狱者的一种就业歧视。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很多普通职务犯罪者出狱后,要比普通刑事犯罪者出狱后更加难以再次拥有就业机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海滢: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在提倡“前科消灭”等制度,但保障他们的再就业权益,不等于放弃对腐败的控制与预防。
资格刑有个特点,它是针对特定的犯罪行为,典型如职务犯罪。这些犯罪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务,并且社会危害后果很严重。那么,要预防他们再犯罪,剥夺再犯罪的条件(即公职人员)身份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起码从现有的社会大环境来看,是对社会更为有益、也更好的一种选择。这与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并不矛盾。
相反,我提倡的对于被判处一定期限资格刑的犯罪分子, 在该期限届满之后, 被剥夺的权利重新恢复, 犯罪人有机会重新做人, 这不仅不会损害刑罚的教育功能, 而且有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这正是刑罚人性化的体现。
至于你所说的权利保障问题,我觉得一方面公务员毕竟只是职业的一小部分,还可以从事其他工作,据说褚时健保外就医后种橙子还种成了橙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应该排斥他们,例如医保、养老等,该有的都要给予,这才是真正的不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