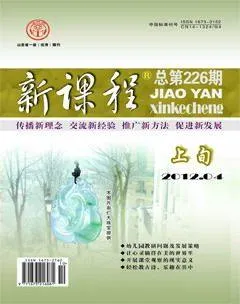叙事视角下记叙文的时间要素
我们都知道记叙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在具体分析文本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是“时间”要素,虽然是第一个分析的要素,但是往往只是在文本中找一下从而得出文本的时间顺序——倒叙还是顺叙,以证明“时间”确实是记叙文的要素。在深入分析文本的阶段时,“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则显得详细得多。如若解释“时间”云云,学生嫌老师啰嗦,老师也觉得多此一举,想来想去是也没什么好讲的,大体的原因是时间谁不知道,有什么好解释的。然而,实际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下面,我们尝试从叙事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记叙文的“时间”要素。
俄国宗教思想家、哲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佳耶夫认为,时间按其特征来说,有三种类型,即宇宙的(其性质是环形的)、历史的(其性质是线性的)以及存在的(即心理上的,其性质是垂直性的)。但是,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不是从抽象的哲学原理开始的,而是从他们的日常起居作息,以及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开始的。时间由此成为叙事作品不可回避的东西。叙事由此成为时间的艺术。因此,从文类角度来看,与叙事文类基本等同的记叙文类必然是时间的艺术。建构主义者认为叙事时间反映的是叙事者对历史时间的主观感受,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可见叙事时间是存在的时间,或者叫心理时间。柏格森“心理时间”学说告诉我们:心理时间的延续不是恒速的,它总是快快慢慢;也不是线性发展的,有时候它会停顿,有时候甚至竟然还会倒退。叙事时间速度的快慢、停顿甚至倒退显然是由叙事者决定的,人作为叙事者的知识、视野、情感和哲学的投入,成了左右叙事时间速度的原动力。作者的价值判断,是操纵叙事时间速度的无形之手。反过来,叙事时间速度的快慢也真实地反映着作者的价值判断。
所谓叙事时间速度,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只有有了相对比较的参照对象,速度的快慢才能显现出来。在叙事文本内部,是与情节疏密度的比较。在叙事文本外部,则表现为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比较。在叙事文本内部,叙事时间速度,是和叙事情节的疏密度成反比的,情节越密,时间速度越慢;反之,情节越疏,时间速度越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叙事文本中,以三句五句话,就讲述了十年八年,甚至几世几劫,这样的叙事时间的流转速度难道还不够快吗?在叙事文本外部,所谓叙事时间速度,乃是由历史时间的长度和叙事文本的长度相比较而成立的,历史时间越长而文本长度越短,叙事时间速度越快;反之,历史时间越短而文本长度越长,叙事时间速度就越慢。历史时间是一个常数,但是当它投射到叙事过程的时候,它却变成了一个变数。在一部叙事作品中,讲述一日事情所使用的文字,有时比讲述一月、一年、甚至十年的文字还要长。由此可见,叙事时间速度决定了记叙文的详略,体现了记叙文情理的倾向性,即作者的知识、情感和哲理的倾向性。如阿累的《一面》。文本的第1、2自然段交代了见鲁迅“一面”的具体时间是“1932年秋天”“一天中午”,第39自然段交代的时间是“在这四年里”,文末交代了写作本文的时间是“1936年10月”。全文共43个自然段,第一部分1~38自然段,记叙“我”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一面”的情况,文本长度是2076字,叙事时间是“1932年秋天”“一天中午”,根据文中第2自然段“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可以断定,“一面”确切的叙事时间也只是半个钟头;第二部分最后五段,抒写“一面”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文本长度是220字,叙事时间却是四年。从叙事时间的速度来看,第一部分大约是每69字需叙写1分钟,而第二部分则大约是每55字就叙写了1年。可见,“一面”叙事的焦点是作者见鲁迅一面的具体情景,而且如果没有叙事时间速度的慢速前行,就不可能增强情节的密度,也就不可能在形象的展现中把鲁迅热爱劳动人民和关怀进步青年的高尚品格和作者对鲁迅先生真挚而又深厚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时间速度的控制,使叙事文本像一条大河,飞泻于峡谷,缓行于平原,那么,时间顺序的变异形态——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就使这条大河波浪起伏,曲折多姿了。在初中阶段,这种时间的变异形态主要是指记叙方式——倒叙、插叙,究其本质就是叙事者对正常的运行方式的干扰、打断或倒装。元好问曾经说过:“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头布袋。”这“曲折”就是叙事者对叙事时间操作的具体体现了。比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关于“美女蛇”故事的插叙。其作用,苏教版的教参是这样分析的:
课文中由相传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引出了关于“美女蛇”故事的插叙。作者是怀着浓厚的兴味来回忆这个故事的。儿童是喜欢听故事的,而这个神乎其神的故事又给百草园抹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给百草园增添了神秘感。插叙美女蛇的故事,更丰富了百草园“乐园”的情趣。后来写想到飞蜈蚣也非常切合儿童心理。而“做人之险”则是作者的发挥,其中糅进了成人的看法。
上述解释虽然不能算错,但是未免浅了一点。因为这样的解释很难解决这样几个疑问:从整个叙事文本的疏密度来看,全文共2467字;第一部分(1~9自然段)共1379字;第二部分(10~24自然段)共1088字。插叙(4~6自然段)共487字;第2段写百草园春、夏、秋三季的景色,历来是教学的重点,共304字;第7、8段写百草园的冬天,共343字。比较而言,插叙的“美女蛇”的故事反而是第一部分中叙事疏密度最高的。不是教学重点的“插叙”为什么疏密度却是最高的?另外,就本文结构而言,没有这个故事,文章也完整,两种生活的对比也鲜明,主题也明确。那么,叙事者为什么要“插叙”故事来打破这种完整呢?因此,我们认为叙事疏密度高说明了这个插叙必定是叙事者聚焦的一个重点,与此同时又用“插叙”改变了叙事时间顺序的形态,更加说明这个“插叙”隐含着叙事者对文本生命的某种认识。从表面层次来看,美女蛇故事确能“映衬百草园神话般色彩,”而且也有助于“乐园”风物的动人,因而也就有助于两种生活的对比。但是这个答案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贬低了故事对表现和深化主题的重大作用,否定了故事是百草园生活内容的必要组成部分,抹杀了作者必须插叙这个故事的深意。从深层次来看,百草园的生活乐趣,除了四季自然景物和从闰土父亲那里学习捕鸟知识外,夏夜乘凉,听长妈妈讲一些离奇的故事,增加对社会的了解,也是重要的一部分。从五光十色的自然风物到复杂艰险的社会生活,从生产知识到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人与美女蛇关系不过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倒影,不是使百草园生活更丰富、更完整、更充实吗?而且使得“乐园”与脱离社会实际关门死读书的“三味书屋”的对比更强烈、更鲜明、更具批判性,从而也就更有力地表现和深化了主题,这就是插叙的又一重要作用。如果把百草园的生活乐趣仅归结为“丰富多彩”的“自然风物”,而插叙也仅是映衬或增加一些“神话色彩”,那显然就贬低了插叙故事对文章主题的表现和深化作用。
关于记叙文时间要素的考察,我们还可以从叙事时间的频率来做一番探究。在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频率的形态如下:
单一的:一个事件,一次描述
多种的:多个事件,多次描述
重复的:一个事件,多次描述
概括的:多个事件,一次描述
由于一次讲述产生不了频率,因此频率这个概念实际上只和“重复”有关系。“当一个事件仅仅发生一次而被多次描述时,我们就称之为重复。”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里为重复下了这样的定义。具体来讲,可以有这些表现:(1)情节的重复;(2)细节的重复。最为我们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鲁迅《祝福》中祥林嫂重复叙述她儿子被狼吃掉的事件。祥林嫂难以摆脱痛失爱子的悲苦心情,逢人便讲:“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在她一次又一次的一字不差地重复叙述之后,人们已经从同情到厌烦,以至于她还没说完,听的人就把她要说的下一句说出来了。通过这个重复说明了这个事件对她的打击之深。至于全镇的人对祥林嫂的话的厌烦的重复,则揭示了作者对听者麻木不仁的批判。而此后在祥林嫂几次仍像过去那样在祭祀时准备分配酒杯和筷子时,四婶却一次一次地重复同样的话:“祥林嫂,你放着罢!”这样一次又一次以同样的话阻止祥林嫂在祭祀时插手,则显示出祥林嫂已为周围的人们所抛弃,这对于祥林嫂最终悲剧的形成具有直接的作用。
总之,一如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所说:“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尽管现代叙事作品中,出现了反时间的实验小说,想要分割时间,淡化时间,甚至还要消灭时间。法国女作家斯坦因就曾经为此而作了多种努力,但最终只能失败。就像人生中不可战胜时间一样,叙事的时间也是不可战胜的。叙事学对时间的研究,给我们分析和解读记叙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
(作者单位 江苏省昆山市新镇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