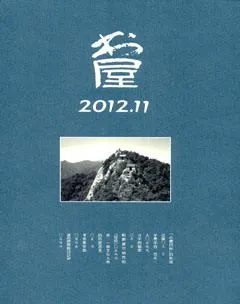白居易的“达观”生活
唐代诗人三巨头中,白居易可以说人生与仕途顺山顺水最为得意。先说李白,才情横溢,除了有近两年的时间在皇帝身边做文学弄臣以此点缀歌舞升平以外,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卒于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里;杜甫则更惨,虽说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人生理想也颇为远大崇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除了“麻鞋见天子”,被肃宗皇帝授予左拾遗和被四川节度使严武表奏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外,好像也没什么大的作为。杜甫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苦与漂泊中度过,五十九岁时,病死于湘江上的一只木船上,藁葬于耒阳。四十多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让他魂归故里,把他的尸骨改葬于老家河南巩县。
在三人中,白居易是唯一一个以进士及第跻身官场的。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考中进士那年,白居易二十八岁,第四名,同时在录取的十七人中他年龄最小。他颇为得意,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这时的白居易“济世”的豪情万丈,直冲云霄:“心中志气大,眼前爵禄轻。”于是他撰《策林》七十五篇,阐述治国之道;作《初授拾遗献书》,向宪宗皇帝表明自己的忠诚与对国事的关心;更是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以表忧民情怀,真可谓“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同时他天真地认为“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但不久他那“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直言脾性终于碰壁,“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公元815年,四十三岁那年,出现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的挫折,因上疏论宰相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立即缉拿刺客,以雪国耻而被宰相们指为越职言事,同时他的仇人说其不孝(牵强说他母亲看花落井身亡,而他却作了《赏花》、《新井》诗)。唐宪宗一听大怒,把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白居易彻底醒悟了,自此以后,他的“兼济”天下之心渐渐滑向了观照己心的“独善”:“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不敢再过问政治,自称“天涯沦落人”,不由生出了“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的感慨,由此开始了他的“奉身而退,行在独善”的生涯:“从容于山水诗酒间”,与自然山水为伴,山僧野老为友,“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不闷”。
五年后,回到朝廷,随后在忠州、苏州、杭州做刺史,为官清廉,深得民心。在杭州,曾修筑白堤,蓄水灌田千余顷。杭州刺史三载,白居易颇为清廉,离任之时,告别城中百姓,写下了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并把自己的一大笔俸银留于官库中,只带走了两块采自天竺山上的太湖石,为此还写诗自问是否有伤清白:“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斤,无乃伤清白。”而离苏州日,郡中市民涕泣相送,这让白居易久久不能忘怀:“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渐荷宠命,去愧无能名。青紫行将吏,班白列黎氓。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树色,尚闻丝竹声。怅望武丘路,沉吟浒水亭。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后来,为纪念他,苏州人民曾建白公祠,祠中有思白堂,并刻有碑记。最后白居易的官越做越大,七十岁那年,以刑部尚书退休,寓居洛阳香山,以蓄姬、嗜茶与饮酒自娱:“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浅把三分酒,闲题数句诗”,并在具有风土水木之胜的洛阳城东南隅建造了一处占地一十七亩的庭园,园内有水、竹、树、岛、石、桥、鹤,有书库,有酒,有琴等,真正过起了“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的神仙生活。公元846年3月,唐宣宗即位,宣宗皇帝很欣赏白居易的诗歌和才能,打算任命他做宰相,没成想这年的8月,白居易去世。唐宣宗悲痛欲绝,赋诗一首以示悼念之情:“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在古代,皇帝亲自写诗哀悼诗人的并不多。在唐代,文人去世后得到皇帝凭吊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谏臣魏征,曾得到唐太宗以诗《望送魏征葬》凭吊:“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草共谁遣”;另一位就是白居易了)。若白居易地下有知,也该很知足。白居易死后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忧郁诗人李商隐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在三人中,要论当时他们诗的社会影响,李、杜完全抵不过白居易。为此白居易还颇为自豪与自得,他在《与元九书》中曾这样写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好友元稹(即元九)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更为惊奇的是当时长安的恶少以浑身刺白诗成为了一种“时尚”。同时,白居易的诗也走出了国门,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安南(今越南)等国,都有其忠实的粉丝。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而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三诗人已离我们而去一千多年,李白的“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也在痛苦与悲壮中夭折,而白居易历经唐朝的八位皇帝,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宗旨,无论“兼济”还是“独善”都做得如此完美。正如唐五代诗人李频称颂其友人所说:“惠人须宰邑,为政贵通经。却用清琴理,犹嫌薄俗听。涨江晴渐渌,春峤烧还青。若宿严陵濑,谁当是客星。”也如白居易自己所言:“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闻有酒时须笑乐,不关身事莫思量。”也许有人说他消极,我看未必,这是儒家与道家、佛家思想的最佳结合(如他在被贬江州时,曾写诗言阅读《庄子》的感受:“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白居易曾有诗写道:“壮日苦曾惊岁月,长年都不惜光阴。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正因为如此,白居易的人生与仕途要比李白和杜甫得意的多,而使得两宋的士大夫们推崇不已:因白居易曾写就《中隐》以明其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为此张志华“在洛葺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范成大则云“中隐堂前入意好”;而陈师道因仰慕白居易出处仕间的进退自如,建起了“思白堂”、“尊白堂”;在宦海中坎坷了一生、屡遭不测的苏东坡则更加崇拜白居易的人生哲学,曾在游西湖时云“未成小隐成中隐”。而叶梦得认为白居易之所以得意晚年,主要因为“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可谓一语中的!
如此说来,这也是一种很达观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