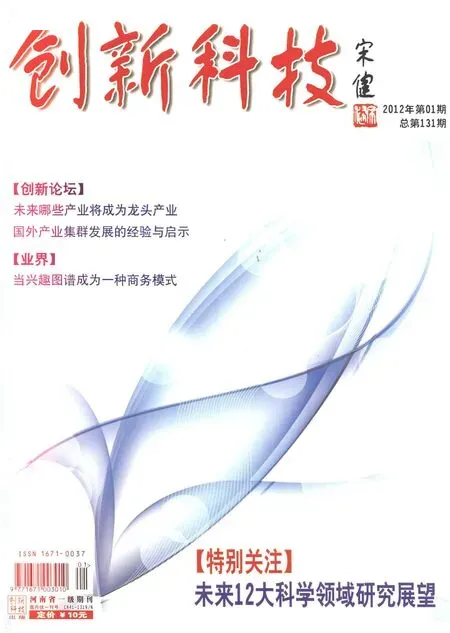反思“雾都”应向伦敦学习
文/王琦
反思“雾都”应向伦敦学习
文/王琦
2011年12月4日,北京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据环保局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数据,当晚19时,北京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达到0.437毫克/立方米,短时达到重度污染程度。
这是12月5日《新京报》的一则报道,标题是“北京大雾致高速封闭航班延误,首都成‘雾都’”。事实上,随着我国近期多个城市大雾天气频繁登场,“雾都”一词已经广泛流传开来。上网一搜,诸如“进入11月,杭城仿佛变身雾都”、“合肥变身雾都,大雾生活喜忧参半”之类的报道比比皆是。
雾都,并没有小说中描述的“像雨像雾又像风”那般浪漫。5日,京津冀等9地遭遇大雾,导致首都机场延误严重,京哈高速堵车50公里,山东近百条高速关闭。对此,气象专家解释称,秋冬季节华北平原出现大雾比较正常,不算是特殊天气现象。不过,如果我们仅仅把“雾都”当做自然现象,很可能会忽视大自然发出的警示讯号。
虽然空气污染与大雾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雾都”肯定会受到空气污染的间接影响。从气象角度来说,雾的形成不仅需要水汽,还需要有凝结核。城市里的汽车尾气、扬尘、工业废气等悬浮颗粒物就是大雾的“帮凶”,恰恰提供了适宜水汽积累的凝结核。凝结核越多,越容易延长雾的时间,增加雾的浓度,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与此同时,雾天风速变得很小,湿度很大,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中各项污染物浓度也会快速上升,进一步加重了空气污染,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12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北京PM2.5监测数据再次爆表,超过了最高污染指数500,此时的PM2.5浓度522,也因为“超出了该污染物的值域”,在美国环保局网站上无法转换为空气质量指数。
提起“雾都”,人们很自然会想到英国伦敦。每当春秋之交,这里经常被浓雾所笼罩,像是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以至于印象派大师莫奈惊呼“我热爱伦敦胜过热爱英国的乡村,而我最爱的则是伦敦的雾。”然而,1952年12月一场“雾都劫难”,让伦敦人看到了大雾的恐怖。当时,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被浓雾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在大雾期间以及雾散后的两个月间,12 000余人因毒雾患病死去,这场灾难后来被列入20世纪十大自然灾害。
痛定思痛,英国人开始重新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决心走出迷雾。他们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减少和抑制污染物的排放;出台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对工厂选址和污染物排放严格监管,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地减少了导致大雾笼罩的各种烟尘和颗粒物。随着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伦敦政府又运用一系列措施,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车发展,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整治交通拥堵等等。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伦敦终于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与航班延误、高速关闭等看得见的有形影响,大雾与污染的因果关系往往容易被忽视。尽管我们没有经历“雾都劫难”的可怕一幕,但向伦敦学习如何反思“大雾”,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防范灾难的降临。从国家层面而言,开征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杠杆用于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调节作用,引导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应提到议程上来;就公民个体而言,少开私家车,多使用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也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请记住,防止大雾成灾,我们谁都不是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