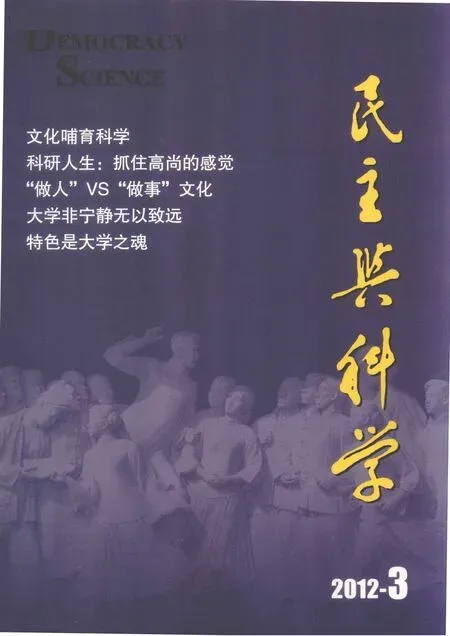文化哺育科学
■孙慕天
文化哺育科学
■孙慕天
20世纪50年代,斯诺(C.P.Snow)发表了那篇脍炙人口的《两种文化》的名文,他说:“在道德生活中,科学家基本是我们知识分子中间最健全的集团;科学本身的组成中就有道德成分,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由此形成自己对道德生活的判断。”科学和道德哪个在先,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但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科学昌明,却是历史早已证明的定论。伟大的心灵蕴育伟大的思想,中国近年来的创新焦虑,其症结就在于此。“人之无文,行之不远”,陶醉在“屌丝文化”中的国家,是危险的。亚里士多德说过:“美比历史更真实。”是高尚的理想推动着文明的历史不断进步。我赞同哈维尔的话:“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发出警告”,我说了就拯救了我的灵魂。
人文文化哺育了近代物理学。
物理学属于科学文化范畴,作为长达五百年的带头学科,在整个实证科学领域,物理学所取得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人们往往忘记,物理学的成功曾经受惠于人文文化,甚至可以说,近代物理学是在人文主义的文化襁褓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一、文化启蒙
科学的物理思想诞生,溯源于文艺复兴时代波澜壮阔的思想革命。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首任秘书奥尔登伯格在致斯宾诺莎的信中说:“杰出的先生,来吧,打消惊扰我们时代庸人的一切疑惧;为无知和愚昧而做出牺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让我们扬起真知之帆,比所有前人都更深入地去探索大自然的真谛。”这是一种弥漫整个欧洲的精神气氛,思想解放的力量,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达兰贝尔描述说:“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句话,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史到昆虫史,自然哲学的这些领域都发生了革命;几乎所有其他的知识也都出现新的面貌……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以及宇宙的景象使我们的观念发生的某种升华,所有这些原因使人们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亢奋。这种亢奋有如一条河流冲决堤坝,在大自然中朝四面八方激流勇进,汹涌地扫荡挡住它去路的一切。……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繁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王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人们头脑中的这种普遍的亢奋,其产物和余波使人们对某些问题有新的认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留下新的阴影,正像涨潮落潮会在岸边留下一些东西,同时也要冲走一些东西一样。”
新时代精神颠覆了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为新物理学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其集中表现是两大思想主潮:
(一)世俗观念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价值核心是出世,人不应屈从于情欲,而应过属灵生活,禁欲并“为罪受苦”。极端的苦修派甚至在柱上静坐30年,长了痈疽任其腐烂生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文艺复兴讴歌人性,向往尘世幸福,鼓励功利事业,以致如韦伯所说的全社会的普遍的成功意识,成为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这是人的觉醒。莎士比亚借汉姆莱特之口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这样的普遍气氛中,出现了第一波清教主义科技热,手工技艺和机械技艺成了值得称道的专长,那些勇于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自称“蹈火哲学家”。清教思想家斯普拉特(T.Sprat)称赞英国皇家学会是“人类的技能和理智的联姻”,并说:“当从事机械工作的劳动者拥有哲学头脑,而哲学家们拥有能够从事机械工作的双手之时,哲学便臻于完美。”
(二)理性精神
中世纪是蒙昧时代,教父的名言是“正是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人们认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是两个至高无上、不可逾越的权威,理性的空间。《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雅克·巴尔赞对那个时代欧洲的世情做过生动的描述:“可怜偏见、愚昧、迷信、荒诞支配着公众,挤压了科学的罪人,害怕震怒的上帝会用瘟疫、饥馑和地震来惩罚他们;他们相信撒旦‘狂暴地在世界上任意游荡’,把他的受害者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为了求得圣人和圣物的保佑而经历千辛万苦,又是去朝圣,又是自贬自卑;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有什么骄傲可言呢?”这种阴暗的思想氛围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所谓“女巫”的迫害。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主持制定的《女巫惩治法》,是欧洲文明史上最野蛮的文件。宗教法庭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残酷刑法对妇女们进行残害,她们被剃毛、抽血、针刺、绞杀、烧死,仅17世纪一个监视官就绞死了220多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妇女;1598年,德国小城维尔茨堡一地,就发生28起公开处决女巫的事件,平均每次有4到6名受害者。伽利略1597年致信开普勒慨叹说:“委实可怜的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准备抛弃错误的搞哲学的方法的人寥若晨星。”
文艺复兴意识形态上最伟大的成就正是弘扬理性。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座右铭是Sapere aude——敢于认识。黑格尔说:“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没有看见过人用头立地,即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与人世的和谐。”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如卡西勒(Ernst Cassirer)所说,人们第一次把“自然王国”和“神恩王国”对立起来:“通过感知,并辅之以逻辑判断和逻辑推论以及悟性的运用,我们就能认识自然王国。”伽利略豪情满怀地说:“给我一个杠杆,再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而拉普拉斯面对拿破仑关于上帝存在的提问时,则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需要这个假设,陛下!”
伏尔泰尽情嘲笑“圣经物理学”,思想的解放和理性的胜利催生了新物理学。伽利略提出了整个新物理学的第一个基本定律——惯性定律,指出力不是运动的原因,而是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相信理性,勇敢地向亚里士多德的教条挑战,明确反对“那些甘愿作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并以亚里士多德的头脑来思想,以亚里士多德的眼睛来观察的人”。难怪当时的革命性自然科学著作都以“新”命名:
1537 年,塔尔塔利,(N.Tartaglia):《新科学》
1600年,吉伯(W.Gilbert):《论磁石……一门被许多论据和实验证实的新生理学》
1609年,开普勒(J.Kepler):《新天文学》
1638年,伽利略(G.Galileo):《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
1672年,居里克(O.von Guericke):《马德堡的新实验》
二、哲学启发
理性主义的哲学是新物理学的接生婆。
(一)16~17世纪:惯性定律
惯性定律解释了力的本质,可以说是近代物理学的真正起点,而它的确立恰恰是伽利略理性主义认识论的伟大成果。爱因斯坦说:“伽利略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经验理性。理性的判断不是诉求权威,而是求诸实验。伽利略说:“只要一次单独的实验或与此相反的确证,都足以推翻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论据。”亚里士多德说:“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去推它时,原来运动的物体就归于静止。”他用斜面实验推翻了亚氏的结论。把两个斜面相向置放,让小球从一个斜面自由滚落,如果忽略摩擦,它能滚上另一斜面并达到同一高度。如果第二斜面的坡度减小,小球从起点滚过的时间就增长;若坡度减为零,就会沿平面无休止的运动。
理论理性。与传说不同,伽利略并未在比萨斜塔上做落体实验,做这个实验的另有其人。但伽利略却做了一个思想实验,用纯粹的演绎推理,从逻辑上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论,显示了理性的威力。
(二)17~18世纪:万有引力
亚历山大·波普说:“自然和自然规律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上帝说道:‘牛顿出世了!’于是,一切都变得明朗了。”而在牛顿诸多贡献中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也许是最重大的了。爱因斯坦指出,伽利略改变了速度,造成加速度。牛顿则建立了普遍的运动定律,认为加速度是同作用于物体上的力成比例的。“这个表征物体加速能力的比例系数,完备地描述了这个(无大小的)物体的力学性质:这样就发现了质量这个基本概念。”牛顿认为万有引力与“物质的量”成正比,而“物质的量与其密度及大小有关”,牛顿反对17世纪认为运动与物质无关的经典表述,认为万有引力是“物质的内在力”:“物体内在固有的基本力就是保持其处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状态的力;它与物体的量成正比。”这是牛顿直接从其自然哲学引申出来的结论,是无法从观察和实验归纳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牛顿能从数学思维出发,逻辑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能同经验相符合。
(三)19世纪:场观念
爱因斯坦指出:“在麦克斯韦以前,人们以为,物理实在——就它应当代表自然界中的事件而论——是质点,质点的变化完全是由那些服从全微分方程的运动所组成的。在麦克斯韦以后,他们则认为,物理实在是由连续的场来代表的,它服从偏微分方程,不能对它作机械论的解释。实在概念的这一变革,是物理学自牛顿以来的一次最富有成效的变革”。他感叹地说:“物理学家们花了好几十年时间才理解到麦克斯韦发现的全部意义。由此可见,他的天才迫使他的同行们在概念上要做多么勇敢的跃进。”
如所周知,麦克斯韦最终做出的发现是位移电流,即交变电磁场,所谓“横向交变”(transverse alternations),就是在两个垂直的向度上连续传递的波场。
问题是场的概念首先是对旧自然哲学观念的变革,原来17世纪以来,在物理学中就存在两个自然哲学范式:超距论和近域论,超距论由牛顿的学生科茨(R.Cotes)公开倡导而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主流纲领,认为相互作用的传递是无需中介而瞬时完成的;近域论,最初是意大利哲学家波斯科维奇(Roger Boscovitch,1711-1787)倡导的,认为物质可以分割为无限小的质点,这个质点因为能影响别的类似的质点,因而是一种力的中心,即力点,因此作用的传递是通过连续的力点进行的一个过程。麦克斯韦明确指出,他所遵循的是波斯科维奇的近域论的纲领,而反对超距论。他说:“波斯科维奇提出的理论是,物质是数学点的集合,每一个点都按照一定规律而对另一个点施以引力或者斥力。”他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中明确指出,“假定粒子以依赖于速度的力而发生超距作用”本身就是个悖论。他深刻指出:“从哲学观点上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这是极端重要的。……无论是就关于现象的实际本质的基本观念说,还是就与相应的量有关的大量次要观念说,这两种方法都是迥然不同的。”
玻尔兹曼认为,麦克斯韦“在认识论上也和在理论物理领域一样,是一个巨匠”。麦克斯韦对哲学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人的思想曾为许多问题所困扰;空间是否是无限的?在什么意义上是无限的?物质世界的范围是无限的吗?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地方都为物质所充满吗?原子是否存在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远自人类开始思维起,这些问题就一直在进行讨论,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旦学会运用我们的天赋本领,这些问题就会重新提出来,它们构成我们19世纪科学的一个本质的部分,犹如先前曾作为15世纪科学的一个本质部分一样。”与当时英国盛行的经验主义不同,麦克斯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的思辨精神,这使他在19世纪英国理论自然科学领域中远远超出侪辈,独树一帜,成为物理学史上与牛顿、爱因斯坦鼎足而三的科学巨星。
总之,没有文化的启蒙,就不能打开物理学发展的道路;没有哲学的启发,就没有惯性、质量和波场这三个近现代物理学的核心概念,从而也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还是爱因斯坦说得好:“哲学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母亲,它生育并抚养了其他学科。”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