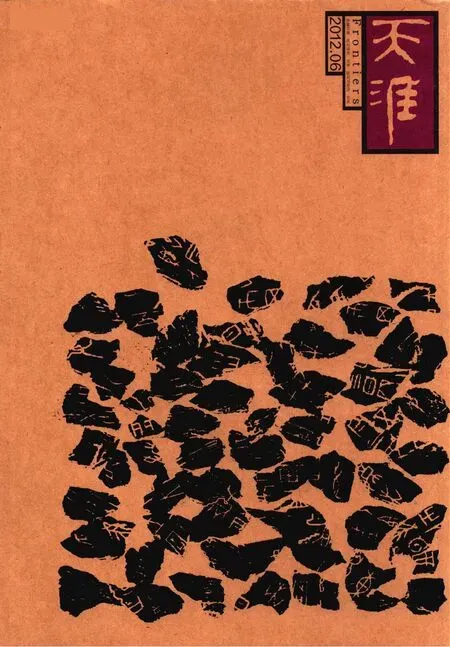良宵
张楚
一
她刚搬到麻湾时,村人并未觉得有何异样。或许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位干净的老太太,衣着素朴,脸上一水褶子,梳了低低的发髻,站在樱桃树下,束手束脚,竟有几分与年岁不相称的羞怯。隔壁的妇人偶来瞅了几眼,闲聊几句,这才晓得是村里王静生的远房姨妈,怎么想起要到乡下住上段时日,这才劳烦她外甥在村西租了三间瓦房。行李也不甚多,几床被褥,一只泛黄的皮箱。随行的还有一只白鹅。白鹅也老了,翼羽暗淡,喙上的肉瘤失了色泽,在屋檐下恹恹卧着。若是人来,她就从包裹里掏栗子、榛子类的坚果,笑着塞进人家掌心,慢声慢语地催促道,吃吧,吃吧。她的牙齿大抵是假牙,白如玉米,笑时几乎不见牙龈。
翌日,鸡没叫上三遍就早早爬起,绕村子转了半圈。四月初,清冷了一冬的村子,难免透些活泼。樱桃就不消说了,顶一树雪,招了细腰蜂。单说荒地里大片的紫云英,于风中凝敛成水晶,流出光和蜜来。后来她走累了,坐上块青石歇脚。有村人牵着黄牛、骡子从她身旁撵过,难免都瞥上两眼。她呢,但凡有人瞅她,都要笑一笑,嘴唇被暖阳打成瓣蔷薇。
也不喜欢串门。村子里的妇女,如果不是农忙季节,屁股底下是安了陀螺的。尤其是此处的女人,舌头都要比别村的长两寸。就有那好事的,借串门的名义来,吃几枚老太太的坚果,喝几盏老太太泡的茉莉花茶,再打听些该问不该问的话,想传与旁人听。可这老太太,安静得像一只猫,村妇们在炕沿上东拉西扯,她也不插嘴。问她退休前是干哪行的?她说,当教师。问她儿女几个?她说,两儿一女。问她多大年岁?她说,忘了。问她老伴是否健在?她说,去世二十多年了。人家问她话时,大眼珠子瞪得溜圆,而她呢,只眯眼盯着墙旮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有时那只老鹅摇摆着肥硕的屁股踱进屋,她就顺手抓了脖子拎上炕,箍在怀里,榆树皮手细细摩挲着。那鹅也不吭声,闭了眼,仿佛在她怀里死去一般。
闲妇们就渐渐没了兴致,不如何来往。只有一个诨号“刘三姐”的,时不时跑上一趟,倒比王静生还勤些。蒸了野菜馅的饺子趁热端一碗来,炖了排骨趁热送几块来,亲闺女似的。老太太推辞几句,就接了,也不见有言谢的套话。“刘三姐”似乎也不在乎。在村人眼里,她本来就是个有点缺心眼的“女光棍”。所谓“女光棍”,是周庄、夏庄、马庄、麻湾一带独有的叫法,专指那些性情如男人的女人。哪个村不出一两个“女光棍”?譬如夏庄,最有名的女光棍是周素英,专跟男人赌钱闹鬼;譬如马庄,最有名的女光棍是刘美兰,蹬着大头皮靴,领了帮唢呐手跑红喜白丧之事;麻湾呢,若说有女光棍,大抵就是“刘三姐”了。“刘三姐”其实长得还算英俏,只是脾性躁,嗓门粗,肠子直,有事没事喜欢扯着铁嗓子唱两句。
二
老太太过了五六日,将麻湾村周遭咂摸透了。这个叫麻湾的村庄,地处冀东平原,西行百里是燕山,东行百里是渤海,怪的却是靠山不吃山,靠海不吃海,反倒以植棉闻名。据说老辈子,宫里用的棉花全由此处沿京东北运河载去。不过现下却是荒了手艺,年轻的跑到城里做泥瓦匠,只有老农人种几亩棉花。麻湾呢,除了村西有块方圆百米的土岗,全然是平地。若是站荒田里环四周,便是由地平线草草勾勒的浑圆。现下清明才过,麦子返青不久,作物都还归仓,除了野花草,只有柳树顶了绿苞芽,飞着些酱色的七星瓢虫。
那天她从村西的土岗下过。虽走得慢,还是呼哧带喘,就顺势找了干净的一块地角坐下。屁股还没凉,便听到不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叫骂声。手搭了凉棚去瞅,却是一个孩子在前边跑,一帮孩子在后身疯追。那孩子蹽得比野兔子还快,转眼就从她身边旋风般刮过,直刮到那黄土岗上。那帮孩子呢,也就不再穷追,只在岗下唧唧歪歪骂个不休。这麻湾的方言倒也有点意思,平心静气说起来时,三拐五拐的犹如唱评戏,骂起人来时则脆生利落,简直京戏里的念白一般。那帮崽子兀自咒骂一通,这才怏怏散去。
老太太瞥了瞥他们的背影,又去斜眼瞅那土岗。不会儿,土岗上便隐约探出个圆头,小心逡巡着岗下。大概看是孩子们走了,这才约略着直起身抖抖索索矗在那儿。孩子套件过了膝的破夹克,晃荡晃荡的,鸡胸脯裹件漏眼的长袖海魂衫。见老太太望他,竟俯身捡起块土坷垃扔过来,不偏不倚冲她额头上。老太太倒是吭也没吭一声,只顺手摸了摸额头,又朝那岗上望去。孩子就不见了。
晚上,老太太蒸了锅馒头,干嚼了半个,就披了羽绒服拎了马扎坐院子里。夜晚的村庄静得早,偶有耗子钻垛草鸡闹窝。墙头似有野猫出没。老太太定睛瞅了瞅,拎了马扎进屋,打开戏曲频道,正演白玉霜的《木兰从军》,忍不住把睡着的老鹅抱上炕,揽在怀里,摸它温热的羽,摸它冰凉的喙,再闭了眼细细听戏。须臾,过堂屋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侧耳听,倏尔没了,过了会儿,脚步声重隐约响起,老太太就问:“谁啊?”话音未落已是一派沉寂。心想这双耳朵,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晨起时,发现锅里的馒头少了几个。心想不会是被野猫叼走了吧?出了院子,又想不起到哪里溜达,就念起了昨日那个野孩子,这么想着,吆喝了老鹅,慢慢悠悠朝土岗走去。她这院子靠村西边,离岗最近,不过三四百米,可若真一步一步量起来又无比漫长。想当年,她能一连串翻百十个筋斗云。
土岗矗眼前时,她叉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岗也不高,只不过人太矮了,岗也不长,只不过人的胸腹太窄了。土岗四周除了杂生的几株野榆钱,便是蒲公英,蒲公英密密麻麻洇成一片,远看仿若一块安静的黄金,近看则是朵朵小向日葵。鼻子里涩香之气渐发浓烈,她从兜里掏出枚榛子,嘎嘣嘎嘣嚼起来。人老了,牙掉了,馋虫还活着,吃了一辈子的坚果看来是戒不掉了。后来她想,何不去岗上看看?就绕到那条斜坡前仔细端详,这一看先就心虚。斜坡虽不是很长,却陡峭得很,别说是她,就是十五六的愣小子也会发憷。断了念想,捶着腰眼慢慢悠悠回了家。
这一晚,老太太做的炸酱面。饭后照例躺炕上看电视。说是看电视,不如说是听电视。眼皮子磕磕绊绊时睁时闭,只耳朵支棱着听胡琴声咿咿呀呀。待听到过堂屋传来“吸溜吸溜”的声响,这才骤然醒来,轻咳两声,声响就淹没在无涯的黑暗中了。她把电视声音调大些,轻手轻脚穿了鞋子下炕,猛一挑门帘,就见一团矮小黑影蹿到院子里。那晚夜空无月,她只瞅到影子晃荡着爬上矮墙,倏地下就不见。转身将过堂屋的灯打开,却见剩下的炸酱面没了,只碗边粘了硬邦邦几根。似乎就明白了。如果没有猜错,这偷食的人,除了岗上那野孩子,也不会再有旁人了。心里难免嘀咕起来,这孩子是如何的一回事?为何吃不上饭?爹娘去做什么了?村里就没旁的亲戚了?便寻思有机会了,定要问问那“刘三姐”。
这“刘三姐”倒是好几日没来。听村子里的喇叭,好像麻湾村家家要签什么合同。自己这房子是租来的,倒也没往心里去。炕上坐了会儿,便又愣愣想起那野孩子的小眉眼,心格外绵软,竟隐隐盼起夜晚的降临了。翌日,未及晌午,老太太就盘算着晚上煮何饭菜。这几天不是干馒头就是稀面条,那偷食的孩子估计也吃不饱。思来想去,便要做“菠萝酱鲫鱼”。
小卖部里倒是有鲫鱼,可却没有菠萝,老太太就买了几根芹菜。芹菜味冲,又有股异香,虽不及菠萝,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回了家就刮鱼鳞剖鱼腹,将肠子肚子喂给老鹅。又将空鱼肚塞上姜片、葱段和豆瓣酱,才用铁锅小火炖起来。这是个岑寂的午后,同往常一样,只听得细春风拂过老屋檐,只听得嫩叶拱出苍树皮,只听得邻居猪圈的约克猪懒懒呻吟……这样闲坐了很久,这才把火关了。光一寸一寸缩,夜一寸一寸胀,她草草喝了碗稀饭,将过头屋的灯打开,早早猫进被窝,照例看电视。
孩子又来了,先是锅盖碰锅沿的清脆声,然后是电饭锅被揭开的兹啦声,再是不当心被热气熏了手又不得不强忍着的“哎呀”声,饭菜入嗓猛然吞咽的咕咚声……最后,是窸窸窣窣的衣裤和门帘摩擦声。不过五六分钟,声音就消散在夜里,又是漫漫的静。她披上衣裳蹑手蹑脚踱到庭院。月亮大而黄,孩子正在翻墙,不晓得是如何了,这回翻了几次都没翻上去。后来,他从猪圈旁搬了块石头,探着身子踮着脚才够住墙头。怪的是他没立马跳过去,而是骑矮墙上,双腿耷拉着呆坐了良久。后来,老太太看到孩子的肩胛骨在月光下一颤一颤地抖索起来。
老太太没敢惊扰他,默然看了片刻回房,靠着门闩愣神。
三
翌日清晨便早早出门。老鹅在她身后摇摇摆摆尾随着。她知道村里有家小卖店,专卖冷鲜肉。那天,小卖部人倒不少,有人在扯成匹的帐子布,看来是村里有人过世了。老太太戴上花镜,观瞧半天,这才吩咐店主从猪背腿上割了一斤,而后带着老鹅回了家。中午时,忍不住一个人跑到黄土岗下坐了个把时辰。风比昨日暖些,吹得骨头酥痒,荒田里的紫云英被阳光照成一团紫雾。可孩子却没出现,她愣愣地盯了会儿野榆钱树,这才走了。及至下午,老太太切姜剥蒜,又配了红椒、桂圆、八角、茴香和十三香,用高压锅将肉闷了,肉香不久弥漫开来。
期间倒是有几个闲妇过来串门。她们有阵子没来了,进了屋先耸动着鼻子问“咋这香呢?”见是老太太炖肉,又夸她厨艺高超,接着喟叹起如今的儿子媳妇们,全是金贵命,虽然都是土里刨食的,却连饺子也包不好,年三十煮破了一锅,简直成了馄饨片汤。老太太只缩在炕脚听,一句话也不插。又听她们说,县政府的人来了七八次,看样子村子搬迁是避免不了的。老太太这才问了句:村子搬到哪儿啊?干嘛要搬啊?她们的兴致就被勾起来了,哄嚷着说,麻湾和附近的周庄、夏庄,据科学家们检测,地下埋着大量铁矿。大量是啥概念呢?就是储存量位居全国第三。全国第三哪,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人四五年前就来勘探,折腾了几年,据说明年就要动工采矿了,这不,镇上天天逼着签拆迁合同。用不了多久,麻湾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地下采矿场。老太太“咦”了声问道,你们搬到哪儿啊?没了田地,日子怎么过?她们就扬着眉角嬉笑说,我们巴不得搬到县城,当城里人呢。钱嘛,不是有赔偿款吗?这世道,有了钱,啥都不用怕……
可算是走了。老太太捶了捶腰,不禁去看锅里的肉。其实本想跟她们问问那孩子的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帮长舌妇,定会好奇她为何问询。何况,又何必非要知晓孩子的事?她跟他,只打了个照面,闲话也没说上过一席。他要是饿了,就来这里吃两口,填饱肚子;他若是有了下家,不再来偷食,自当没有过这回事。老太太眯眼在炕上打起盹来。等睁开眼,天已大黑,蹒跚着去过堂屋看看炖的肉,明显是吃剩的。孩子吃了不少,看来很对他胃口呢。老太太竟有些隐隐的得意,方沉沉睡去。
次日早早就起来,栽了两垄韭菜。韭菜根是王静生送的,顺便捎了一粪箕子猪粪。这个远房外甥,跟她并不亲近,反倒有些罅隙。老太太也并不介怀,送了他一双自己绣的棉拖鞋。王静生接了,又闷闷地抽了一袋烟,这才趿拉着鞋转身离去。等外甥走了,老太太就坐到屋檐下晒太阳,晒着晒着有些恶心,想必是这几天受了风寒,随口吞了几粒药片,倒头睡起来。中间醒来几次,只觉得骨头酸软喉咙胀痛,喝了口热水又渐渐迷糊过去。其间闻得老鹅嘎嘎乱叫,想必是饿了来讨食,却没气力爬起来喂它。醒来时太阳已爬上屋檐,就拌了糠菜去喂,却发现老鹅没了。
这老鹅,跟了她十三年,是她从小区门口捡的。肯定是谁家的孩子从宠物市场买来,养得不耐烦随手扔掉了。城里的孩子,就是没耐性。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揣兜里带回家。当初也只是小小一团鹅黄,睁了惊恐的眼动也不敢动,谁成想竟长成偌大一只呢?儿女们是极少来的,通常只有她和它,晨起去中山公园散步,中午吧唧吧唧嚼着青菜,听收音机里唱着老戏,傍晚呢,窝在沙发里打盹,半夜醒来时方将电视关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想说话了就和它唠叨两句,生气了就踹它两脚,它不记仇,依旧影子似的随着她,贴着她,腻着她。
老太太难免心慌起来,颠着老寒腿在院子四周搜寻一番,仍没得踪迹。猛然想起那孩子,心就咯噔了一下。该不会夜晚来时不见吃的,索性将它逮走炖了吧?
那晚,灶冷灯灭,她早早在过堂屋候了,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果不其然孩子仍是来了。当他在灶台上翻寻时,她冷不丁一把就攥了他胳膊。他胳膊如此干枯,挣了两挣竟没有脱开。老太太随手开了灯,这才不紧不慢地问道:“我的鹅呢?”
这倒是她与他头一次如此近地说话。他比前些日子似乎更细瘦了,有那么片刻,她竟怀疑他会不会被过堂风给吹走。他的眼也是红肿的,嘴角生了水泡。老太太又问道:“是不是你把鹅偷走了?”孩子点点头。她想也没想就从他后脑勺扇了一巴掌,“是不是把鹅给吃了?”她颤抖着声音问。孩子又是点点头。老太太“哎呀”一声,顺势从锅台拎了把刷锅的炊具,捋起他衣袖就抽打起来。抽着抽着便瞧得他胳膊上全是银元大小的红斑,一圈连一圈,看得心里麻麻幽幽,索性撒了他,一屁股坐在灶台上,默默盯了他半晌,这才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孩子一愣,却并没有动。老太太听他嘟囔道:“我奶奶死了……我杀了它祭祀……”老太太不再搭理他,转身回了屋子,和衣躺下。
这一躺就是两天。中间清醒时老太太想,该不会是大限已到吧?然而转念想想,死在这个叫麻湾的村里也没什么不好。这个村子,地上有棉花,地下有铁矿,也算是宝地了。迷迷瞪瞪间又觉得自己化了妆缓步走上那戏台,不成想环顾四周,琴师未来,台下一个人也无,竟怅然起来,旋尔又自嘲,都这把老骨头了,竟还怕没人来听自己唱戏……
等再次睁开眼,屋里的灯怎么就亮了。侧身朝门外望,先看到炕沿上摆着副碗筷,碗里尚冒着热气。老太太爬起来张看,却是碗疙瘩汤,香油花浮着,白鸡蛋卧着,鸡蛋旁是几粒剥好的新蒜。老太太心里热了下,小口小口着吸溜起来。大抵是饿得塌锅了,虽然缺盐少醋,竟觉得格外香甜。就想,会有谁来呢,若是静生或“刘三姐”,断不会悄没声地来了又走,看来,也只有那孩子了。定是他过来找食,见她卧床生病,这才煮了疙瘩汤。看她睡得香,又不忍叫醒,才将疙瘩汤放在炕沿上,睁眼就能看到。小小年岁,心眼倒是不少呢。虽然他将老鹅杀了,心里百般怨恨,可谁没办过蠢事呢?何况一个细脚伶仃、饥肠辘辘的孩子?她突然萌生起拜访他的念头。来了半月有余,她还没正式拜访过谁呢。老太太就拿了手电筒出了院子。
夜晚的村庄,和白日的村庄,气味是不一样的。白日的村庄是属于动物的:属于槽子边的黄牛,属于圈里的约克猪,属于栅栏里的奴羊,属于篱笆里的凤头鸡,属于墙头的野猫,属于麦秸垛的刺猬,属于草丛里的春蛇……那气味掺在灶坑里,掺在孩子的鼻涕里,掺在男人的尿液里,是重的、冲的、浓的、腥的、烟火气的;而夜晚的村庄则属于植物:属于韭菜,属于樱桃,属于桃花,属于榆钱,属于一切静默生长着的神灵,所以那味道是甜的,是淡的,是凛的,是澈的,是悄然入心入肺的……老太太走在夜里,骨头似乎也轻灵起来,平时十来分钟的路,只走了七八分钟。到了黄土岗才想起,那条斜坡太陡了,以她生锈的腿脚,白天攀爬上去已是不易,何况繁星漫天的夜晚?怏怏地在岗下站了会儿,蒲公英的甜涩又隐约着扑进鼻孔。
还好,病又隔了一夜就痊愈。上午,就接到了大儿子的电话。她没想到儿子会给她打电话。他说话向来简洁。他在电话里说,妈呀,你生日快到了,还记得吧?有个香港大公司的老板,做了你一辈子的戏迷,专门从香港飞过来,要给你隆重的庆祝一下,光赞助费就掏二十万。你过几天拾掇拾掇,赶快回省城吧。
大儿子五十多岁了。他秉承了他父亲的一切:暴躁、酗酒、打老婆。他早把她盘剥的只剩一具衰老的身体。每到发工资的日子,都会带兄弟来分钱,此后一月不见踪影。说她手头没攒下钱谁信呢?去年跌了一跤,路也走不了,孩子们谁都不吭声,也没带她到医院看治,如果不是几个戏曲学院的弟子出了手术费,她剩下的日子怕也只是瘫烂在床上。如今她好不容易偷偷跑到乡下,不成想还是被他找到。她轻声轻语地告诉他,她是不会回去的,她喜欢这个叫麻湾的村子,她要在这里老死。
“那你就死那儿吧!永远别回来!”儿子在电话里咆哮起来,“反正这辈子你的命比草还贱!有福也不会享!”
命比草贱……命比草贱……她的眼眶就湿了……
“老太太啊,发啥愣呢?”
她抬头,却是“刘三姐”推门进来。“刘三姐”手里捧着碗懒豆腐。
“我用黄菜叶跟豆腐渣熬的,闻闻,闻闻,比猪肉都香!”“刘三姐”边说边咂摸着嘴,“趁热吃了吧,世界上最好吃的懒豆腐,就是我‘刘三姐’做的。”
四
那天晚上,老太太炖的清水排骨汤。喝完了汤,天方擦黑。她觉得有点热,就脱了棉衣在院里给韭菜浇水。浇着浇着,耳畔便传来谁家的收音机声。有人正在唱《春闺梦》,是张氏与丈夫王恢互诉衷肠那一场。听声音不是王缺月就是赵恒秋。毕竟是晚辈,功夫还是有些稚嫩。听着听着,她不禁将水桶缓缓放下,轻声轻语唱将起来:
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
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我想到如今。
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华虑变生。
因何一去无音信,不管我家中这肠断的人。
她恍惚又站在偌大舞台之上,金丝绒帷幕拉开,司鼓开始打倒板头,倒板头打完,胡琴声一响,满场肃静无哗。一瞬间,她仿佛就成了张氏,对着夫君埋怨。虽是埋怨,却是娇憨的、惊喜的、委婉的、意犹未尽的。她窃笑、她颔首、她掩面、她莲步生灭……当她最后佯装拂袖时,她仿佛听到戏台下传来惊雷般的叫好声……
唯有墙边传来“咕咚”一声闷响,她才猛然梦醒,身子打个激灵,木木地朝墙边看去。
这一看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却是那孩子从墙头跌了下来。看来没什么大碍,他慌里慌张地拍拍身上的灰尘,这才怯生生凝望着她。
“你怎么又来了?”老太太沉着脸道,“你偷吃了我的鹅,这回又想偷什么?”
“我……我……”男孩诺诺道,“我只是来瞧瞧,你的病好了没有。那天晚上,你的头比开水还热……”
老太太眯眼看他。他就支吾着说:“我刚才在墙头听你唱戏……一不留神掉下来了……”
老太太这才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说:“以后不用爬墙头了,奶奶给你开着门。”
就领男孩进屋,给他热了排骨和米饭,盛得鼓尖才递给他。孩子大口大口扒拉着,她就问:“你爸妈呢?”“全死了。”“怎么回事?”“病死的……”“爷爷奶奶呢?”“爷爷早死了,奶奶……奶奶……”男孩哽咽着说,“奶奶前几天心肺病犯了……你那只鹅,我杀了做供品的……”“还有亲人吗?”“有个大伯……是个瘸子……”
男孩将碗筷放下,呆呆凝望着房梁。老太太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先把排骨都吃了。”男孩快速地瞥了她一眼,又埋头闷闷吃起来。他饭量委实很好。他总共吃了三碗米饭,排骨也啃得精光。
“以后跟谁过呢?”她仿佛问自己,又仿佛问孩子,“这么小,比火旗高不多少……”
男孩就放下碗筷,径直往外走。老太太伸手拽他,他没动。老太太说:“你喜欢吃糖吗?柜子上的铁盒里有。有大白兔的,还有金丝猴的。”
男孩说:“我从来不吃零食。”
老太太撇撇嘴说:“哪里有孩子不贪零食的?”
男孩黯然道:“我爸妈活着的时候,也没给我买过零食。”
老太太叹息着说:“以后奶奶给你买……”
男孩瞥她一眼,嘟着嘴转身走了。不会儿,老太太听到屋外关门的声响。这次,他不是翻墙出去的。
随后几日,男孩都过来共进晚餐。家里好像还没如此喧闹过。老太太特意让王静生打集市买了张八仙桌。桌上通常是一凉一热。热的呢,是老北京菜,什么番茄腰柳啊,炸灌肠啊,砂锅狮子头啊,樱桃肉啊,都是最拿手的;凉的呢,无非是萝卜樱子、香葱、新韭,抑或小嫩菠菜,用海天酱油和酸酱细细拌了。两个人,就在炕上面对面坐了吃。孩子呢,通常只闷了头扒饭,很少动筷子夹菜。吃一阵偶然抬头,老太太便往他碗里夹一箸菜,嘴上唠叨着:“十来岁的小子,吃穷老子。多吃,多吃。”孩子也夹了肉丁或腊肠,犹犹豫豫着往老太太碗里塞。老太太就笑。如果两人都不言语,屋内便只听得牙齿咀嚼食物的声响,不过声响又不同:老太太是细嚼慢咽,老牛反刍般半晌才动下嘴;孩子呢,则像猪崽抢槽子般呼噜呼噜,眨眼间一晚米饭就下了肚。老太太说:“你慢些吃,吃得太快,胃哪能受得了呢?可要当心,年轻的时候是人找病,老了啊,就是病找人了。”孩子仍是大口大口地吞咽,仿佛没长耳朵般。那一日,孩子忽然放下手中的碗筷,郑重地对老太太说:
“我……我想求你个事……”
老太太故意说:“那可不行,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孩子眼神就黯淡下去,老太太这才说:“好吧,我不要好处了,只要你拜我为师,学一出《红拂夜奔》就成。”
孩子仍垂着头,半晌才说:“我估计活不过明年了。要是我死了,你把我跟我爸妈埋一块吧。”
这话从一个孩子的口里出来,老太太一时就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应答。孩子又慢慢说道:“坟就在岗上。我喜欢吃肉,到时候你给我坟头……放一块猪头肉就行了……纸钱呢,多烧些,我好给我爸妈买新衣裳……”说完了又继续埋头吃起来。老太太就强笑着说:“你个兔崽子,小小年岁,竟想些不着边的事儿,就是死,我肯定也在你前头。”
老太太面上挂着笑,心下却不时犯愁。孩子为何要说这番话?不像是睁着眼说假话,难道是得了什么绝症?又想,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如何安顿为好?虽说有伯父,看来也是薄情寡义的人,不然怎会让孩子孤身独住?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啊,按常理,晚上还赖在娘被窝里暖脚的。便寻思着去找村里的干部,好歹找个人家寄养才安妥吧?实在不行送福利院,也比夜里孤零零守着土岗强,也比被孩子们整日欺负强,起码不至于吓破胆,只到晚上才敢出来。
那天,男孩夜间又来,老太太炖了半只芦花鸡。刚把鸡大腿撕下放孩子碗里,“刘三姐”夹着团棉花就来了。“刘三姐”脸上本来堆着笑,愣眼瞅到男孩,突然一声尖叫,吓得男孩兀自撒腿就跑。男孩跑了,“刘三姐”还抚胸长叹,竟是副失魂落魄样。老太太乜斜着她,冷冷问道:“抽羊角风了吗?”
“刘三姐”说:“我的天亲啊,你咋敢让这孩子跑你屋里头?”
老太太说:“他又不是十恶不赦的人,我干嘛不敢让他来?”
“刘三姐”垂头顿足地嚷嚷道:“他可是个瘟神哪!你不知道,他爹妈出去打工,被人骗去卖血,得了艾滋病,去年全死了!艾滋病啊!你老人家可知道这是啥病?你还敢跟他一块吃饭!不想活了你!”
老太太茫然地瞅着“刘三姐”,说:“他爹他妈有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刘三姐”急赤白脸地说:“咋没关系?!他妈怀孕的时候就得病了!这孩子生下就有艾滋病!”
老太太不再听她絮叨,开始收拾碗筷。“刘三姐”一把将碗筷夺过,顺势扔进垃圾桶,又匆忙提了垃圾桶快步出屋。显然,这个麻湾唯一的“女光棍”是被彻底吓着了。当然,麻湾唯一的“女光棍”被彻底吓着了,也就说明整个麻湾村被彻底吓着了。
五
老太太翌日起得晚。如若不是敲门声愈发大起来,定会再睡个回笼觉。等她将门打开,倒不禁愣住。房北围站着七八个女人,有相识的,有不相识的,还有半生不熟的。见她迈门槛出来,都不约而同向后退了几步。老太太用手压了压发髻,她们又是碎步挪腾。很显然,她们都知道孩子的事了。看来“刘三姐”的舌头,也并不比她们的短多少。
那个清晨,这帮子妇女围圈住老太太,七嘴八舌问个没完。譬如,他何时开始到她这里蹭饭的;譬如,他吃过之后的碗筷,她是否用开水烫过?譬如,他有没有跟她讨要钱物;譬如,她以后是否还会叫他来吃饭?显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末一个问题。
老太太目光漠然地越过她们,扫到了房前一棵梨树。梨树也是素白,不过却比樱桃多了分莹润。女人们仍喋喋不休,仿佛她们若不是如此这般盘问她,倒真是对她不起。她后来实在有些厌烦,就说,我筋骨有些受风,要去屋里好生静养一番,你们还是各自忙各自的去吧!
女人们怔怔地盯了她看。她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关门回屋。站在过头屋里,耳边还响动着她们嘈杂的议论声。
待到日悬中天,老太太又去了黄土岗。空中飞着乱柳絮和蒲公英,老太太不停打着喷嚏。这样行到岗下,又歇息片刻,这才一点一点向上爬。爬了没几步就腰酸腿疼,寻思寻思又径自下坡,仰头朝岗上望去。
男孩就站在岗上俯视着她。他只穿了那件漏眼的海魂衫,细瘦胳膊支棱着。他看她一眼,她看他一眼,谁都没有说话。老太太“哎”了声再去瞅他,他仍站在那儿,犹如刚从泥土里钻出的豌豆苗。他的瞳孔与眼白,倒如昼与夜般泾渭分明。
“你下来,”老太太朝男孩摆摆手,“以后别住这儿了,搬到奶奶那儿。”
男孩猛地摇摇头。
“别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想小鬼至。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怕的?我都不怕,你还有什么怕的?”
男孩仍是摇摇头。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奶奶给做砂锅白肉吧?”
男孩转身就跑了。岗上又空旷起来。
看来,这孩子是怕连累她,没准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老太太蔫头蔫脑回了家,捂了棉被静躺。晌午刚过,王静生就来拜访了。王静生来了后并未言语,先是在炕沿上默默卷了支旱烟,咳嗽着抽完才去瞧他姨妈。他姨妈这才从被窝里钻出来,盘腿坐在炕席上。王静生说,关于她跟孩子的事,他听别人说了。别人呢,也没啥恶意。以前他跟父母住岗上,跟村人不怎么来往。去年他父母病死,剩他一个,都是她奶奶送粮送水。前些天他奶奶死了,还有个伯父。可这伯父是他奶奶的养子,打自初就跟他父亲不和,又是个瘸子,看来指望不上。孩子的病不是好病,别人才不敢跟他往来,怨不得别人。老太太就别瞎掺和了,省得别人戳着脊梁骨说闲话。“姨啊,你这辈子,”王静生顿了顿说,“听到的闲话还少吗?”
这倒是老太太搬到麻湾村以来,头一次听王静生讲这么多话。王静生说完,又卷了支旱烟抽起来。老太太这才转过身说:“回去吧静生,我有分寸的。”
王静生就趿拉着鞋走了。
那晚,老太太做好了饭菜,孩子却没来。老太太看着桌子上的卤煮和油条,一口都吃不下。八仙桌就在炕上摆了一宿。半夜老太太睁开眼,盼着那饭菜已被孩子吞咽得精光,不过,油条仍硬邦邦躺在笸箩里,盛卤煮的碗已凝了一层油。叹息一声,却是怎么都睡不着了。
村长是头午来的。这是个有点驼背的中年人,面目红肿,穿双皱巴巴的皮鞋,一说话嘴里就喷薄出酒气。他先自报家门,而后一屁股坐到炕上。他说,他本来早该拜访拜访老太太,可他实在太忙了。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村长了。这不是他能干,而是他必须能干:谁让他们村地底下有铁矿呢?这个村子不起眼,却埋藏着大把大把的金钱。县里让他们年底前全部搬迁,可要让这帮庄稼人离开住了半辈子的窝,倒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他忙呀,比奥巴马还忙,这才没顾忌上那孩子。再说了,孩子有毒,人还是少接触为好。“他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最后村长打着哈欠说,“我跟书记会解决好他的事。如果有问题,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老太太“哦”了声。村长似乎很满意,又说:“你要是有啥困难,尽管跟我说!我虽然不是骑马的驾鹰的,可毕竟还是一村之长嘛。”
老太太笑了笑。
村长前脚走,老太太后脚就出了门。她手里端着个铝盆,盆里是五六个大馒头。出了院门,村长赫然就堵在门外。他皱着眉头瞥她一眼,又瞥了瞥馒头,铁青着脸说:“真是个老古董。你没长耳朵吗?嗯?拿我说话当放屁吗?嗯?”
老太太没吭声,径自朝前走。村长一愣,随即吼道:“站住!你给我站住!”老太太仍是走自己的。村长三步并作两步过来,一把扯住她衣襟:“你给我回去!回去!不是说了吗?没你的事!”
老太太站在那里,一声都没吭,只默然眺望着远处的土岗。
六
儿子是第二天上午到的麻湾。
他是坐夜车来的。省城离麻湾不过一千四百里,可除了火车还要倒三次长途汽车。他腋下夹个皮包,走起路犹如身后有恶鬼追赶一般。他连问带打听地找到王静生家,让王静生带他去找老太太。王静生让他连弟喝口水,也被断然拒绝了。看来他真是有十万火急的事。王静生领了他穿街过巷,到了老太太住处。铁门四敞着,院里栽着韭菜、菠菜和萝卜秧子,一群花腰小蜂在阳光下嗡嘤着飞。还有几棵樱桃树,花期已过,葳蕤枝叶上顶着几枚枯花蒂。他们悄悄进了屋。老太太正在炕上收拾皮箱,见了儿子,只是茫然地点了下头,然后继续把衣裳一件一件折叠好,再放进散发着樟脑味的箱子里。
儿子似乎就放了心,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说:“哎,我真是白着急了,原来你已经准备回去了啊?”
老太太看他一眼,将皮箱拉链拉好。儿子埋怨道:“你的手机也不开。不开你拿它干什么呀?我昨天找了你一天,都是关机。”又瞅一眼王静生说:“你们家也是,好歹安装个电话啊,有个大事小情的多不方便。是不是?”王静生就陪着笑脸点头称是,又说姨妈住这里的日子,自己照顾得不是很周全,还望见谅。两人又闲聊几句,儿子才对老太太说:“你最近还好吧?这个礼拜日就是你寿日,香港的李老板星期六就飞过来,饭店呢,就定在凯撒大酒店。毕竟是李先生面子大,省电视台的还要全程录像呢。快回去吧,窝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干嘛?”
老太太将皮箱从炕上往下拎。拎了几次都没拎动,王静生赶忙伸手接过来。儿子继续唠叨道:“破鞋烂衣裳的还要它干嘛?给静生老婆好了。人家伺前伺后也不容易。”王静生连忙说,她老婆是个胖子,比母熊还肥,姨妈的衣裳肯定不合身。儿子说:“算了算了,我们快走吧。出租车司机还在村头等着呢。我们直接打车去市里,好歹还能赶上下午的火车。”
三人就往门外走。王静生帮老太太提着皮箱。等出了大门,老太太把皮箱从他手里接过,抽出拉杆,拍了拍他的肩,就朝土岗那厢走去。王静生“咦”了声,忙扭头看他连弟。他连弟已然将他们拉开五六米,又狐疑地去看老太太,嘴里喊道:“姨妈!姨妈!走错了!”老太太没应答,王静生只得又朝他连弟喊:“彦春!彦春!彦春!”
儿子这才扭头,蹙着眉朝老太太喊:“妈!你糊涂了啊,出租车在村东呢!”见老太太不语,声音就又挑高些。他嗓门本来就粗大,这下倒真像是用喇叭喊话了:“回来!往这边走!回来!往这边走!”老太太大抵聋了,只顾弯着脊背迈着碎步拉着棕色皮箱一步一步朝前走。儿子大概在王静生跟前有点上火,他小跑着过去,一手按捺住皮箱,另一只手死死拽住她衣角,晃着她身体喊道:“妈!你傻了啊!这是去哪儿啊?!怎么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老太太这才回身默默注视着儿子。儿子虚胖的脸上全是汗水。儿子身后是王静生,王静生身后则是些街坊邻居,“刘三姐”也伸着脖子缩在人群里,几度想踏上前来,又都犹豫着退回去。他们若即若离地环在左右,仿佛是专门来看热闹的。老太太一把甩开儿子的手,继续拉着皮箱西行。儿子倒也不敢再造次,只得跟在母亲身后边走边絮叨:“人家可是给了赞助费的!不瞒你说,说是二十万,其实给了五十万!图个啥?不就图见你一面,听你唱两句《春闺梦》和《锁麟囊》?人家拿你当宝,你可不能把自己当宝,傲气值几个钱呢?”
如果有人从土岗上俯瞰,便会看到一行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迤逦前行:最前面是位拖着皮箱、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后面是两个神态疲惫焦虑的中年人,再后则是稀稀拉拉、端着胳膊嗑着瓜子的闲人。老太太走了好一阵才到岗下。她再次转过身看着儿子,看了会儿,方才叹息道:“回去吧,你。听话啊。”儿子哭丧着嗓子喊道:“那你呢?你这是去哪儿啊?”老太太伸手擦了擦他额头的汗,扔下皮箱径直朝坡上走去。
这条坡不长,但是陡,爬满了蒲公英和矢车菊。老太太曾在黄土岗下徘徊多次,却从未真正上去过一回。她深吸了口气,这才徐徐弯下腰身,晃晃悠悠往上爬,爬了没几步就有些气喘,冷不丁一个趔趄,险些就栽滚下来。众人在坡下不禁一阵尖叫,她听到儿子劈着嗓子喊道:“妈!下来!快下来!这是唱的哪出戏啊?”她装作没有听见,只是将腰俯得更低,胸腹几乎就要贴上地面,手里抓住花草茎叶,身如脱水的弯狗虾般一拱一拱朝坡上蹭。当眼前蓦然出现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时,她不禁抬起脖子瞅了瞅。男孩就站在她上边。他还穿着那件海魂衫,小脸大抵有几天没洗了,灰头灰脑的。她就慢吞吞地说:“没事儿,别管我!”嘴上这么说着,手还是颤颤巍巍伸过去。当孩子冰凉的小手紧攥住她榆树皮似的掌心时,老太太身上忽就有了气力,手脚在瞬息都热了起来。有那么片刻,老太太确信双腿其实就踏在棉花般洁净干燥的云朵里,每向上微微跨一小步,就离天空和星辰更近了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