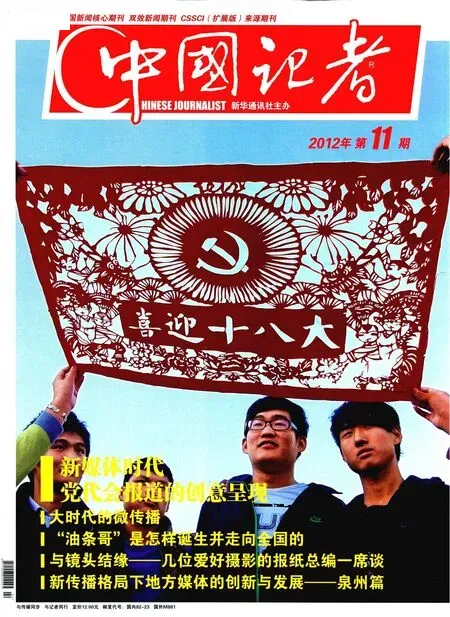扎根泥土,让新闻与理想更贴近——在新华社实习的经历与感悟
□ 文/杨荣荣
记者是社会的触角,肩负公众的期望与社会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记者有多敏感,社会的感知器官就有多灵敏。从本科接受新闻教育至今已有6个年头,一直以新闻人自居,虽然最近因为实习、求职忙得焦头烂额,但始终坚信自己将走上新闻职业岗位,践行新闻理想。
人家问:“做记者有什么好,风里来雨里去,哪里危险去哪里,女孩子就应该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好好嫁人。”是的,我不否认稳妥的工作和家庭对女性而言有多重要,不过与为百姓生计谋福利、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相比,个人的安逸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正是对国家进程的参与感让我对记者这份职业如此坚守。
让我走近你
在新华社实习时,我曾采访一位同性恋者。前期沟通中,他只肯以“吴”来介绍自己,对家庭、工作、朋友等信息三缄其口。我阐明只是想听他对年轻人当中流行的“耽美文化”的想法之后,他终于答应在西三环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动身前,我花了一下午做心理建设,预想该怎么拉近距离,说服他袒露心声。不想见面后,吴在交流中说最多的一句话却是:“你还想听吗?”
我从一开始的暗暗激动到慢慢沉下心,走进他近十年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吴甚至对心理焦虑和阴暗直言不讳。一方面,对于压抑良久的特殊人群,也许正是因为记者不直接参与他们的日后生活,单纯为了报道而来的短暂交往给了他们一个倾诉的机会,让他们能毫无压力地吐露心声;另一方面,即便那3个小时的会面已经偏离了“就事论事”的采访目的,但却让我有了因为记者这份职业而受依赖、受信任的动容。
2010年实习恰逢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新华社CNC英语电视台正筹备开播,因为学过摄像,我主动请缨扛着摄像机去拍抗美援朝老兵,有一位当时年过80的老兵王顺才,他在采访结束后提出一个愿望:想通过电视节目寻找他失散多年的老战友。我站在摄像机后面,听着他毫无停顿地念着一个一个人名,心中很酸也很难过。我没法开口告诉他,这期节目是面向海外观众英语播发,您的战友很可能看不到……
这么想来,做记者似乎有很多无奈,发现得多,解决得少,但记者走进社会各个角落,挖掘鲜活的人和故事,通过媒体告知公众,能够让大众的目光投注在这些应该关注却没有关注的角落。也许关注之后,才是走近,才是反思,才是解决。
扎根泥土
从“新春走基层”到“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再到“最美乡村教师”,开展“走转改”活动以来,集中涌现的新闻作品鲜活感人,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究其根本正是因为新闻战线回归了优良传统,坚守了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
今年8月底,为了毕业新闻作品,我背上行囊独自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探访游牧文化。鄂温克族小姑娘艺涵4岁就被父亲放上马背;布里亚特小伙子巴雅尔从记事开始就拉弓放箭,骑着小马放牧,草地深处的牧民仍拉着一串勒勒车追逐丰美水草。密实的草尖开始在转冷的天气里一天天变硬,水膘落成黄膘,是到宰羊的时候了。牧人在羊群中打量一眼,牵只大羊,抓抓膘,一拍尾巴领出羊群,草地人的传统是按住羊腿短刀开膛,手伸进胸腔把心拉出来,短短几分钟就没了动静。
另一方面,36岁的鄂温克族牧民斯琴染起了黄发,嘎查(村)里的族人脱下了蒙古袍,年轻人纷纷放弃游牧生活外出打工,流传下的传统手艺后继无人。蒙古包集中在旅游景点,哈那墙也不再是木头而被钢筋水泥取代,牧民开始定点安居……一位牧民老人对我说:“牧民离了草原就像离开了母亲,没了家。”他靠在安居平房的家门口远远望着草原的方向。
如果没有驱车五六个小时进入草原腹地,坐在蒙古包里和牧民一起喝着奶茶,我对草原的印象也许就停留在坝上如同得了牛皮癣的草皮,对牧人的印象还是景区里操着地方口音的牵马人。即便是在呼伦贝尔这样的北方边境,也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多元被迅速磨平,而重新反思我们为什么会指责现代化对传统的冲击,我们可以变得“现代”,住高楼,用电子产品,却不能允许牧民如此?为什么会感叹他们世风日下,风俗不再?原始和现代的边界在哪里?哪种更好?
黑夜里的呼伦贝尔草原满是打草过后短茬的冷香,每隔几里一束短促的灯光是打草季节久宿在草场的牧人,北斗如勺、满天星斗低垂天极,银河如牛奶一般倾倒到草原上,愈发临近呼伦贝尔新巴尔虎西旗,城市的灯光照亮了我的眼睛,经过在草原上半个多月的游荡,愈发开始反思对游牧文化的多元与传承,这是看过听过之后的疑问,也是用脚走出来的思考。
新闻界前辈萧乾曾说过,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侦察兵的阵地永远在前线。唯有迈开脚步,才能逼近真实;唯有说服了自己,才能告知大众。
站在师长的肩膀上
在新闻行业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老话依然成理,在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上能得到这么多好老师和前辈们的指点也实则是我的福分。
2010年在新华社特稿社实习,第一次写稿就选择了喜爱“同人”创作的特殊群体,这些女孩大多14到24岁,往往受到日本动画漫画的影响而对男同性恋文学抱有异乎寻常的好感。社会学家也开始逐渐关注低龄化的腐女群体在社会角色建构、青少年自我认知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在编前会上提出这个想法,各位老师给予了极大的包容,鼓励我迈出了最难的第一步,最终通过寻访挖掘她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引发的问题,写成特稿Gay Dream Believers在《南华早报》发表。
在毕业选题上,我与导师有过多次坦率而真诚的讨论交流,就我提出的多条不成熟选题,导师李彬老师在信中回复道:“就选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而言,本来就该有这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还生怕你们有什么顾虑,不敢畅所欲言,而只是唯导师马首是瞻。我希望你们都能像甘老教导那样,‘不敢与老师辩驳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敢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结合个人兴趣和社会发展需求,最终确定写新闻作品——现代游牧人。李彬老师意味深长地教导道:“从长远发展考虑,如能把游牧文章做好,则于国于民、于学问、于自己都善莫大焉……以一生中难得的年华和机遇,做一件问心无愧的事情,这比虚度年华更有意义。”之后在草原的行走探访游牧人家,这段脚踏实地去听、去看、去思考的半个月,的确是我走向职业新闻人道路上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在实习中来自老师的提点和自己的体悟同样重要,适逢新闻战线开展“走转改”活动,我在国家博物馆采访参观“走转改”活动图片展的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其中,来自新疆建设兵团日报社的王遐老师讲起采访阿拉山口荒原上坚守27年种植防风林父子的经历,她说:“大多数记者都来自普通家庭,在中国的城镇、乡村生活着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对于记者来说走基层就是回家,即便路途的遥远、条件的恶劣,也不能阻止记者履行职责,担负报道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