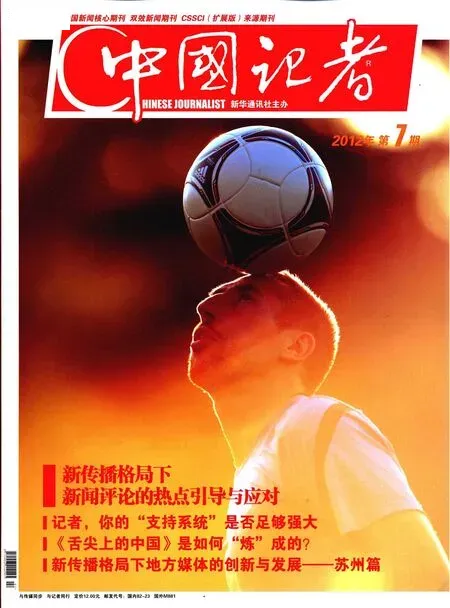“达人”马丁的求职路
□ 文/本刊记者 陈 芳
在近几年的电视节目样式中,嘉宾主持的角色功能不断凸显。他们中很多是资深媒体人,但并不产生于自家电视台内部。这一方面体现了电视人才产生机制的多元,另一方面也为传媒人的业态转型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本刊近期“跨界英才”栏目将持续关注这一特殊的新群体。
中国教育电视台求职真人秀栏目“职来职往”的18位嘉宾主持叫“达人”,达人们测试、点评求职者的现场表现并为其职场规划提供意见建议。其中一位就是本文主人公马丁,他因言辞犀利被冠以“毒舌”称号,但因出发点真诚,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粉丝”。
在过去两年中,除了担任“职来职往”的“达人”,马丁参与的节目在20个上下。密集曝光量为他赢得了知名度,当然有更多人纳闷“这哥们儿哪儿冒出来的啊”。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马丁自嘲:“哥们儿是突然冒出来的,但冒出来之前一直没闲着啊。”
找工作,失业;再找工作,再失业……
从小就爱讲故事、演小品、参加各种比赛的马丁,从天性上来说就是个爱玩、爱闹、不受约束的人。“高中毕业时我想考广播学院,去当播音员。但我妈不同意,她是大夫,传统观念,认为进公检法系统更好。后来就考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丁说,“但个性是无法改变的。说实话,法律我还基本上能接受的原因是逻辑思维和表达这块很有意思,但我对背法条和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又比较反感。所以大量时间用在了课外活动上,运动、参加社团和谈恋爱。”
大学毕业后,马丁找到了上海一家排名还挺靠前的律师事务所。家人对此很支持,户口最后也落了上海。但他实际上没干过一天律师。“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是北京人,刚毕业时和我闹分手,我舍不得,一定要把她追回来,在失恋和挣扎的过程中又回来了。”马丁笑说,“那时候肯定走不掉嘛,那个年龄,打死也要回来。”
回来之后要养活自己,就找工作。一次陪女朋友去人才招聘会。马丁看到一家豆浆机械厂招聘总经理助理。感觉这职务“貌似不错”的马丁就投了简历,对方也正好看中了他。“待了三个月我就走了。老板说,‘小马,我觉得你小伙子不错,你跟着我,三年之后房车都有’。我是打算好好干。但发现主要工作就是陪老板喝酒,可以连喝一礼拜,然后昏天黑地地吐,通过那三个月我就知道,我肯定不是生意人,起码不是这种生意人。”
辞职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马丁又找了一份工作,还是陪女朋友去招聘会的意外收获。那家企业叫北京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当时在替外企招聘员工。马丁递上简历,对方就问他英文怎样,他答凑合吧,就是敢说。于是现场口语测试五分钟,过关,这份工作就算搞定。但又是待了三个月,辞职。“原因和前一份工作恰恰相反,就是太闲了。朝九晚五,但上班没什么事,人家来办档案什么的,就抄一份档案,给人开具证明等,就是简单的文案工作。每周五下午还有各种活动,比如参观博物馆、参加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活动等,所以基本上属于三休日。逢年过节,发奖金可高了。我就觉得无聊,然后又失业了。”
这期间,遇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DJ招聘。内心一直渴望做传媒的马丁参加了考试,过了两关,到第三关时被刷下。原因是专业不对口。“其实我在学校也是广播台的,声音条件也还可以。但主考官说我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又没有北京市户口,想走这条路很难,不现实。”
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一直没忘了传媒这行,不知天高地厚去考,被刷下来之后找工作,算是找到了毕业之后第一份真正的工作。”马丁说,“就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
当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合办了一个汉语教学项目,叫IUP,公开招考对外汉语老师。马丁顺利通过笔试、面试进入了最后一关。却因打球撕裂韧带,被同学背进考场。这一关剩下20人,逐一进场,放映一个教学片断,然后给5分钟时间准备,接着就是15分钟现场模拟教学。台下坐了三个真不懂汉语的外国学生,侧面坐一排领导和老师,要求应聘者模仿教学片断。考试结束后,一瘸一拐往外走的马丁没想到被项目负责人叫住,当场告知已被录取。“他们都觉得我教过对外汉语,因为一起考试的好多是中文系研究生,还有博士生。好像最后录取的就我一个是本科。所以在后来的教学当中我有很多课要补啊,其他人中文水平尤其是古文水平都很高,我的长项就是能寓教于乐,活学活用,也可以说就是表达能力吧。”马丁说。
马丁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多。“这两年多的意义在于,教出去的东西可能还不如学到的东西多。”马丁说,一是补了很多中文的课,二是重新梳理了价值观。学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哈佛的、耶鲁的、普林斯顿的、牛津的、剑桥的等等,他们大部分都是博士生,还有一些已经工作,如美国的律师,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用一年时间,从零起点到听说读写熟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小班甚至经常的一对一、一对二授课却做到了。“我感慨他们的人生态度。追求理想,决不放弃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他们选择的专业,包括到中国来学中文,都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的时候特别专注,玩的时候特别疯。全中国到处去旅游,对北京比我还了解,他会削尖了脑袋找那些好玩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想,人的一生这么短暂,我也要找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
在新浪立了7次三等功
当了两年多对外汉语老师,一个朋友介绍马丁去新浪兼职。因为教书虽然辛苦,但还是有弹性时间,上午教书,下午就可自由支配了。当时新浪做网络访谈,请了很多名人,各频道编辑忙不过来,他们想找兼职者做视频聊天。“我一看,虽说这不是电视也不是广播,但也是个媒体,而且能面对很多名人做节目。我特感兴趣,就去了。”马丁说,“第一个名人是刘墉。为了做节目,我一个礼拜把他的书都翻了一遍。第二个是娱乐明星刘孜。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多月后,新浪老板就跟我谈愿不愿意全职过来。”
马丁大概算是中国互联网第一个专职主持人,所以每次被亲朋好友问起工作都很尴尬,“网络还有主持人?”“你这是正经工作吗?”……家人当然也不理解,从清华辞职,到新浪工作,收入还不如以前高。
在新浪,马丁做了一名最基本的编辑,名片上印的是多媒体制作部,因为还没有视频的概念。那是2003年,网速太慢了,大部分人看的都是文字对话。从2004年初到2007年,每天三场访谈,三年完成近2000场。每周一个作家。每次都要看看书,挑出问题来。“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2006年做刘醒龙的访谈,他的小说《圣天门口》是上中下三册,当读书频道编辑把书给我拿来时,我都要哭了。”马丁笑言,“但这种积累对想成为主持人的我来说是种最好的学习。”
那时,马丁觉得和新闻焦点人物对话的荣耀感和成就感都是很强的。当时他一般要上午10点采访新闻人物,下午1点钟是明星,3点是专家,5点是作家,工作强度很大。“新浪的激励机制就是立功,通报表扬,对年轻人来说,新浪是有魔力的,环境简单,大家合作都挺愉快的。那时候感觉加班就成了必须,不加就难受。”马丁说,“我立过7次三等功,立功的话奖金会高一些,最重要的是荣誉感和升职机会。我就是一步一步从编辑到高级编辑再到节目组主管、新浪视频节目中心总制片人、新浪商业视频部总监。”马丁说。
“新浪带给我的是眼界,谁来了我都不怵。”马丁很感激这段工作经历为他提供的积累。最一开始做就不紧张,因为特别亢奋。“终于有机会获得访问者的身份,可高兴了。”马丁说,“对待每个人我都很认真,会提前准备,尽量问和别人不同的问题。”也经受过磨练,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看视频,但如果主持人表现不好光看文字直播的网友也会很不客气。“这主持人是哪儿来的”“怎么问这么弱智的问题”,网络的互动特点决定了主持人随时能看到受众反馈。“网友有多喜欢嘉宾,就有多看不上你。”马丁回忆,“就说超女访谈,2005年李宇春来的时候聊得很好,但张靓颖来的时候就有粉丝质疑‘这主持人是玉米,他在刁难我们家靓颖’等等。”
这些质疑声也敦促马丁提升自己,于是他四处请教。问过一个中戏的朋友,但那朋友说:“现在是你最好的时候,充满了新鲜和好奇,充满了真挚。没什么问题啊。”还想过要不要到中国传媒大学深造,专门拜访了吴郁教授,请她给推荐几本书。没想到教授也说不用:“你去学什么?学播音主持发音,你可能没有他们标准,没有他们字正腔圆,但是你不是那种类型的播音员。学访谈技巧?这个你已经练出来了呀。”后来,马丁的方法就是多看别人的东西,还有多练来提高自己。
2007年,马丁第一次“触电”——担当北京卫视“国际双行线”主持人。虽然太想表现好的马丁用力过猛,再加上和栏目气场不够契合,马丁一年多一直“没有找到感觉”,但这个机会让马丁看到了希望和努力的方向。
“是通过朋友介绍得到的机会。”马丁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从根儿上是做了好几档互联网原创节目,产生了一些影响力。”
2006年,到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做了一次嘉宾之后,感觉这个形式很不错的马丁就把它简化并复制到了新浪,栏目名叫“小马锐话题”,最开始常态是一周一次,后来就变成了周双播。但凡有好的选题就随时抓来做,主要是社会新闻类访谈。第一期的话题是博客,当时博客刚兴起,请的嘉宾是徐静蕾和洪晃。“到离开时一共做了200期左右,我自己是制片人、主编、主持人,全是我自己弄的,带了一个实习生作助手。后来慢慢成立一个团队,就有了两三个编导,一起商量着来。”马丁介绍,“和电视一样,但是我们比电视容易操作,没那么难,再就是快,第三个就是比电视更原汁原味。比如家乐福事件时我们的题目是:爱国应该更理性还是更血性,请了李承鹏和郑也夫,两人当场就吵起来了。再如许霆案,节目放出去之后第二天,评论是17000多条,老板都震惊了,因为视频相对于文字来说,收看量和评论量少得多,因为网友不方便,没那么耐心。结果这次视频上了新浪评论排行榜的前三名了,而且是自己原创的。这个题目当时报纸已经有了,电视还没有做。我一般看到一个有价值的新闻,上午看到,下午就动手,晚上或第二天早上就做,播放也没那么多环节,啪一点马上就放了,就讲究一个以快制胜。”
在新浪的另一个得意之作是“股市播报”。2007年,领导下任务,要马丁做一个财经节目。他就先去找财经频道总监,问新浪财经什么最热门,点击量最高。当时当然是股市,简直是人人炒股;再到网上看看有没有有关股市的视频节目,一点都没有;再看看电视上有没有相关节目,有“证券时间”,股评等。“股民想赚钱又不懂,所以电视就做股市分析。互联网能提供什么电视不能提供的?那就是互动。两者一结合,我就是要做一个充满了互动的股市网络视频分析。”马丁说,“就先做了一个栏目叫‘开盘播报’。”这个栏目火到几次扩版,还获得了企业冠名。
终于成为“镜头前的人”
“做‘国际双行线’是兼职,从头到尾就没找到感觉。”马丁坦诚介绍,“第一,我没做过那么大的场,新浪的演播室从改造到设计就是我管的,是我的主场,谁来了我也不怵。而(国际双行线)场子大,现场一百个观众,环节又特别复杂。我是新人嘛,又不知道镜头在哪儿,那么多镜头,完全进了大观园了。从一开始就不那么自信,而且患得患失。从我想考广院到去电台又不成, 绕了这么多圈子,网络也算是曲线吧。终于能做一个卫视的挺有名节目的主持人,非常珍惜又非常不自信,编导也觉得你是新手,比如我跟人聊天吧,我想继续挖这个问题,编导就在耳返(注:电视行业术语)里说,别挖了,按照我的本子走。”
“新浪老板很好。我做兼职时也有一些反对声音,说什么马丁里里外外的钱都挣着等等,老板特意在中层干部会议上说,这样的话以后不要让我再听见了,马丁在外面越有名,越说明我们新浪视频做得好。我很感动。”马丁说,“除了‘小马锐话题’和‘股市播报’,我还做了‘娱乐播报’‘新浪体育播报’‘伊人在线’‘读书名人堂’等。凡是那时候的新浪原创视频节目都是我做的。也不感觉那么累,因为我和频道合作,资源都在他们手里,我只是告诉他们节目可以怎么做,然后就试验,不断修改,两三个月后就成型了,如果不好看就拿下来,因为没有很高的成本。而且播放时段又不受限制。所以可以不断地试,不好我就给它干掉,然后再提一个新方案,一直到觉得这个不错,网友真的喜欢看。我们的流量是非常精确的,比收视率调查更准确,多少个IP,多少个独立用户,多少个PV,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这些原创节目为马丁带来加薪和升职机会,而且带来了他更为看重的媒体影响力。“会不断有节目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做嘉宾,或者告诉他们我请的嘉宾的联系方式。”马丁说,“2010年我离开新浪,然后电视生涯正式迎来高峰。我这一年多里参与了差不多20档节目。我的朋友说,没半年你就烦了。在他们看来,何必呢?因为实际上我在新浪的职位已经不低了,以我的年龄和阅历怎么又跑到前台做这种露脸、蹦蹦跶跶的事呢?可我有一种从小没条件吃糖的孩子一下子被放到糖果店的感觉,一年半了,有时候也累也烦,但基本上很开心。”
离开新浪之后,马丁和朋友合伙成立文化传播公司,做自制节目,也作活动。
“我对自己的定位很简单,就是外在表现是镜头前的公众人物,想做的事情就是影响能够影响到的人。”马丁说,“现在节目做得杂,毕竟是电视新人,不会有人为我量身定制。但不再跨界,不再网络、电台都做了。电视门槛挺高的,我知道自己有能力或者潜力,是电视观众想看的那种真实、个性化的主持人,但是我没有人脉,缺乏机会。前段时间我获得《新周刊》评选的年度‘最佳人气电视嘉宾奖’,前面好多领奖的老师说中国电视缺乏新意总是老面孔,很多做电视的资深人士对中国电视的现状不满。但是我发言说,你们了解一个一直想做电视却没有机会的人的心情吗?我用了十年才绕进来,所以说我多么珍惜机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电视准入门槛太高,近亲繁殖,低水平重复,不是学广播电视专业的人很难进。不过现在逐渐好起来了,越来越多圈外人得以进入。”
谈到未来,马丁说找到一半自己的方向了,就是他最近开始主持的江西卫视“深度观察”,每周二到每周六的日播新闻谈话栏目,每期50分钟。这个节目虽然目前名气不那么大,但全国同时段收视率很靠前的。“我一天录四期,站12个小时,感觉腰都要断了,我还特别认真,编导都特别钦佩我太敬业了。我为什么这样?”马丁很知足地反问,“谁的江湖地位不是这样搏出来的?凭什么你一上来就有人给你量身定制一个栏目?呵呵,就希望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不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