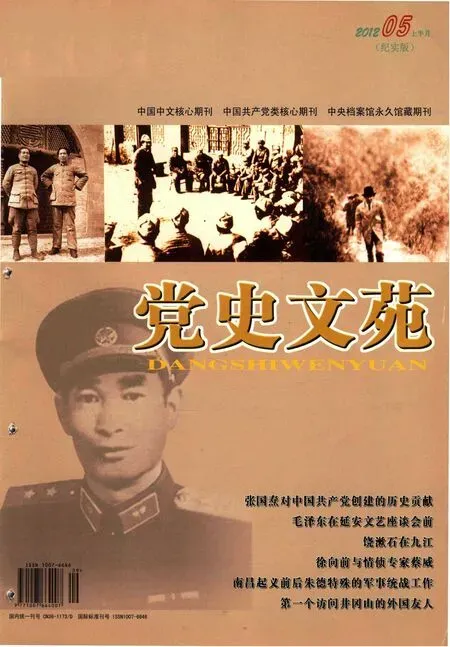论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之战略博弈——解读游击区形势演变路线图的一个视角①
黄宗华 卫平光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06)
论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之战略博弈
——解读游击区形势演变路线图的一个视角①
黄宗华 卫平光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06)
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边区的形势跌宕起伏,经历了主力部队西征之后的迷茫期、重建第二十八军的精神提振期、西进东返的战略转折期、深入开展游击战争的辉煌期、反击新“清剿”的极为困难期、岳西谈判的柳暗花明期等阶段。造成这种形势演变路线图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国共双方在边区的战略博弈之高下,是解读游击区形势演变的一个视角。当任何一方的战略部署合乎实际、针对性强、高于对方的时候,边区的形势就偏向哪个方面,就对哪个方面有利,反之亦然。这充分说明,战略规划的正确与否、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形势的高涨与低落,关系到革命形势的演变路径,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
鄂豫皖边区 国民党 共产党 战略博弈 游击区形势演变路线图
1934年11月至1937年7月,鄂豫皖边区在红军主力转移、力量极为薄弱、国民党军队严酷“围剿”的形势下,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最终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确保了革命的红旗在大别山依然飘扬。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了主力部队西征之后的迷茫期、重建第二十八军的精神提振期、西进东返的战略转折期、深入开展游击战争的辉煌期、反击新“清剿”的极为困难期、岳西谈判的柳暗花明期等阶段。造成这种形势演变路线图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国共双方在边区的战略博弈之高下,是解读边区形势演变路线图的一个视角。
一、主力红军西征前后双方之战略举措——边区陷入迷茫
鄂豫皖边区主力红军的撤离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第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斗争。第二次是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留下红八十二师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主力红军离开边区后,留下来的党的领导机关主要有中共鄂东北道委和中共皖西北道委。中共鄂东北道委下属的党组织有罗(山)(黄)陂孝(感)特委及红安、光山、麻城、新集等县委,所属武装有罗山教导营、光山独立团1个营、光西战斗营和武装工作便衣队等共1500余人,分别坚持在位于黄安、礼山、罗山、经扶等县山区被分割的小块苏区内。中共皖西北道委所属的党组织有赤城、赤南等县委,所属部队主要有一路游击师、二路游击师、三路游击师、道委特务队、商北大队、银沙畈战斗营和少数游击队、便衣队以及红八十二师共1300余人,活动于赤城、赤南、六安六区、六安三区、霍山六区5小块互不相连的苏区内。[1]p4-5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基于全国斗争形势,两次命令鄂豫皖边区的主力进行转移,客观上造成鄂豫皖边区斗争力量的减少,特别是1934年11月的转移后,边区党组织仅剩两个道委,军队仅剩2800余人,且绝大部分为地方部队,很多是伤员和年老体衰的战士。加之1934年11月的转移从决定到开拔仅仅5天,思想动员和准备工作不足,对于边区在主力部队离开后如何开展工作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划。鄂豫皖省委仅在临行前指示鄂东北道委“转告高敬亭,责成他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为基础,加上地方武装,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和进行秘密工作”。[1]p6至于游击的具体方略和鄂豫皖今后的发展规划和期许,无论是鄂豫皖省委还是党中央都没有详细提出。置于当时的境况来考量,红二十五军的西征是在全国苏区均陷于被动情况下的战略转移,中央苏区也是仓促开始长征的,因此,要当时的党中央和鄂豫皖省委对红二十五军离开后的边区斗争进行详尽规划是不现实的苛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主力红军西征前后,共产党方面对鄂豫皖边区今后的战略规划是粗线条和不翔实的,边区事实上沦为自生自灭的状态。
而国民党方面,在这一阶段的战略规划比较从容而且明晰,其重点是彻底清除共产党在鄂豫皖边区的军政力量和影响力。这从其兵力配备和战略部署可以得到印证。国民党仅派遣18个团尾追西征的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部署在鄂豫皖边区“清剿”数量仅2800人、分散且很多是老弱病残的留守队伍的军队,竟达56个团、10多个保安队及一些地方民团。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张学良的指挥下,将边区划为四个“驻剿”区,分片对各苏区和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第一“驻剿区”由国民党第二十五路军负责,梁冠英为总指挥(兼豫鄂皖“清剿”总指挥),指挥部驻罗田县;第二“驻剿区”由国民党第六十七军负责,王以哲为总指挥,军部驻潢川县;第三“驻剿区”由国民党第五十七军负责,何柱国为总指挥,军部驻黄安县;第四“驻剿区”由国民党第十一路军负责,刘茂恩为代总指挥,指挥部驻霍山县。[1]p5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在红二十五军西征之后,仍将边区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域,派遣大量军队进行“围剿”,且进行了周密规划和部署,反映了国民党方面对这一区域的高度关注。
两相对比,很明显地看出,鄂豫皖省委和党中央虽然对红二十五军西征之后的边区斗争进行了一定部署,但战略部署很匆忙、很粗糙,对边区今后的坚持和发展缺乏明晰规划。回归历史场景来看,在全局陷入被动的情况下,鄂豫皖省委和党中央对鄂豫皖边区也确实是无暇顾及,以致鄂豫皖边区在红二十五军西征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无领导集体、无领导核心、无拳头部队、无斗争规划的迷茫状态。而国民党方面战略清晰,重点明晰,规划详尽。因此,在红二十五军西征之后,边区斗争陷入低潮,苏区受到极大摧毁,边区各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被压缩在深山中,斗争形势十分恶劣。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在该阶段战略运用的得当和共产党方面的仓促无规划。
二、重建红二十八军与西进东返前后双方之战略举措——边区旗帜不倒
在红二十五军西征之后,鄂东北道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采取正确的战略应对新的形势。一是健全组织,调整和充实鄂东北道委。由王福明任书记,道委常委由王福明、徐成基、何耀榜、吴光陆、罗厚福5人组成。二是明确了主要任务。决定尽快健全党的各级组织;组织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开展游击活动,牵制敌人兵力,策应红二十五军转移;迅速安置好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伤病员。三是重建鄂东北教导团,强化军事力量。鄂东北道委将罗山教导营、光西战斗营和红二十五军西征后留下的鄂东北独立团部分指战员重新组建了鄂东北独立团。四是与高敬亭取得联系。1934年12月下旬,道委派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徐成基率领独立团前往皖西寻找高敬亭。五是鄂东北道委所属各级党组织均以便衣队的形式开展活动。六是改变斗争策略,争取持中间态度的保甲长,瓦解敌方阵营。七是重建红二十八军。1935年2月,高敬亭在得知红二十五军西征后,决定重建红二十八军,并召开会议决定由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全面工作。自此,边区又形成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有了一支主力红军。八是在面临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红二十八军在1935年5月放弃西进陕南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的计划,决定扎根鄂豫皖边区开展斗争。
综上所述,在该阶段,共产党方面针对新的情况,从主力红军西征之后的迷茫状态逐渐步入规划今后斗争的正常状态,开展了切合实际的政治、军事、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稳住了阵脚。特别是重建红二十八军、形成边区统一的党政军领导集体和核心以及西进东返,对边区的旗帜不倒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其中,红二十八军的建立,“其数量不满一千人,但在任务上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也得到了很相当的胜利”[1]p44,更重要的是向大别山民众传递出共产党和红军仍在大别山斗争的明确信息,争取了民众;形成以高敬亭为首的边区党政军领导集体,使得边区的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不至于一盘散沙;西进东返,决定扎根大别山坚持战斗,是确保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决定性战略决策。因为“西进”只不过是革命力量的又一次从大别山转移,但“东返”却奠定了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基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使得边区得以保存,进而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因此,在该阶段,共产党方面的战略举措基本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重大变化,不存在重大的战略失误。
反观国民党方面,其采取的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继续“清剿”。红二十八军重建不久,国民党觉察到大别山区革命武装在逐渐扩大,遂调军队分别从霍山、立煌、太湖向凉亭坳一带合围“清剿”。1935年4月下旬,国民党“豫鄂皖剿总”重划防区,更改“清剿”计划,将兵力增至61个团,把原来的4个防区改为3个防区,另以第二十五路军主力组成“追剿”部队,企图用“驻剿”和“追剿”相结合的手段在两个月内消灭边区革命力量。同时采用碉堡战术对边区分片包围,进行扫荡。二是加大宣传攻势,实行“户籍连坐”,企图隔绝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严禁食盐、火柴、油等日用品运入边区。
两相比较,在该阶段,国共双方的战略都不存在重大失误,都为着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了有效的决策和执行。但该阶段,共产党方面“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致使很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2]p405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边区没有摆脱被动局面。但重建红二十八军,形成领导核心和西进东返,奠定了边区继续斗争的基础,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举措。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其未能充分利用共产党方面在主力红军离开后的迷茫期,而且更大的失误在于没能有效阻止红军的“东返”和潜入大别山。因此,该阶段的整体形势仍然是国民党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共产党方面处于求生存和疲于奔命的状态。但是,由于国民党方面关键战略的错误和共产党方面关键战略的得当,形势已经蕴含着向边区共产党有利方向转化的因素。
三、深入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双方之战略举措——边区重现辉煌
红二十八军从建立到西进东返,经过4个多月的曲折斗争,总结出了适合游击战争的斗争策略,并将其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指导整个边区的革命斗争。一是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方针和战术原则。1935年7月,高敬亭在安徽太湖县店前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提出了 “拖垮二十五路,相机打十一路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基本作战方针和 “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反之则打”的战术原则。不久,又提出 “缴获不多不打,反之则打”的战术原则。二是制定分散活动、渗入平原地区活动的战略。红二十八军在分散活动几个月后,感到比以往集中行动灵活机动得多,因此,高敬亭在湖北蕲春县三角山召开会议,决定部队继续分散活动。同时,部队跳出山林,渗入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破敌人的围剿。三是进一步具体化游击战术。在三角山会议上,强调战术上要以伏击为主,以长途奔袭、化装智取为辅,力争出敌不意,歼灭敌人;作风要英勇顽强,进攻要勇猛突然,敢于短兵相接同敌肉搏;防御则机智顽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适时反击;转移则迅速隐蔽,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四是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加强便衣队建设。1936年3月,在安徽太湖县召开的柴家山会议上,总结了部队由集中到分散、由山区到平原作战的经验,并且作出了几条决定:第一,继续贯彻三角山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第二,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部队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以分散活动为主,主力会合或集中行动的时间,由军领导根据情况决定;第三,进一步加强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骨干,放到地方建立便衣队组织,支援和配合部队行动。[1]p14第四,实行“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互相配合。在主力部队分散到外线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边区各地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在根据地及其游击区域积极打击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组织,配合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各地便衣队在内线积极开展活动,并不断从山区向平原地区和白区发展。
综上所述,共产党方面在作出扎根大别山开展游击斗争的战略决策之后,具体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大别山的地形地貌,制定出了合乎实际情况的游击战术原则,并将其上升到战略地位,改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仅能够有效、灵活地破除国民党方面的“围剿”,而且抓住机会、适时地对国民党方面进行打击,特别是创造性地实施便衣队这种藏兵于民的方式,使得国民党方面疲于应付“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游击战,武器优势、兵员规模优势、阵地战经验较丰富的优势都发挥不了作用。因此,共产党方面在这一阶段的战略举措,抓住了国民党方面的软肋,抵消了国民党方面的优势,合乎了当时当地的形势。
至于国民党方面,面对共产党方面的战略调整,也进行了新的战略规划,主要包括:一是调整 “清剿”领导人。1936年2月,蒋介石免去梁冠英的 “清剿”总指挥职务,任命具有较高战略战术水平的卫立煌为 “清剿”总指挥。二是实施新的 “清剿”方略。具体包括:调整兵力,配备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参与围剿;增加碉堡和封锁线,对边区进行纵横交错的分割包围;变换战术手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围、追、堵、 “驻剿”并用。三是掏空共产党方面生存的群众土壤。国民党对于重点 “清剿”地区,实行移民并村、组织民团防守、安插坐探监视、强化保甲制度、 “十户连坐法”等方式,妄图隔绝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四是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和红军活动区域实行禁运粮、油、盐、布、医药等物质的手段,妄图困死红军。国民党方面采取的上述战略举措,不可谓对 “清剿”不重视,投入的兵力也很多,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狠,但其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国民党方面在明处,实行的战术主要是阵地战,而共产党方面化整为零,藏兵于民,在暗处,化解了国民党的整体优势。不仅如此,而且在局部地区共产党方面在战斗力方面还具有相对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国民党方面的薄弱环节。
因此,在这一阶段,国民党方面采取的战略虽然给共产党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由于共产党方面采取合乎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有效抵消了国民党方面的优势,使得国民党方面的十多万军队发挥不了作用,而共产党方面则可以利用便衣队、游击队骚扰国民党方面,建立基层组织,组织民众,红二十八军主力则适时地抓住机会对国民党方面进行攻击,使得国民党方面顾此失彼。针对共产党方面的分散游击战略,国民党方面别无他途,唯有长期围困方可有效。这也决定了短期内,国民党方面是被动的,而共产党方面是主动的,造成的局面也就是共产党方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较有影响的战斗共34次,歼敌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三省边区的45个县,这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形势最好的阶段”[1]p20。
四、反击新“清剿”期间双方之战略举措——边区陷入困境
在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中央表明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和党中央暂时摆脱了长征以来所遭受的围追堵截的局面。由于陕甘宁边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枢和富庶地区,且国民党在周围部署有重兵,因此,国民党方面的基本意图在于逐渐压缩其生存空间,使其逐渐臣服。但是,共产党留守在南方的游击部队,活动于中心地带和富庶区域,接近国民党的统治中枢,时刻会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国民党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继续加紧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驻守鄂豫皖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新的“清剿”。
国民党方面在这轮 “清剿”中采取的战略举措主要包括:一是调整充实 “清剿”机构。1937年4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设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派刘峙、陈诚、孙连仲、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王树常、刘茂恩、胡宗南等19人为委员,以刘峙为主任委员,并将“豫鄂皖边区主任公署”撤销,成立“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下设岳西、信阳、经扶3个督办处,任命卫立煌为公署督办,并授予他调整撤换辖区地方有关官员的权力。[1]p20—21二是实施新的“清剿”方针。卫立煌总结多次“清剿”失败的教训,强调切实贯彻“剿抚兼施”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方针,要求国民党各级政府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加强“防卫”。三是对“清剿”便衣队高度重视。便衣队在三年游击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国民党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因此,卫立煌要求在“清剿”主力红军的同时,对便衣队要进行彻底“清剿”。四是配强军事力量,调整战术。国民党方面投入“清剿”的正规军共38个团,同时,将地方分散的保安团相对集中,又调进了原在平汉铁路以西的湖北省保安部队8个团,使得鄂东北地区的保安团由原来的4个增加到12个。[1]p21同时,在战术上将部队由原驻城镇改为进山扎寨,重点地域广筑碉堡并由正规军驻守;抽调精锐部队编成“追剿”纵队,由督办公署统一指挥,实行“深入穷追”和“分头兜剿”。五是实行军政协作。之前的“清剿”基本上是军队唱独角戏,在这次“清剿”中,国民党的各级政府配合“清剿”,制定了移民并村、“霸路”、“跟路”、搜山、倒林、“摸鱼(半夜突然包围一个村进行搜查)”、宣传“赤匪罪恶”等配套手段,妄图隔绝红军和老百姓的联系,将红军困死。
面对国民党新的战略部署,共产党方面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开展广泛宣传,号召群众反“围剿”。鄂东北道委在得知国民党即将开始新一轮“清剿”后,散发了《为肃清国民党侦探坐探告劳苦群众书》,宣传西安事变后的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开展反侦探坐探的活动,投身于反“围剿”斗争之中。二是开展大规模“肃反”。在该阶段,高敬亭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部署反“围剿”上,而是在鄂东北整顿“道委”,错误地开展“肃反”斗争,使鄂东北地区党和军队一些优秀的领导遭到错杀、扣押,影响和削弱了领导力量。三是将红二十八军主力长时间停滞于鄂东北一带。四是调整鄂东北独立团领导成员,将一批缺乏实际作战经验的同志提拔到重要指挥岗位。
两相对比,在这次“清剿”与反“清剿”斗争中,国民党方面从指挥机构、军队调配、战术选择、军政配合等方面都作了细致周密的部署。而共产党方面由于前三次反“清剿”的胜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麻痹轻敌思想,对严重形势缺乏高度重视,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未做必要的准备。特别是错误开展的“肃反”,使得大批优秀指战员和领导人被错杀和扣押,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军队的凝聚力;将军队主力长时间停滞于国民党重点“清剿”区,延误了战略转移时机,陷入国民党军队包围之中;新提拔的指战员缺乏实战经验,等等。加之,边区遭受长期的围困,军队的补给非常困难。因此,在这次反“清剿”中,共产党和红军方面遭受重大损失,皖西北和皖鄂边的各级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军队被打散,边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五、岳西谈判前后双方之战略举措——边区柳暗花明
国民党方面在1937年4月至7月对鄂豫皖边区进行了效果很显著的“清剿”,使得共产党方面的主力红军被打散,分散在各地的便衣队遭到前所未有的全面 “清剿”,建立的群众基础大部分被摧毁,控制地区基本丧失,具有战斗力的仅剩突围出来后在岳西游击的手枪团第二、第三分队。国民党方面的战略得当和共产党方面的战略失误,使得鄂豫皖边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革命的太阳随时都可能在大别山陨落。但是,以高敬亭为首的边区党组织是有战斗力、战略眼光与魄力的党组织,他们在绝境之中捕捉到新的机会,从而实施新的正确的战略,很快扭转了局面,使得红旗依然高扬在大别山。
共产党方面在绝境之中采取的战略举措主要包括:一是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军事局势,以此来作为自己战略规划的基础。由于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红军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无法获得党中央的指示,但高敬亭等人非常注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国内局势。当他看到国共合作的消息后,立即带领部队从鄂东前往皖西,找到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探究消息的准确与否。二是认真研读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和《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国共合作抗日的纲领性文件,深刻领会党中央的精神。三是认真研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具体方案。在看过中央文件的第二天,高敬亭在岳西主持干部会议,商讨了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具体方案,决定力争主动,在党中央未派领导人来之前,以红二十八军的名义向国民党 “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四是一面同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同时防止国民党方面对红军方面进行偷袭,做两手准备。五是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扭转了边区和红军极为困难的局面,确保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利益。六是阐明举国一致抗敌御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积极疏通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情绪。同时,要求大家警惕国民党方面的背信弃义,严防国民党方面搞突然袭击摧毁游击根据地。七是选择最为安全的路线到达黄安县七里坪集中,进行整编训练,组建新四军第四纵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在大别山保存革命的种子。 [2]p404
反观之,国民党方面在该阶段没有继续强力地进行“清剿”,使得共产党方面利用整个国家局势的演变,获得了调整和柳暗花明的战略转机。但是,国民党鄂豫皖地方当局的转变不是主动为之,而是迫于整个形势的急剧变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急,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的积极推动下,1937年7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界知名人士举行谈话会,并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表明了团结一致抗日御侮的决心。卫立煌等人也认识到 “共产党和红军是剿不尽的”,“抗日形势不可挡”[3]p28。在日军的压力、全国抗日浪潮的声援、国共两党中央达成协议、蒋介石表明抗日决心等因素的影响下,国民党鄂豫皖地方当局已经丧失了彻底“清剿”边区党组织和军队的外部环境,这也是岳西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外部条件。
在国共双方这一轮的战略较量中,共产党方面很显然占据上风。主要体现在:一是游击一隅,放眼全国。共产党方面在绝境之中,充分运用国际国内有利环境,以外部压力促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妥协。二是不等不靠,敢于负责。共产党方面在领会中央精神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变战略上的被动为主动。三是精心细致,规划精到。共产党方面在谈判条款、行军路线等细节上做足功夫,不给国民党方面任何口实和偷袭机会。而国民党鄂豫皖地方当局的失误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没有继续“清剿”,懈怠于最后关键时刻。二是没有认真分析全国大的局势,对可能出现的谈判规划不周。因此,在这一阶段,共产党方面在面临绝境的时候,充分运用外部有利条件,主动将国民党方面拉到谈判桌上,既解除了眼前的困境,又获得了在大别山长期扎根的条件与机会,真可谓绝处逢生,柳暗花明。
六、结语
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共双方都根据对方的战略部署和外部环境进行了战略规划,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战略层面的博弈。鄂豫皖边区跌宕起伏的形势演变路线图,说到底是国共双方战略博弈的结果,当任意一方的战略部署合乎实际、具有针对性的时候,边区的形势就偏向哪个方面,就对哪个方面有利,反之亦然。这充分说明,战略规划的正确与否、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形势的高涨与低落,关系到革命形势的演变路径,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同样如此。如何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根据本地的区域特点和既有基础,积极主动地进行科学、有效地战略部署,直接决定着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变路线图,直接决定着本地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得失,直接决定着本地在全国的位置,直接决定着本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所作贡献的大小。○
注释:
①此文在2011年9月的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红色岳西”的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得到与会专家的指导,在此一并感谢。
: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王辅一.新四军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黄宗华(1976—),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副研究员、博士。
卫平光(1979—),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硕士。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