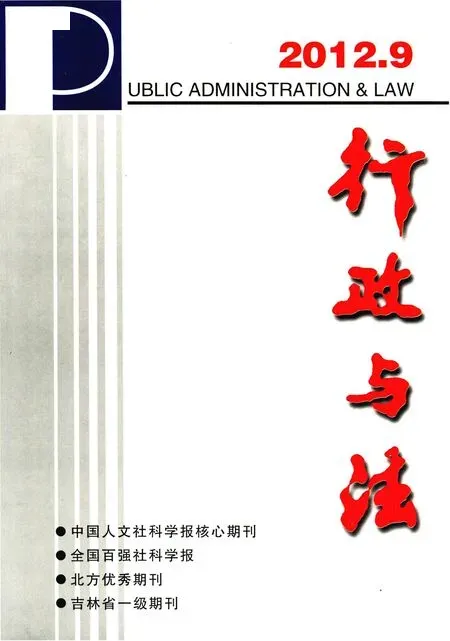论侵权法中的价值平衡思想
——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
□叶延玺
(复旦大学,上海200438)
论侵权法中的价值平衡思想
——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
□叶延玺
(复旦大学,上海200438)
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是侵权法中的基本矛盾,也是侵权法的二元价值目标。侵权法中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均体现了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思想。我国《侵权责任法》在总体上也体现了这一平衡思想,但由于负担了超出其功能范围的社会救济职能,其在个别制度的设计上仍有违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精神。
侵权法;权利保护;行为自由;平衡
权利之所至,自由之所止。侵权法是权利救济法,其最终目标是权利保护。但是,权利保护必然构成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二者的对立乃是侵权法中的基本矛盾。一部科学的侵权法律不能单一地追求权利保护,还必须顾及行为自由的价值,并实现二者的平衡。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整部侵权法的发展史就是顺应社会变革,不断实现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之动态平衡的过程。本文拟通过分析侵权法在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试图阐发侵权法中的价值平衡思想,为侵权法的未来发展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科学解释及适用有所裨益。
一、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价值冲突:近代侵权法的逻辑起点
古代法对于损害事件有两个基本态度,一是宿命论,二是结果责任原则。依照宿命论的观点,“除非有特别的干预理由,合理的政策应当让损失停留在其发生之处。”[1](p50)在宿命论的观念下,一个人遭受不幸“意外事件”被认为是命运的安排或上帝的惩罚,自然应当由受害人自己承担这一后果。另一方面,古代社会对于人身损害盛行血族复仇,后逐渐被选择赔偿取代,并最终形成法定赔偿制度。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损害赔偿制度必然适用结果责任,即“有损害就有赔偿”。尽管中外古代法中也确实存在过错责任的荫芽,但结果责任才是这一时期侵权法的主要特征。宿命论令受害人对其遭受的损害自负其责;而对于存在明显加害人的损害,则要求加害人依据结果责任承担全部责任。在这样的责任分配机制下,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价值平衡则失去了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产生,人们越来越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然而,任何社会活动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风险因素反过来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理性的人在决定从事某项行动之前,或多或少地都要对其行动风险作一番衡量。在结果责任的赔偿体制下,行为的风险后果完全由行为人一方独自承担,行为人必然会更加谨慎地从事各种行为。对于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纯粹加害行为,如抢劫、盗窃、毁坏他人财物等,以结果论责任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对加害人进行制裁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当一种行为不仅符合行为人的私利,同时也具有社会价值时,例如生产和交换行为,结果责任就不能胜任正义的要求。此外,某些行为符合行为人的私利但通常不会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可以认为具有社会价值,因为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具有社会价值的行为,如果对其可能造成的风险完全由加害人承担,就会严重打击人们从事这些行为的积极性。那么,如何鼓励人们积极从事有社会价值的行为,同时又对这类行为的风险在相关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成为法律面对的难题。这一难题在侵权法上的表现就是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价值冲突。
在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的社会里,人们总是比较重视当下既有利益,而对未来可能利益的需求则不如前者那么重要。欧洲工业革命之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对权利保护的要求在理论上胜于行为自由。但从欧洲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出于对未知领域进行广泛探索的需要,鼓励参与各种风险活动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此时,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结果责任为主导的、以权利保护为单一价值取向的赔偿制度就难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趋势。行为自由的重要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行为自由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近代侵权法就不能继续坚持权利保护的一元价值取向,而必须兼顾行为自由的需要。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价值冲突也就成为了近代侵权法的逻辑起点。
二、归责原则: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基点及其演变
(一)过错责任: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基点
虽然过错要素在罗马法中早已存在,但它不具有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功能。因为在无过错之人也要遭受惩罚的情况下,过错要素本身是无关紧要的。[2](p28)过错责任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真正起到平衡作用肇始于《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将过错责任与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等一并确立为近代私法的基本原则有其时代的背景。其一,在思想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将中世纪的迷信和愚昧涤荡而尽,理性主义取代了神权思想。其二,在政治方面,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成为了现实。正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民法典》被认为是“自由个人主义的胜利”。[3](p99)其三,在经济方面,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的工业革命程度基本上和英国处在同一阶段。[4](p10)在这样的背景下,宿命论和结果责任显然已不合时宜,过错责任当然地成为最佳选择。过错责任不仅符合当时道德观念和人格尊严的理性要求,还为个人行为自由与社会安全(权利保护)找到了最合适的平衡点。王泽鉴先生对此作了十分中肯的评述:“任何法律必须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两个基本价值。过失责任被认为最能达成此项任务,因为个人若已尽其注意,即得免负侵权责任,则自由不受束缚,聪明才智可得发挥。人人尽其注意,一般损害亦可避免,社会安全亦足维护。”[5](p13-14)《法国民法典》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因其深具人文关怀和实用效果,被德国、日本等大陆法国家广泛采纳。
在英美法系,虽然学理上对过错(fault)在早期法律中的重要性有不同观点,但十分明确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主张侵权责任就需要证明过错的存在。[6](p13)英美法中的过失有两重含义,它既指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又指某些侵权责任中的主观要素。[7]就其实际功能而言,与大陆法国家的过错责任一样能对权利保护与行动自由起到平衡的作用。“法律的功能就是保护权利并赋予其效力。除为了尊重其他人的自然权利而对其进行限制,人们都是自由的。”[8]个人的自由应当止于他人权利所在之处,但自由与权利的边界是模糊的,于是要由法律在二者间竖立起界碑。在过错责任原则的指引下,行为人可以尽其所能地参与社会交往活动而不至于动辄得咎,他人的权利也得以保障。过错责任基于其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作用而成为近代理性法的重要标志。
(二)过错客观化与过错推定:过错责任基于其平衡作用的内部调整
由于过错主观标准的不确定性及其证明上的困难,为实现过错责任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功能,还需要对其进行内部调整。“构成行为内在特征的不同人的性情、智力和教育等各不相同,法律无法一一顾及。”[9](p108)主观标准须依赖于特定行为人的各种特殊情况,难以为一般人的行为自由提供具体的指引。因此,依赖特定行为人内心状况的主观标准就被以“理性人”为参照的客观标准所取代。客观过错标准有几个明显的优点:其一,一般理性人标准可以避免主观标准下因特定行为人的经验、知识、性格等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简化案情事实;其二,由于理性人标准不考虑个人的特殊状况,可以促使行为人在更大程度上履行注意义务;其三,客观标准可令一般公众对其行为后果具有更高的预见性。[10](p54)但是,过错标准的客观化在带来前述优点的同时也牺牲了部分人的行为自由。在客观标准下,过错责任的判断不再取决于行为人自身的理性标准,而取决于其无法掌控的外在客观标准。因此,个人行为与其主观意思的关联被弱化,特定个人对其具体行为后果的预见性程度被降低。过错的客观化虽然在总体上提高了不特定的一般人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但降低了特定个人对其具体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在现实生活当中,既没有抽象的理性人,也没有抽象的行为人和权利人,只有具体的原告和被告。因此,过错标准的客观化虽有其合理性,但其实际效果是加强了对权利的保护,而降低了对行为自由的保障。从主观标准到客观标准,过错责任作为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基点已经悄悄向权利保护一端滑动。
在一般情况下,受害人对加害人主张损害赔偿必须举证证明其过错的存在。但是,于某些特殊情形,“如要求被害人于损害事故发生时,就加害人过失负担证明责任,无论从知识程度、技术水准或经济能力观之,实均近乎不可能。坚持此种原则,殊无异于责令被害人放弃损害赔偿之请求”。[11](p66-67)过错责任虽然在理论上为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划定了边界,但于实际操作当中,受害人往往因不能举证证明而无法主张其权利。尤其在加害人直接掌握对其不利的证据或者易于提供相关证据之时,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由加害人负担证明其无过错之责任,才符合过错责任平衡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之根本精神,亦符合公平正义之法理。然而,过错推定必竟是过错责任的例外情形,其适用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将矫枉过正。对此,各国实体法对过错推定多采法定主义,严格限制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从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平衡的角度来看,过错推定将二者的平衡基点向权利保护一端又推进了一步。
(三)无过错责任:风险行为与权利保护间的平衡
19世纪末,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频频发生。许多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概率性,虽尽合理之注意也无法避免。许多此类事故的损害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没有关联或者其过错难以查明,若依过错责任标准,相关受害人的权利将得不到任何救济。在此情形,过错责任已无法独立地实现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无过错责任应运而生。
就称谓而言,德国和法国称之为危险责任,英美国家称之为严格责任,中国大陆及我国台湾地区则通常称之为无过错责任。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及历史演变不同,危险责任、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内涵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危险责任与严格责任的称谓相对保守,而无过错责任的称谓则相对激进。但是,不论何种称谓,其责任基础均在于行为的风险性。对于这些风险行为引起的损害,如果依照过错责任,实际上是将这部分损失分配给了受害人,显然有失公平。在此背景下,过错责任所达致的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关系已经被破坏,就需要通过新的归责原则对“允许从事危险行为”相应地进行平衡。[12](p256)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所对应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一是过错行为,一是风险行为。除了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等共同要素外,对过错行为进行归责的关键要素是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而对风险行为进行归责的关键要素是行为风险成为实际损害。这类风险行为并未包括在传统的过错行为当中,或者只是偶然地以过错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无过错责任并非是在相应范围内对过错责任的替代,而是对过错责任的补充。[13](p158)从平衡角度来说,过错责任要平衡的是一般行为与权利保护的关系,而无过错责任要平衡的是危险行为与权利保护的关系。
总之,过错责任虽然为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确立了基本的平衡点,但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行为自由与权利保护的范围均有扩大的趋势,二者之者的冲突逐步加剧,过错责任在二者之间确立的平衡状态也不断被打破。过错的客观化与过错推定实际上是在过错责任的框架内对这种失衡状态的微调。但是,对于在科技发展和工业发达背景下形成的诸多高风险行为所致的损害,过错责任已经无济于事,而必须在这类风险行为与权利保护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危险责任或严格责任因此而产生,并最终形成无过错责任。透过归责原则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侵权法顺应社会现实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进行平衡所付出的努力。不过,归责原则只是为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确立了平衡的基点,侵权法的许多具体制度和规定也不同程度地贯彻了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思想。
三、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其它平衡机制
(一)因果关系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调节
在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中(本文采“四要件说”),归责原则仅仅解决了责任基础问题,而真正将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联结起来的则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不仅关系到责任成立与否,还进一步关系到责任的范围。因果关系的确定方式直接影响到权利保护的限度与行为自由的程度,其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平衡的影响程度不亚于归责原则。
“任何国家之法学领域中,均不能避免因果关系之问题,却未见到何一成文法典对之作成具体规范!”[14](p95)有关因果关系的具体内容均出自学说理论,目前,侵权法中的主要学说有: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疫学因果关系说和盖然性因果关系说等。[15](p100)不同理论学说对因果关系认定的严格程度不同,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效果亦不相同。条件说在各种学说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最为宽松,只要某一行为系某一损害发生之条件,即认为二者间具有因果关系。若依条件说,行为风险将被无限放大,可能产生“因一颗马蹄钉而失去一个国家”的结论。相当因果关系说将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限制在一般人可理解的范围内,避免了行为风险的无限扩大,在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确立了恰当的平衡点。然而,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相当性”却是极不确定的概念,致使其平衡的效果极不稳定。此外,对某些因果关系复杂的案件,如医疗、药品损害、环境侵权等,相当因果关系说尚难直接适用。疫学因果关系说和盖然性因果关系说等则是对相当因果关系说之不备的进一步完善。
疫学因果关系说与盖然性因果关系说均不追求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是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虽然概率的计算在不特定事件中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仅仅使用这样的频率来确定一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这样的表述也总是建立在不充分的信息基础之上”。[16](p424)无论不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多高(除非百分之百),推定特定事件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都存在不确定性。依照疫学因果关系说与盖然性因果关系说对损害赔偿的认定,虽然加强了权利保护,但同时也扩大了行为风险。从平衡的角度来看,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基点,而疫学因果关系说与盖然性因果关系说则将平衡基点推向了权利保护一端,以应对特定情形下权利保护不周的局面。
(二)惩罚性赔偿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平衡的影响
“侵权法主要有两大功能:补偿与威慑(预防)。一般认为,侵权法通常不具有惩罚功能,该功能应由刑法承担。”[17](p11)随着无过错责任和责任保险的兴起,侵权法的预防功能逐渐减弱,补偿功能越来越凸显。虽然侵权法的惩罚功能也常被人们提起,但一般所谓侵权法的“惩罚”功能不过是其补偿功能的反射效果,与惩罚性赔偿中的“惩罚”有本质区别。侵权法律关系属于平等主体间的私法关系,侵权损害赔偿自然应适用等价原则——损失多少,赔偿多少。通过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受损的权利获得救济,“逾矩”的行为得以矫正。如果说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是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基础,损害补偿制度则对二者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维护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责任事故频发,对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然而,一方面,作为加害方的企业通常具有经济上的优势,并且总是趋向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作为受害方的消费者常处于弱势地位,不具有与大企业相抗衡的力量,并且因损害金额较小、诉讼成本过高等原因在权利受损后常常放弃救济。在此情形,损害补偿已经不足以维护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平衡,惩罚性赔偿所特有的威慑功能就越来越受到司法机构的青睐。惩罚性赔偿虽然在普通法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20世纪以后才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得到广泛运用。[18]这恰好说明了它应因了时代的要求。惩罚性赔偿通过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加重企业方的赔偿责任,鼓励受害的消费者积极寻求救济,体现了“法律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功能”。[19](p20)
惩罚性赔偿在英国主要适用于“被告已经计算其行为带来的利润将远远超过对原告的赔偿”之情形。[20](p401)美国也是如此。在著名的Grimshaw诉福特公司一案当中,[21]福特公司明知其某一车型的排气缸存在缺陷并容易引发事故,但经过计算,消除该缺陷的成本要高于其造成损害所需的补偿费用。如果按照补偿原则,福特公司很可能不会积极消除该缺陷以避免造成更广泛的人身损害。此案的成功适用表明,惩罚性赔偿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如此,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却一直受到学界的批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批评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取代了刑法的惩戒功能,但又缺乏刑法的程序保障”。[22]但支持者认为,“惩罚性赔偿试图防止的是产品责任案件中的许多大规模风险并未被刑法所界定或认识,尽管此类公司不端行为实际可能造成的公共风险远远大于贴上犯罪标签的行为”。[23]从这个角度来看,惩罚性赔偿弥补了侵权法与刑法之间的空白地带,具有独立于刑法的特有功能。这些对惩罚性赔偿合理性的讨论仅仅涉及企业行为方面。然而,基于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要求,还必须考虑受害人一方权利保护的因素。关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受害人获得超出其实际损失的高额赔偿的依据,有学者认为,“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不仅包括经济损失和社会不利,还包括情感上的自然损害”。[24](p400)这一解释似乎颇为牵强,因为即使所谓的“情感上的自然损害”客观存在,但不唯独存在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而是普遍存在于人身损害案件当中。惩罚性赔偿对企业行为的规制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对特定案件中受害人获得的过度保护作出合理的解释。
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不能从孤立案件中的受害人一方得到解释,而必须从社会整体层面进行理解。对特定受害人的高额赔偿可以抵消加害人获得预防成本与补偿费用之间的利润差额,从而促使其采取措施减少潜在损害,最终保护不特定人的权利。因此,在预防成本高于补偿费用的情形,惩罚性赔偿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失衡状态起到了重新调整的作用。
(三)侵权法内的其它平衡机制
作为权利救济法,侵权法的制度设计和条文规定均体现了权利保护的精神,但出于行为自由的考虑,侵权法又不得不对权利保护的范围和程度进行合理的限制,从而实现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总体而言,侵权法通常根据具体情形增减行为人的责任来实现二者的平衡:一是减少或免除行为人的责任,如限额赔偿、过失相抵、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二是加大或扩张行为人的责任,如连带责任、替代责任、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等;三是在权利人与行为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如双方均无过错时的公平责任。所有这些制度均在具体情形下体现了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精神。
四、评《侵权责任法》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效果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权利保护是侵权法的根本出发点,将其置于立法宗旨的地位本无可厚非,但是,权利保护即意味着对他人行为自由的限制,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权利保护的一元价值追求很可能对行为自由造成过度限制。加之我国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尚不完善,《侵权责任法》承担了本不属于其功能范围内的社会救济功能,进一步加大了对行为自由的限制程度。尽管如此,《侵权责任法》虽然没有在第1条将行为自由置于立法宗旨的地位,但其大部分制度仍然体现了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价值平衡,唯个别制度有违这种平衡思想。例如,《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规定的见义勇为者对受益人的请求权虽然符合社会道德风尚,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侵权法的平衡思想和制度功能相违。在“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的情形,应由国家对受害的见义勇为者给予救助。受益人自愿补偿的应予提倡,但要求其承担法律上的补偿责任似乎过严。《侵权责任法》第24条关于公平分担损失的规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第24条的规定主要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害、加害人不明、意外事故、为相对人利益受害等情形。[25](p106-107)《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制度本已进行了权衡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该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些既有解决方案的适用效果,淡化了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平衡的思想。此外,《侵权责任法》中最不符合该平衡思想的当数第87条关于高楼抛物的规定。该条不仅未顾及对一般人行为自由的保障,还明显违反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当然,《侵权责任法》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等多方面的因素,任何制度的设计都难以周全,因而不能过分责难于立法者。但是,通过阐发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二元价值和平衡思想却有助于在司法释解和适用过程中认识到这些制度的缺陷所在。从根本上讲,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不足。由《侵权责任法》解决本应由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解决的问题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权宜的制度设计不仅破坏了《侵权责任法》内部的平衡精神,也不利于我国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进一步完善。
[1]O.W.Holmes,The Common Law,Macmillan&Co.,1882.
[2](德)鲁道夫·冯·耶林.罗马私法中的过错要素[M].柯伟才译.中国法律出版社,2009.
[3](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M].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
[4]Se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VI,edited by H.J.Habakkuk and M.M.Post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
[5]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VivienneHarpwood,LawofTort,CavendishPublishingLimited,1993.
[7]See Percy H.Winfield,The History of Negligence in the Law of Torts,The Law Quarterly Review,April,1926;Edward J.Kionka,Torts in a Nutshell,West Group,1992,pp.47;W.V.H.Rogers,W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Sweet&Maxwell,1989,pp.43.
[8]Roscoe Pound,The Role of the Will in Law,Harvard Law Review,Vol.68,1954.1.
[9]O.W.Holmes,The Common Law,Macmillan&Co.,1882.
[10]See Kenneth S.Abraham,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ort Law,Foundation Press,2002.
[11]邱聪智.从侵权行为归责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M].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
[13]See Kenneth S.Abraham,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ort Law,Foundation Press,2002.
[14]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5]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6](美)H.L.A.哈特,托尼·奥诺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M].张绍谦,孙战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7]John Cooke,Law of Tort,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2.
[18]See Clarence Morris,Punitive Damages in Tort Cases,Harvard Law Review,Vol.44,1931,8.
[19]Roscoe Pound,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42.
[20]PhilipS.James,GeneralPrinciplesoftheLawofTorts,Butterworth&Co.(Publishers)Ltd.,1969.
[21]See Grimshaw v.Ford Motor Co.(1981)119 CA3d 757.
[22]StephenDaniels,JoanneMartin,MythandRealityinPunitive Damage,Minnesota Law Review,Vol.75,1990,1.
[23]Michael Rustad,In Defens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Testing Tort Anecdotes with Empirical Data,Iowa Law Review,Vol.78,1992,1.
[24]PhilipS.James,GeneralPrinciplesoftheLawofTorts,Butterworth&Co.(Publishers)Ltd.,1969.
[25]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王秀艳)
Study on the Ideology of Values-balancing in Tort Law——Balancing between Right Protection and Action Freedom
Ye Yanxi
Right protection and action freedom forms the essential conflict in tort law,and they are basic values of tort law.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causal relationship,punitive damages and etc systems embodied such a balancing spirit.The Tort Liability Law of PRC displayed such a spirit as a whole.However,for the Tort Liability Law of PRC burdened too much social remedy functions,several systems in that law violated the balancing spirit.
tort law;protection of rights;freedom of action;balance
D923.7
A
1007-8207(2012)09-0109-05
2012-06-15
叶延玺(1982—),男,江西九江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法总论与民法解释学、侵权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