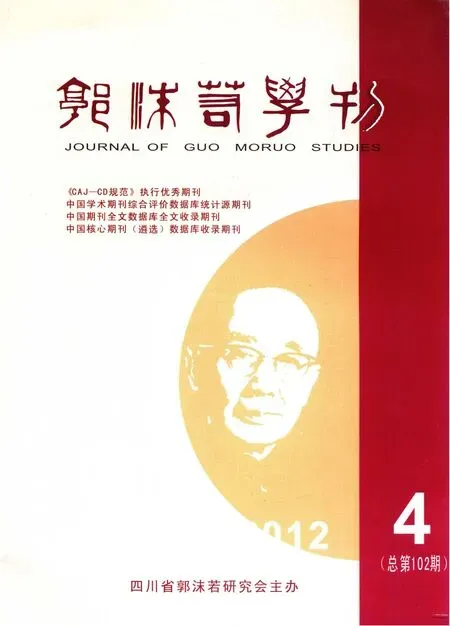汪静之与郭沫若
邓牛顿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36)
1985年9月,我在浙江富阳参加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会时,于主办方安排的富春江游船上,得以拜识“五四”著名诗人汪静之先生。那时,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汪静之与郭沫若这两位青春型诗人之间的交往。直到2002年,汪静之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沪召开,得到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漪漪讯》,方惊人地发现汪、郭之间有那么多的交往和友谊。《漪漪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汪静之和符竹因之间的情书集,也是汪静之爱情诗创作的主要情感源泉。
尔后十年间,我学术课题甚多,未能及时地将这些相关资料进行梳理。直到今年7月20日,上海举办汪静之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文物捐赠仪式,我才着手,以汪静之情书《漪漪讯》作为主要线索,并参照西泠印社2006年出版的六卷本《汪静之文集》,整理出汪、郭诗人交往录,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份生动、翔实而珍贵的史料。
现在,让我们走进历史现场——
一、结识于“《女神》周年纪念会”
“前夜开《女神》周年纪念会,后至沫若、达夫寓所与沫若抵脚。和他们谈得很有趣。沫若确有大诗人风度,温和而慷慨,冷静而活泼,诚哉满身皆有诗气味矣!”(汪静之,1922年8月7日信)
《女神》出版周年纪念会,1922年8月5日晚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纪念会由郁达夫发起,参加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和庐隐女士诸人。汪静之和应修人一起代表湖畔诗社与会。
1982年4月15日汪静之《建议成立郁达夫纪念馆》时说:“郁达夫与郭沫若是创造社之双星。郁生前与郭齐名,并与郭同样蜚声日本文坛。在‘五四’新文学创造时期,发表小说最早的是鲁迅,而出版小说集最早的是郁达夫。”“1922年在上海民厚里泰东书局编辑部,我亲闻沫若对我推崇郁达夫的小说和旧体诗,并说自愧弗如。当时郁达夫也在场,面部表情是很难为情的样子,口称过奖,但并没有认真否定郭的说法。”
1985年9月在富阳纪念郁达夫会上,汪静之又一次忆及当年情景,“我把郭、郁当老师,但他们不以老师自居,愿当老大哥,视我为小弟弟。他们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很年轻,像个小孩子。”
1986年3月,汪静之自述生平时说:“郁达夫、郭沫若以前我都没有见过,在会上一见如故,会结束后,郭沫若要我和修人一起回他们的住处,郭说他已看过《蕙的风》(8月1日出版的)。他们创造社的三个人住在泰东书局编辑部,创造社的书刊都在那家出,他们住在那里,白吃饭,不拿工资。那夜谈得很好,郭沫若很喜欢我,像对待一个小孩子,抱了我亲嘴,他三十一岁,我二十岁。郁达夫也很喜欢我。他们是大人,喜欢小孩子。”
二、此后的交谊
“昨天郭沫若、郁达夫来看我,我就伴他们游海滨。(友人来访,我以海滨贡献)我们各唱新诗数首。以试验新诗唱法。他俩唱了几首日本的恋歌,颇有情致。谈及恋爱问题,达夫大赞日本女子。又论中国文坛前途,当负扫尽迂腐气和流氓气的责任,不得不努力肆劲前趋。在海上高谈阔论,浪声亦为之齐奏。”(汪静之,1922年8月9日信)
1930年11月30日汪静之《出了中学校以后》一文回忆:“1922年,我离开杭州一师,曾在吴淞中国公学住了一暑假(邓按:读暑期英语补习学校),常常带着书到海边草堤上去独坐,一边读书,一边看海。那海波的活泼的风度,海云的变幻的神态,都是我所最熟悉的。有一次和沫若、达夫同游海滨,直玩到半夜,讨论新诗读法,大家试读。沫读我的诗,读得很慢,好像唱昆腔一样,每个字音都拖得很长。他的读法和胡适之的读法完全相反,胡适之读新诗不用哼哼调,就和说话没有分别。接着我读他的《湘累》,我便把他们两人的读法折中了读,虽带一点哼哼调,但亦不离语言的自然的声调太远。”
“明天要赴申,应郭、郁之邀约。”(汪静之1922年8月11日信)“我觉得我的脑子不够用,身体又很怯弱无气力,我以为有病患;昨天叫郭沫若给我试验过(他试验得很仔细,全体都试到),说是没有什么病,不过因为少运动之故,所以不很强健。真的,我自古以来不曾用气力去运动过。以后我要注意些了。(郭君是在日本学医的,他不曾进文科学文学,只是自己研究,至于文学的学问恐怕有些文学博士还不如他。)”“前夜和郭、郁谈论嬉笑,直至夜半后四时才睡觉……”“郭君在日本的住宅是叫做抱洋阁,因紧临着海洋,风景绝佳。他叫我将来去和他同住,倘若我要到日本去的时候。”(汪静之1922年8月14日信)“昨天珮声又叫我到郭沫若那里去问他,伊的鼻病危险不危险。到郭处有二十里路远,我坐在电车里只顾看书,看了几篇《空山灵雨》,等到下车的时候,方知袋中的皮夹被扒手借用去了。好在皮夹内只有两块钱和一张十几块钱的蹩脚皮袍的当票。到郭处适他他往,只得转回。”(汪静之1922年8月23日信)
“我的病沫若哥替我看过,并非前额窦炎,是一种鼻腔肥厚症。他说此病普通很多,完全不要紧,无害于脑筋。常用盐水洗洗就是了。不过洗盐水是很麻烦的。”(汪静之1924年2月23日信)“我在沪时是和沫若哥同枕睡,我是他的小弟弟,他用手腕给我做枕头,抱着我睡,并且亲吻:望你不要起醋意,我们同性的人亲亲吻是不要紧的。即如你和你的姐妹亲一万个嘴,我也不会吃醋。”“沫若他们的学艺社要在杭州办一个大学,沫若已定为文科主任。”“沫若的妻儿已到日本去了,因为上海地方太坏,不宜于小孩子住。他想带妻儿到杭州钱塘江边去住家。”(汪静之1924年2月29日信)“日本是一个花的国,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其中很有美的趣味。我计算明年春樱花开时可和你到日本去游一次,倘若沫若有工夫和他同去更便当些。”(汪静之1924年信)
三、爱看《茵梦湖》
“《茵梦湖》(小说)、《活尸》(戏剧)是中国翻译界的两本很有价值的书。望你细看看,可以得到无限悲凉的安慰。”(汪静之1922年7月19日信)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汪静之积极从文化时潮中汲取滋养。他多次讲他爱看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其中也包括《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作。
《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郭沫若的译作。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说,“《茵梦湖》的共译者钱君胥是我的同学,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体文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脱的体裁,失去了原作的风格。因此我便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原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体验,我是靠着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到了1924年1月末,汪静之在给符竹因的信中再次述及:“《茵梦湖》是羡慕财富的丈夫的女子的好教训。以丽沙白自幼与来印哈德要好,后却嫁与富家儿奕理虚,虽因其母有意要嫁与奕理虚,实亦伊自己羡慕奕理虚的富贵奢华之心理。到后来重会来印哈德时伊才知他和伊才是真正的精神相爱,才是一对幸福的好鸳鸯;才知伊是被羡慕富贵的虚荣心所误了。作者用一首俗歌来代伊说话:‘纵有矜荣与欢快,徒教换得幽怨来。若无这段错姻缘,纵使乞食走荒隈我也心甘爱!’这歌好极了!”
四、彼此评诗
“适之、作人他们说《蕙风》好,我现在自己看看除了三五首外实在都是坏诗。这是我这一年进步了的原故。现在最好的诗人总算郭沫若,其他都不佳。我们(漠、修、雪)的诗毫不惭愧地尽可与老郭并驾了。毫不自夸地话,比老胡高明多了。老胡整理国故的本领的确好,诗便不行了。去年老胡说看着我们做诗很羡妒,漠华说道:‘我们努力几年,总有气死胡适之之一日!’只要没有十分了不得的意外事发生,我们四人努力做去,将来定可成第一流文学家(不仅诗而已)。”(汪静之1923年信)
“修人对我说《支那二月》是乱排的,只照长短排得好看,并不依诗的好坏为秩序。还有一层,我已经出名了,他们还没有什么荣誉,所以把我的放在中间。这是真的,普通人家都是把有名的人的东西放在前面,不管好坏。修说故意要改了这种俗习,沫若恐怕也有诗拿到《支那》上来发表,修说也不把他放在前面。”“沫若说这一期我的三首诗最好,其余都不佳。但以为……”(汪静之1925年2月28日信)
那时年轻人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了自信,甚至还有点儿自夸,哪怕是面对胡适之、郭沫若这样有影响的人物,也敢说自个儿的作品好。
到了1979年春,汪静之返顾当年诗坛情景,有了历史主义的眼光。他说,“新诗坛第四本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夏天出版),是异军突起。这才是真正的新诗,这才是新诗的开山祖师。《女神》是火炬,热情奔放的革命浪漫主义,鼓舞了千万青年。”“《女神》里有一句诗:‘新诗人还在吃奶’。郭沫若是吃饱了惠特曼、拜伦、雪莱、歌德、海涅、莪默·伽亚谟的奶。湖畔诗社四诗友当时只有《女神》和几十首翻译的外国诗值得学习,我们是缺奶的营养不良的婴儿。《女神》是奔腾澎湃、波浪滔天的大江,湖畔诗社四诗友的诗不过是山涧小溪的涓涓细流。”(《回忆湖畔诗社》)
五、见证郭沫若的生存状况
“昨晚和修同到沫若家中去,沫若同他的安娜一同做厨子,忙着弄菜做饭给我们吃,吃了一种日本做法的菜。直谈到十点钟才回来,我和修睡,桃仙和伊母亲睡。昨夜和伊睡在床上谈到二点钟才睡着。”“我今天又到沫若处去玩来。他问我他在西湖时第二天你没有去同游,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已把你解说过了。他现在很苦,三个儿子累煞了,一天到晚绕着他,要纸、要画、要书、要抱,要……又是哭,又是叫。他的安娜也辛劳得很,养育了三个孩子,人也老了,而且两三礼拜之后又要生儿子了。他因为爱文学不爱做别的事,所以情愿吃点苦而不到四川去当四百元一月的医院院长(现在四川还要他去)。他现在穿的是十三年前的日本学生呢制服,黑色已经变成黄色了,领、袖、扣子都破了,坏了。(我去年正月见他穿的也是这套破制服。)他说他上街都是穿这套学生装,有一次买菜,遇着一个卖菜的老妇人,那老妇人见他这样子以为是厨房师傅,对他说:‘大师傅,你的菜篮太小了,可以换一个大些的。’(大师傅就是厨房火头。)他说卖菜的人常常当他大师傅。”“沫若说他曾写信到扬州第二师范去替我找事,但回信还未来。”(汪静之1925年2月25日信)
这些现场的记述,与郭沫若的自传与自传性小说散文相互参照,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痛苦与艰辛。
六、人生路上
1925年
“我于今天(邓按:汪静之1925年2月26日前往天津)早上上船,船于下午一句钟开出,此刻已经六句钟了。今天是修人、沫若、旦如、友舜、叔和六人送我上船的。”“沫若说了许多关于卫生的话,现在大略告诉你,望你实行。他说饭不可吃得太多,有些饱了就算了,有半饱就可以了,但须咀嚼得非常非常细,每一口饭必须要嚼五十下。菜蔬要多吃些,菜蔬不可煮得太熟,须要半生不熟的。水果当然更要多吃。他说鸡蛋、豆浆、鱼肝油的确补的,望你多吃吃!还有新鲜空气与运动最为要紧,每日须到空气新鲜的野外去走一次(你可和你妹妹同去),运动不必太多,每日做做早操,走走路也就够了。还有生活有规则也是很要紧的,天天于一定的时候走起,一定的时候吃饭,一定的时候睡觉。他自己说他这些话是很要紧的,望你一定要照这样办!你若不听我的话,不照这样办,我是不高兴的!你非照这样办不可,否则对不住我!我爱你心切,一心要把你憔悴的身体养成强健的身体,你怎可辜负我这样的深厚的爱?!至于我,你放心,我从今天就实行了。”“德桢你去看过伊没有?如未去,望你以后不要去看伊了!沫若说同肺病接触者很危险,你同伊谈天时,伊若溅了极小的一滴唾涕在你脸上,你就不免要传染,极小的一滴唾涕里肺菌有几千万。肺病者的房间、用具、椅凳都是危险的。他说灰尘里虽也有许多肺菌,但被太阳一晒就死了。总之,同肺病接触者是很危险的。他说肺病也是最利害的,无药医的,世上多数人由此而死,假使有人发明医肺病的药,那是人类最大的恩人。他说肺病只有初期可以养养,吃药是无用的。他说德桢恐怕无希望了,有一点肺病的人不能生儿子,一生儿子即刻就会变到第三期。他说肺病只好卫生预防,不让生起来,生起来了亦须于第一期急忙调养得好,但笫一期自己不觉得,医生也不容易看得出来,等到知道了已是第二三期,无望了。望你小心谨慎,以后千万千万千万不可再去看德桢,伊来信看了也须即刻烧了,并洗洗手。”“沫若说杭州医生钱君胥最好,须要他看了才的确。我就叫他介绍,他说回去就写信,信寄你由你转与德桢,叫伊持信到旗下东坡路钱氏医院去看,他当要看得仔细些。沫说看肺病胸前要解开,叫伊不要顾忌。钱君是日本留学生,沫若很佩服他的医学。”“沫说肺菌到肺里是肺病,到骨髓里是背痛,到肠里是肠结核,到血管里是什么结核,他说背痛初起也可以医,他说德桢两样病都是很危险的。望告诉德桢,伊若要命,就赶快去看医保养。我并非叫你丢了朋友,不过叫你不要去看伊,以免传染。”(汪静之1925年2月27日信)
“……学艺社的书都由商务出版。我想我先去入社,明年或后年你也入社,你赞成么?”“学艺大学下半年开办,沫若对我说有大学预科(高中部),我想可托沫若设法,我打算明天写信给他。”“沫若似乎说他是《学艺社》的编辑委员主任(或者只是编辑委员,并无主任)。他有一部小说已由商务排印。我入了社随便出什么书都很便当。”(汪静之1925年2月28日信)
1926年
“1926年8月底,我经人介绍到芜湖的安徽省第二农业学校去教国文,9月、10月教了两个月。10月里北伐军攻下了武汉,我看见报纸上说,郭沫若当了政治部副主任,我就去找他,要参加革命。我认为军阀腐败,想在革命军里做点事,心里舒服点。那时中国轮船不能在两军之间通行,外轮可以,我是坐外轮去的。上船后,听说郭沫若跟总司令蒋介石到南昌去了,我就在九江下船,去南昌找郭沫若。在上海时,我同郭沫若常见面,他要我带竹因去,竹因不肯去,郭沫若就到我们家来看我们。”
“1926年10月底我到了南昌,去到总政治部大办公厅里,一看见郭沫若,他就抱住我亲嘴,我已经二十四岁,是大人了,他还把我当小孩。他要我到武昌总政治部去工作,做宣传科编辑。”(《汪静之自述生平》)
1937年
“1937年9月初离开杭州回徽州去。在绩溪县住了三个月,日本鬼子在绩溪丢了炸弹,我们就回村子去。在农村住了几个月,家里有几亩田,吃饭还可以,用的钱没有。《爱国诗选》四册1938年3月出版。卖诗的钱还剩一千用不了多久,我必须出去工作。看见报纸上说,郭沫若当了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我一个人先去找他,芜湖已被日军占领,我从家里走八十里到歙县,再经金华、南昌、九江到武汉。找到郭沫若,他说你怎么不早点来?人都用满了(我看报纸后没有马上去),他说想想办法,过了些时,他说三厅要加一个处(第四处),你到这里工作,已给总司令部上了公函。我就住在岳父店里……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郭沫若说没有批准加处,本来可以准的,但日本占了安庆,再上来就是九江、汉口了,紧张了,单位要搬家了,地方越来越小,要节省开支。我着急了,一家人怎么活?”
“章铁民在军官学校四分校(原黄埔军校)工作,他进去时是国文教官,写了一篇文章在校刊发表,主任(韩汉英)看写得好,叫他做秘书。我写信给章托他找工作,他同主任讲,主任就同意我去,我又带了一封郭沫若的信去。学校对我很优待,叫我当上校国文教员……”(《汪静之自述生平》)
历史表明,诗人汪静之的出现与成长,得益于“五四”思想解放的时代环境。这位湖畔诗人既得到了胡适、周作人、鲁迅、朱自清、刘延陵等的支持,也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等的关爱。说明一个相互切蹉、彼此支撑的文学环境,对发展我们的事业有利。我之所以会冒着酷暑辑录上述文字,不但因为这些艰难存世的文献,真实而生动地记录着新文学运动前驱者们的人生足迹与感人情景,而且予我们当今的文学发展以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