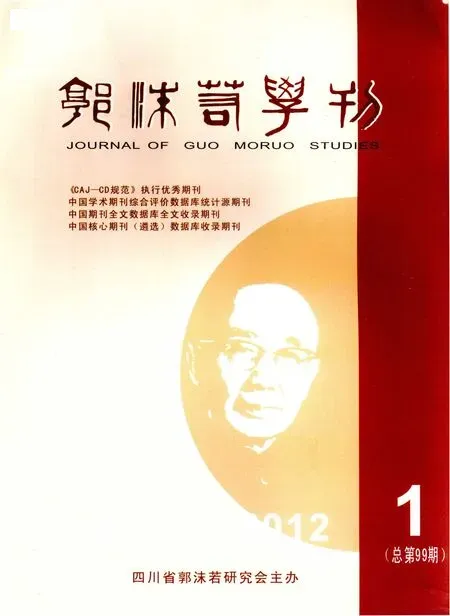郭沫若名物新证研究述评*
侯书勇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郭沫若是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巨擘,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处在新旧中西交汇之际,郭氏的治学思想与方法也体现了其既继承传统又融会新知的特色。名物新证是郭氏古文字、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运用唯物史观承继传统的考据学,并参之以考古学、人类学等“新兴的科学的观点”[1](P196),融会古今中西的治学特色。通过考察其名物新证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局限,可见其治学思想与方法之一斑。笔者不揣谫陋试就此略作述评,以就教于方家。
一、名物新证略说
在传统典籍传笺注疏中,名物制度和音韵训诂一样,是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2](P1-20)。就“名物”而言,最早见于《周礼》。刘兴均先生曾对《周礼》中所见19处“名物”用例作了分析,认为“名物是古代人们从颜色、形状(对于人为之器来说是指形制)、功用、质料(含有等差的因素)等角度对特定具体之物加以辨别认识的结果,是关于具体特质之物的名称”,并将《周礼》中所见名物分为“禽兽”“甸邑”“田制 ”“ 物产 ”“祭 牲 ”“ 饮 食 ”“ 祭 器 ”“ 几 席 ”“ 玉 器 ”“ 服 冕 ”“ 旗物”“车涂”“兵器”“卜蓍”“宫室”“用器”等23类[3](P12-30)。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则将我国传统名物研究分为四类:(一)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与《方言》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基础;(二)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后又从《诗经》训诂中独立出名物研究;(三)名物学的展开,涉及礼学、格古、本草、种树、物产、类书六个方面;(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主要集中于清代乾嘉学者相关研究,涉及衣服、饮食、住居、工艺等方面[4](P8-31)。
青木正儿所列基本涵盖了传统名物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作梳理亦较为细致。但若从研究材料和方法上考察,可简略将传统学者名物研究分为两途:一为就传世文献典籍范围内作综合互证;一为将传世文献典籍与地下所发现之实物材料互证。前者自两汉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家传笺五经以来,一直为学者研究的主流;后者可称为名物新证,早期见于王肃、刘杳以地下所发现之实物材料订正《诗经》中犠尊、象尊之毛传、郑笺说,至两宋时期金石学兴盛而得以较大发展,元明衰微,清乾嘉以后复兴,至清末民初因古器物的大量发现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若说传统名物研究以经史典籍尤其是五经中的《诗经》、“三礼”为主,到了近代随着古器物的大量发现及传统四部分类法被西方输入的学科分类体系所取代,名物研究亦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一、随着碑刻、封泥、陶器、铜器、简牍、甲骨等古器物的大量发现,传统的金石学向古器物学发展,代表人物如为曾提出为后学“肇启山林”之古器物学的罗振玉(1866-1940)等[5];二、随着经学主导地位的边缘化和史学逐渐走向中心[6],名物研究更趋向于史学,代表人物如王国维(1877-1927)等;三、随着文学的发展,一些学者更多地从文学角度作名物研究,代表人物如青木正儿等;四、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部分学者则从考古的角度作名物研究,代表人物如李济等[7]。当然,这里是就其大致发展趋势而言的,各方向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而是相互关联,只是主次稍有不同而已。
就史学发展趋向而言,王国维在其代罗振玉所作《观堂集林序》中曾自道其学云:“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据程君之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橅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疑辞。”[8]在此王氏清楚地谈到其学所自出,乃以乾嘉考据方法研究地下出土之新材料的程瑶田和吴大澂,当然亦“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9]。王氏将地下出土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旧材料互证并提升到理论高度,先后提出“二重证明法”和“二重证据法”,[10]在学界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如其清华国学研究院弟子徐中舒所撰《耒耜考》所考“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全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11](P72)郭沫若亦步王氏之“轨躅”而参之以“新兴的科学的观点”,在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研究方面取得了海内外公认的成就,名物新证研究即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名物新证研究的成就与得失
郭沫若名物新证研究散见于其甲骨文、金文等论著中,而以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为主,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兵器类;(二)服饰类;(三);车马器;(四)其他。下面试择其要者略作述评,以见其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一)兵器类。郭沫若金文研究中多处涉及青铜兵器,这方面代表作为《说戟》、《释干鹵》。在《说戟》一文中,郭氏首先回顾前人关于戈戟的研究情况,认为《考工记》已言之甚明,汉人因不解胡、援、内古义而仅据汉制以为臆说,后来学者崇信汉说使戈戟之制遂晦。宋人黄伯思作《铜戈辨》“始辨识戈为击兵而非刺兵,并据古戈头存世者剔发胡、援、内之古义”。清人程瑶田初“疑戟之形当如十字,援与内横置,有刺在胡之上”,并绘有一想像图;后因古戟所出无与所绘之戟相似者遂改前说,认为戟内末之刃即刺而非刺别为一物,近人王国维、马衡以其后说为确。郭氏则从两方面辨其非,认为程氏前说较为接近实际:一、就文法而言,《考工记·冶氏》“与刺重三鋝”句“刺”之为物当与胡、援、内等戈体分离而后始可以言“与”;二、就古物戈戟自铭情况言,内末有刃而自铭曰戈如“差勿戈”、“邾大□戈”等为之反证。由此认为,戟之异于戈者必有“刺”,“刺”当如郑玄所说“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此物当如矛头,与戟之胡、援、内分离而著于柲端;“刺”与戟体本分离,柲腐则判为二器,故存世者仅见有戈形而无戟形也。进而,郭氏由戈戟进化过程考察了其演变轨迹:“古戈无胡,仅如单独之棘刺之横出而已,古人所谓棘者当是戈。继进始有胡,继进始锋其内末而成二刃。更进始于柲端著刺而成戟,戟有雌雄,雌者戟内之无刃者,雄者有刃者也。古戈至秦汉而渐废,古戟至秦汉而改制。汉人于戟之雌者亦谓之戈,戟刺与援内合为一体,更进则古戟之内变而为銎”。最后,由古戈铭中与戟相关诸字字形(、)证明古戟必三出,并绘有一想像图。郭氏所论戟的形制后来得到汲县、辉县战国墓考古发现的证明,其论戟形制的演变则与事实有出入[12](P155-189)。正是郭沫若以从文献文法分析、出土实物和古文字字形等多方面印证,将戟形制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其期待“尚在萌芽期中”“田野发掘”的研究思路为戟的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13(]P188-220)。
在《释干鹵》一文中,郭沫若将古文字字形、文献典籍和人类学材料相结合,考察了古代盾的形制及其演变。首先,郭氏通过对小篆()、金文中干字(、、)及从干之字(、、、)字形的考察,发现干字有从圆点和从一两种情况,“凡从圆点作之干字必先于从一作之干字”,“就从圆点作者以观之,余谓古干字乃圆盾之象形也。盾下有蹲,盾上之∨形乃羽饰也”,并证以非洲朱庐族土人所用盾形。其次,由此考辨先郑(郑众)、后郑(郑玄)对《诗经·秦风·小戎》“蒙伐有苑”毛传所作的解释,认为先郑用毛意以“治羽而覆于中干之上”得之,后郑说为画羽则非。再次,郭氏又从“五盾之制”、汉画像(武氏祠)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并从铭文字形()及人类学资料(非洲丁加族、亚洲岛民之盾)考证了“古干亦有无羽饰者”。最后,综考卜辞、金文中干字种种异文字形有“像方盾形者”(甲骨作、、,金文作、、、)和“像圆盾形者”(、、),前者商承祚释为毌,郭氏认为“毌实为古干字,特字早废,许因贯字从自作,故以贯穿意解之”。就古盾形制而言“,象方盾形之毌字见于卜辞及金文中器之较古者,象圆盾形之干字卜辞所未见,且见于金文中器之较晚者,据此可知古干之进化。盖干制之最古者为方盾而上下两出,其后圆之而上下左右四出,更其后则于盾上饰以析羽,而以下出为蹲,遂演化成干字之形。入汉而后,羽饰与蹲具废,干字之为象形文,二千年来吾人知之矣”。在释鹵方面,郭氏根据《说文》“:橹,大盾也。从木鲁声。樐或从鹵”,认为“大盾之橹当以鹵为本字,象形,橹樐均后起字,鹵之用为盐卤字者,乃假借也”,并证金文即 鹵字,“像圆盾之形而上有纹饰”,金文中诸字亦鹵字“,作长方形而上下各有三出”,金文中、诸字“亦当释为鹵,或书为字,亦无不可”,又证之以人类学材料如“菲律宾人所用之盾”。最后郭氏通过对干鹵的考释总结道“:要之,干鹵均为盾之象形文,其制自殷代以来所旧有。殷制作方形,上下两端均有出,面有文饰。周人圆之,干上以析羽为饰,以下出为蹲。鹵以字形而言,上端似亦有饰,下则无蹲,……秦汉以后形制又变,古干鹵之制乃幸得于古文字中保存其大略,故备述之如此”[14(]P413-428)。郭氏将干字释为盾形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在文字考释上是一重大突破,其释鹵字则多存疑,然而郭氏将古文字字形、文献典籍记载和人类学材料相结合考释古代名物的思路与方法颇值今人借鉴。
(二)服饰类。这方面的代表作为《释黄——古代象形文字中所存之古佩玉考》。首先,郭氏考察了金文与文献中黄字出现情况,铭文中“多以巿黄对言”(如“赤巿朱黄”、“赤巿幽黄”等),典籍中巿作芾若黻、黄作珩若衡,由二者比较可知“黄、珩、衡为一物”。说金文者多以黄为假借字,释为佩玉之横,然而“古人赐佩,何以仅赐其佩上之横而不及其他?”郭氏先考察了“古佩玉之制”:虽“全制终无由确定”“,将来如有古墓发掘,就冢中珠玉之位置或可以回复其原形,而文献所载实无以知其全也。然其大略,则上有双珩而下垂三道,所不可知者唯蠙珠琚瑀之如何贯缀,如双珩之如何安置耳”。再“返论黄字”:从字形看“,凡此等殷周古文之黄字(按:郭氏所举例如小篆作,金文作、、等形,下同),及从黄之字所从之形(如金文 堇 作、、 等,囏作;甲骨文作堇,囏作、等形),与许慎所说实大相径庭,盖其字并不从田,且亦无炗声之痕迹也。细审其结构,当为象形之文,无形声可说。更参以金文,凡言锡佩者无虑四五十例而均用黄字,毫无例外。然则黄字实古玉佩之象形也,明甚。由字形瞻之,中有环状之物当系佩之体,即双珩之所合成。……上有佩衿以系带,……下则正垂三道,中央所悬之冲牙为磬形,故有若垂四者;省其左右之双璜,故复垂二矣。是故黄即佩玉,自殷代以来所旧有。后假为黄白字,卒至假借义行而本义废,乃造珩若璜以代之,或更假用衡字。后世佩玉之制废,珩璜字义各限于佩玉之一体。又以衡为横之本字,故说为‘佩玉之横’,其失弥远矣”。再征之以传世古玉:吴大澂《古玉图考》载“璜”、“珩”、“佩璜”各四器,但以每片为一器,且多横置之,郭氏认为“实当竖置,合二而成环,两端之孔左右相缀。中央纵横各贯一组而成十字。上系一物以系于带,下则通过中央二孔及尾端二孔合垂三道而系以双璜冲牙,于是‘黄’成矣”。再证以卜辞及金文图形文字,其于古玉之构成尤多所启发,进而构拟“一黄之构想图”,其“于古佩玉之礼节亦示相合无间,佩制之失已二千余年,今所考者虽未敢云全当于事实,然必相去不远。所有待者乃将来地底之发掘与文字上之相印证而已”。最后又从民族学、人类学材料看,“欧洲古代与原始民族之‘布络奇’(brooch佩饰)颇多下作三垂,上呈环形,与黄之古文相似者,此亦有力之副证也”。文章最后讨论了黄、亢的关系[14](P349-374),并在《释亢黄》一文据梅原末治所摄古玉佩照片作了进一步申说[14(]P511-520)。对于郭氏的论断,陈梦家曾于1936年在《黄字新释》中提出质疑,继在1957年3月所撰《盠器考释》中认为“金文名物之‘黄’不是玉器而是衣服的一种”,即带或革带,在1962年重写《释黄》文中基本认可唐兰所提论据[15(]P434-437)。唐兰从五个方面论证黄不是佩玉,“可以是革带,也可以是丝或麻织的带”[16](P86-93)。而孙机先生根据最新出土玉饰材料辩驳了陈、唐诸说而认同黄为“佩玉说”[17(]P124-138),而同样根据出土佩玉材料的孙庆伟先生则更认同陈、唐诸说[18(]P175-184)。然而诸家皆未对黄字构形多做解说,黄与佩玉或革带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郭氏的《释黄》、《释亢黄》无疑将问题研究引向了深入。
(三)车马器。1930年11月所作《毛公鼎之年代》除了正确考订毛公鼎的时代及树立了铜器断代的标准和范例外,郭氏也较为系统地考证了“舆马诸名物”,或申论前说,或辩驳前说,或提出新解,重点考察了“”、“朱”、“虎冟熏裏”“、金甬趞衡”等。对于“”,郭氏引述孙诒让、吴式芬、王国维诸说而“以孙说为是”,认为当“言有若 帱以贲饰之也。故省之则为‘’或‘帱’”。对于“朱”,郭氏首先释“声 读入乱,而与虢字义近,殆假为靼。……靼,柔皮也。即 是鞃,鞃者,轼中也。‘朱虢’或‘朱靼者,盖言轼中以皮鞔之而涂之以朱”字前人释为旂、襡或幭均不确,孙诒让疑为鞎之异文“尚有可商”,而认为“乃 靳之古字,……靳乃为马之胸衣,故古字从衣,象其形上有环以贯驂马之外辔,故从束,斤声也。至鞎与靳,余谓当为一字,均字 之晚出者也。……既知之 为靳,则自是二事,故录与 吴彝分言。其合言之者,盖二物同以‘朱虢’若‘朱’为之也。对于“虎冟熏裏”,郭氏首先考辨了冟与鼏字“字形同意,同从冖声,且同属明纽,则冟与鼏古殆一字。鼏者,盖也,字通作密,又通作幂,幂亦或作幎。孙释冟为冥之说,至此可得以较为妥当之说明,即小篆冥又由冟字而讹变者也。是故‘虎冟’当即‘虎幂’、‘虎幎’,亦即《诗》之‘浅幭’”,而“毛郑释幭释之 说均不足信。通观诸彝铭,凡关于舆马之装置几于应有尽有,惟有一事未审,则舆马之华盖是也。舆盖乃最重观瞻之物,王之所赐不至尽为无盖之车,不应于车上诸名物多所列举,而于舆盖乃无一器提及。余见及此,乃知‘虎冟’之当为舆盖之覆,其上画以虎文,非以虎皮为之也”。对于“金甬趞衡”,郭氏首先驳辨了徐同柏“读甬为釭”说,而认为“金甬”当为“吉阳筩”,“‘吉阳’当即吉祥‘,筩’当即《说文》钟下重文之銿。‘吉阳銿’殆谓銮铃”。郭氏对于“舆马诸名物”的考证,有些的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如“虎冟熏裏”、“金甬”的考证;有些极具启发意义,将相关研究引向了深入[14](P560-581)。
除了上述兵器、服饰、车马器诸名物考证外,郭氏还撰有考证青铜礼乐器的《杂说林钟、句耀、钲、铎》,由考订器物进而考证作器者和时间的《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考证祖妣称谓的《释祖妣》,考证天干地支由来的《释干支》等,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或已成定说,或对于今天的研究仍有启发意义,仍值得我们重视,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名物新证研究中所见旧学与新知
处于古今中外大碰撞的激变的时代潮流中,郭沫若对于新旧有相当的自觉意识,如他对于王国维的看法就明确指出王氏虽“以清代遗臣自居”,在“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但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虽“在中国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1]6-8后者虽不乏意气之词,但可见郭氏善于把握学术发展的主流而能“预流”。①从郭氏名物新证研究中,不仅可见其旧学根底深厚,而且非常善于吸收时代所赋予的“新的科学的观点”。
就旧学而言,郭沫若在1928年流亡日本之前并未做过专门研究,其旧学根底主要由就读家塾、高小和中学堂时期奠定的。未发蒙前从母亲学了不少唐诗,1897-1906年在家塾中“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其间大哥郭橙坞教读段玉裁《群经音韵谱》和《说文部首》。1906年入嘉定高等小学堂,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高足帅平均《今文尚书》讲义是其最喜欢的一门课,“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学’得到了印证,因此特别感觉兴奋”。1907年升入嘉定府中学,感兴趣的仍然是经学,从廖平另一高足黄经华学习《春秋》;1909年暑期在家中曾闭门“读完《史记》及《皇清经解》若干种”,1910年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没有东西可学,只是读写课外的东西。林纾的小说,梁任公的论说文字,接触得比较多。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19](P7-12)。其后留学日本,于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医学部学医,至1923年大学毕业,其间与其后走上文学创作、翻译与研究之路。郭氏虽然喜欢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终因时代潮流的冲击未走上旧学研究之路,但其旧学根基就此打下,为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等打下坚实的基础。郭氏旧学根底在其名物新证中有很好的体现,如前述《说戟》《释干鹵》《释黄》《毛公鼎之年代》等文,皆是在综述传统诸家之说基础上结合新出土材料提出的新观点、新论证。这也是从小受过系统旧学和新学教育的那一代学者的共通之处,然郭氏无疑为其中之佼佼者。
就新知而言,无论是社会变迁还是各种学术思潮,郭沫若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对其所处的时代潮流有着清醒地认知,非常善于利用各种“新的科学的观点”,如在名物新证研究上利用新兴的古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下面就此略作申说。
(一)古文字学。古文字学传统上称为金石学或钟鼎之学,至近代始渐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有学者认为“古文字学这个名词”是由王国维“所手定的”[20(]P5683-5698),也有学者认为1934年唐兰在北大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是其最终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郭沫若身预其流并成为最重要的古文字学家之一,名物新证本身即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内容,自有这方面的鲜明特色,这里仅述其对古文字字形的充分利用。汉字尤其是古文字的特点是象形,虽然宋、清已有学者从字形角度考释文字,如晚清学者孙诒让对偏旁分析法的运用,但充分利用古文字象形特点研究古代名物典制的是王国维。王氏1913年夏间所作《明堂寝庙通考》即“由古器款识中发见古宗庙之制,嗣读《仪礼·丧服传》而悟古燕寝之制亦当如是”,其所利用者即古文墉字金文作“”、“”、“”、“”,甲骨文作“”,省作“”,小篆作“”、“”诸形,“由此观之,则二字所象可知,并知四栋之屋实起于制字 以前,殆为宫室最古之制矣”,惜这部分在收入《观堂集林》时删去[21]。在1929年12月29日致容庚信中,郭沫若提到:“近见《雪堂丛刊》中王国维《明堂考》有甲骨文诸字说,《观堂集林》中所载者已删去,王似已自悟其误,然恐有先入见窜入人心,弟之《释版》中疑(似拟字之误——编者注)即附正此说。”[22(]P39)郭氏所说《释版》后未见发表,但其对于王氏由古文字形悟出古代宫室之制当甚了然于心而有所契焉,此在其名物新证研究中有充分体现,如前述《说戟》《释干鹵》《释黄》等文皆为由古文字形切入者也。
(二)考古学。郭沫若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除了要把先秦的典籍作为资料外,不能不涉历到殷墟卜辞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刻。就这样我就感觉了有关于考古学上的知识的必要”。郭氏选择日本考古学权威滨田耕作所译德国学者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并将它译为中文出版。通过这本书,郭氏受教益很大:“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就的话,也多是本书赐给我的。……最要紧的是它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真是勤勤恳恳地说得非常动人。作者不惜辞句地教人要注重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观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这些方法在本书的叙述上也是很成功地运用着的,本书不啻为这些方法提供出了良好的范本。我受了很大的教益的主要就在这儿”[23(]P1-5)。虽然当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之中,郭氏亦未参与考古发掘或深入考古现场,但其名物新证研究有不少从是从考古学角度入手的,如《说戟》认为“刺”与戟之胡、援、内分离而著于柲端,柲腐则判为二器,故存世者仅见有戈形而无戟形也,后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
(三)人类学。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早在1932年即撰文指出,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九三〇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之一(其余一种不用说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二册)。他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疏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寻找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进程”[24](P215-223)。郭氏人类学知识主要来源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依据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然亦不限于此,如《释干鹵》引用“ThelivingRacesof Mankind”、“CustomsoftheWorld”等书中所载诸后进民族所用盾支持其说。
从我们前面对于郭沫若名物新证研究的简略梳理可见,身处新旧中外大碰撞的激变的时代潮流中,郭氏不仅旧学根底深厚,而且非常善于以其敏锐的眼光把握住学术发展的时代潮流,汲取各种“新兴的科学的观点”,如上述唯物史观、古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融会旧学与新知,作贯通的研究。故郭氏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出成就,而且尤在能“例示”名物新证研究的新途,对于我们今天相关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注释:
①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谈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见陈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叶国良.从名物制度之学看经典诠释[J].(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21期合刊)。
[3]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
[4]青木正儿.名物学序说[A].中华名物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杨小召,侯书勇.罗振玉与古器物学[J].求索,2009(1).
[6]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J].汉学研究,1997,15(2).
[7]李济.古器物学的新基础[J].李济全集第五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罗振玉.《观堂集林》序一[A].王国维遗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9]王国华.《王国维遗书》序三[A].王国维遗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0]侯书勇.“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2).
[11]徐中舒.耒耜考[J].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杨泓.中国古代的戟[J].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四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5]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6]唐兰.毛公鼎‘朱韨、蔥衡、玉环、玉瑹’新解——驳汉人‘蔥珩佩玉’说[J].唐兰先生金文论集[M].北京:紫金城出版社,1995.
[17]孙机.周代的组玉佩.中国古代舆服论丛(增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8]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0]徐中舒.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J].王观堂先生全集·附录[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
[21]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J].1915年发表在罗振玉编校的《雪堂丛刻》第三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5月据“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上虞罗氏排印本影印”。
[22]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23]郭沫若.译者前言[A].美术考古一世纪[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24]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J].素痴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