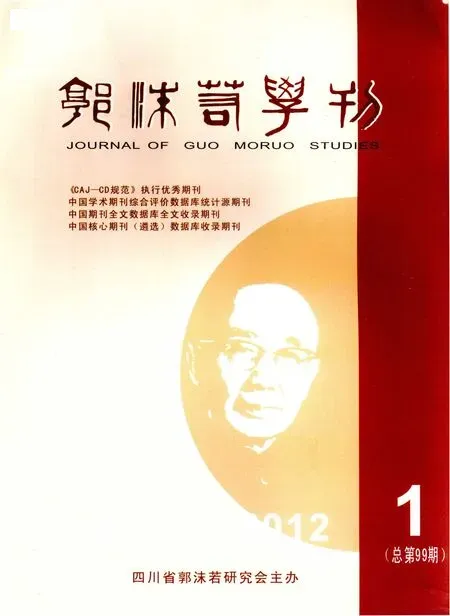郭沫若中后期小说创作模式的演变*
贾剑秋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始于1918年止于1947年。在长达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其小说创作模式的建构历经探索期、转型期和定型期三个阶段。在早期探索阶段,经过杂糅多种中外哲学美学元素、文化精神后,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复合体模式形态。随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日、苏特色的普罗文学后,其小说模式在动态渐变的过程中逐步转型发展,由早期阶段以主观表现和浪漫抒情为主的复合体形态,转向抒情与写实结合而偏于抒情性的“革命浪漫主义”,再进一步走向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结合,最终形成既有激情昂奋的浪漫诗性气质,又具客观写实倾向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模式。
一、个性主义、浪漫主义小说转向后的两种形态
1924年,郭沫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在宜兴之行的社会调查中看到民生凋敝的社情而萌生朦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郭沫若的文学观念开始由表现自我的个性主义反封建转向政治上的反资本主义;艺术主张由追求文学的主观性、纯美性转向强调社会革命中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尽管如此,作者的创作转型并不如他的思想转变那么顺利。1925年至1936年,郭沫若小说创作经历着长期左冲右突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作者在具有日、俄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普罗文学”影响下,努力寻找着小说模式突破的通道,在寻找中艰难地选择、实验或坚持。既有对“私小说”的眷恋不舍,也有对“革命文学”小说的积极倡行。其小说模式开始试着突破个性主义的浪漫主义,而向另两种形态——现实主义和具有左翼特色的“革命文学”进军。
试图转型时郭沫若便陷入理论与创作实践脱节的困境。1924年作者已觉悟到“今日之文艺,是我们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文学的价值是做革命途上的“宣传利器”。[1](P299-300)怎样发挥“宣传利器”的作用呢?就同“为人生派”选择现实主义以利对社会人生起作用一样,郭沫若也有选择具有客观揭露和批判作用的现实主义,而疏远主观性极强的浪漫主义的意愿。因此,1925至1926年其思想转型的表现极为峻急,理论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向现实主义靠拢,尤其是向代表“第四阶级”文学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向靠拢。强力主张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的出现。认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2](P311)尽管他首先选择的是走现实主义路子,然而其创作实践却无法跟上思想理论的步伐。这两年创作的八篇小说,与其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稚拙效仿,不如说大多仍沿袭着以前“私小说”的写实窠臼。除《落叶》延续前期的主观抒情风格,《马克斯进文庙》以主观议论见长外,收入《水平线下》诸篇和《曼陀罗花》《红瓜》等仍然书写作者的生活琐事和悲戚心境,间或能见到以内心独白方式表现出的介入现实的批判态度。创作艺术呈现内与外的书写结合,情与实的刻画交融等特点。所不同的是,小说中主观性的直接抒情或情绪性的大段内心独白大为减少,像《湖心亭》里以排比句形成激烈的情绪气势的表达,在此时类似风格的小说中已较少见,而由对话组织的叙事成分却大大增加,也能见到作者看重写事写人,甚至写性格的企图。如《曼陀罗花》对哈君婴儿由病到死过程的细致描写、对哈君夫人虚荣冷漠和哈君懦弱善良性格的刻画;《湖心亭》对城隍庙景象、看相人的势力、商贩的奸猾等细节的生动描绘;《亭子间中》浓重的氛围渲染与精细的环境描写(虽然描写尚未摆脱诗性的情感特征)等,都凸现郭沫若向现实主义小说转型的努力。诚然,此时郭沫若小说创作转型的姿态还不十分明朗,在一种朦胧的期待与努力中挣扎。作者感慨:“一看好像呈着一个平静的冷淡的面孔,但那心中,那看不见的心中,却有回肠的苦痛”。作者“回肠的苦痛”隐藏在略显平淡、冷寂的现实叙事中,在叙述个人私生活时,添加“对社会的一些清淡的但很痛切的反映。”[3](P403)小说创作意图和叙事策略的些微改变并不意味作者已走上转型通道,“回肠的苦痛”实际包含着这种隐现的内心艰难转型的苦痛。或许,郭沫若此刻还没为转型做好思想上、艺术上的充分准备,还缺乏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积累;也或许,此时的郭沫若身心已沉浸于社会革命大潮,而无暇顾及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深入探索。所以,其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并不表示郭沫若小说创作模式转型成功。事实上,在他宣布诀别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后,并没彻底走上其强力呼唤的现实主义之途,其小说创作艺术和美学风格徘徊于老路,小说模式除增大了写实成分外,仍摆脱不了类“私小说”形态。
另一条路子是尝试“革命文学”小说创作。1926年郭沫若以文学参与革命的态度相当激进,认为“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要彻底根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对于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4](P323)就郭沫若而言,要“彻底反抗”浪漫主义是困难的。既难以割舍长久形成的艺术经验,又想取得创作姿态的突破,最便捷的方法是以集体主义性质的革命浪漫主义替代个人主义性质的浪漫主义,既保留了想象、夸张、激情抒发、主观表达等浪漫主义核心品质,不违逆艺术经验的定式,又能传递有关社会、阶级、革命、集体、暴力等群体政治意识与现实反动意图。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那里郭沫若看到了他所需要的浪漫质素和革命话语。普罗列塔利亚的“革命文学”特点和作用十分切合郭沫若此时此刻的文学革命要求,“它的特性是唯物的,集团的,战斗的,大众的。其次,它是观念形态的艺术,在普罗列塔利亚的解放运动中,它有了很重大的战斗和教养的作用。”[5]因此,“革命文学”这种形态成为郭沫若当时追求的理想的小说模式。“革命文学”小说富有革命和浪漫的气息,尽管当时左翼理论家还未提出“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概念[6],客观上“革命文学”成为郭沫若转向“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的最早尝试。1927年,郭沫若从事了一年多社会革命的“实际工作”后,写了代表其努力转型实绩的“革命文学”成果中篇小说《一只手》。“革命文学”以蒋光慈“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为典范。郭沫若的《一只手》则以“革命加激情说教”成为“革命文学”小说模式的另一种表现。这种模式在华汉、洪灵菲等中国普罗作家笔下有所体现。①《一只手》是郭沫若对“革命文学”小说这种理想模式的实践文本。小说情节围绕工厂的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展开,充满“第四阶级”的革命诉求和社会革命家的政治宣传鼓动色彩。小说中“几千百年来被压伏在胸中的无产阶级怒火”取代了过去小说里的个性主义诗情;革命激情扩张了主观想象的程度,现实因极度夸张的介入而显得虚幻——主人公小孛罗拿着被资本家的机器切下的自己的一只手向压迫者投掷;瞎眼的老孛罗在妻儿死后,点燃了“烧毁一切的”大火,在大火中竟“睁开眼睛”,只见“一片赤光”,火光中“有钱人的天国完全变成地狱了”。除了这类脱离实际的虚幻描写,还充斥着大量激情澎湃的宣传说教。主观政治话语被大量植入后,客观的写实性、批判性成分大大稀释,即使前面几部分有较为充分的对小孛罗生活命运的现实描写和客观叙事,也只是为给后面的政治宣传张本,使后来“克培”(德语:共产党,指中共领导者)的政治说教有所附丽而已。同年,郭沫若还写有《新的五月歌》。因其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已无法见到此作之“革命文学”风貌,但从作者自传《离沪之前》的内容看,《新的五月歌》应是“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尝试。1930年的《骑士》和1936年的《双簧》《宾阳门外》可以视为其“革命文学”小说创作余绪。这几篇小说都有自传性质,《双簧》和《宾阳门外》自传色彩更浓,甚至就是自传的改写。《骑士》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较为明显。尽管小说的现实主义情节的叙事性仍然比较薄弱,但人物形象和言行细节的刻画都采用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技巧。在小说刻画的人物群像中,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马杰民、革命者金佩秋、万超华、白秋烈、章铁士等人既有作者本人及其革命同好的身影,也有当时政治革命家普遍具有的风采。虽然,作者自云“是一九三零年所写”,然而发表却在1937年。显然,此时作者的“革命文学”实践,在文坛“典型论”声浪中,已进入较为规范的现实主义创作之境,可以推断,作者在原初基础上重新作了符合现实主义创作要求的修改。故其内容与30年代初期的“革命文学”一致,而艺术上却疏离了“革命文学”窠臼,更为亲近较为理性的偏重写实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
郭沫若的“革命文学”小说创作不像蒋光慈那样,依靠大量的文本实践,建立起自己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美学体系和独特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事模式。郭沫若的“革命文学”小说创作只是作者参与政治革命时,目标明确地“以文艺作宣传的利器”的尝试,创作目的不在文学本体的使命性,而在革命利用文学的功利性,文学是被动的,革命是主动的。因此,压制小说的艺术精神表达,忽略小说的创作技巧,削减小说的美学意义等,在郭沫若那里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凡是革命文学就是应该受赞美的文学,而凡是反革命的文学便是应该受反对的文学。应该受反对的文学我们可以根本否认它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简捷了当地说它不是文学。”[4](P316)注重政治功利属性放在小说创作的首位。不可否认,郭沫若有关“革命文学”的理论比较单薄、简陋,缺乏特定而清晰的文学规范与美学标准,概括而言,只需做到其一,内容表现革命:替被压迫阶级说话,要反映兵间、民间、工厂间生活;其二,是写实主义的,要反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文学。郭沫若依照这两点原则进行机械地教条地创作,自然无法达到他早期阶段小说的艺术水准,也不能与蒋光慈之“革命+恋爱”式小说一起,在“革命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平分秋色。而且,“革命文学”小说创作仅是他浅尝辄止的实验。1927年后,郭沫若留居日本,生存环境和创作环境已不允许创作“革命文学”小说,其主要精力转向历史文化研究,无法将“革命文学”小说创作按照“革命浪漫主义”小说标准在艺术形式和美学水准上予以完善和提升,故此量少,也未成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30年代创作的《骑士》《双簧》《宾阳门外》等几篇“革命文学”小说,虽忠实了“表现革命”和“写实主义”,仍缺乏必要的艺术形式的表现与主题内涵的提炼,口号、说教及政治话语的阐释将小说本体意义上的模式形态几乎淹没。“革命文学”小说创作对郭沫若而言,是不成功的文学实践,不过,人物的概念化和简陋的小说情节的政治性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先声。
二、“革命浪漫主义”小说模式的建立
经过前面一段时间写实性的类“私小说”和抒情性的“革命文学”小说实践后,郭沫若小说创作有了思想和艺术的积累与发展,促成他在完全摒弃个人主义浪漫主义的同时,努力向具有左翼特色的新的浪漫主义小说模式——即“高尔基所说的第三种东西,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7](P218)靠拢。“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具备了更多现实批判因素,具有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相类的精神追求与创作取向的一种模式形态。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形态构成的重要部分,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8](P108)只是二者艺术表现上有差异。革命浪漫主义富有革命理想(或幻想、空想)色彩和政治激情;革命现实主义则更具客观理性的现实态度。创作于1935-1936年,收入《豕蹄》中的7篇历史题材小说,可以代表郭沫若“革命浪漫主义”小说模式。标志着郭沫若由个性主义浪漫主义向“革命浪漫主义”的成功转型。此时,郭沫若思想上已较为深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念,创作有了明确的转型征象。据其自传记载,1927年尾到1928年出国前,郭沫若曾系统阅读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党对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等理论书籍,以及格列夫《无产阶级的哲学》和中共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日本普罗文学刊物《文艺战线》等左翼文献。留居日本期间,日本的“普罗文学”运动影响颇大,作者自传多次记载购买和阅读日本“普罗文学”刊物之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正值日本历史小说创作之风盛行。②这些理论修行和文学影响,增强了郭沫若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度和分析社会问题的理性深度,也为其提供了历史小说创作可资的思想指导与艺术参照。作者的创作理念已能比较明确地接受和消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长期客观的科学考古和史料整料工作培养的理性作风,也为其历史小说的写实风格铺垫了基础。于是,郭沫若为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审视和批判立场,采用以史料的重新解释讽喻现实的小说创作模式。历史小说蕴含的讽喻精神,被郭沫若视为介入现实的重要手段。小说中的讽喻并非随主观性情的喜好任意发挥的游戏之笔,而有着严肃的思想负载。如作者所言“以讽喻为职志的作品总要有充分的严肃性才能收到讽喻的效果。所谓严肃性也就是要有现实的立场,客观的更具科学的性质”。[9]这批基于现实立场和讽喻目的历史小说,成为郭沫若式“革命浪漫主义”小说模式的成熟之作。之所以称为“革命浪漫主义”之作,在于小说富有想象和激情的浪漫主义躯壳里,汲收了现实主义典型化养料,实现了被左翼文学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模式构造。其小说创作采用的典型化创作原则“不仅熔化了革命浪漫主义原则到自己里面来,而且它也体现了认识或认识方法的全部原则的。”[10](P21)小说在浪漫激情和历史想象中,用典型创造的手段,实现了介入现实的意图。创作中,更有深度和理性的文学寓意替代了以往肤浅的概念化的理论说教;生动形象的写实替代了虚幻浮泛的情绪宣泄;婉曲、象征、夸张手法的运用使悲壮、含蓄、幽默讽刺等美学特征凸现清晰。小说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手法,将历史的想象和虚构与现实批判结合,借历史人物和史实重绘,阐述胸怀政见,借古喻今讽今,寓意深远。创作技法上重视运用浪漫主义的虚构、想象、夸张和现实主义的生动的细节描写,将浪漫主义的情感与现实主义讽喻结合,伴随强烈的情绪宣泄而刻画出一系列新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虽为古人,言行举动却具有现代意义,承载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忧愤、嘲讽、审视的态度。寄托着作为社会革命家的郭沫若,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忧虑,以及明确的现实政治立场。由于这些历史小说较为成功地结合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塑造和典型细节刻画的创作手法,并贯穿着浪漫主义“就感性知识作了理论的概括,然后又加以理想化”[8](P100)的艺术表现和强烈的情绪色彩,而彰显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楚霸王自杀》和《孟夫子出妻》是郭沫若“革命浪漫主义”小说较为典型的样本。其中随处可见激情贯穿下作者审视现实的态度,以及在想象驱遣下细腻写实的典型环境描写和细节刻画:
《楚霸王自杀》写战场景象——雪后皑白的乌江浦岸,人迹鸟影皆无,村落荒败,一派萧疏,长江在太阳清辉下“滔滔地鼓着它血样的水,流着……”溃乱的兵士们“像浪花一样”,涌到江边,停止、洄旋、溃散,人马相杂,散乱于江边,“像潮退后的杂色的海苔和蚌壳”,情景鲜明生动,历历在目。在想象驾驭的写实笔触下,垓下之战的战场景象,人物的动作行为和景象的设置、转换极富镜头感。楚霸王的疑人、送马、与吕马童对话的叙事以及决一死战的勇武,视死如归的神态等细节刻画,交织着作者对楚霸王的批评、叹惜、景仰和赞美等强烈情绪,一代霸王走向穷途末路遭遇的种种败落、凄凉、无奈、悲壮,依靠环境的描写铺衬、气氛的点染烘托而栩栩如生,作者对理想英雄的感性认知与主观评价通过典型创作的方法得以呈现。丰富的史实想象,现实主义典型化手法,浪漫主义文采笔调等综合运用,使历史人物理想化、形象化,达到了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革命浪漫主义艺术境界。
同样,《孟夫子出妻》中,在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立场时,虚构孟夫子可笑可鄙的言行,对当政者给予嘲讽。小说一方面依照典型化手法展示作为一家之主和国家“亚圣”的虚伪做作,对“伪君子”形象予以辛辣嘲讽,影射现实社会的统治者、强权者。另一方面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夸张,勾勒历史人物原型,再以现实主义典型化方法给予历史原型现代性的灵魂再造,历史原型包涵的现实意义构成小说深刻的喜剧性讽喻,因而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美学品质。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典型刻画手法的运用有时已达精纯的地步。比如刻画孟子形象时,采用现实主义精雕细刻的手法,描绘其禁欲练功的行为细节——
把两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鸡要叫的一样,把颈子伸起来向后屈,仰望着天,闭着嘴用鼻孔纳气,有得五秒钟的光景用口吐出又把头复还原位。
当他纳气时,他那瘦削的胸廓从凹陷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数得清楚的。
中国两千年来的精神偶像竟是如此荒唐可笑的干瘪样,这种夸张又不乏精细的刻画将神化的圣贤拉回到现实人世,凸现出强有力的讽刺效果。细节的丰富想象加生动描写,使得浪漫主义的虚构和夸张借助现实主义的技法表现而获得真实深刻的现实审美效应,对历史的重审和解构在现实主义的干预下具备了深刻的现实讽喻意义和批判价值。
《秦始皇将死》《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齐武士比武》诸篇虽有大量的主观性议论和内心独白,客观写实性的细节、环境描写相对较少,但人物形象依靠现实思想表达层面的心理刻画,或对话描写得以呈现。秦始皇的残暴、司马迁的坚贞、贾长沙的的忧愤高洁、齐武士的愚昧斗狠等形象特点仍是生动典型的。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的现实意义体现出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作者干涉现实的态度。郭沫若以历史故事的重新解读和历史人物的浪漫重绘,表达对社会时政问题的客观分析以及对现实执政者的批判嘲讽,其现实主义精神显而易见。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创作思想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立场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模式,成为郭沫若小说模式建构通向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模式的桥梁。
三、“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模式的形成与实践
40年代是郭沫若小说创作模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定型期。这个阶段只有《金刚坡下》《月光下》《波》和《地下的笑声》四篇小说问世,这四篇小说是郭沫若小说创作的收官之作,其小说创作生涯就此画上句号。这几篇小说代表了郭沫若小说模式的最终型态。“革命现实主义”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关的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指称都与“革命”“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有丰富联系。左翼文学观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而革命现实主义就包含着革命的浪漫主义”。[11](P6)因此,“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又常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它与“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有许多重合之处、相类之处。这个概念一方面显示了它来自左翼文学体系的血统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特征,另一方面在文学表现上强调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混融的结构形态。因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与“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并非泾渭分明。在前苏联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系统中,“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与“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常常纠结不清,没有显豁的理论壁障或美学界限。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情况看:“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中强调浪漫主义的手法运用和情感气质的参与,如夸张、想象、虚构以及主观抒情特征,人物和故事追求奇事奇境,空想或幻想成份浓厚,具体细腻的现实描摹不足。“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则以理性的现实主义写实精神为基础,重视发挥现实主义的技法手段,因为与具有浪漫品质的“革命”关联,也与具有理想(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关联,而沾染上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气息。在创作方法上,“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既反映现实,又表现理想”[8](P76),而理想的表现往往贯注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所以笔者认为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艺术表现上主观情绪色彩的浓度、客观写实手法运用的多寡以及理想表现的虚实不同罢了。即“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主观抒情色彩更浓,而客观写实手法的运用不及“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丰富;前者表现的理想主观性、虚幻性更强,而后者反映的理想则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由于二者小说形态的相近性,郭沫若小说创作模式从“革命浪漫主义”发展到“革命现实主义”具备水到渠成之易。
此时,作者身处抗战和战后的国统区,时局紧张动荡,环境尘嚣纷乱。作者面对更多的是现实的苦难而非感性的幻象,虚构和想象已无法满足作者对现实的介入,情绪书写亦无法替代对现实社会的干预。惟有让“革命浪漫主义”深化,到达更具革命力度和批判强度的现实主义之境,方能获得更为强大的介入社会的力量。深化“革命浪漫主义”,是在秉承革命叙事传统前提下,强化现实主义的内容和手段,疏远想象、虚构、夸张等浪漫主义基质。在构建“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模式中,郭沫若将亲近现实题材,注重现实主义叙事作为支撑“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小说刻画的重点是现实苦难的群体实景而非个人主观抽象的情绪。手法运用方面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创作取向有向现实的深度与批判的强度开掘的努力。这四篇小说,反映现实苦难,揭露社会丑陋,针砭人性之恶,刻画现实中富有理想精神的人,使郭沫若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美学意蕴渐显丰满。
从这四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和反映的内容与手法,可以见到郭沫若“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模式走向定型的轨迹。《金刚坡下》和《月光下》作于1941年7月。前者如早期“为人生派”的现实主义小说模式,以提出问题“谁写出了这幕悲剧”开头和结尾,讲述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中三个女人各自的不幸遭遇——逃难、被骗、被抢。后者以主人公家庭贫病交加的生活境况和细节的描写,反映普通贫民在抗战期间的大后方因生活陷于绝境而走向自杀的悲惨现实。两篇小说基本上是对小说人物、事迹持客观实写的态度,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结合,尚未达到左翼文学观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为事”“为人”“有所为”③的高度。从小说实写社会生活的表现看,采用现实生活题材,和旁观者的叙事视角,以及具体可感的细节刻画和客观写实的故事讲述,呈现小说的现实主义风貌。一年后写的《波》,讲述难民船上一段悲愤的插曲——一对年轻夫妻的小婴儿,在逃难的江轮上遭遇日机轰炸时啼哭,被同船难民抛入江中。这篇小说不仅揭示了现实苦难,且有了“有所为”的意识:“我们要报仇”。1947年写的《地下的笑声》则将现实主义小说形态推向“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标线。小说将主人公充满情感的内心独白与第三者叙事结合,写一对归国留学生夫妇,在大后方遭遇的悲剧命运——日本飞机大轰炸致孩子丢失、丈夫炸断了腿又患上肺结核,妻子为救夫被迫“舍身饲虎”“抵押贞操”而染上性病,后又传染给丈夫,最终家破人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笔力并不在于竭力反映客观生活的苦相和内心的强烈忧愤,将小说写成凄凄惨惨的既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提不出鼓舞人心的理想”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是力求做到革命现实主义所需要的“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透过现实,指出理想的远景”。在左翼思想观里,革命与理想相连,革命的终极是实现理想。理想也与乐观相连,乐观基于理想的支撑,乐观就有抵达理想彼岸的希望。“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就是需要以乐观积极的理想主义精神挑战现实,塑造向现实社会挑战富于革命理想的人物。小说主人公贫病交加,陷于绝境,但相信“天上要现彩虹,夜空中要出彗星”。虽然男主人公眼瞎腿残,疾病缠身,内心并没有感到悲戚、孤独,苦痛,一心希望治好病,做个身残志坚的音乐家,谱写出《大隧道群鬼大合唱》,替大轰炸中死去的地下亡灵发出声音来。女主人公舍身救夫,是为了夫妻双双能参加抗日的革命理想。之前,二人怀抱理想在“战地服务队”工作,到了重庆,妻子因参加具有革命色彩的《黄河大合唱》丢了工作。走投无路时,她仍有坚定的理想:即使丈夫没救了,也要“走另外一条更捷近的路——但不是死,而是走向认真抗日、认真做人、没有人吃人的地方。”《地下的笑声》所写的现实极其凄惨、黑暗,主人公的生死挣扎基于他们心存的理想,活下去,有所为,即便死去,也要发出“地下的笑声”“,在地府的深渊里看见光明。”小说以第三者视角叙写夫妻二人的困苦现实,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发生发展,又以主人公的独白传递情绪化的理想。现实与理想的交汇,使人物身上的悲悯色彩淡化,反而彰明反抗现实的坚强精神,逾显理想的坚定崇高。小说不仅达到了左翼文学观要求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为”的高度,而且两位主人公虽然没有被塑造成“既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同时又是现实的人”[8](P105-107)的革命现实主义英雄形象,但二人被写成了精神的强者,不向社会黑暗屈服,不向悲剧命运低头,他们身上洋溢着与黑暗现实抗争的“革命”气息和理想主义的积极乐观精神。郭沫若采用变通处理手法,将他们塑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具有革命实际意义的理想的贫民英雄。
诚然,这几篇小说仍带有诗人气质的情绪发挥,语言运用的主观感性书写仍然存在。《地下的笑声》里“丈夫”的内心独白具有浓厚的主观情绪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会模糊“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模式特征,而与“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的模式难分界标;《月光下》对“逸鸥”心理活动的刻画仍有较重的“私小说”的遗痕。但是,不可否认,郭沫若小说创作模式的建构,在现实主义形态方面是有所发展,并且表现亦较为明晰。上述情绪书写和主观意识的表达生发于现实之境,建立在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理性观照和强烈不满,以及对贫弱者的高度同情基础上,具有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怀意识。小说选取的题材对象具有客观现实性,作品人物生活于当下现实社会,没有夸张和虚幻成分,《地下的笑声》人物所具备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绝无革命浪漫主义超尘拔俗的不平凡气概;第三者的叙事语言和介入他者主观情绪的表达呈现出作品的客观理性态度。而且这几篇小说,已见不到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常见的激情澎湃、气魄昂扬、文采飞动的艺术表达。相反,却清晰地凸现出革命现实主义的“为事”“为人”“有所为”的创作态度,以及对人物、环境、细节的客观写实的描写。限于作者小说艺术技巧的缺憾以及难以摆脱的诗人气质性格的影响,这几篇“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品质和审美度打了折扣。但最后的封笔之作,按照左翼文学“既重现实,又重理想”的标准衡量,已达到了较为稳定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审美峰线,标志着郭沫若小说创作模式的最终形态。
郭沫若小说创作模式,在他决定反叛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后,经历曲折起伏的创作实践,从写实型的类“私小说”转向“革命文学”,以“革命文学”的思想传统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导下,转向“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创作模式,再由此而过渡到现实主义与浪漫理想结合,而偏重客观写实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模式。其动态多变的小说创作模式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照了中国左翼文学思想与小说创作走过的路径,揭示了具有左翼文学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也即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模式形态的形成规律与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特殊的研究价值。郭沫若虽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名家大师,却以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模式的探索成果,为研究中国现代左翼小说留下了可资参考的范本。
注释:
①华汉《马林英》中的主人公与《一只手》中的主人公都有相似的浪漫的革命传奇色彩和激情鼓动暴力革命的说教等表现和描写。这是一种与“革命加恋爱”小说有差异的模式形态。
②当时,日本作家受制于写现代题材,而借历史题材书切身之痛。这类小说以史为背景,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具有讽刺精神。参见张香山《目前的日本历史小说》,《作家》第1卷4号,1936年7月15日。郭沫若的创作情况亦如此。③左翼文学观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应涉及“为事”“为人”“有所为”即:“事”涉多数人命运;“人”是被压迫、被损害者;应提示读者:面对现状,要有所为。参见茅盾《夜读偶记》第5页。
[1]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A].沫若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A].沫若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郭沫若.《水平线下》叙引[A].郭沫若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郭沫若.革命与文学[A].沫若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洪灵菲.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A].文艺讲座第1册[M].神州国光社版,1930-4-10.
[6]瞿秋白.革命的罗曼蒂克[A].地泉[M].上海湖风书局,1932.
[7]陈春明.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8]茅盾.夜读偶记[M].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
[9]郭沫若.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J].质文(第2卷1期),1936-10-10.
[10]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 [A].徐国利,陈飞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4卷)[M].大象出版社,2009.
[11]方维保.当代文学思潮史论[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