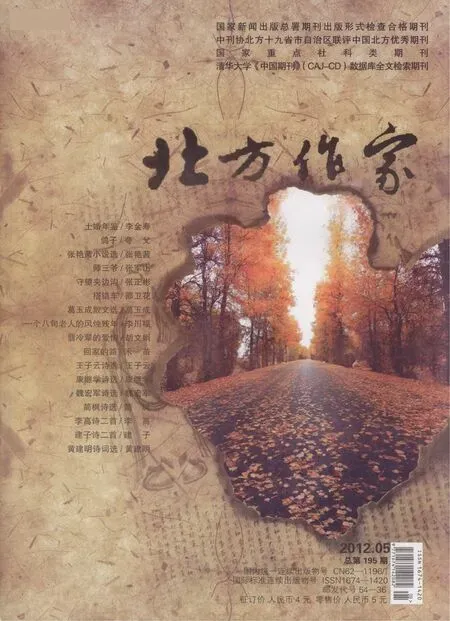师三爷
张军山
1
师三爷死了,就在夜里个两点。
门咣地一声被推开,我爹直戳戳地看着我娘,说完又瞅我一眼。娘手中原本欢实的抹布,停在碗沿上,不动了。
我定定地看看爹,又看看娘,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师三爷跟我爹同岁,老伴儿跟我娘同岁。老伴儿三年前就扔下师三爷,不完美地走了。现在,师三爷又好端端地突然走了,谁都想不通。
我扭过头,目光投向窗外。师三爷就活脱脱在眼前。他静静地依着庄门,坐在门槛上,看不清原色的中山装,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目光呆滞,凝视前方。一支两米多长的皮鞭,直愣愣地穿怀而过,竖在那儿。双手一上一下,紧紧地将鞭杆咬住,仿佛随时等待集合的钟声。
咋死的?突然,我娘脸上满是惊讶地问道。
2
师三爷的离去,到底还是让我觉得多少有些伤感。
要说,村里50户人家,时常会有人离去。或老死,或病死……唯独师三爷的死,让我格外多了些悲悯。除了师三爷曾给过我响亮的一皮鞭外,还有,师三爷的小儿子师娃子跟我是从小学到高中最好的同学。
师三爷家离我家并不远,一个居民点,中间仅隔了四个庄子。那时候我是恨过师三爷的,预谋要将那鞭子偷偷折断,可最终没得逞。原因是师三爷每次收工,都要将鞭子小心地一圈一圈绕好,然后挂在里屋炕沿边墙壁的铁钉上,我根本下不了手。再后来,就把这折鞭的事给淡忘了。再说,我那时是因为师娃子,才被美美地抽了一皮鞭。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师三爷抽我时的表情。我的惨叫声比皮鞭与物体接触后发出的“啾啾”声要高出好多分贝。这皮鞭声之后的惨叫声,到底还是引来很多村民。我终于在人群里瞅见我火急火燎的爹,他大睨着铜铃般的牛眼,用怒火烧着师三爷。我只怯怯地瞄了师三爷一眼,他双手紧紧地攥着鞭子,愣怔在那儿,面对村人的口舌,一声不吭,满脸愧疚。我爹的火烧了半天,最终也没烧开锅。最后只好拽着我回去了。师三爷大张的嘴巴,惊愕的眼神,颤抖的鞭杆,却永远刻到了我的记忆中。
那年,我刚满八岁。师三爷也就四十岁出头。
自此,我耳边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响起那一声鞭响,脆生生的。一想起来,浑身的肌肉就不由自主地收紧,还带着颤抖的。这种感觉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爹才从我倔强的口中,知道了我是替我的好朋友师娃子白白挨了一鞭。爹娘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琢磨了我半天,然后我娘愣是嚷着要找师三爷讨个说法。儿是娘的心头肉。那时我不懂,只是死死拽住娘的衣裳,不让她去。我就看见娘抹抹眼睛,不再吭声。
大概一个星期后,师三爷牵着师娃子到我们家。师三爷的脸笑得像一朵盛开的黑玫瑰,说不该打娃儿,不该打娃儿!说着松开师娃子,抚摸着我的头说,我看看,还疼不疼?我一甩头,挣脱师三爷的抚摸。师三爷手臂就悬在空中,刚刚盛开的玫瑰瞬时发蔫。我娘的脸也变得不好看起来,我爹呵呵地笑着没说话。师三爷旋即又重新笑起来,看着我爹,说,我知道我下手重,娃儿一定受不了。我娘说,事情过了就过了,何必呢。临走时,师三爷还留下了一包白沙糖,算是对我的安慰。我娘说什么也不要,推搡几次,也没塞进师三爷手里。师三爷说,再生分还得抽他一鞭子。我一听,又惊叫一声。大家都笑了。那天晚上,我还偷偷扒开背心,用手摸了摸那条纵贯脊背和腿部,缠绕我很久的青黑色的蛇,还隐隐觉得疼痛。
后来,我也时常能听见师三爷把那根赶马的皮鞭甩得脆响。那声音像是特有方向感,顺着风能独独钻进我耳朵。不顺风,依然能听得真切。每次师三爷出车,都要从我家门前过。三匹高头大马拉一架车,师三爷端坐上面,指挥若定。伴着吆喝,皮鞭高高甩起,轻落马背,发出清脆之声。我的心立刻被揪起,针刺,难以言表。我从不敢正眼看师三爷,总是隔着院门板缝,偷偷张望,大气不敢出一声,生怕他朝我望过来的眼神,霎时变成锐利的皮鞭。直到他潇洒快乐地扬鞭策马绝尘而去,我才半天缓过劲来,出门看尘土飞扬过后安静的马路。
因为师三爷的皮鞭,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敢再经过他家门的。等我再长大些,不怎么怕了,隔三差五去找师娃子玩。但很多次去他家时,隔着关得严严实实的庄门,都能听见师三爷把皮鞭打得啪啪直响。我那时以为师三爷是着了魔,不出车也在屋里练鞭。每每听见鞭响,我就像听见老虎的呼啸声,疯似地往回跑。
师三爷的鞭子成了我心里的一个魔。
3
师三爷的爷爷就是赶马车出身,到师三爷他爹十几岁时,就完完整整地继承了爷爷的那杆皮鞭。等师三爷他爹娶媳妇后,娘生第三个儿子时,大出血。儿子活下来了,娘却死了。活下来的就是师三爷,排行老三,叫师五顺。叫师三爷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师三爷的俩哥哥,老大早年跟爹赶马车,长途送货,路遇匪帮,为保东家货物,与土匪干起来,最后被打死。师三爷他爹抹干眼泪,就让老二跟他学赶车,还没出师,老二得痨病死了。只剩下师三爷了,师三爷他爹就不想让他再赶马车了。苦着拼着也要让他读点书。可后来,社会变了,师三爷他爹就又把这杆皮鞭庄严地交到了师三爷手里。
那些年,师三爷成天赶着马车,可谓是风光无限。等师三爷第一个儿子出生,他突然就生出一个念头,不能让儿子孙子也跟他一样,赶一辈子马车。
1982年,村里的田地分到家家户户。师三爷对马匹和皮车情有独钟,便以熟成地为代价,换取了一辆马车和三匹俊马的所有权。
师三爷赶着马车,算是又风光洒脱了好些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师三爷的马车闲了。看着手扶拖拉机摇摇晃晃地从他面前经过。师三爷就坚信一个道理,赶马车到老是没前程的,只有让三个儿子有知识,走出山村,才是正事。
师三爷一门心思供儿子们上学。为此,还招来村里人讥笑。放着壮劳力不用,上什么学。都说师三爷脑子被鞭抽了。每每这时,师三爷只是呵呵地笑,并不争辩。
师三爷的马车就停在后院。每天天麻麻亮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圈里看马,添草,顺手,走到马车前摸了又摸,瞅了又瞅。偶尔,也会把马车套出来亮亮相。春上撒播,秋上打撵,师三爷还是会风风光光把那歇了好久的皮鞭又甩得啪啪响。上岁数的人见着,远远笑着跟他打招呼,师三爷哎,到底是老把式啊!师三爷则幸福地咧着嘴:不行了!老了!老了啊!然后口里咦地一声,把长长的鞭子甩得高高的,一阵风似的经过。
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每次周末回家,时常会看到师三爷,他看我的眼神没那么锐利了,皮鞭抽在马身上发出的声音也没那么响亮了。但鞭落声起,我心里还是有一股股隐隐作痛的感觉。到底没昔日的惨烈了。
我总觉得师三爷是一个特别神秘的马车夫。神秘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特别喜欢听皮鞭的尖叫声。我从爹娘口中知道,师三爷继承父亲遗业,赶着马车从山南到海北,从白天到黑夜。他不要儿子再赶车了。直到师娃子考上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才知道了这个秘密。原来那时我每次去找他所听到的鞭响,其实不是抽在地上,而是抽在他背上。他的俩哥哥也难逃皮鞭之苦的厄运。不过,兄弟三个都被打进了大学门。师娃子说他从没在皮鞭下惨叫过,每次鞭子落到身上时,他都两手抱头,纠紧身体,咬牙死挨。我从师娃子诉说时绷紧的神情中,还是能隐隐感到他的疼痛的喜悦。终了,他说,谢谢你曾为挡过的那一鞭!我苦涩地笑笑,说实话,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
师娃子给了我一拳,笑笑。我也笑笑。
师娃子考上大学那年,我落榜了。
当师娃子的喜讯传到村里时。我偷听到爹跟娘说的话:还是师三爷鞭法重啊!三个娃儿硬是给打进了大学门!你说我们这……我娘深深地叹了口气,那还是娃争气,不争气的,就是打死也是白的。还能咋办?只有再读一年!
当时,我就很庆幸自己没有师娃子被“鞭策”的经历,否则,我宁愿去赶马车。我再次落榜那年,我问过师娃子,他能挺过来且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说,为了不再被鞭打!
我又笑笑。终于开始由衷地佩服师娃子了。
4
20世纪90年代,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小四轮拖拉机,干起活来噌噌噌,师三爷的马车彻底被淘汰了。他再也没赶着马车干过农活。时间久了,我发现师三爷眼里就多了失意。师三爷望着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突门口经过,开车人得意地坐在黑皮沙发里,胸前抱个圆圆的铁圈,师三爷就呆呆地闻着黑烟味,发愣。愣上好久,愤然起身回到院里,望着墙上的皮鞭,继续发愣。他禁不住走上前,小心地取下皮鞭,端详着,把玩着。
老伴儿瞅半天,唠叨道,望啥望?三个娃回来一趟不容易,赶紧不劈柴去!师三爷一想到在外地工作的三个和尚,心里到底还是涌上了阵阵暖意。
师娃子和他的俩哥哥回来那天,我去了他们家。那是一个四合院,我曾经熟悉后来陌生现在又熟悉的四合院。自从那一鞭之后,我已有好多年没进去过了。是怕那皮鞭再次误响在我背上。这次,我进去,倒是看见墙上挂着的皮鞭,黑黝黝的鞭杆,被手掌磨得光亮光亮的。鞭绳,像一细长的蛇,均匀地缠绕鞭杆上,很好看。我禁不住第一次抚摸了它,到底没曾经的那般可怕了。
这次,是我给了师娃子一拳,笑说,死娃子,到底回来了!外面咋样?因为“师”和“死”在我们方言里发同一个音。所以,小时候我们都管他叫“死娃子”。现在这样叫他,他脸上似乎有了淡淡的不快,但马上还是笑容可掬道,还行!这句还算谦虚的话之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外面的姑娘有多性感……我听得云里雾里,羡慕得要死要活。
那几天,师三爷脸上的笑容就像春天的桃花,开得粉灿灿的。在爹娘眼里,什么是家?儿女们都在,才算是个家。师三爷老伴忙了上顿忙下顿,满是褶皱的脸越发灿烂得跟成熟的核桃。逢人便讲,儿子来时买了好多东西,还有没见过的吃头。杨五爹,闲了到家里偿偿?杨五爹就羡慕得口水直淌。见着我爹,说,老同学,得空到家坐,“狼吃的”带了好多东西,见都没见过,看有好的你也选一样。这话是我爹后来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那天到底“得空”了没有,我爹没说。只是我爹说这句话时,脸上多少沾了点羡慕之情的。
我后来得知,师三爷的三个儿子走时,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养活那畜牧干嘛?于是做主把师三爷圈里养得膘肥体壮的三匹马卖肉贩子了。
师三爷三天嘴里没进一粒米没进一滴水。
5
23岁那年,我结婚了。
我娘说,师娃子也结了,媳妇长得还真是好看,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脸蛋上都能滴水。娘艳羡的表情显而易见。我嗯了一声,躲过娘的眼神,没再多问。因为我媳妇的长相,不是那种打着灯笼难找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那种。我娘对我媳妇的长相是心有耿介的。我倒是每次看见漂亮女人,常常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我结婚后,打拼几年,生活基本稳定,在城里买下三室两厅楼房。我没想到的是,媳妇告诉我,她打算让爹娘搬来一起住。她说,爹娘一辈子不容易,都快六十的人了,也该享享福了。再说,有了小孩,总觉得只有跟爹娘儿子住一起,家才完整,温馨。我被媳妇的话感动了,举双手赞成。可这样想法,一提出来就被我爹折衷,冬天城里住,夏天还种他那一亩三分地。
我看着媳妇,媳妇说,老人有老人的想法,我们得尊重。他们一辈子根深蒂因的生活方式,一旦突然被打破,也许对他们来说,现在幸福日子比过去困难的日子更乏味,在城里比在农村更痛苦。你说呢?
我笑笑,吻了媳妇一口。
于是,每年冬天第一场雪悄然而下的时候,爹娘也回到了城里的家。整个冬天,媳妇把爹娘伺候得服服帖帖,我爹枯瘦黝黑的脸,也在每年春天回村时,长一圈肉,白很多。
每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都要隔三差五回村里看爹娘。每回去,我都一定要去看看师三爷。好几次,我看到师三爷坐在门槛上,怀里搂着那根皮鞭,目光呆滞。门前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过往的车辆络绎不绝。最多的是摩托车,还有大小不同的拖拉机,偶也有小轿车我走过去,问,师大伯好!他缓缓地抬起头,啊半天,然后看着我,木然地笑笑,回道,好好好!然后照旧朝着马路上愣神。我便越过师三爷头顶,朝院里瞅。空荡荡的院子,显得格外空旷寂寥。这时,师娃子他娘便端着一只盛满开水泡馍的大搪瓷碗走了过来。她弓着近乎90度的腰,走到我跟前,使劲抬了抬头,才对着我勉强笑笑,问,望你爹娘来啦?我点点头,哎了一声。她把开水泡馍递给师三爷便转身又佝偻着腰走了。我听见师娃子他娘自言自语道,他们什么时候也能回家来就好哩!我还清楚地看到她后背高高的驼起,像一座小小的山包。我又看了一眼师三爷,他正大嘴大嘴吃着开水泡馍,完全无视我的存在。
我问娘,师娃子回来过没有?娘说,没见回来。我才想起,我还从来没见过师娃子媳妇长啥样。我娘告诉我,三个媳妇也都是结婚时来过一回,再没闪过面。
6
两个星期后,我们一家三口再次回到村里。一进屋,娘就凄凉对我说,师娃子他娘死了!我一惊,自言自语道,上次回来我看还挺好,怎么这么快就……
我娘说,喝农药死的。
啊?喝农药死了?我近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爹沉着脸说,老了老了,脾性一点都没改,咋非要走这条路呢?多给娃们丢脸!
我娘这才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师娃子娘的死。
我娘说,师家三个儿媳妇,一个比一个出脱,一个比一个扒家。这不,师娃子娘得了哮喘,三个儿媳妇整整讨论了一个月。焦点是,谁接去治疗。北京的大媳妇说,老三离家最近,由他们负责接诊,相对方便些;三媳妇听了,就把电话打给老二,说,成都气候温润,适宜治疗这种病,相对科学合理些;二媳妇则把电话又打给了老大,说,你们住皇城根下,医疗技术发达,是最优方案。理论了半天,老娘已经喘得要死要活了,也最终没得出个结论。说话一个月过去,大儿子实在过意不去了,也没跟媳妇商量,跟俩弟弟商量后,偷偷把娘弄到了北京,心想生米煮成熟饭了,媳妇不行也得行。
师娃子他娘到北京没住上半月,就回来了。村里人都羡慕地问,大城市灯红酒绿的,咋不住了?师娃子娘苦涩地笑道,住不惯,还是家里好!说完偷偷抹把眼睛。
回来哮喘倒是好多了,饭量却减了一大半,精神头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于是,整天跟师三爷并排坐在门槛上发呆。这不,发了没多久呆,昨天半夜里,就喝了一瓶农药。据说,喝药前还净了身,把寿衣都穿好了。
我娘又说,两天前我还跟师娃子他娘暄过。师娃子娘说自己心里寒得慌,咋都想不通,说着说着眼睛里就水汪得满满的。师娃子娘到死也没说想不通的到底是啥。还是后来我爹从师三爷口里知道,说师娃子娘在北京,大儿媳跟师娃子她娘说了狠话。多狠的话,师娃子娘没说,师三爷也没说。
师娃子娘一死。诺大的院里就只剩师三爷一个人。我再次回到村里时,就再没看到门槛上呆坐着的师三爷了。我娘告诉我,自从师娃子娘走后,师三爷天天做噩梦,害怕得不得了,就把电话打给儿子们。三个儿子儿媳妇全回来了,把庄子和地全卖了,21万,刚好,一家七万,分走了。没房没地,师三爷老泪纵横地跟着师娃子去了省城。
听说再也不回来了。
我欣慰地跟爹娘说,这样还好些!师娃子还算是个孝子,我那一皮鞭没白替他挨。
7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在村里见到过师三爷。每次回去看爹娘,晚饭后出来在居民点转悠,经过师三爷家门口时,我还会顺着挂着铁锁的门板逢往里瞅瞅,赫然看到上房墙上挂着的皮鞭,还依然沉睡在那里。我知道师三爷可能因为城市舒适的生活,早已把钟情一生的皮鞋忘到了脑后。
我转身,笑笑,忘了也罢!
我疑惑地问爹娘,庄子卖了,咋锁着?娘说,庄子就是六娃子买去了,他全全是为那几十亩熟成地。我点点头。六娃子、师娃子和我都是小学初中同班同学,关系最好。只是六娃子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回家种地。后来娶了个媳妇,脸上的褶子比六娃子他娘还多,还深。不过,六娃子一家三口是和他爹娘吃住在一块儿,日子过得蛮消停,蛮融洽的。前几年,土地成金蛋蛋,六娃子也挣了不少钱,就想再多种些地,过好日子。恰好师娃子三兄弟要卖庄子和地,他就买了。
今年春天,我又去看爹娘。经过师三爷门口时,着实让我吃了一大惊。
师三爷突然又回来了!仍跟多年前一样,搂着皮鞭,坐在门槛上,与多年前最大的不同是,现在连那呆滞的目光都没了,像一具泥塑,直椤椤塑在门槛上。对于我的到来,他似乎全没有察觉。我喊了一声师大伯,许久,他才缓缓睁了睁眼,下意识握了握鞭杆,朝四周瞅,像是在寻找声音发出的地方,最后才把目光软弱无力地落我身上,皱了半天眉,道:你是?
我怔了半天,心想,师三爷可能真的老了,竟连我都不认得了。我大声地告诉他我是谁谁谁。他转过脸去,拧起眉头,像是着实在想。想了半天,从表情看,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然后又定定地看着我,淡淡地笑笑,哦了一声,答非所问道,还是自已家好啊!
师三爷这句话,彻底把我搞懵了。我顿时觉得师三爷神经出了问题。我再跟他说话时,他就不再答理我,闭着眼睛,自说自话。我回到家,一问娘,才知道,师三爷离开村子的这三年,过得不容易。
师娃子媳妇是奔着老大老二给的数量可观的生活费,才同意把师三爷接去的。师三爷去后,一下子打破了三口之家往日的宁静。一开始她嫌师三爷是车夫,身上脏,给师三爷规定了几个不准:一不准师三爷坐家里的沙发,二不准师三爷用家里其他人的碗筷,三不准师三爷乱动冰箱里的东西……慢慢地,这“不准”的条约数目却与日俱增。不准师三爷用卫生间的马桶……这样,师三爷每天就只好去小区外面的公共厕所解决内急。之后,又借口师三爷身上散发着刺鼻呛人的味道,不准师三爷擅自打开自己卧室的门。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师三爷赶了一辈子马车,走南闯北,啥理不懂。老了,身懒了,气味重了,不能跟年轻人计较。于是就整天关着卧室门,不让臭气冲出去熏孙子儿媳妇。没多久,师娃子媳妇就给师三爷重新置办了一套锅碗瓢盆,借口人老了跟年轻人吃不到一块,让师三爷自己动手,缝衣足食。当然还有个基本条件,每天在她做饭之前,必须把他用过的家什全部收拾妥当,放回自己的卧室去。而且最好是,她出现在家里的时候,师三爷最好不要出现在家里。
这下,师娃子就觉得媳妇的要求有些过了。嬉皮笑脸地跟媳妇商量,不料媳妇给了师娃子一句:你觉得我不好,那我走,你跟你爹去过吧!
这话一出,师娃子就变哑巴了,该咋地还得咋地。
这样,师三爷的生物钟就得调了。调生物钟师三爷不怕,早年他赶马车,起五更睡半夜,白天睡觉,夜里赶路的事常有,这点怕啥。于是,每天早上七点以前,师三爷摸黑起来,轻手轻脚用自己的碗筷家什,吃了开水泡馍或烧了苞谷面糊糊,三下五除二收拾完毕就下楼到外面溜达去了,不管刮风下雨,硬是挺着。中午赶在十二点前就匆匆吃过,再到外面溜达,等两点半媳妇去上班了,赶紧回来眯一会儿觉,起来抓紧吃了饭,赶在六点儿媳妇下班前下楼,直到十二点儿子媳妇睡了,师三爷才蹑手蹑脚地回来。有时候,怕打扰儿子和媳妇亲热,就干脆在小区的长椅上凑合一晚上。
8
三年,整整三年啊!
师三爷就是这样过来的。这三年里,师三爷是想过回村里去的。他常常想起当年赶着马车风餐露宿的日子,就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吃不了的苦。每当师三爷回忆过去的时候,也就特别想回自己一把一把刨出来的家。可一想庄子和地都已经卖人了,他哪里还有家。又一想,自已都古来稀的人了,也活不了几年了,死了就了了,谁都了了。只好凑合着活。
有两件事发生之后,师三爷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他不想凑合了。不知咋了,师三爷后来半夜突然起夜次数越来越多,尿频尿急!因师娃子媳妇规定他不能使用卫生间,所以一直在床下面放着一夜壶解决问题。这天夜里,儿媳妇和儿子亲热,正到好处,不知咋地,夜壶没拿稳,咣当一声,就重重地砸到地板砖上。师三爷握了一辈子皮鞭的手,不应该出现这种失误,可就是出现了。小两口正在翻云覆雨,这突然一声巨响,就把小两口吓萎了。师娃子朝爹的屋怒视一眼,没说什么。可师娃子媳妇却怒了,只套了个裤头,冲出房门就是一通河东狮吼。究竟骂的是什么,到现在我娘也没跟我提起过。可能师三爷压根就没跟我娘说,或许说了,是因为话太难听,我娘不愿当着我们的面说罢了。反正听说是,当时,三媳妇发了疯,不依不饶,师娃子都给媳妇下了跪。按娘的话说,师娃子媳妇骂的那话,把师三爷前三辈子后五辈子都骂周全了。
那天晚上,师娃子狠狠地给了媳妇一记耳光。
师三爷反倒是狠狠地收拾了师娃子一顿。师三爷说,媳妇是客,忍得,骂不得。
师三爷是忍了。
第二件事发生后,师三爷就再也忍不住了。自从那天恶骂之后,三媳妇在条约里又新增了一条:不准老公儿子进师三爷的房间!
师三爷等三媳妇将条约宣布完毕,就把眼睛睁得跟铜铃一般大,只是一句话都没说。显然,那敢情自己连儿子孙子面都见不着了。早上,孙子还睡,师三爷就出去了;中午,孙子刚放学,师三爷又出去了;晚上,师三爷回来时,孙子早就睡着了。但师三爷还是觉得儿媳妇兴许只是说说罢了。没料,三媳妇说到做到。
他可以忍受任何别的侮辱,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见不到孙子。师三爷这才是发火了,朝着师娃子发了大火了。如果手里有皮鞭,师三爷绝对会抽得啪啪响。他朝屋子四周瞅了瞅,没瞅见皮鞭,就钻进自己的屋里,一直再没出来。
第二天,三媳妇走了,师三爷也走了。
9
师三爷就这样又回到了村里。好在,买走师三爷庄子的六娃子小两口接纳了师三爷。六娃子的丑媳妇每天都要给师三爷端一碗饭送过去,看着师三爷大嘴大嘴吃着,觉得师三爷怪可怜的,自言自语道,谁都会有老的这一天,做儿女的也真是!
这句话,六娃子的丑媳妇本是说给自己听的,却被师三爷听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师三爷眼里就汪满了水,然后掉进了饭碗里,溅起了汤花。
第二天早上,放羊的张四爷看见师三爷搂着皮鞭,躺在师三娘的坟头,身旁撂着一只空农药瓶。
这年,我三十八岁。师三爷也就七十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