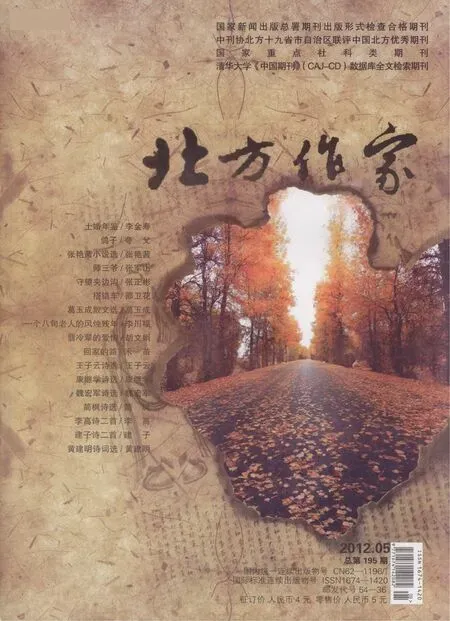一个八旬老人的风烛残年
李川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大西北一个边远的村庄里,一位叫农月根年过八十二岁的老奶奶与世长辞。村里的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含泪为她送行。
第一章巧秀女有了婆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月根老人只有十六、七岁,正是姑娘家鲜花盛开般得年华,她美丽、端庄、朴实,温柔、沉静、落落大方。她长着一双大眼秀眉,一口洁白的牙齿,丰满的圆脸总是充满了笑容,一头蓬松乌黑的头发闪闪发亮,多数时间是盘在后脑勺上。虽个头不超出一米五六,但不管是用土布做的大襟衫,还是用洋布做的衣服、裤子,穿出去都是合体干练,让人看着顺眼。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她把脚给裹小了,解放了又放大了。那双半货脚的鞋头子总有她绣的花,很引人注目。裹脚的那些年里,她那两只裤腿时时用布带扎着。她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让人能看出她心中的快乐和对生活的急切。她是个巧手的女子,巧到上炕的针线活缝衣绣花难不住,下地的茶饭花样,谁吃了谁称赞,村里那些档次高些的人家娶媳妇,老人过寿总是请她去缝衣做针线,过年时候也是请她去做饭菜,村里人常把她叫大匠人。有一天,这个漂亮、聪明、精明强干的黄花闺女嫁到了这偏远的小村庄。
她找的老公欧志平也不逊色。他和谁都能和得来,啥时见了人都是满脸堆着笑,即使遇到烦心事,火从肚子里冒,也是到嗓子眼边咽下去,舒展着眉,嘴一咧不把它当一回事;他待人总是那么宽厚,村里人没一个人说他坏话,都把他叫和事佬。虽然中等个,气质却是很好,黑油油的头发像在发光,圆脸庞,一对大环眼睛,一口小羊牙,洁白整齐;他的脸色什么时候都是红润的,走起路来胸脯挺得直直的,在小村庄称得上是个美男子。
农月根婚后生了三个姑娘,因家境贫寒,大女儿湘楠自小就给人当了童养媳,二女儿叶楠很小就抱给了别人抚养,小女儿惠楠年纪虽小,但性格外向,脸色白里透红,颧骨两块显得红润,暗带着风情月意,眼睛不大但很有神,蒜头鼻子长到这瓜子脸上虽差了点,可被乌黑的又浓又长的头发一装扮便也是一点显不出不好;两个长辫子很喜人,看上去也是一个精灵、畅快、很有心机的女孩子。一小点年纪,家中把她当成唯一依靠的对象,啥都依着她,即使做错了事,也是没一个人去指责她,成了两位老人的精神寄托和希望。他们不明白,咋就没生出一个儿子。
第二章 取婿养子,为女成家
日复一日这个家正常往前走着,几十年竟是一晃就过去。但老俩口心里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空虚。平日里和兄弟亲朋甚至是陌生人聊天,每说到儿子的问题,便是自觉低了人一等。为了他们的晚年,周围有些好心人也给他们出过不少的点子,自己也不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思来想去,总是拿不定主意。
正在为此发愁找不到头绪的时候,有人上门提亲让他们将本村的一个叫伊飞峰的小伙子招为门婿。对此,虽是觉得好但老俩口却是举棋不定。其时惠楠十五岁,那要招的女婿,却是比她大九岁,还带着前房留下的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孩子。两位老人是觉得还有考虑的余地,可姑娘却是婉言谢绝,并整天闷闷不乐。有时独身倒在炕上,用被子抱住头沉思烦闷,时或以沉默寡言与老人斗斗气。也是啊,一个黄花闺女还没出嫁就带个孩子,小伙岁数又大,长得老气,真也是无法面对朋友和同龄人。怎么办啊?
最终,小伙子伊飞峰被介绍人带到姑娘家,农月根两口子老人是真心细心地打量着这个陌生人。带来的人虽然穿着补缀过的一套粗布衣服,然而收拾的干净整齐,长相很标致,从他穿的那件紧身单衫就能看出他肌肉的发达,肩膀和两臂棱棱突起,增加了强悍气魄,那张长条脸上,浓眉下面闪动着一双又大又重精明过人的眼睛。特别在说话时,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目,整体看上去是一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后生,七岁父亲被抓了兵,母亲改嫁,他给地主放牛。打草,没进过学堂,但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农田地的活没一样不会。两口子从心底里喜欢上了小伙子,再也顾不上与女儿磨三缠四,就做主成了这门亲事。
从此农月根两口子踏实了,诚心实意地待女婿爷俩,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孙。这般,算是老少有了归宿。可姑娘的愿望却是就此而破灭,这为这个家庭留下了阴影。
解放了,人变了,地变了,家里面的桌櫈全换了。咱穷人彻底翻身了,成了土地的主人,全家人都高兴。一门心思在田地里耕耘,庄稼也是连年丰收。更令人高兴的是抗美援朝打响了,也是政府第一次在这边远村庄征兵,女婿报名参军,被批准了,县乡工作组的干部带着全村组织好的能扭会跳的青年人,敲锣打鼓来家送喜报,院子里站满了人,连门前地里也是人挤着人。农月根两口子合不拢嘴,眼睛笑得都成了一条缝,心想活了半辈子人也没见这么热闹过,又是今天是在自家的门口。
全家人在喜忧中送走了女婿,光荣和自豪感倍增,可忧愁也没因高兴而放弃对他们的折磨。那几天,两口子比往日起得更早了,起床一会到地里瞅瞅,一会看看圈里的牲口,一会又发呆似站北墙拐上一直向远处张望,一会又高兴得说长道短谈古论今,一会又觉得屋子里空荡荡的少了些什么。可四年中连连不断的立功喜报给当地政府敲锣打鼓送上门,一家人常悬着的心也就踏实多了。地方党组织也把培养军人家属的事列入了议事日程,姑娘惠楠今天参加县里的培训班,明天又去到区乡开会,又被组织吸收为中共党员。四年之后,女婿伊飞峰光荣还乡,不久就去担任了公社信用社主任。一连串的高兴事,使满面红光已开始变老的农月根两口子时常脸上露出笑容,逢人就谈抗美援朝的战事,见人就说姑娘女婿的精明能干,看上去那股高兴劲儿和小孩子差不多。
一九五八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北风凄凄,黄叶坠落,只有五十三岁的农月根的丈夫欧志平因病突然去世了。如泣如诉的鸣咽声仿佛要撕裂了人的胸膛。几天过度的悲伤农月根面容憔悴不堪,她满面愁容,双目失神。她的泪水流干了,心也像碎了。可贤婿为报答岳父宠爱之恩,走遍十里八乡买到了沙枣木为岳父做好了一口寿材。过去这里的老百姓只是听人炫耀那些有钱人家讲排场孝顺父母的人才能为老人做这样的寿材,但从来没见过。这是一件不仅震惊当地老百姓的事儿,也为农月根老人减轻了一份悲伤,增加了一份安慰。但是,最终沉重的沙枣木寿材却是不仅没有完全抬走农月根老人的痛苦悲伤,倒使农月根婶增加了几份对生活的忧愁。
第三章忘记悲痛,一切为这个家
欧志平的简单葬礼结束后,农月根是长沉缅进了对往事的回忆和往后生活的忧虑当中。这个她和丈夫费尽心血经营了几十年的家,虽说一个走了,但这个家必竟还上有老下有小总共六口。这样,不久,已是年过半辈的农月根开始打起精神,努力用新鲜事和眼前孩子的兴奋、顽皮、一点一滴忘却自己心中的痛苦,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对生活报以无限希望,开始抬着大框和青年人一样奔跑在大集体的田野上了。
“大跃进”前后在“共产主义”深入人心的时候,农月根婶就没一个固定的家,今天搬这个队,过几天又搬另一个队。青壮年劳动力全部上炼钢铁的工地,或到青年突击队,干最累最有突击性的农活,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小学生娃娃。农月根大婶白天上班为队里的生产干完太阳干月亮,晚上加班加点为一家人的穿戴熬通宵,还没完全进入冬天,大人小孩的棉衣棉裤,鞋袜已全部准备就绪。发给的布票不够用,就够用也没钱去买,她就用以新换旧,以大换小的办法,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把大人的改给大娃娃穿,大娃娃的改给小娃娃穿,补丁一个落一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困难时期。尤其是烧柴及粮食副食都不富裕,常在家做饭的人便是更难以安排了,已由大婶变成了大奶的农月根奶白天拼命干着不起眼的家务活,晚上躺倒在炕上却总是惦记着明天,待到把明天全家人吃喝拉撒想清楚了,她也睡着了。她凭着她的一双灵巧勤快的手把这些处理的妥妥贴贴。过去的冬天,因为条件差,大人小孩只穿着一件棉衣,棉裤,没有衬裤衬衣一说,房子除仅有的热炕,没有煤生炉子,房子犹如冰窖,冷得从被子里伸不出手。而农月根奶,每天早晨在别人起床前,她便将已准备好的从滩上打来的母珠头花儿柴放在火盆中起床前点着,分别把大人小孩的衣服给烤热,把一片火热的心送到了全家每个人的心坎上。这样儿的日子,杂粮多细粮少,甚至全家粮食短缺,早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小孩上学拿什么,连鸡食、猪料农月根奶都有详尽安排停当。因了这样,即使六0年非常时期甚至是家中人口增加到九口时,全家人也是没断过顿。
一九六0年春天,女婿伊飞峰去地委党校在一个县里办的分校集训。每月口粮二十斤过点,可女婿的饭量重,又没有副食,干的活还累,农月根奶怕把女婿饿倒了,心痛得老放不下,便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从家里人身上扣出点来,用大食堂打给照顾孩子的口粮,每天省一点,省下的面炒成炒面带去,让他接济。大半年过后,女婿从党校回来,还是见饿的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农月根奶看见女婿皮包骨头的样子心酸了。
六0年生活非常时期,学生的口粮都随着学生由学校供应。孙子在公社学校上学,离家十几里,而每天口粮却是低到二两五,每到星期六放假回到家总是嚎啕大哭。农月根奶心软了,孩子大哭她小哭。她就想,我们怎么吃苦,那怕是让饿死了,也决不能让孩子们受罪。这样,从此她把大食堂发给大人的用谷糠和母株头籽做的代食品每天省一个,星期天上学的时候,备作这一星期孩子口粮的补充。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人、孩子吃进去的代食品过多,吃下去排泄不了,一个个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大声嚎叫,她就拿着棍子一个个从后边掏,有时因凝成的硬块太坚硬,掏出来的时候肛门上鲜血都流了出来。
上个世纪,农村人畜饮水不分,家家放着一个能盛两铁桶水的大木桶。农月根奶所在的村子,距有水的涝池有近二百米,用水,仅人饮水一天就得抬三次。家里无论是谁去抬水,都少不了月根奶,她总想着就是她累出个什么毛病,也不能让孩子们和她一样。最早出嫁的大女儿湘楠看望她的时候,见她这么忙,怕把她累倒,总劝她不要这样拼死拼活地干。农月根奶总是说:你妹妹惠楠常在外忙公家的事,孩子们都小,我不干谁干。没事,我还能行。湘楠也看到这个现实,就无话再说。
过去,农村缺医少药,不少人有病不能医,也没钱医。这般的,家里大人小孩只要是谁有了病,月根奶就心急如焚,总是跑远跑近,用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单方偏方给治,连小孩子癫疯都用偏方治愈了。
农月根奶爱生活,爱她的家,爱家里所有的人,疼女婿,疼孙子,疼孙女,但最疼的还是她的排行末尾的姑娘惠楠。惠楠共生六个孩子,每到生产的前一月月根奶就开始做准备,鸡呀、蛋哪、米啊,只要是能找到的她都给准备齐,六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去医院接生,都由她亲自接生,亲自伺候保大人孩子安全出月,出月后三个月之内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干,全由她一人包揽。家里副食紧张,她便老操心鸡下不了蛋,下蛋后就悄悄存起来,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让孩子们拿去供销社换灯油和笔墨。她常是公开地或背过其它家人给这个女儿每天打两个荷包蛋。粗粮多的时候,一笼馍馍中有玉米面的,有细白面的,她宁肯自己和其它人不吃细白面的,也要这儿藏儿,藏起来给这个女儿惠楠留着,甚至关心到姑娘每月来例假,在炕头睡三天,她端着碗送三天的饭。
农月根奶对女儿孩子们充满了她心中的爱,家中发生任何变故,她都是每天晚上拖着沉重的腿子上炕,早晨用支撑她身子的半货小脚精精神神,下地干活。她有子宫下垂和腰腿病的重症,很严重的时候,她只能是在晚上上炕后啊呀啊呀地偷偷哼哼,从没喊谁给她买过一片药让她吃。两个胯骨上压出的老茧,出血破了让孩子们给她用剪刀修一下。有时候,这般的病魔折磨得她连行走也困难。她实在无法忍受时,顶多比往常迟起一会床,天亮了依旧不停地料理家里的一切。否则,上地干活的,下队开会的,放学回来的肚子里没进的,书包里没背的。就这样忍痛受累,含辛茹苦,心里总盼望着想着有一天孩子们长大她就可以轻松些了。这一家八九口人无论大人、孩子的身上沾满了老人的汗水、泪水,为了这个家她操碎了心,累坏了身子骨。然而,现实只能是孩子大一个往外走一个,每往外走一个都揪住她的心,很长一段缓不过劲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月根奶竟是就到古稀之年,成了农月根老奶奶。个头变小了,从侧面看上去已有些驼背,脸如枯萎菜叶子,布满了皱纹,一个个的老年斑清晰可见,两只眼睛凹陷下去,头发变得花白。行动无可挽回地变迟缓了,走路慢腾腾的,显得笨拙,行步虚怯怯,四十多岁时满口的牙就全掉光了,从来没说要修补修补。这会儿,多年的整日忙累,她瘦如干柴了,颧骨上翘,脸下面的下巴颏往上钩起。好在有个过得去的胃,一般不和她找麻烦,软硬多少只要能下去都把它给搞烂了,饭量依旧如故。
第四章 长夜难明
几十年的光阴从农月根老人身上流过去,到今天,美丽、壮实的肌体已经衰残,内心支撑她的力量也跟着变软的躯体一起衰老。已记不清是从何时起,她脸上失去了笑容,皱纹一天比一天深,与孤独、寂寞、苦难相伴,直到在这个世界上消逝。在她的命运中,那些后来的意料不到的事情后,接二连三的出现。凶险的门一旦打开,令人吃惊的事就会一起冲进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农月根老奶奶满怀着忧虑悲伤从冬天烧炉子做饭的房子里搬出来开始与女儿惠楠和孩子们分居,搬进了一套里套外的三间房的外面两间。这房子进门就是一个早已被淘汰了的解放时从地主家分来的破旧长琴桌,琴桌前面放一张与此配套的方桌,东北角是一个能睡四五个人的土炕,炕南边靠窗是一个空旷的走道,炕上铺着一个竹蓆子,上面又铺着一块已铺过多年的毛毡,已经盖过多年的这床被子棉絮都疙疙瘩瘩的,迎着太阳就能从被子上看见一块块的亮点。房间没有任何照明设备,也没任何洗刷工具,空荡荡的,无法感觉到是有人住着。平常这间也没人进出的屋子,从此便只有农月根奶与孤独、寂寞、苦难相伴,一个人孤零零守着了。夏天还可以凑合,冬天外面刮大风,房子里刮小风,犹如冰窖,漫长的夜晚冻得她缩做一团,头戴的那黑平绒帽子从没有取下来过。她度日如年,在这屋里度过了近十个冬天。她伤心地痛哭流涕,彻夜不眠。她没法理解,她是犯了什么天罪,辛辛苦苦一辈子竟然是落了这么个下场。老天爷就这么不公平!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等待更残酷的命运到来。
不知什么时候,农月根老奶奶头上给戴了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不能随意去女儿惠楠的卧室,因冬天这屋生火炉,来人接待全在这屋,怕丢她们的人。农月根老奶奶穿的棉袄是有一年孙媳妇为她做的老衣,后来没衣服穿就先穿上了。这么地,几年过去,大襟衣服的前面和两只袖子全是黝黑了。不来客人进去嫌她又脏又臭,惠楠会看不顺眼瞪大白眼指责她。有一天,天气冷得说话都能在眼前看到口里出来的白气,家里来了一很久没上门的亲戚,尽管在门口已听见熟悉的声音,她没敢马上进去,正在迟疑,那位亲戚隔门看见了她,就出门亲手把她扶进门去。老人心里不踏实,就给客人说了实话:“人家不让我进来。”客人还在,惠楠瞪大了眼睛,用白眼翻着她。客人走后,她就受到了一顿责骂。她不敢反驳,怕会有更“好”的待遇。
刚离开女儿惠楠卧室另居时,每天的两顿饭有孙女儿叫她进到惠楠屋里自己端碗,吃完饭就出门;到后来,看她油头垢面,她只能站在门口,等大人或小孩把饭盛好之后送到门口递她让她端走,吃完后把碗送到门口重由大人或小孩接进去,且每顿不论干稀,只给多半碗。这种急转直下的待遇实在让月根奶奶伤心,也让她无法接受。每当夜幕降临,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后,胃里面空荡荡的,就像吃了草一样难受,饿得用两只手又挖胸又按肚子,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耳朵里一片嗡嗡声,仿佛有一面铜锣在头脑里轰鸣,眼睛直直盯住房子的上梁,越想越悲伤,越想越恐惧,再想起今后漫长岁月,身上都像起了层鸡皮疙瘩。啥时间是个头啊!没一个人能理会她心中的痛苦。她没想到她过去的一腔爱心,大半生辛劳洒到这个家中会是这样的报应。女婿、孙儿、孙女儿怎么对待她,她都能想得通,最想不通的是自己亲生女儿,从小就疼爱她,娇惯她,什么事都依着她,几十年她把心中的爱全给这个最小的女儿了,在她身上不知流了多少的汗水,泪水,心都快要操碎了,今天她怎么以这般的心如此待她?多少次她想来想去找不出头绪,只是一个劲流泪,经常能在早上看到她眼睛红肿,整天连句话都不说,有时实在憋闷得慌,见鸡骂几句,见狗恨几声。但凭她自己的感觉,今后生活会比现在更艰难。想着想着恐惧、危机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由困苦转化为半痴半呆的眩晕。她躺在炕上,先是喉咙发干,眼前黑暗,眼睛上好像遮着一层什么东西,然后便是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制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她的哭声是那样凄凉和悲惨,不知哭到什么时间,她才能朦朦胧胧的入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不久之后,她慢慢地适应大人和孩子给她的这种待遇,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压力减轻了。但饥饿仍然威胁着她,她利用家里人上地或外出的机会到队里别人家去,那些好心人无论什么食物都管她一饱,看着门外面没人时赶快让她回家。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大女儿湘楠去油坊换油,心想路过妈家顺便看妈一眼。平常别人都说妈吃不饱到别人家要饭吃,甚至拾着吃上坟烧纸没烧完的油香,还有的说到移民的地里吃生洋芋等,自己亲眼没见,总半信半疑,就拿了四个蒸馍去给母亲送。到庄子边上的马路旁。她左看右瞅,正好看到老妈从一个墙角走过来,就赶紧把这四个蒸馍给了母亲。不巧,事儿被惠楠看见了,第二天早上女婿和惠楠都在麦场上打胡麻,还有几个移民也来帮忙,当那么多人的面,惠楠怒气冲冲骂湘楠:“他妈的庇你给的好,拉到你们家去养着去。”大家无一敢插话,可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饥饿逼得农月根老奶奶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尊严。有一年冬天,炉子都生上好几天了,大女儿湘楠想来看看母亲。到妹妹惠楠家,见母亲穿着单薄,棉袄袖口和衣服下边子棉花都露了出来,鞋也已穿的没了后跟,在院子里晒着微弱的太阳,顺便就把她拉到惠楠的房子递给一个小凳子让坐在炉子边烤火。不一会,惠楠从鸡圈里拿来一个给鸡吃食的盘子,盘子里面给鸡的面条全冻在了盘子上,就把盘子放在炉子上烤着,一会儿盘子里的面条全化了,坐在炉子旁边的农月根老奶就把盘子里化的面条用那黝黑枯干的手抓着吃到嘴里了。大女儿湘楠很吃惊地问:“妈,这么脏的你为啥要吃这个?”她妈说:“我饿得没办法。”湘楠看着老妈,心像刀一样地挖割,从此只要有空她就往她妹妹惠楠家看老母亲。这年已经到深冬了。有一天,蓝蓝的天空中洒满了懒洋洋的阳光,满地的白霜。天虽晴,气温很低,寒风刮得干冷干冷的。大女儿湘楠又到了妹妹惠楠家,只有妹妹一个人在家,她到母亲房子里看,空荡荡的,没有炉子,也没门帘,房子冷如冰窖,在妈的炕上摸了一把,炕冰凉,出门后就抓住妈妈冰凉的手走到了妹妹惠楠的热房子里,把妈安排在炉子旁坐下。她知道妹妹惠楠有些倔犟,就先很平和地问:“惠楠,妈睡的那房子怎么那样冷?炕也冷啊!”惠楠说:“哎呀,那昨下午煨着是不是又灭了。”湘楠又说:“我听妈说这些天都没热过,这会把妈冻坏的。”妹妹惠楠没吱一声,脸上却阴云密布,嘴里开始满腹牢骚。姐姐湘楠只好调转话头。正在说话间,老母亲看见墙边上的一口大缸上放着一个筛子,里面放着白白的馒头,乘人不备,就起来用沾满污渍干瘦如柴的手从篮子里拿了一个馒头。惠楠一下就急了,赶忙起身一步跨过去,从老人手里夺过了馒头说:“你饿死着呢?吃那么多拉裤子谁给你洗?”老人眼含着泪坐着了,对着姑娘惠楠说:“阎王爷不要我的命,你们说怎么办?要是这样不如把我掐死算了。”湘楠气愤不过说妹妹惠楠:“你怎么这样?一个馍拿到手里你就让吃去,你这也太过分了。”惠楠紧绷着脸,大声吼道:“我再给她吃多少,她能给我干什么?你说得好,你拉到你家里养。”湘楠感觉和妹妹没法说下去,只好无奈地流着眼泪回家去了。
农月根老人很虚弱了,脸色灰白,有时又变得青紫,蓬乱的头发已很长一段没人给她梳洗了,几年没人在她身上擦一把水。她感冒了队里的关义光给她挑羊毛丁,上衣脱后,脊背上的一层厚厚的污垢,黑得看不清皮肤。她的行动已很困难了,多数时间躺在炕上,下炕只能柱着一根棍子。太阳好的时候,只要有点劲就想到门口见见蓝天和太阳,但从下炕到门口要用好长时间,费很大气力。当她在门坎上坐稳后,脸上无丝毫表情,好像眼前的一切都很陌生。后来,她住的房门又给用门扣从外面给扣上了,即使想出去也不那么随便了。农月根老奶奶躺在炕上越想越难过,活了一辈子,老天不睁眼,连看看蓝天晒晒太阳的权利都得不到了,这个世道就这么对我!
在农月根奶奶去世前一年的五、六月,孙女在城里批发了辣面子在家卖。队里王兴武到家里来买,进街门还没站稳,农月根住的房门咚咚地用棒捣得直响。女儿惠楠听见,喊三女子给奶奶开门说:“你看奶奶是不是要解手呢?”门一开本已站不起身的老人,竟是一下不顾一切连滚带爬到门口院池子的菜地里,急乱地用手拔起长着的蔬菜就往嘴里塞。显是老人家已几天没进食水。惠楠看到,感到是给她丢人了,气急败坏地跑到老人跟前,屁股上用脚踢了两下,并且低声骂道:“你饿死着呢。”可不管这老女儿踢也好,骂也好,农月根奶只是不停地往嘴里塞菜叶子,并且连嚼带咽。王兴武很不好意思,出去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农月根老奶奶一年四季最大的奢望就只是无论什么吃的能填饱肚子,显然,连这,也只能是一种梦想。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挨过。农月根老奶奶整天躺在炕上,但却是把所有的听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开门的声音上。因为她胃肠的难受迫使她只能这样。好多天过去了,有一天给她一碗饭,有一天一口都不得见,她脸上消瘦不堪,黄中带黑,眼睛像两只黑洞,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躺在炕上缩作一团,手足不能自举,孩子们喊三五声都没一点动静,只有那眼睛睁开,方看出是个活物。她连伸手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睛睁的时候只是瞧着你,再细心观看她的眼睛里带着那样悲凄无奈的神色,望着真是一种穷途末路的样子。
一九九三年农历四月中旬,这个偏远的小村庄小麦兴致勃勃地繁荣生长,遍野是绿油油一片。那惠楠可能是为了让奄奄一息的这位母亲尽快踏上黄泉路,竟是只留下躺在病床上的亲生母亲和从来不会做饭的老公进城去了,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才回来。待回来已是月底,老人早已是目不睁,口不张,只有心脏在微弱跳动了,只剩了极微弱的一口气息。但这惠楠看了却是丝毫没显一点心痛之感。她大概是在想:怎么还没咽气。
农历四月三十日,这惠楠让孩子去通知了自己的大姐湘楠。湘楠到了老妈的房间,看到情形,好心酸地喊了几声妈,可没应声。湘南流着眼泪,在母亲的身边哭着说着:“妈,实在是对不起你啊!但我确实没有办法啊!你能体谅我的难处吗?啊妈。”可老妈丝毫没有一点反映,湘南终于明白,老人已经不行了。人们就从这天下午起待在了惠楠的房间里,聊天说地,没人为她喂一片药,也没人为她灌一口水,甚至于再没一个人进这个门看一眼。老人的生命就这样在凄惶和寂寞中苍白地飘落了。
农历五月初一,天刚蒙蒙亮,天空晴得无一丝云彩,高大的白杨树上落着的乌鸦在不停地叫着。大女儿湘楠起来连厕所都没上,就到母亲住的房间。可是一进门却发现炕上没有了人,左瞅瞅,右瞅瞅,最后发现母亲是不知什么时候已从炕上滚到了靠窗户的炕道子里。湘楠连喊带拉地把老人家从地上抱到了炕上。一看,摔下去头上碰得一个大包,一点气没了。想必是咽气前难受得滚来滚去滚到了地下的。其它人到后,整理了一下老人的衣着,按当地习俗就请客准备着为老人送行。
老人过世三天要出殡了。天比初一天还蓝,刮着一阵阵清风,没有人披麻戴孝,湘楠、惠楠、叶楠及几个孙女守在棺木前,只要有吊孝的人进门,主事的便喊声来人啦,守灵的人就开始呜呜地哭一阵,待吊孝人烧完纸后,就停了哭重开始说长道短。当主事人宣布了起棺,“八仙们”便抬起棺木走。村里不少的人听说这天出殡,心情都很沉痛,只要是能来的都参加到这个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中。一路上不少的人眼含着泪痛心地说:“六0年生活困难也没把人饿死,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却当了饿死鬼,真是可怜!村民甚至无所顾忌地愤恨地骂起来:惠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她一定会遭报应的。
根据当地的习俗,老人没有进老坟一次下葬,而是用土块把棺木围起来待后进坟埋葬。丘葬后,送殡队伍逐步散去,湘楠、叶楠也都回了自己的家。悔恨自己没有照顾老人痛哭流涕,哭得像泪人一样。惠楠到家后坐在炕沿边上,边喝茶边和几个人说天道地,好像自己从禁固中解脱了,悠闲自得的样子。
第五章诚挚的忏悔
农月根老人丘葬后,村里人有的为此痛心气愤,有的在气愤中怀起抱打不平之意。而那惠楠依然还那么硬。当村民们的风言风语传到她耳朵里,她不仅没一点悲痛惭愧之意,相反,她是涨红着脸,把脸绷得紧紧地在居民点里走到人多的地方骂街:“他妈的,谁家屋里不死人?老娘伺候得不好,老人还活了八十多岁;你们伺候得好,老人才活五六十岁!”她的话落地后,没一个人抬起头望她一眼,谁都没理。这么地骂罢,约莫一二分钟过去,见人们这般,自己站在人群边上就没一句话再说了,很没有意思的神情。最后,她涨红着的脸终于像是由于感到难为情而变得唰白,耳朵和脖子都变红了。
随着光阴的流逝,几年后,这惠楠的丈夫因病去世了。丈夫丧事时她也是和母亲过世一样,慢悠悠坐在凳子呜呜哭泣的声调是颇显出了一种悲哀的意味,可没一会她就不悲了,像是忘了还没抬出门的丈夫的冷尸,坐在炕上和别人又谈天聊地起来,大说二讲,时而发出笑声。
丈夫的头七过后,她像是很快就恢复了原气,不久就到城里自己最小的儿子贵才家伺候正在坐月子的儿媳妇月莲去了。儿子和月婆住工厂里给的一间正房,她只有住在不到十平米的伙房里。住惯了农村大房子的她,在这间房子里既要给月婆做饭,又要在这里睡觉,早晨跑到晚上,一天洗洗涮涮几次,她的心烦闷得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丈夫在世前,经常向她问寒问暖,一有头痛脑热,就把开水和药倒到自己手上的这种优惠待遇自是不可能见了,甚至连说点真心话的人也找不到了。她每天哭丧着脸,看见什么都不顺眼,有时候哭着闹着,整天不吃不喝,给儿子发一些无名火。媳妇出月子不久,就闹腾的回老家。
一天,儿子贵才和媳妇玉莲都上班去了,她没等儿子媳妇下班就把饭全做好了,坐在橙子上等着。但贵才单位有事还没到家,媳妇月莲进门就端起碗盛上吃饭。惠楠看见就十分生气了,数落儿媳道:你这个没有教养的,连声猪狗不问就吃,一点礼法都没有!媳妇月莲平常已是攒下一肚子火,这时,便开始向外喷发了。儿媳回击:“我晚上还要加班,饭吃过就得走我早吃一点咋了?怎么叫个没礼法?”两人越吵越厉害。媳妇的几句话显然是气坏了这婆婆惠楠,这惠楠心想你还敢顶嘴,老爷子在世时都把我双手捧着,你算什么东西!就从屋子里跳出来躺在院子里,两只脚来回不停地在地上蹬来蹬去,哭喊:“我不活了!我活不下去了!”院子里的邻居也都隔着窗户看着,没一个人出来劝。后来儿子贵才回来了,没头没脑地被妈惠楠骂了一顿,说:“你马上把你那个奶奶给离了,否则你就不是我儿子!”儿子贵才没法把她拉起来,又无法说她,只好找大哥帮忙,夜间三点钟才罢休。此后,心中的空虚威逼得她烦躁不安,每天夜里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似得,睡着后恶梦涟涟,不时被恶梦惊醒。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痛苦中,整夜地失眠,身体虚弱多病。她心情沉重,有说不出的忧伤,泪水湿透了枕巾,时常中午眼睛都还是红肿的。
八个月过去了,六十出头的惠楠和儿媳妇的矛盾不断加深,婆婆进门,儿媳出门,两人的脸什么时候看上去都拉得长长的,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两代人实在无法一起过了,她单独住了,但空虚,孤独,没法消失。
她搬进一个五户人家的院子里一间平房。刚住下她觉得比较平静,没住几天往事便如河里的浪花一浪高过一浪,白天晚上常常梦见自己的母亲扶着拐杖向她要吃要喝,梦见丈夫在大声责骂都是你把这个家扰乱了,让我们的名声搞得这么臭!有时候,她从梦中惊醒,仿佛恍恍惚惚地看见妈妈和丈夫站在自己的床边,吓得冒一身冷汗,心惊肉跳,眼皮也直哆嗦。就像什么东西咬着自己的心。她恨不得自己用把刀把自己捅死,来偿还欠下母亲的债。很长一段,她不思饮食,心虚了,血压高了,身体抵抗力下降,三天两头儿子媳妇陪着去诊所打吊针。她总认为是死去的母亲和丈夫在缠着她,是上帝神佛不宽恕她。每当她被恶梦惊醒或想到过去对母亲的所作所为,就双膝跪地,仰面闭目久久祈祷:“神佛啊,过去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为了贪图享受,把替换我半辈子的她老人家,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还限制她的自由,让她在精神上生活上蒙受重大创伤,让她带着饥饿的身子离开了人世。你饶恕我的亏欠和过犯吧。我违反了做人的道德,我在下辈子加倍偿还。我的神佛啊,老天爷,我说的是真话,不会骗你,你相信我吧!我求求你,你就赦免我的罪过吧,保佑我平平安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家中发生的变迁,大点的孩子都不言而喻。在一个春节的聚会中,大儿子贵福,二儿子贵荣,小儿子贵才单独坐在了一起。小儿子贵才说起了母亲近来心情,身体,问咱们怎么办?大儿子贵福接着话题道明了自己的观点,说出了兄妹共同的心里话,兄弟三人观点一致,态度都很明确。大儿子贵福说:“咱家过去发生的事兄弟姊妹都清楚,在家乡的村庄咱们家丢失了人间最珍贵的东西,这不是丢失了哪一个人的面子,而是个人和这个家族生存的最基本做人的道德准则。咱娘的过失,咱们只能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在她的有生之年,要把她丢失的东西在我们这辈人身上捡回来,让她老人家活得静心,活得顺心。从此兄弟姊妹只要有空就去赔老娘聊天,吃饭,过年过节争着把老人家接回自己的家,要不就是大家一起提着好吃好喝的去和老人同乐。
惠楠老人知道自己的过失儿女全都目睹,越是儿女们来得勤,越是经常拿好吃的,买好穿的,就越觉得自己心中的伤痛,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在心上,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内疚。夜深人静她睡不着觉,想到自己的过失流着眼泪,真感觉无地自容。
人们送走狗年,迎来猪年的日子。过年前一个月,大儿媳把惠楠请到家,一天三顿饭做熟亲自递到老人手上,早晚牛奶蛋糕,中午下午都是肉食鱼虾,一星期给她洗一次澡,又把铺铺盖和穿的用的全拿来洗得干干净净。惠楠老人只是一个劲难过地擦着眼泪,总觉得媳妇做到的,她一个也是当女儿的没对老母做到,心中无比惭愧,现在又这么大年岁,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心里就更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