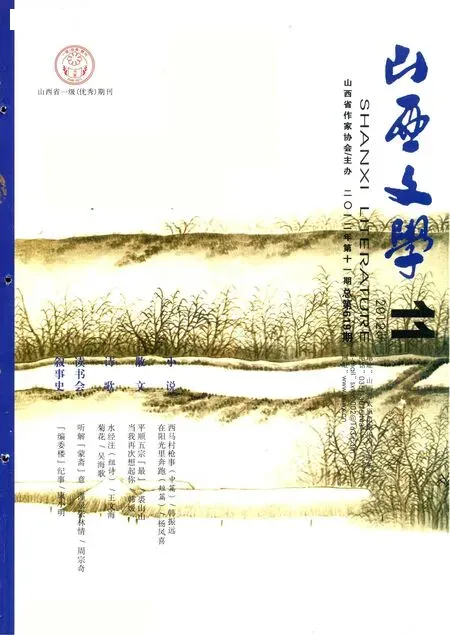当我再次想起你
韩 媛
1
米米说我的样子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彼时的我正以一种极度颓废的状态陷落在一只庞大的沙发里,明知她的形容是准确的,但还是抬抬耷拉着的眼皮,说,做人要厚道,米米你好歹把我也形容得整齐精神一点儿,比如说,一块方方正正的军用棉被什么的。
说完这句话,我有点儿后悔。唉,有的时候,你极力想克制和避免什么的时候,总是不能如愿,总有一些人和事,包括自己一不留神蹿出来的一句话在干扰你,把你不遗余力地拉回你不想涉足的情境中来。
我说米米你知不知道,回忆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会伤人的,所以我一直不太敢回忆。你看这北方七月的城,天地都像着了火一般,树叶花草都在打蔫儿,而我,像一尾失神的鱼,没头没脑地,一遍遍地被沉入回忆之湖中。
穿过岁月的层层帘幕,我看到自己坐在教室里,耳边是哒哒哒的粉笔声,眼睛里却是教学楼前面的那方篮球场,层叠的云,映在雨后的水洼里。
你看,我一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我在上课的时候走神,那种哒哒哒的粉笔声过一会儿就换作了外面别的中队上军体课时练擒敌拳的“嘿嘿哈哈”声。在我的课桌里,塞着好几封同时寄来的信,那时候,信真多,每天不写信,就会觉得这一天虚度。可是到最后,我也只能记得一封这样的信,在信中,素素说,落,好久不见你,你在我的印象中都变成一块四四方方的军用棉被了。
我惊诧于她的比喻。我在课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回信,我说,你的比喻形象而生动啊,我觉得不只是我一个,我们这帮同学都成了军用棉被了,我们穿一样的制服,一样地作息,上一样的课,吃一样的饭,连宿舍里私人空间的布置和摆设都是一样的,极其整齐划一,早已没有了独特鲜明的个性。
几年以后,我在大街上与素素不期而遇,她已经成长为一名小学教师,而我,就像当初收到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注定的那样,正毫无创意地当着我的小警察。我们热络地拉着手,即使是坐在柳巷的一家快餐店里也舍不得松开。据她自己说她不记得说过这种经典的语言,可是我却一直把它记在了心里,会记一辈子,因为它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我在警校四年的生活和状态。
刻板,无趣,毫无新意,味同嚼蜡。
可是,我为什么还要想起它?
2
我把手机抓在手里,几次翻出依依的电话,在拨通之前,又快速地挂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很想说我想念她,又怕她连听这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十几年了,我们毕业,离别。见过四面,每一回的她,都是形色匆匆,而此刻,她也许正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沉默或者忙碌吧。她总在忙碌,总在奔走,她不知道,为了她不肯出席毕业聚会的事情,我遗憾了好久。
有人说,百思不得其解啊,她为什么不来呢?我说少见多怪,这有什么,虽然我来了,但是我也有过不来的念头。他们奇怪地看着我,像看一个冷血无情的怪物。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子,难道你们敢说自己心里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和念头?十三年,十三年聚个什么劲儿?十年都不聚,就算还残存着些真情意,也都在岁月的流逝中消失殆尽了。
心里有个声音说,落,这样不好,你太刻薄,你无权责备任何人。
我笑了,其实我只是在演示一场梦境。有些话,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敢想,却不敢说出唇。
其实我还有另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我要说的是,我并不赞成故意缺席。之前的话都是气话,我发誓,我不是真心的,我耿耿于怀,只是因为,在深深深深想念这座校园的时候,不能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走近它。
至于依依,我觉得我能理解她。关于她的流言,许久以前就有,一次比一次憔悴的面容,可以直白地说明一切。如果要继续她的话题,我们只好谈谈十几年前的过去,不谈后来,亦不谈当下。
我很遗憾,在别的同学大谈特谈很久以前那些少年往事的时候,依依不能和我一起谈谈属于我们共同的经历。
在那个有着四百米跑道的每到夏天就野草疯长的操场的角角落落里,应该有我们共同留下的痕迹。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一阵尖厉的哨声把我们从温暖的被窝拉起来,集合到初冬寒气逼人的操场上,演习一种查缉某种标语的活动。我和依依在队列里,彼此一望,便钟意为好搭档。凭借我们的判断和依依的长腿,在这个操场上我们的战果辉煌,比任何一个小组都要多。然而,组织者竟然没有做任何点评,这半夜的活动以一种高亢的形式展开,而以一种低迷的形式匆匆收尾。我和依依都闷闷不乐,第二天都不怎么开心,十足像是受骗少女。自那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活动,我们俩都会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方,相视,然后撇嘴,鼻子里再重重地哼一声。
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那么在乎别人的一句话,赞美或者褒扬,好胜心那么强,那么喜欢被人知道自己的成绩,总是喜欢在大家的目光里小小地出一番风头。
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了依依,当我准备和她分享这段往事的时候,她会不会也和素素一样,说,哦,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呢。
我有一只盒子,里面装满了相片和信件。我搬了几次家,把它搬腾来搬腾去,总也没想过要打开它。只是因为怕回忆,怕回忆在缓慢展开的时候,被现实生活一下子打断。时间,我总感觉太紧张,该上班了,该工作了,该开会了,该回家了,该吃饭了,该睡觉了。没有宽广的时间背景,最好不要打开回忆的画面,那是一幅长长的卷轴,如果在打开的半途中戛然而止的话,我会很痛苦,所以,就那么放着就很好。
但总有人和事,我说过的,包括自己的一句话要使人猝不及防地展开回忆。那么,现在,我决定打开它,并且只取出其中的一帧相片来,其余的,留待以后吧。也许以后会有充足的时候打开,也许永远不会有机会打开它们,也许,就像在聚会时大家拿着话筒嘶哑着嗓子嚎叫的那样,也许我会忘记,也许我会想起,也许,已没有也许。
我的儿子说这上面是谁啊?
我说,依依阿姨。
他说,怎么穿着绿军装啊?
我说,那不是军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警服,只是,我记不清该称做八几式。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爱着这身橄榄绿的制服。上衣是小翻领,小卡腰的,裤子是镶着红边的大裆裤。细数数,那四年间发的制服,是足可以在T型台上表演一场公安服装秀的。光是领花盾牌警衔肩章就够搜罗一兜子了。而橄榄色,比起现在的藏青色来,更容易引发我对年少时的梦想、自豪感等等这些东西的回忆,爱做梦的年龄,把橄榄色深深植根于心间,然后梦想成真了,最初的眷恋也就成了心底最深的怀念。
依依坐在宿舍楼前的花池边,头微微地扭向左边,嘴角俏皮地上扬着。就算没有这帧照片,我也始终会记得这样的画面,依依穿这身小翻领、大裆裤的制服是多么帅气,从来没有人敢否认,我们说她“英姿飒飒”,这个词应该是从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里学到的,让我想想,哦,是演乾隆皇帝风流韵事的一部戏吧,我只记得主题歌,里面唱“山川载不动太多的温柔,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好像皇帝在出行过程中见到了一位绝色的江湖女子,打心眼里发出一句这样的赞叹吧。扯远了,总之,依依身材修长,这身制服让她一穿,真的英气逼人到无人能比。
依依和我当时的关系并不“铁”,我们甚至四年都没有同过一间宿舍,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得其乐,行色匆匆,顾不上多说一句话,但我总是会惯性地想起她,而非他人。
依依有浓密微翘的长睫毛,双眼皮,细长的一双秀眼,眼角微微上挑,尖尖的下巴。她自信地冲着我笑,让我在当时的一瞬间甚至于多年以后的今天都为之吸引,不能忘怀,心里总是颤颤地涌起两个字“惊艳”。
我和她,当时正在花池边胡聊瞎扯,聊天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等待集合吃饭的哨声,然后列队唱着歌儿去食堂。所以依依的怀里理所当然地抱个饭盆,即使是小号的,在今天看来还是显得有些突兀。当然,我怀里肯定也有一个,只是当时的情景没有被图片的形式记录下来而已。我们的饭量都很大,但是依依吃了不长肉,而我,无法同依依相比,如果还能用军用棉被来比的话,那时的我,就是一块刚被大太阳烘烤过的棉被。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着天,不住地说,怎么到点儿了,还不吹哨啊,饿死了都。
然后依依突然问我,你这几天有没有写什么东西?
我说,没有啊,生活太单调,没什么可写的。
她说,我觉得你还是别放弃。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神色变得有点凝重起来。
我就笑了,好吧,就冲你这句话,我也不会放弃,等我哪天没工作了,沦落街头,忽然意识到还可以卖字为生的时候,我会很感激你的。
真奇怪自己竟然能说出“沦落”这样的话来。我们于是哈哈大笑。因为知道有了“铁”饭碗,所以才不知深浅地说出来这两个字吧。
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沦落”到卖字为生,然而却知道,能“沦落”该是何等洒脱自在,“沦落”是一种人生境界,真要做到,实在太难,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因为舍不得。
但是,依依,我感谢她在那个傍晚对我说的话。她说她喜欢我的文字,我心里欢喜,一直到今天,依然欢喜。
像两条直线一样,我们曾经交于一点,而后在有限的人生里只能专注于自己生命线的延长,我们都是凉薄的人,好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热络到那种形影不离的地步,但我并不觉得这是我们的缺点,对于一般情况下互不打扰的友谊,我们都应该是满意的。在我们之间应该永远存有一种遥远而亲切的回忆。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我要说的是,亲爱的依依,虽然,说什么都没用,但是,我真的愿意去为你分担些什么,如果你愿意。
3
我参加聚会回来,米米问,落,有没有见到你的初恋?
我也想见,很遗憾,没有。
为什么?没来?
不是没来,是根本就没有。
不信。
是真的。初恋这两个字多美好,像一片青柠一样,淡淡的酸,淡淡的涩,淡淡的甜,清凉爽口。如果我有过,我也巴不得要见见。
还是不信,她说,我可以去调查。
我说米米你几时变得这样八卦?而且竟然连我的话也不信。难为你为我这样上心,调查去吧,祝你成功。
也许是该有一场恋情的发生,好来成全十几年后米米这难得的好奇心。在那些形单影只的日子里,我热衷于抱着一撂书(形形色色,内容丰富,但是除了快考试的时候,里面是绝对的没有课本),拎着粗细不等的毛笔,再夹一卷练习书法用“元书纸”到教室里去,偶有花前月下的时候,也是和女同学在校园里走一走。头两年的时候,大家的喜好都差不多,所以站在宿舍楼的窗前,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男生女生,被书和笔墨纸张武装着,神色庄重,步履匆匆。到后来,就多了双双对对卿卿我我的场面。我旁若无人地看书写字,孤单的感觉从来也没有过,我不惆怅也不遗憾,我很感激自己曾经以一颗单纯饱满的心沉浸于看书和写字中去,虽然学习和书法最终也没能实现一种超越,但那些一个又一个星空黯淡或者璀璨的夜晚,给予了我足够谋生和应付日后繁杂事务的能力,此外还有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包括对一个真正帅哥的鉴赏能力,这是后话,暂不提。呵呵。
我说,米米,我可能暗暗地喜欢过某一个或者两个,呵,也许是三个男生,而且不局限于我们这个小集体中的这些人,但那都是些懵懵懂懂的情愫,我可能是因为他们跑步或踢球的样子帅,或者不太爱说话,有一些深沉的气质,或者是笑的时候眼睛很好看什么的而喜欢他们的,却都只是瞬间的情绪而已,我对他们的感情还没有来得及在记忆里划一道浅痕就消逝了,而且,我敢保证,他们都不太知情。
我一直都不是个出众的女孩子,而且根本不喜欢在本该很自在的年龄被一些狭隘的感情拘束,我喜欢的是一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的生活。这样的人自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情感经历。但是十多年后,大家又聚在一起,有的男生说,落落,你的眼睛当年是高到天上去了,平素连瞅我一眼都不肯。另一个接茬,说,嘿,你知不知道,当年他是如何喜欢你的?
我说也许放在当年,我听到这句话时会感动和探究去,一塌糊涂也未可知。但是行年见长,我已经学会了宠辱不惊,绝对不会因为一句这样的话而动情,哪怕一点点。
我只是稍带点不屑地说,喝高了吧,话太多了。
那个男生,我们在毕业当天的聚会上曾一起离开酒桌,向宿舍的方向走。我们都喝了三瓶啤酒,步子稍稍有点踉跄,但是都很快活,没有一丝离去的不舍,我们在这座校园里待了太久,早就想离去。那晚的月色很好,我们快活地交谈着,提到我的小师妹。我们实习回来,她已经放假回家了。我心里清楚,他是很喜欢我的小师妹的,有不少男孩子都喜欢她,冲着我和她的关系不错,他们有时也进行感情贿赂。这个词用得也不合适,其实当年的他们都很纯真,一团孩子气,借着和我说话的机会打听一下牵挂着的小师妹,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只是遗憾,他们谁都没有成功。我的小师妹后来被她有些权势的父母许以一户条件很好的人家,但日子过得并不滋润。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在我的眼里统统乏善可陈,如果真心喜欢,就该表白,就该去争取,哪怕失败,也不枉做一回男人。然而他们都太怯懦。但其实也不能怪他们,我们原本都是怯懦和自卑的孩子,除了当初考上这所学校的分数外,再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资本,到我们完全认清了这所学校的面目后,连这点儿可怜的骄傲也都统统丧尽了。这几乎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共有气质。对于人生,对于社会,我们实在是太单薄,无能为力。直至现在。
我拒绝和男生合作,霸着麦克风,一个人一句女声一句男声地唱《北京一夜》,就是喜欢那样苍凉的旋律,还有满面尘灰的感觉。话筒被一个男生抢过去,然后他龇牙咧嘴地大声吼,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唱北京的一夜?!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这首歌于别人无关痛痒,于他,却是绝对的意难平。他热恋的女朋友,在去北京求学的日子里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头。然而他的光景依旧不错,有很好的家室和前景,命运对于他总是格外垂青,好像一个孩子,丢失了一个心爱的宝贝,还可以再找回一个,日子照样流光溢彩,于是他活得底气十足。只是再怎么样,总还是可以被回忆打败。我可以看得到,在一刹间,他的心痛,脉络清晰,层次分明。
我把话筒从他的手里夺过来,继续跟着屏幕上的歌词唱,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多么老到而经典的唱词!不管你爱过没有,喜欢过没有,爱过谁,喜欢过谁,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也不过都是过往,都是尘埃,纵然是情满天下,爱透一生,也总有风流人散尽的一刻。像是一句佛谒,又仿若是一柄带着寒气的薄刃,削铁如泥,得到它,瞬间便可以割除心中那些虚幻的奢望和念想。
4
没有发黄的墙壁,亦没有古旧的常春藤,图书馆只有一间屋子,里面陈列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籍,蒙着蛛网和灰尘。满园中只有从宿舍到食堂的一条林阴道,水泥抹就的,已经被踩得不像样子,斑驳陆离,到了雨季的时候,走在上面,会有沙沙的声音,仿佛要被酥掉一样。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场景,既不精致,也不罕见,但这些朴素的场景联结在一起,与我们橄榄色的身影和年轻的面庞相映在一起,即便是在苍凉的冬日里,也显得生机蓬勃。而今想起,既亲切又温暖。
这座校园太年轻,没有什么历史,人物或者陈迹都没有。空间太小,小得容不下更多的秘密和回忆,然而我依然可以滔滔不绝,总也有说不完它的话题,甚至于那硕大的,能隔着警服叮人的蚊子我也不忘说出来,至于月季花,因为在其他文章里提起来,暂时可以不必再费笔墨。
除了每天要去的教室,最亲密的地方当是操场,说实话,形象真不怎么样,简陋、粗糙。每到秋季开学,先得集合起大队人马锄去上面一人多高的杂草,这种劳动最少得持续两天。劳动也是快活的,因为不必待在课堂上受许多纪律的约束,也不必忍受严厉的军训,可以肆意地谈天和说笑,两个月的假期中总有些愉快的话题。因为有了这许多的内容在里面,所以操场的外表可以忽略不计。
我的运动天分实在有限,军体成绩总是差强人意,但我喜欢在操场上举行的任何一项活动,尤其是军训汇操表演,观看,或者跟着一起做。阅兵式和分列式都好,每一次在整齐的队列里,踢起正步的时候,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因为这个原因,军训的时候我很用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步的确也踢得很好。每到金秋十月校庆的时候,红旗飘扬,口号嘹亮,场面尤其壮观,颇有些“沙场秋点兵”的味道。这种场面赋予我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恒久的,里面有豪情,亦有坚忍,还有一些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总之今生今世都难以割舍和抛别。
有些记忆是植根在心里的,想忘也忘不了。细小而茂密,平常一点点地落在那里,不惊动人,但它的力量却又是醇厚而绵长的,可以醉人。记忆里其实不光有可以津津乐道的内容,也不乏那些枯燥、乏味和茫然空虚的经历,我问自己,比起现今的生活来哪一种更美好?我答不出,然后告诉自己,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可比性。
我曾经在二十多岁时候的某一天,忽然想起该为我的警校生活写一点东西出来时,却怎么也写不出。也就是说,我从来也没有用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它的回忆中去,但这个情结却一直在心底纠结着——像不像一种爱情?特别绵密,特别隐蔽?
我想起,毕业离校前那个夜晚,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微风吹起,月挂中天,周遭是处子般的静谧。后来我独自坐在花池边,最后一次端详这校园里的一切,现在回头看,真具有仪式感———这分明就是一个告别仪式。另一种生活即将展开,心中溢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但丝毫也不为未来担心,因为许多事情是注定了的,比如职业,甚至于具体的部门。那些憧憬更多的是对一种全新生活内容的向往,为了不必再天天进教室进行千篇一律的学习,不必再重复单调的日程,我显得有些急不可待。
事实上,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见面,就算不是很快,最晚,今年年底应该没有问题。2008年7月下旬的一天,当我像一只胀满了风的帆船一样,兴致勃勃地打点起行装,准备启程去赴与她的一场约会时,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打击到只能以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的姿势陷落在沙发里。我的好朋友米米安慰我,说警督培训只是延期,又不是取消,总有一天,你会顺利地成为一名警督的。
我说米米,我并不急着当警督。
米米说,知道啦。你只是急着想再次投入你母校的怀抱去。
我说其实现在的学校和我印象中的已经完全不搭界,几近面目全非。她崭新鲜亮的样子让我觉得陌生,我走近她的时候,心里会别扭,我更喜欢她朴素的样子,静静地立在两个村子之间,在我的想像中,偶尔,她会像母亲,像呼唤在外贪玩的孩子一样唤我的名字。
在不久以前的毕业聚会中,我已经比较亲密地和她接触了一次。现在的她,锦衣层叠,珠翠满头,当我行走于校园中的时候,我浑身不适应,我的回忆因为找不到熟悉的场景来寄托,显得格外飘忽,无着无落。那时候,一场雨刚刚过去,我终于在篮球场上看到了与当年一模一样的场景,层叠的云,映在雨后的水洼里。四周静极,能听见树叶之间交谈的细小声响,宛若谁的轻叹。我抬起头,望那密布着的雨云,就像十七年前第一次迈进校门时的那样,眯着眼睛。然后心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刹那心惊,许多人事,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默默地过去了——我自己,已在步入中年的路上了。
难道不是?
我们都老了,已经老到可以晋升警督的年龄。警督,这真是一个标志性的警衔级别。那些大姑娘和小伙子们会把我们称做阿姨或者叔叔。当然,往老境里走并不可怕,能有往昔的岁月相伴,也算可亲。
我承认,这是一个情绪高涨的夜晚,我的思绪像一条绵长的小溪,它在月夜草丛里秋虫的鸣叫中流出来,幽微、广寂,在不为人知的心之角落抵达我的字里行间。
我为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
我说米米,我才不怕你说我矫情。人在渐渐老去的过程中总是要有一点点怀旧的。我曾经很决绝地说,我对警校没有感情。现在我准备收回这句话,然后,在即将到来的那四十多个日子里,我可以在她那里寻找一些曾经失落的东西,他们可能储存在某些建筑、植物、甚至于某些故人的姓名里面,我想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寻找他们。
十几年前,我离开她的时候,酷暑的天空呈现出的是一片瓦蓝色,灿烂的阳光笼着青春的浮梦,一切都那么美好。今天,短发已经很长,明眸快要转为黯淡,飞扬的梦想已经云散,留下的,只有一颗静看世事浮沉的平常心。
唯一不变的是,每次听到她的名字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她的怀抱里再做一回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