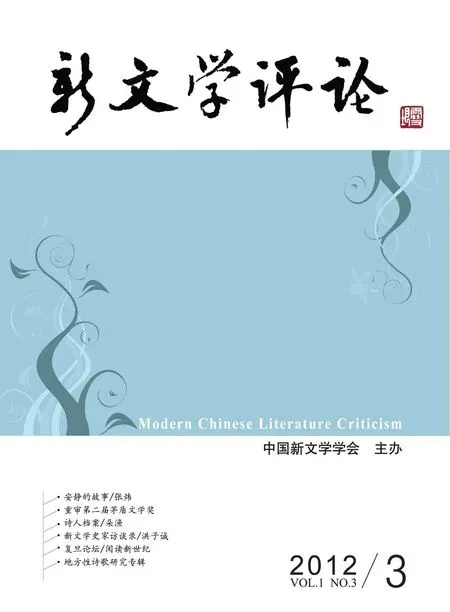海口诗歌印象
◆张伟栋
二零一零年,我举家南迁,落户到海口。一下飞机满眼的奇异景象,让我有置身于异国之感:宽阔的街道被整排的椰子树占领着,而天空开阔得出奇,空气散发甜湿的味道和明晃晃的白光,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表情,竟然使我神奇地想起《美狄亚》中的一句台词,“你怀着一颗愤怒的灵魂,离家远航,穿过海上的礁石,定居在异国的土地上”。多年来的北方生活,四季变换的物候和漫长的冬季,让这个热带的岛屿如此奇异和新颖地出现在我的目光之中,使我本能地寻求语言的庇护。文学中的热带生活,我所熟知的是沃尔科特对特立尼达的描写,那里有着适于裸体和懒散、散文和柠檬的小提琴的夏天,沃尔科特的诗中有很明显的散文化的东西,也善于使用繁复的隐喻,古怪地将热带的两种节奏,热与湿、晴与雨、光与影、日与夜,融合在一起,散文化叙事的容纳和繁复隐喻的想象所造就的是一种热带的语言,带有粘稠、湿热、茂密、忧郁的地理特征。另一位给我帮助的诗人是瓦雷里,整个夏天我在反复重读《海滨墓园》,这首诗依靠单纯的北方经验是无法完全理解的,在前两节中,大海和太阳所交织出的空间,是如此的具体又抽象莫测,大海永远在重新开始,太阳休息在万丈深渊的上空,标注出热带岛屿的诗歌边界和变换的节奏。
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
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微沫形成的钻石多到无数,
消耗着精细的闪电多深的功夫,
多深的安静俨然在交融创造!
太阳休息在万丈深渊的上空,
为一种永恒事业的纯粹劳动,
“时光”在闪烁,“梦想”就在悟道。到海口之后,最先熟识的是诗人李少君,他热心真诚,而且言出必行,有着大多数诗人都不具备的组织才能,脑子里不断地计划着各种诗歌活动,我的诗人朋友一般都孤独、不善交往,有时候我会惊奇,他怎么会如此精力充沛,而他的诗歌始终带有温婉润泽的江南之风,在自然山水之中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始终认为他的《自白》一诗,就是他写作的蓝图:
我自愿成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
定居这青草的殖民地
山与水的殖民地
花与芬芳的殖民地
甚至,在月光的殖民地
在笛声和风的殖民地……
但是,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
最终做一个内心的国王
一个灵魂的自治者
李少君的写作也影响了海南年轻诗人对诗歌的认同和对语言的组织,个人的心性被编织在山水的韵律当中,一遍遍地给以辨认和淘洗,在这里诗歌既被当做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精神练习,最终回闪的是对灵魂居所的寻求,就像布罗茨基所说的,“对于灵魂来说,也许没有比这更好的居所了”。符力、陈亚冰、林森、陈有膑等的诗歌作品都带着这种品格,比如符力的《小镇暮色》:
从野外归来,少年带着草木的气息
他说他春天钓过鱼的那个地方
被填平了
有人在那里卸下钢筋
打下水泥桩子
我说我记得那个地方
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我跑步经过那里
一个女人在水边洗菜
几丛翠竹披着霞光的新衣
白鸟噗噗飞起来
除此之外,我们彼此挥挥手
朝着各自的方向
消失在小镇的暮色中
不听风吹落木
不看火烧云铺在西山上
其实,海南的诗歌有着两种相互对照的倾向:像符力的作品,还有纪少飞、艾子、潘乙宁等海南本土诗人的作品具有热带地区诗歌的特征,地理特征天然赋予的两种重音节奏,偏重散文化的诗歌内部空间的开掘,隐喻和自然主题、物候意象的繁复转换等;另一种倾向是,来此定居的北方诗人却始终带有北方诗歌的质地硬朗和对超验事物追问的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多多和耿占春,多多的诗歌即使是对海南生活的书写,也带有着北方的寒冷气息,《白沙门》一诗中回旋的“无人”的合唱,恐怕只有北方诗人才能写得出来。佩索阿曾细致地区分两类诗人,他说:“有两种类型的诗人——一种思考他们的感觉,一种感觉他们的思想。第三种类型只思考或只感觉,而不写作诗歌,因此便并不存在。那些深思其所感的诗人被叫做浪漫派;而感受其所思的诗人被叫做古典派。”多多和耿占春就属于佩索阿所说的古典派。耿占春的诗歌超拔、大气,具有评论家少见的文学才能,他那首可以和叶芝的名诗相类比的《当一个人老了》,有着参悟生死的真诚与智慧: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是自己的赝品。他模仿了
一个镜中人
而镜子正在模糊,镜中人慢慢
消失在白内障的雾里
当一个人老了,才看清雾
在走过的路上弥漫
那里常常走出一个孩子
挎着书包,眼睛明亮
他从翻开的书里只读自己
其他人都是他镜中的自我
在过他将来的生活
现在隔着雾,他已无法阅读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的自我还没诞生
这样他就不知道他将作为谁
愉快地感知:生命并不独特
死也是一个假象
与耿占春同在海南大学任教的贾冬阳,其作品简洁透亮,也偏向于对沉默事物的捕捞和言说,《消失在白雾深处》将诗歌的基座放置在了事物“孤独”的深处:
太阳还未升起
海滩上白雾茫茫
有人沿着岸边
独自行走
最后消失在白雾深处
我看着他
觉得这是一个
正在退隐江湖的人
而如果他只是个
空手而归的渔夫
日出之际
他右手边
越来越亮的海水
恐怕就不会
让他像我们一样激动
我很想知道
石梅湾
它会不会让一个
孤独的人
空手而归
蒋浩来海南定居较早,海南也成为他写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这批作品有着对日常事物耐人寻味的收留和体察,而指向我们无法企及的真相,语言神妙而给人启发。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小诗》,其实也是一个诗歌范本,对语调、节奏和诗歌肌理的把握都堪称典范:
月亮从松林里升起来。
树皮上的涟漪,树干里的回纹
也升上了树巅。触摸过树巅的手已不是月光,
粘在一起埋进了旁边的防波堤。
海是一个隆起的空壳,那么大,
波浪也只弄脏了它部分的沙滩。
那些在海上安抚额头的手也不是月光,
它们翻开一层层发灰的灰。
我的手还停留在我的手臂的尽头。
臂弯掉下一些光线和风,
掌心捉住几枚松果和贝壳。
我把它们放在书桌上。
它们从前就在这里,
灯光正画出一对旧影呢!与蒋浩年龄相仿的诗人江非,也创作颇丰,他在海南的写作,一直延续着他在北方开拓出的宽广的路数,当代的景观在他的诗歌当中以镜像的方式显现出来,而使得他的诗句具有较清晰的指向性,我注意到弗罗斯特、金斯伯格和洛威尔的语调被编织在他独特的嗓音之中,也使得他的诗歌有着较为复杂的质地,比如他的《我已经三十八岁》,其实可以和洛威尔的《中年》对照来读,两者都有着对时间变换所带来的真实感的深刻体察:
我已经三十八岁,再有两年
就是四十岁,就会
和某一年的
我的父亲相遇
再有两年,我会感到
记忆力不好
肾大不如以前
屋顶也许开始漏雨
耳鸣,蝙蝠
也许是信天翁
将窥见我的本性
我可能还会想起我的祖父
一个我未曾认识的男人
一个早已见过我的人
想起我曾和他
一起在地上行走,外出
翻土,打开忧伤的土地
四月的昏昏欲睡中
他是音符
我是词语
三十八年,我走过的路
已足够我接近死亡
足以让我学会低语、自责
让心静静地停下来
看着每一种事物在中午的光里
自由地出入
但是坐下来,看着窗外
我的喉咙里还是充满了幼马回家的声音
另一位“70后”诗人唐煜然以身体的隐喻来展开对世界的探求,在色情感和疼痛感的平衡中来完成语言的叙述:
没有找到合适的新欢之前
我们不会分手
这种纯肉体关系将得以维持
对此双方坚信不疑
虽然已经没有任何肉体之外的接触
即使脱下的衣服
也不会挂在一起
即使两具肉体配合得天衣无缝
即使多余的动作越来越多
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两个人躺在床上
忘了是谁说了一句:今天22号了
窗户已关紧,窗帘也拉上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具体发生了什么在简略地进行了对海口诗人的阅读之后,我想回到文章开头,我所提到的热带岛屿诗歌写作的问题,记得江非曾和我聊过热带地区不适合写作,他给了我很多的例子,但我忘记了,无独有偶,沃尔科特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郑重地给以辩论,他说:“冬季给文学和生活增加了深度和阴郁,而在四季常青的热带,连贫穷或诗歌似乎都不能深沉,因为周围的自然界和它的音乐一样,是如此欣欣向荣、兴高采烈。以欢乐为基础的文化注定是浅薄的。可悲的是,加勒比地区为了推销自己,鼓励无所用心的欢乐和灿烂辉煌的空虚,非但成了避寒的去处,而且也成了逃避只有四季分明的文化才能产生凝重感的地方。”这个问题在海南同样存在,但在沃尔科特看来,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虽然每一种文化都是由城市创造的,但诗人可以完成这个城市未完成的抱负,沃尔科特以自己同乡安的列斯人圣琼·佩斯为例,是他使得这个岛屿复活,“瓜德罗普的大椰子树终于能背诵《赞歌》了”。这样的类比对我们有着同样的意义,海南的诗歌所努力创造的一种“地方”语言,有着它自己清晰的向度和文化的理解,它也必将展示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就像沃尔科特所预言的,“作家发现自己目击一种文化的黎明正在一枝一叶地形成时,会产生欣喜的力量,为自己适逢其时的好运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