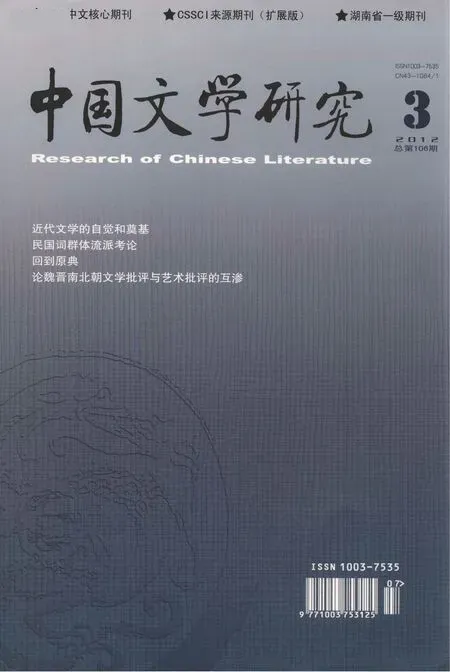新时期文学狗意象的文化流变
江腊生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文学是人学,写动物不过是从别一样的角度来关注人性世界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尽管生态文学的呼声日渐高涨,狗的意象在新时期文学中频频出现,却一直充当修辞的工具,作家很少正面书写“狗性”,更多的是“以人之心度狗之腹”。实际上,不同的作家笔下,狗意象的嬗变,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心理,也体现了作家审美意识的流变。一定主体的人与狗的关系,传达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道德立场或者文化价值取向。因此,把握新时期文学中狗的意象,对于理解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倾向,具有抛砖引玉的意义。
一、人道主义的温情载体
人类文化是自我中心的文化,表现在对待动物方面,即为“物种歧视”。所以人道主义反思首先是从展示动物的悲惨境遇开始的。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描写了“文明狗”巴克被人折磨而至野化的遭遇;其另一部小说《白牙》中的白牙,不仅在肉体上遭到人无情的伤害,而且还在精神上受尽凌辱。作品所流露的多是对动物的人道关怀,其中的情绪感染强于理性思考。显然,这类作品在关注动物遭遇的时候,通常将矛头指向人性。狗的意象往往成为人道主义、人性的载体,凸显的是“人性”,而非本体的“狗性”。
就中国文学而言,很少针对某一种动物书写其本质的属性,往往通过寄兴手法,言此而意彼。新时期以来,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难以继续主宰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通过种种外在意象来寄寓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狗”意象成为了张贤亮、巴金、冯骥才等人笔下的隐喻系统,人与狗之间的命运纠葛,展示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世界。
张贤亮的《邢老汉与狗的故事》中,狗成为一条贯穿全文的人道主义主线。它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1〕小说开头定出一个基调:“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和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的。”在配合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提之下,朴讷、勤劳、本分的农民邢老汉,并未能按照传统中国农民的娶妻、生子,温饱有余的简单理想中度过他的一生,而是一再遭遇错误路线的无情摧折。当他张罗着建立家庭的时候,农村“大跃进”运动不仅没有兑现“共产主义”的许诺,却让他一再失去组建家庭的希望。70年代的大饥荒中,与逃荒女子温暖却短暂的生活很快结束,为了排遣失去女伴的寂寞,老汉养了一条黄狗。但作为他生活的唯一安慰和寄托的狗,也在当时匪夷所思的“打狗运动”中被枪杀了,邢老汉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下凄然老去。这是一曲凄婉的挽歌,又是一篇极其严厉的控诉辞,也是民间朴素情义的深情颂歌,朴实、沉郁、凝重而又动人心魄。
在张贤亮的笔下,狗是逃荒女人的替代,也是一群小人物之间民间情义的隐喻。在邢老汉与逃荒女子之间,作者并没有用“爱情”这样的词语加以描述,在邢老汉与村民之间,也没有用同志般的温暖加以体现,只是一种民间社会最为朴素的情义。然而,在张贤亮看来,造成老汉悲剧的原因,不是某些具体的个人,真正的凶手是当时非人性的极左政治路线。即使对那些枪杀黄狗的民兵,也没有给予过多的指责,他们与队长魏天贵一样,也是迫于无奈。狗的意象只是一个外在的叙述载体。作家用外在的人道主义叙述,控诉和揭露当时极左的政治路线。因为越是渲染人与狗的感情之深,就越是反衬出失去狗之后的孤寂和悲伤;越是强调黄狗是老人唯一的安慰,就越能揭露极左政治路线的非人道。这个外在的符号载体,决定了小说文本的脉脉温情只是一种政治的情感,而非入肌入理的人性思考。狗的形象,没有走进,也无法走进人性的纵身之处,它只能通过一种外在的变化,达到悲剧气氛的渲染。
本质上,这种动物形象与人道主义的审美追求相结合,正是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文化体现。看似笨拙的叙述方式,颇类似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和话本小说,具有一种土头愣脑的、质朴的民间风格。“田螺姑娘”,狐仙,花妖,等都是将动物人化,将民间最基本的人性关怀、人道主义情感融注在一个外在的动物身上。一方面,赋予动物人的性情,人的爱恨,成为人们一定时代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狗的形象的出现,在政治情感充盈的文本中,扩展了文学弥足珍贵的诗意空间。张贤亮的小说正是通过这一动物形象,缓释了文本中无法掩饰的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情绪冲突。狗的意象最大的成就恐怕就是将政治情感和民间情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作家苦难控诉的目的。
二、文化之根的符码
如果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的叙述支点在于情感的寄托,其中将政治情感和民间情义比较完美地在外部进行缝合,那么,郑义笔下狗的形象则反映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提供了适时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之根。
《远村》在叙事结构中始终并存着两条线索。一条讲述老羊户杨万牛的情爱悲剧,另外一条则是牧羊犬黑虎的生平行状。两者在叙述过程中交替出现,相互对照。杨万牛在退伍后,才发现恋人叶叶以换亲的方式无奈嫁给了四奎。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以“拉边套”的方式继续着这痛苦而无望的爱情,直到叶叶执意要为他生一儿子而死才告结束。相对于杨万牛的被动、无奈、压抑和扭曲,另外一条线索的“主人公”——牧羊犬黑虎似乎活得更象个“人样”。在小说里,黑虎是一只穿行于山野的自然精灵,既热烈奔放地追求爱情,又毫无畏惧地与凶残的狼虫虎豹博斗,活得汪洋恣肆,死得悲壮崇高,映照得受世俗羁縻的人黯然失色。相比之下,杨万牛的民间生存空间显得落后、壅闭、贫穷、保守。
郑义的目的是“写他们这一代人为了土地和自由的英勇战斗,写他们的艰苦劳动,写他们被扭曲的爱情……这被扭曲的爱情婚姻关系中,竟深蕴着那么纯素无华而感人至深的东西。”〔2〕(P27)作家没有设置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立面:深陷民族传统习俗之中的人是软弱的,而作为动物的黑虎则是强悍、勇猛。杨万牛、叶叶等人无奈而又坚韧地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他们没有黑虎那般热烈奔放,纵横恣肆,却有着人类生存的韧劲,这一点和黑虎身上的勇猛无惧达成一致。作家希望将黑虎身上体现出来的原始生命力注入到无奈而又坚韧的肌体中去。
在张贤亮的笔下,“狗不时地用湿漉漉的、柔软的舌头舔他的手,会使他产生一种奇妙的柔情,并联想起和那个要饭女人生活时的种种情景;狗的那对黑多白少的、既温驯又忠实的眼睛,能唤起他对她一连串回忆,使他进入一个迷蒙的意境,因为那个女人的眼睛同样是那样的忠实,那样的温顺。”狗的人化,本质是一种人道主义化,其身上主要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涌动的温情和民间的情义。狗被当成一个人来写,而对于狗的动物习性则很少关注。在郑义的笔下,黑虎则是一条活生生的,散透出原始狗性的牧羊犬。为了保护羊群,它勇猛无比地杀入狼群,并用自己的生命与豹子相拼。黑虎代表的正是一种经过人化,却又保持一定原始野性的民间话语系统,而杨万牛、叶叶等人则是坚韧地挣扎在民间伦理系统之下。杨万牛的回忆、梦和幻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闪回跳跃,呈混乱无序状,与人类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形成同构关系。而黑虎的故事则采用朴素的时间直线推进方式,以隐喻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之昂扬奋进,舒展放达。二者在民间层面上达成一致。因此,《远村》没有一般寓言小说那样太强的文化功利性,也不以居高临下的俯瞰姿态来启蒙与拯救民间的生存民众。他无法厚此薄彼,而是将狗性的一面契入人性之中,在狗性与人性之间寻求一种理想的沟通途径。如果说贾平凹高举自身的人性之镜,将商州的民风民情作一番唯美的过滤,那么郑义则是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完成民间文化的审视和生命能量的激发。
近年来一直畅销的《藏獒》则以精神符号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野。作者写藏獒,有一种直接用动物精神启蒙人类的冲动。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作者将自己对人性的美好愿望寄寓在一群藏獒身上,这群藏獒就是一群人化的藏獒,它们身上集中人类所应具备的美好品德。作家在小说结尾不能自已地写到:“那种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那种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在那片你只要望一眼就会终身魂牵梦萦的有血有肉的草原上,变成了激荡的风、伤逝的水,远远的去了,又隐隐地来了。”〔3〕(P347)过去我们非常熟悉的词汇,透过一群藏獒向读者传达出来,简直是一部感人至深的道德文献。透过这群道德化、人化的藏獒,完成了一次时代人性理想的呼唤和拯救。
藏獒世界就是一个人化的世界。冈日森格与饮血王党项罗刹角斗一场,仿佛不是动物之间的角斗,而是侠客之间的人格较量。大黑獒面对主人要它咬死冈日森格的命令,而自己对冈日森格又产生感情的情况下,无法选择而撞墙自杀。大黑獒那日在大雪灾中如何用自己的奶汁救活了被困在帐篷里的尼玛爷爷一家四口,白狮子嘎保森格在失败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而跳崖自杀。这些狗性,本质上已经远远不止于人性的境地,已经成为一种神性,一种现代人的宗教。当现代人被困于自己所建造的水泥建筑之中,传统的道德体系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支配下已经岌岌可危,《狼图腾》、《藏獒》相继问世,体现了当代人在市场经济下的时代文化心理,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的集体情绪。在小说后记《远去的藏獒》中,作家将狼和藏獒进行了一番比较:“狼是卑鄙无耻的盗贼,欺软怕硬,忘恩负义,损人利己。藏獒则完全相反,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藏獒一生都为别人而战。狼以食为天,它的搏杀只为苟活,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狼和藏獒,不可同日而语。”〔4〕
其实,无论是狼性还是獒性,都是当下人性的不同维度。当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观念不断遭到消解,新的道德观念尚未建立时,充满野性的狼性和具有神性的獒性自然闯入人们的视野。恐怕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精神中缺乏人类最重要的心灵资源,缺乏永恒的神圣的内心真正服膺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于是不得不臆造这类獒性崇拜来充当替代品。很显然,《藏獒》的问世无意中承担了特定的文化责任,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符号。问题是一旦这种文化精神成为小说确定不二的主题时,小说本身成为一种道德文献,必然牺牲小说本该具有的文化复杂性和精神深刻性,流淌在文本当中的仅仅是一股难以遏止的道德激情和教化冲动。
三、底层境遇的写照
关于“底层”的叙事一直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重要的一脉。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底层”被赋予了“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性内涵。因此,在任何时代,无论是被允许还是被禁止,“底层叙事”总是首先在“道德”上占据话语高地。近年来,“底层叙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具有“思想时尚”意味的热门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故事”的讲述往往借助于一定的意象来表达作家的叙事态度、道德立场。透过“太平狗”眼中简单化的阶级图景,陈应松作品更多倾向于一种“类型化”的、仅凭一点道听途说即可想象的“底层叙事”,传达一种“人不如狗”的底层生活状态。
相比较于其他作家将狗性作人性来写,或将狗身上的野性和忠诚努力注入到人性中去,体现一种道德文化的传递,陈应松的《太平狗》中,则将一只山狗与民工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结合起来,狗的形象不仅仅是忠诚和生命的坚韧,更是底层意识的表现符码。小说叙述的笔触沉到民工生活的底层,让一人一狗走进最恶劣的生存困境,状绘最原始的绝命厮杀,书写他们人不如狗的骇人场景和悲惨命运。
一条名叫“太平”的赶山狗,带着与主人一样的城市想象,离开神农架来到城里。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深山的程大种,一心想着到城里来打工,自然是不方便带着一条狗进城,他粗暴地打它,砸它,直至打晕过去。在他心目中,赶山狗属于乡村的符码,而城市则是明显高于乡村底层的文化想象。城市想象的高位使他无法顾及人狗之间的自然真情,而狠心将跟随的太平一顿痛打,这集中折射了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主人进城打工的迫切与和期望。可太平还是凭着气味跟上了主人,和主人一起来到了城市。
从乡村符码转换到城市符码,人与狗的命运完全被捆缚在一起。一条狗,一个人,在这个庞大芜杂的城市里,在这所谓的“太平盛世”里,人的命运象狗一样的贱,被歧视,践踏,欺骗,甚至杀戮!城市人认定“太平”是一条疯狗而要将其打死时,程大种竟然将自己的手放进狗的嘴里,证明“太平”不是一只来自山野的疯狗。脸上的兴奋与淋漓的血手,映衬的是市民的冷漠与隔阂。程大种“城里”的亲姑妈“像个泼妇”,“怀着绝世的仇恨在屋里保持着沉默”,以致把来自家乡的侄子和狗拒之门外;程大种打工的几个地方也“照例”存在着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超大、劳动所得被盘剥、生命被贱视乃至被草菅等现象;而土狗太平九死一生的遭遇也充满着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狠劲儿……每一个场面都血腥、肮脏、悲惨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当我们读到“为什么这样对待一条狗?为什么对这条狗有如此深的仇恨?”时,不由联想到过去的阶级图景。城市人、城市物被打上了“极尽凶残”的标签,而程大种等民工与土狗太平则被摆在一个被“随意蹂躏”的位置,完全可以套用“城市把人变成狗”的说法。因此,阅读小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妖魔化之后的城乡对立及由此产生的仇恨。这样意图明确的“主题先行”,不但让作者试图融贯其中的“激情”变为矫情,而且让读者对这种叙事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说这一文本对外部复杂世界的认知。人的狗化,体现了人们对底层话语的关注,也容易导致对底层话语的过分渲染和盲目青睐,缺乏文学应有的节制和隐忍。
反过来,陈永林的《毒不死的狗》中的狗为何能不死?因为它是村长家的狗。这只狗为害村里,想毒死它的村民都怕村长怪罪,所以,吃了掺毒食物后的狗倒在谁家门口谁就赶紧救活它。小说中被异化成一副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模样的狗正是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力象征,它凌驾于众多的底层民众之上,失去了“狗性”,却承载了乡村社会太多的辛酸与恐惧。围绕着狗发生的荒唐故事,作者走进底层民众生存的状态与空间,触摸到乡间社会的文化根本。
四、性的隐喻符号
“性”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人类的一种生理本能。它以力比多为衡量尺度,能够突破生理层面,直接进入社会层面,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命题。如果性能在其生理层面上自由的发展,不受道德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压抑和干涉,就能将人引向一个自由、率性的发展方向,体现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机。相反,产生性压抑的人,会逃脱意识的控制而宣泄自我感情,这时便产生了性的异常,通常转移到对自己的迷恋或者对动物的依恋。很多文学作品以“狗”意象来暗示或象征爱情或性爱,揭示人性深处一些神秘而又永恒的内涵。
王凤麟的《英格兰警犬》中,那条叫英格兰的狗在与女主人桂香一起出现时,是一个性符号。桂香在与狗亲昵时,内心一直存在这样对狗的认可:“你真是一条好狗。我真希望你不要离开我,永远和我呆在一起”。她想着,脸竟有些红,因为她对丈夫郑炮也经常说这类话。在郑炮出门时,狗与她的亲密可替代她与丈夫的亲昵。贾平凹的小说《五魁》里,开篇就写到狗对新娘子的追逐。小说中处在性饥渴中的少奶奶竟然与狗同眠。当狗被害死后,少奶奶遂走上了自毁面容而自杀的道路。《美穴地》中,掌柜的性生活能力差,不得满足的四姨太养了虎儿与自己亲热。在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中,作者把性压抑和性渴望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通过一系列狗的意象来表现文革年代的禁欲和改革时代的纵欲。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两只狗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交媾,引发了处于畸形岁月的人类强烈的好奇心。狗的任情任性与人的欲望禁锢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兴致盎然地观看,进而不能容忍它们,在它们生命的自然力张扬到极致时戕害了它们。第三章《冲动》中,动物园饲养员赵敬东暗恋漂亮的表姐张闹,竟把一条母狗想象成张闹,并与其发生关系。显然人狗之间的畸形关系,注定了小说的悲剧性结局,这是对文革时代压抑人性罪恶的控诉,而狗与人在性的层面上发生联系,则缘于作者对人性深层机关的触摸。东西指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这好像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就像卡夫卡敢把人变成甲虫,纳博科夫挑战道德禁令。”〔5〕狗的意象使作家“摸到了写作的开关”,承载了性所代表的人性深处的一些永恒。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时期文学的狗形象一直是工具型的,一直被当作叙事的修辞策略来运用,狗之本体意义上的生命存在一直未被人们严肃思考过。为了突破一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束缚,或者文化观念的统摄,处于表达焦虑状态的当代作家总是将狗的意象负载上一定的文化精神,将狗性书写转换为各种文化符码,为小说文本涂上了浓厚的文化意味和社会意义。在这些文本中,人与狗之间有了文化或精神的张力,形成了一个紧张而又深远的诗意空间。然而,作家赋予作品过重的文化负担,狗性在一种人性、神性的解释性叙述方面承载了太多,阻碍了作家真正走进人狗互动的世界。真正的文学生态,应该既要肯定“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也需赋予狗世界自身的独立性。
〔1〕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N〕.文汇报,1986-9-8.
〔2〕郑义.远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杨志军.藏獒〔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杨志军.远去的藏獒〔A〕.藏獒〔M〕·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东西.东西与《后悔录》〔N〕.广西日报,2005-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