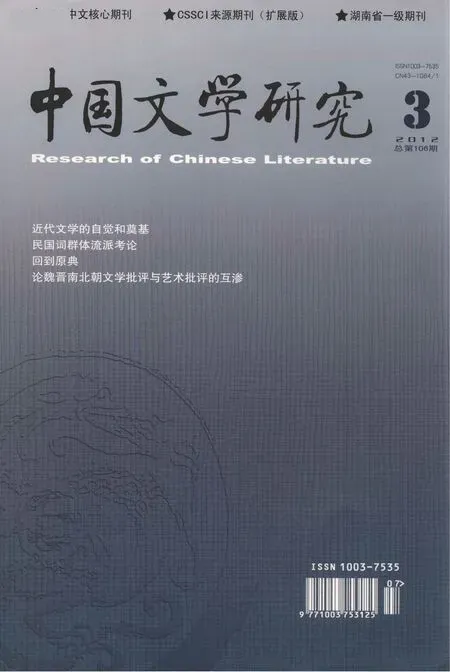理想与目标的契合——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周晓平
(嘉应学院文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诗界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它的酝酿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并非哪一个人在思考“诗界革命”,同样,它的历史成果也不是归结为哪一个人的功绩,它是一个整体的力量推演而走向终极。但是,“诗界革命”的成功却离不开黄遵宪,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黄遵宪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诗界革命”的历史标杆。
一、“招牌”与“实绩”——“诗界革命”的“名”与“实”
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正式提出了“诗歌界革命”的口号,它生动地反映了诗坛的变革要求和改良派诗歌创作的兴旺发展。诗歌界革命”的口号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是极其有力的批判和否定。它所要求的创新是在外来思想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在诗界“锐意欲造新国”的自觉努力〔1〕(P11-13)。
这个口号的提出,固然重要。起码在文学领域都有一个基本印象,而且了解是怎么回事。但是“诗界革命”不能仅仅是口号的提出,对于它的推行,“不能光打雷不下雨”,而要有实际的“干货”,梁启超们似乎缺乏的就是这种货色。梁启超在现成的基础上,当他认真阅读了黄遵宪的诗作时,那种赞美和推崇是发自由衷的。他的有关理论是建立在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实践之上的。比如,梁启超根据黄遵宪的诗歌创作整理并提出了“旧瓶装新酒”、“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一套理论,作为“诗界革命”的目标追求。进而认为,文学先注重救国,后注重诗歌审美,既可改良群治,又可有益人生。正是这种历史潮流的汇流,在诗歌理论与实践上,黄遵宪与梁启超达成了相当程度的默契。“诗界革命”的潮流,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两者建立了“恩师与益友”的良好关系。他们很快将自个的理论和创作汇入到“诗界革命”的洪流之中去。进一步说,黄诗对诗界革命的影响当然与梁启超的极力推重有关,而黄诗之所以受到梁启超的推重,是因为梁启超本人深受黄的诗歌影响。不是梁启超将黄遵宪的诗作拉进了诗界革命,而是黄遵宪的诗作通过梁启超对“诗界革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一种“船”与“水”的关联。例如,为了使诗歌充分发挥“感人”作用,以“开民智”,他们把视线转向民间或转向国外。黄遵宪在1902年与梁启超书,他建议《新小说》上的诗歌形式不必模仿古人,而可以采用“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名曰“杂歌谣”的形式,它立即被梁启超所采纳〔2〕(P37)。
谈到“诗界革命”,有人常常把梁启超看成是重要的推手,然而,相对于黄遵宪,梁启超还有一定的差距。梁启超是一个宣传家、社会活动家,作诗不过作为风雅政客的点缀,并没有下过大的功夫。对此,他名言不讳:“丙申、丁酉间,其《人境庐诗》稿本,留余家者两月余,余读之数日,然当时不解诗,故缘法浅薄。”〔3〕(P4)“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3〕(P66)既“不解诗”,又“不能为诗”,当然不会潜心研究诗歌的历史和现状,更不要说深谙诗歌的发展规律。客观地说,他的诗歌革新理论主要是从别人的创作中提出,自己切身的创作体会并不多。实际上,他是从变法前对诗歌的不重视,转发为热情鼓吹“诗歌之用”的。显然,他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不免带有某种程度的疏阔,多一些随心所欲。可是黄遵宪则不同,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变革与诗歌变革有机的融合;另一方面也是顺应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这样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诗歌理论就具有厚实的历史性建构。
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体系和创作实绩早就呈现,它甚至在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数十年就存在。梁启超鼓吹“诗界革命”的《饮冰室诗话》,便对黄遵宪作了几乎无以复加的赞许,把他推为“诗界革命”的首席代表。无论黄遵宪本人还是其他改良派人事,谁也未曾对此提出异议。“诗界革命”是“先有实绩,后有招牌”,换句话说,在“诗界革命”之前,黄遵宪就做起了“诗界革命”的工作了。也是在《新民丛报》时期,诗界革命在进一步发展起来,黄遵宪的诗歌不断向前发展,声名远播,在理论上和创作的实践上双双达到完全的成熟。这时他的诗作被梁启超明确推为“诗界革命”的理想目标,他的“别创诗界”的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诗界革命”的纲领。黄遵宪身体力行直接在“诗界潮音集”发表诗作。于此,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诗作十分推崇。
二、“诗界革命”的宣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这样写道:“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杂感》)从20多岁的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口号开始,它就预示了“诗界革命”的迟早发生,它表现出“诗界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也表现出在这个历史必然中黄遵宪的历史推动。然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年轻黄遵宪即使很早地提出了那些理论,但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其影响不免边缘化,尽管有“我手写我口”这样重要的理论。甚至有人歪曲地认为,它是年轻黄遵宪一时的感性之作。只是到了后来,黄遵宪名气大了,其诗歌理论及创作才有了影响。而梁启超在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时,黄遵宪已是功成名就了,“居高声自远”,梁启超提出的口号虽然迟,但也不碍黄遵宪诗歌的影响和传播。
《夏威夷游记》标志着“诗界革命”的真正开始,或者说标志着“诗界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自觉的发展阶段。“诗界革命”完全成熟的标志,是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专栏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主张,作为“诗界革命”的理想目标。梁启超的所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里蕴含了一种古今诗歌的继承关系,与当初梁启超所提出的所谓“新诗”——“以撏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相比较,这时的梁启超诗歌理论才比较成熟了。从字面的意义来说,“旧的风格”就是古诗的风格,所谓“新意境”就是诗歌创作要有新思想、新内容、新材料。这一目标,比“三长具备”①的要求又进了一步,已不在强调“新语句”的有无。黄遵宪诗歌自然更加备受青睐:“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诬也。”〔3〕(P37)有人对于“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理论含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并不能代表“诗界革命”的方向,认为这是变内容而不变形式的一个范例。认为诗歌变革,虽然是内容决定形式,但诗歌的形式同样可以反作用于内容,如果按照梁启超的思路,势必出现内容与形式的“终必会出现牴牾”的现象,并运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勃兴的“新诗”,试图证明之。这当然代表一种较高的要求。其实梁启超的“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理论,强调的是诗歌的继承,过渡时期的诗歌,必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必揠苗助长。早在1868年,黄遵宪认为,俗儒的陈腐观念已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人们的创作灵感,吟诗作对陈陈相因,拾人馀唾,六经无所,不敢写诗。〔3〕(P89)为此,年轻的黄遵宪对复古派的古典诗给予了嘲笑。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这一口号无疑是当时诗界的一声反叛的号角。“五四”新诗时期,胡适说:“我常想黄遵宪当那么早的时代何以能有那种大胆的‘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并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4〕(P29)
黄遵宪论诗的终极目标,即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不断地进行创造,以写出“真我”之诗。毕竟,黄遵宪也深受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的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古”的“拘牵”,尤其在他的旧体诗中受古语、旧典、旧诗体格律的影响还是蛮深的。但是他深谙这种影响的利弊,正因此,黄遵宪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进行革新。他为了摆脱“古”的“拘牵”,他想“自立”,用“流俗语”写出“我之诗”,用“我手写我口”理论来规范自己的创作方向。“我手写我口”是相对于“古的拘牵”的对立面来说的,诗歌创作要杀开一条新路,就是要突破古诗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严重束缚,还其自由之本色。其目的就是要颠覆“古的拘牵”,创造“手”与“口”一致的新诗,表现了一定的革命性;也反映了诗人要求对旧诗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较为全面的批判的精神。
黄遵宪《杂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他诗论的文化哲学基础〔5〕(P103-104)。这是“诗界革命”的先声。1891 年,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具体地提出了诗歌创新的主张,从诗歌的语言、形式、风格等方面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他直接称自己创作的诗歌为“新派诗”。与他随行的“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还有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但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成为失败新派诗的代名词;夏曾佑的《绝句》诗,以冰期、巴别塔地质学“新名词”及《旧约》中的神话入诗,完全是呓语。他们的实验之所以失败,就是好高骛远,缺乏诗歌创新的扎实的根基。这种“新名词”在诗界革命初期夏曾佑、谭嗣同的所谓“新诗”中是可以找到不少的。所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3〕(P328)只有黄遵宪的诗,才是真正的“新派诗”,他对于诗歌的创新,建立在前人发展的基础之上,对旧式的诗歌内容与形式进行“扬弃”。梁启超认为黄诗之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两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
三、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内在发展要求
从1877年起,黄遵宪出使国外1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除了中间的偶尔回国之外,他一直生活在海外。这种视野极为宏阔,欧风美雨的影响包括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对他触动颇深,感慨良多。黄遵宪以无比的好奇与崭新的眼光看待西方的世界,新生事物在他面前便焕然一新。观山赏水,抚今追昔,更加激起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评判古今,表现为不同一般文人的高瞻远瞩;对待新事物的热烈赞颂与支持,总表现为站在时代的前列,揭示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深情呼唤之;反映国内外政治事件,以国家、民族的高度,表现出忧国忧民和变发图强的主张。因此,诗歌的生活题材得到巨大的拓展,新风格、新意境不断得到铸造。诗歌创作在黄遵宪的笔下成为了无所不能表达的新鲜艺术。应该说,梁启超诗歌改革的理论“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意境”,黄遵宪落实下来了。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在诗歌理论上还主张思想内容的创新。他认为新派诗应有“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6〕(P79)。这种所谓的“物”与“境”,在他看来就是,首先要取材、叙事十分广泛;其次,更重要的是要“采近事”,特别是要引进西方的观念。黄遵宪与一般士大夫不同之处就是他所具有开放的思想。所以黄遵宪的诗被称为“诗史”,这就是他“采近事”之功。而且,黄遵宪把“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歌主张推向了发展,而着手了诗歌形式的“革命”。
当然,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毕竟不像酒和瓶子关系那样简单。黄遵宪毕竟不是梁启超,长期的诗歌创作经验使他探索了一条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正是从这个规律出发,他认为,诗歌内容发展了,诗歌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诗歌形式的问题亟待解决。他身体力行地在诗歌的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新。他主张诗歌创作形式的“散文化”,“以文为诗”,追求诗歌表达的形式自由成为他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特点。例如《旋军歌》〔6〕(P351):“金瓯既缺玩复完,全收掌管权。胭脂失色还复还,一扫势力圈。海又东环天右旋,旋旋旋!”、“辇金如山铜作池,债台高巍巍。青蚨子母今归来,偿我民高脂。民膏民脂天鉴兹,师师师!”长句、短句参差互用,主要表现为七五、七五、七三句型,读来非常顺口流畅,很有气势,很能体现“诗界革命”的发展要求。
然而,考察还不能到此为止。只要梳理和考察一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到现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梳理和考察一下自1898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梳理和考察一下以黄遵宪、梁启超的从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分化出来并转变为晚清到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的全部历史活动,是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诗界革命”绝不是一个孤立出现和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黄遵宪、梁启超们以改造社会文化为终极目标、以改造中国文学为实施步骤的一个带有阶段性与全局性的“一揽子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更明确地说,“诗界革命”是和他们相继发动的“文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构成一个相互联系与影响、相互推动与促进的有机整体。他的诗论是全面变革封建文化思想的文化革命论。因此,旧文学的改造和新文学的创立,不是从“五四”,而是从此时就奏响了声震寰宇的序曲。“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当然是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形式,“诗界革命”以这样的诗风作为理想目标,无疑,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预演。因此,黄遵宪的诗歌主张与“诗界革命”运动的理想目标也完全相契合的。
〔注释〕
①所谓三长,即:“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1〕张永芳.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张宜雷.近代文学变革散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N〕.《申报》1924年版:29.
〔5〕参见张应斌.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J〕.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4).
〔6〕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