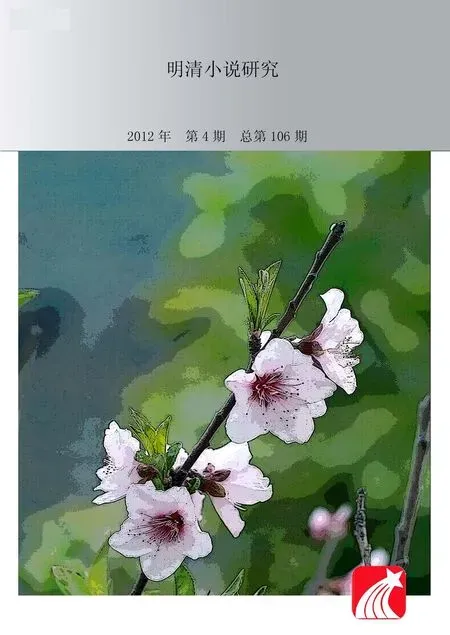林纾小说翻译实际收入新探
··
林纾翻译所得甚丰,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开的,令世人津津乐道的趣闻谈资了。相信他晚年频频得子、“有人王霸子成群”地让友朋纷纷艳羡之外,“林译小说”每年不间断大量问世带来的“天”字号稿酬,同样也会让众人为之动容,甚至有伊索笔下的狐狸够不到葡萄后的那种酸溜溜的味道。
一、“造币厂”一说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先生提到了林纾“造币厂”一说。
前期的翻译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①;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转变为中文作品,而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假如翻译工作是“文学因缘”,那末林纾后期的翻译颇像他自己所译的书名“冰雪因缘”了。
文中所加的注脚引用《续闽川文士传》来介绍“造币厂”一说的来历,它说明钱先生的说法其实与乃师一脉相承。在《林纾传》中,陈衍曾评道:
(纾)作画译书,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②
师生的说法两相对照后,发现钱钟书称引的字句有两处讹误(辍作“缀”,即作“辄”),也见证了年少轻狂的钟书君更加苛刻。因为陈文下面还说到林氏的仗义疏财,而钱钟书则一味声讨林译到后期进行的“买卖”、“货币”转换,直斥其已沦为唯利是图了!
周作人的个性倒是蛮直爽,坦率得很,吐露了自己对林翁稿酬嫉妒得眼红的不满来:
倘若别人也有这样的利益,我想,在半生中译成二百种书,——即使是独立译述,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30年代出版的寒光《林琴南》,引用了周氏上述评价后,毫不客气地指出,“周先生批评林氏的文字”,“统是无理的挖苦”,并且质问批评者:“周先生他的稿费现在不也是很值钱吗?说不定有时在六七元以上,为什么他不肯动手像林氏那样译出好好坏坏将近二百种的外国文学来给我们后学研究和欣赏呢?”③
可见高酬与丰产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肯定也会是文人(如林纾)决定从事某项工作的一种动力。
二、高估与林译实际字数
既然林纾稿酬甚丰,那么我们若是再追问一句:到底“丰”到何种程度呢?这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甚至可以说是学界至今还夹缠不清的话题。
最近书籍非常走红的陈明远先生,用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现代文人的收入问题,出过一本类似“鲁迅经济学”的专书(《鲁迅时代何以为生》),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他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为林纾在商务印书馆的收入做过一番详细的统计:
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受读者欢迎。他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140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2~3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6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译述小说共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1995年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可见由于林纾翻译小说的畅销,所得稿酬超过了一般规定的两倍。④
这种计算堪称是对前人所谓林纾翻译工作室宛如“造币厂”最形象的现代解读了。按照这种上千万元的稿酬收入看,林纾岂不可以列入时下韩寒、杨红樱等当红最牛作家的富豪榜之内了吗?难怪陆建德先生那篇为林纾辩污的文章《不妨略剖卖文钱:“企业家”林纾与慈善事业》(《中国企业家》2008年18期),俨然将林纾归入因成功而热心公益的“企业家”的行列。
其实仔细瞧郑逸梅的相关说法,也不是前后一律的。他的另一篇文章《林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中说,商务给林纾的稿酬是每千字十元⑤。
而顾颉刚的回忆是“五元”,他曾说:“圣陶尝告我,谓商务印书馆购小说稿,以林琴南氏稿出价为最多(每千字五元)。”⑥
我们再看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专家,已出版了两部林纾研究专著的樽本照雄先生的估算吧。在他的《林纾研究论集》内的《林纾落魄传说》一文中,樽本先生认为“五四”后的林纾在经济收入上远非“落魄”,而是极其充裕,多得足以叫板对手蔡元培校长的收入。不仅自奉有余,且能扶贫济困,广做善事。而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一般教授的刘半农、钱玄同等则更是望尘莫及。
在林译收入的统计上,樽本先生也与中国学者迥异:他采取了“保守”的林译小说的字数统计法,每部书以“10余万字”计算。19年“1200万言”的林译作品,乘以“1千字6元”,得出了“72000元”收入的结论⑦。比陈氏的估算(20万)少出了一半有余。
为了搞清中外学者在“林译小说”每部书的具体字数上的出入,笔者又进一步查证了林译序跋中林纾本人提供的相关数字: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凡八万余言”。
《云破月来缘》“可十万言”。
《深谷美人》“余以二十五日之功译成,都五万四千余言”。
《橡湖仙影》“可十六万言”。
《迦因小传》“都十三万二千言”。
《冰雪因缘》“迭更司先生叙至二十五万言”。
《块肉余生述》“分前后二篇,都二十余万言”。
《歇洛克奇案开场》“寥寥仅三万余字”⑧。
“近译得小说二部,约二十四万字”⑨。
这十部书共计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余言,平均十二万四千余字。
而陈希彭在《十字军英雄记》叙中也说:“计吾师所译书,近已得三十种,都三百余万言”。
可见林氏本人及其学生估算的每部小说,字数也约在十万上下。
即使以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的林译小说丛书来验算,出入也不会太大。十部书的字数分别如下(单位/千字):
《离恨天》48;《吟边燕语》72;《撒克逊劫后英雄记》140;《拊掌录》38;《黑奴吁天录》124;《块肉余生述》297;《巴黎茶花女遗事》51;《现身说法》112;《迦因小传》151;《不如归》68。
平均一部11万字。扣除标点符号所占约五分之一的字数,一部应该不足10万字。
因此,按照林译小说每部10万字的规模,陈先生给林译小说收入算出的天文数字(合1995年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应该像日本学者那样减半才是。
三、令人想不到的分润问题
或许更令今人感到困惑的是,文人经济学研究角度给出的林译收入,即使保守性地减半之后,也不一定就是林纾最后的实际所得。
今人津津乐道的林纾创造的一桩奇迹是,他是“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那么与之合作的口述(兼笔译)者是否就不分润,完全做林译小说的免费义工呢?林译的高酬扣除合作者应得的部分,那么还会让世人艳羡不已吗?
包天笑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为林纾收入算过一笔还不糊涂的帐:
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⑩
林纾与人分润一事,他自己在一封书信中也有交待:
献丁贤弟足下:所译书恐晚来有酬应之事,不如移作日间三四点钟中多译千余字,赶一礼拜中译完。即不完,一礼拜后,明日起以夜补之。后此吾弟可自译抄好交来,愚为改删(王庆通亦然)。其所得润六成中,愚分三成有五,吾弟则二分有五,钱较多而工较省,愚亦省费时日,吾弟以为如何?(以弟之笔墨,经愚一改,必可成。万万勿疑)兄纾拜。
献丁为陈器,福建闽侯人,一字献琛。林纾与他合译过《深谷美人》、《痴郎幻影》。从林纾写给他的信看,“六成”中林纾得“三成有五”,陈器则“二分有五”。也就是六元中,林纾需分二点五元给他的合作者。
按照林纾这封信和包天笑的记述,可知林纾自己拿到的商务高额稿酬(六元)经他从中剖分,其实际所得仅为一半有余。
那么,被陈先生算出来的林纾1000万元收入,按照每部实际字数减半之后,还要再减半。剩下来的约有300~400万,还是多过樽本先生计算的7.2万。其中间差异,来源于未按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数值进行换算。民国初年(1919年前)1银圆的购买力约折合2009年人民币100元。如此相乘,则7.2万折算后应该是陈先生或许认可的720万(扣去口译者的分润,则有约400万)。
四、从捐赠到主动索欠款
世人通常认为林纾稿酬高。李勇军《民国中期稿费标准摭谈》说:商务给林氏开的稿费为千字6元,而当时翻译稿费一般只有千字1~2元。如果能达到千字6元,那就是十分优厚的“高稿酬”了。因此他又以“特殊”稿费来看待林纾的翻译所得。然而谁又会想到,根据上面的分析,林纾稿酬不仅没有世人通常想象的那么高,而且他还向商务索讨过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欠款。
这件事与他初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合看,反映出晚清新兴的稿酬制度逐渐为文士接纳的曲折过程。
1899年,继林译《茶花女遗事》吴玉田刻本在福州问世后,汪康年在3月16日《中外日报》刊发“用巨资购得”《茶花女遗事》,欲“另用铅字排印”的广告,引起高凤谦去函表示异议。
于是《中外日报》5月26日又刊登《〈茶花女遗事〉告白》加以更正:
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昌言报馆白。
围绕此书在上海重印,汪康年、高凤谦(后来还有林纾)前后发生的纠纷,从一个侧面说明汪康年是意欲按照现代出版的方式给译者“重金”报酬的。然而不管是负责与汪康年交涉的高凤谦,还是出资在福州印书的魏瀚,均未萌生谋利之想。高凤谦即坦言:“现在所以发售者,不过欲收回成本,并无图利之心。”
包括林纾,在他移家杭州,经上海时专程拜访汪康年,不遇,留下二册《茶花女遗事》译书,在寄给汪康年的书信时也绝口不言“利”字:
昨阅《中外日报》,有以巨资购来云云。在弟,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唯书中虽隐名,而冷红生三字颇有识者,似微有不便。弟本无受资之念,且此书刻费,出诸魏季渚观察,季渚亦未必肯收回此费,兹议将来资捐送福建蚕学会。请足下再行登报,用大字写《茶花女遗事》每部价若干,下用小字写前报所云致巨资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兹某君不受,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合并声明。鄙意如此,亦两无所碍,想足下当可允从也。
在稿酬“巨资”跟前,林纾不愿取分文(“弟本无受资之念”),可谓是高风亮节。这位一生服膺理学的文人,身上颇有儒家那种“君子喻于义”的烙印。
可是到了林译后期,琴南在用翻译大量“造币”,广进财源,而译稿因质量问题亦让高凤谦不满之际,他照样开口向商务索要少算的稿酬。
按顾颉刚的回忆,叶圣陶曾经告诉他,“林氏亦慎计字数取酬,每馆中误数时,林氏辄去函补值云”。
有据可查的一次在1916年,林琴南致信高梦旦(凤谦),称过去十几年来商务支付稿费时,计算字数不够精确,前后少算了许多,希望能找补一些。因为林纾是老朋友关系,高梦旦不敢怠慢他,专门找了个实习生谢菊曾来处理此事。
谢菊曾刚进商务印书馆,办事相当认真。他从图书馆借出一整套林译小说,逐页重新核算被漏计的字数。最后,他发现以前计算原稿字数,遇到一行只有三四个字的即抹掉不算,而每行中碰到有添加在旁边的整行小字,也往往略去不计。逐一重新核算之下,谢菊曾发现被漏算的字数超过了10万。
林纾这次“找补”,最终讨回了自己该得的600多元(或许要跟从前的合作者从中剖分,各得一半矣)。
从翻译之初的捐款(助学)到后来的主动索欠,林纾最终完全认同了文人劳动所得稿酬是合理收入的这种现代观念。
总之,过去由于有关林纾“造币厂”说法的盛传,加之后人不去仔细辨别(忽视每部小说的具体字数、合作者的分润,还有商务的漏算),因此对商务印书馆给予他的稿酬不断夸大,最终得出了一个令人咋舌、艳羡却又徒有虚名的经济学“天文”数字。对当事人林纾来讲,其实际收入却并不尽然,真正是枉担了一世“造币厂”的盛名“美”誉了。
注:
①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钱文原注脚为:前注[25]所引《续闽川文士传》:“[纾]作画译书,虽对客不缀,惟作文则缀。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辄得钱也。”参看《玉雪留痕序》:“若著书之家,安有致富之日?……则哈氏黩货之心,亦至可笑矣!”
② 汪兆镛《清碑传合集》三编,上海书店1988年版。
③ 寒光《林琴南》,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1935)版,第15、16页。
④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⑤ 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⑥ 钱谷融主编《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又见王勇《林纾与〈东方杂志〉》,《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⑦ [日]樽本照雄《林纾研究论集》,清末小说研究会2009年版,第285-286页。
⑧ 以上见阿英编《晚清小说丛抄·小说戏曲硏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⑩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六十九《在小说林》,(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