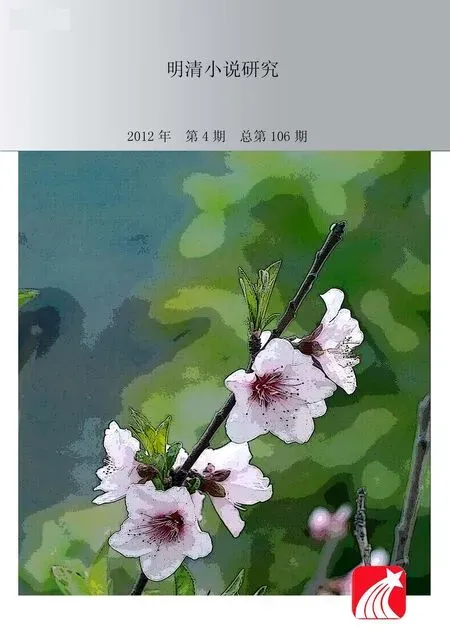社会认知与明清小说的理论转关
··
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迅速刊行,得益于大量生员加入小说创作队伍并作为小说的读者①,使得白话小说迅速在文人阶层进行传播。他们对此前小说的浅陋所表示出来的不满②,促使其对白话小说进行品评和改写,如苏州地区参加白话小说编改、创作的文人有18人,撰写序、评者16人,校阅、刊刻者15人,其中著名的有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纶、毛宗岗、褚人获等,皆穷困不得志,依靠书坊刊刻小说度日③。面向市民的白话小说,在明末有着广泛的受众④,刊书谋生便成为落魄文人的谋生手段。文士参与小说改编、刊刻、创作,并对小说的地位进行理论总结,从道德文章的角度来审视小说的创作与刊刻,不仅改造了小说叙述策略,提升了小说的表达技巧⑤,而且还从经史观念和文章创作的角度,对小说的社会功用进行了重新概括,将小说视为与经史、诸子、诗文相并列的文体,初步完成了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
一、小说文学功能的重新认知
郭绍虞先生曾言明人视六经为文,清人视六经为史⑥。意谓文学视角下的经典,不过是圣贤性情的表述而已,可以我之心思揣度一番;史学眼中的经书,那是事实的记录和典章的留存,只能持严肃之态度去考据。明人对经学尚且如此看待,对文学、史学自然更少拘谨。在他们看来,诗文传统的变化,是合着时代的节奏变动。今之诗文,恰是古典滋生出来的后代,如李贽就直接论到:“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⑦文既然没有古今之分,只要合乎世态人情,都是天下之至文,那么,晚明流行的小说,自然也是正统经史演变的产物。此一通脱论述,遂成为民间文士审视小说的理论基调。
标名“可一居士”的《醒世恒言序》径直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为导愚适俗,或有籍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把经、史排除出去,其余的诗文之类皆小说,这一说法还算客气。但随即就把作为通俗小说的“三言”,视为经、史的辅助,倒是认真。言外之意,通俗小说也与经、史有着相似的内容,自然具有同等的社会意义。对于这一点,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予以了解释:“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小说在魏晋时期,被列入史部,其所叙人和事本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获得与之相符的历史地位也正当其理,虽然小说尚奇,然立意存乎道德,故里巷之事,通乎朝政,俗民之语,合于经史。绿天馆主人言“史统散而小说兴”⑧,认为经书远比不上小说动人:“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能令人动容,自然入乎人心,远比高高在上的宣示有效得多,因而肯定小说与经典相当的“感人”的教化作用。金圣叹评价《三国演义》、《水浒传》,便是将历史与小说比对,肯定小说的史学价值。从史实上来看,他说:“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也。”⑨《三国演义》并非凭空臆造,而是事出乎史;从文法上看,“《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都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⑩,如此而言,这两部小说既合乎史实,又用史家笔法,确实与正史、经书可以相提并论。
演义小说合乎史学传统,而其中所蕴含的旨趣又与经学不谋而合。张尚德说《三国演义》“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忠、敬、节、义的敬重和对贪、奸、乱、佞的厌恶,要比单纯的说教更形象、更直观、更有说服力。夏履先刊刻《禅真逸史》,在“凡例”中言小说“处处咸伏劝惩,在在都寓因果,实堪砭世,非止解颐”,通过因果报应劝善惩恶,不单是令人一笑而过,而是寄托了深沉的道德示范和人伦劝谕。闲斋老人序《儒林外史》,也说“稗官为史之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认为史书的鉴识作用,小说同样可以担负,而且其人物情节与生活在当下的读者更为相近,人物际遇、故事情节感同身受,更有助于风俗教化。惺园退士也说:“余谓是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先师不云乎:‘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读者以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几稗官小说亦如经籍之益人,而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尔。”若能抱着省思的态度阅读,小说中的人和事要比经典的说教更引人入胜、更动人心魄。即便是写花妖狐魅的《聊斋志异》,高珩也期望读者“能知作者之意,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以贯之”,读出其中寄托的丑恶善良和人生感悟,体会到劝善惩恶的社会教化意味,认为其与六经圣贤之论遥相呼应,而且其征实意味的故事,更生动形象。即便被曹雪芹标榜“不敢干涉朝廷”的《红楼梦》,在王希廉看来:“虽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而子以其言为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实也?”有惊世骇俗的教化意义,更容易引发读者共鸣,承担更为深沉的认识社会和教化民众的责任。
明清小说家将小说视为经、史的辅弼,强调小说中所蕴含的劝善惩恶、关乎风教的作用,确实提升了小说的地位,努力推动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在这一提升的背后,却也反映出传统的以诗文为正统的文论力量对小说的抵制。这种抵制,与其说来自于阶层本能对“通俗”的抵触,莫不如说是程朱理学制约下的文统对小说“奇幻”笔法的反感。
二、“入于文心”与“偕于里耳”
明清小说家明确了小说不是“入于文心”而是“偕于里耳”,不再固守传统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以文合道,而是依照市民的口味进行创作,强调市民情调和草根精神,这使得小说的旨趣发生了根本转变。
中国小说本出自“作意好奇”,带有明显的“娱玩”的性质。即便用纪传体,也是为了形成一种“真实的虚幻”,在亦真亦幻中塑造人物、敷陈情节。明代小说批评家多固守诗文传统,批评小说的奇幻笔法,诟病处多在小说不合史实或现实的情节,将小说中的怪怪奇奇视为叛经离道。冯梦龙不否认小说情节、人物有真、赝之分,但在他看来:“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相对于史,通俗小说的差别在于是否“真”;相对于经,通俗小说的价值在于是否合乎教化。如果事真,那就当被视为“史”,不应当受到排斥;即便事“赝”,如果理“真”而合乎“经”,那通俗小说同样可以如经学那样担负起教化、鉴戒的作用。晚明小说论者不讳言小说的虚构,他们将之称为“奇幻”。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就对此进行解释:“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小说所描写的虽多为奇人异事,也只是以现实的逻辑对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剪切处理,其故事情节、人物际遇却皆来自于日常生活。睡乡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序》进一步解释到:“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夫刘越石清啸吹笳,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已经意识到小说中的巧合是现实矛盾的集中体现,人物性格是对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故此“奇”乃合乎生活实际,乃宗有其实。
将“虚幻”视为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正面承认,而且加以提倡,将小说从诗文征实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促成了明清魔幻小说迅速成长。袁于令就说《隋史遗文》言正史纪事以传信,遗史搜逸以传奇。传信者贵真,而传奇者贵幻。作为以传奇为笔法的小说,追求奇幻正是其传统技法。他还发挥《西游记》的笔法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正是因为奇幻笔法,小说情节、人物才能够尽情腾挪,有了开阖自如的情节和似幻似真的人物塑造。睡乡居士认为《拍案惊奇》之所以二刻,正在于亦真亦幻:“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其所捃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在“虚幻的真实”中,小说更富于社会真实感,能够在满足人们好奇的闻见渴望中,使人获得价值预期和心理满足,起到理论说教所无法达成的道德示范和行为引导。
示范和引导的前提是要“偕于里耳”,即小说文本足够通俗,才能引使最广大的受众阅读。蒋大器曾称赞《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能够被一般文人阅读,正是其广泛流传的缘由。张尚德也称赞其“以俗近语,隐栝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其作意就在追求以通俗而被于天下之人。作为书商的冯梦龙更清楚这一点:“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要面向最下层的民众,小说才能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其社会作用才更深沉广远。但他刊行小说的“通俗”,是相对于文言小说的古奥和民间说话的浅俗而言,而非尽用口语、俗语。这可以看作小说刊刻者的共识。蒋大器曾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单靠民间流传,会愈来愈下,最终流于浅薄。但文人小说又难免酸腐,胡应麟曾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故尔宋元明大量笔记小说,难以在民间流播,皆在其言深奥。因而冯梦龙、凌梦初在改编、刊刻时,意识到“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而应按照市民的阅读习惯,且依照文人的眼光,“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提纯了民间白话的叙事能力,加强小说的感染力与表现力,得到民众的喜欢。
小说成为明清文学的主流,得益于白话的使用,尤其是以“谐于里耳”作为立足点。钱大昕就肯定白话小说的历史功用:“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在他看来,能令识字者和不识字者都能听懂小说,而且受到感动和教化,其移风易俗的作用远超过儒、释、道的说教。罗浮居士《蜃楼志序》也说“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认为白话成为小说的基本要素,对近代小说的成型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完成了中国小说近代化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认识。
三、小说个性的强化
尽管世代积累型小说的个性化倾向并不十分明显,但在明清小说论者的眼中,还是寄托了作者的深广忧愤,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如在李贽看来:“《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敢问泄私愤者谁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实际是以历史故事寄托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历史反思。天都外臣《水浒传序》也说:“人有才,上之不能著作金马之庭,润色鸿业,下之不能起名山之草,成一家言,乃折而作此,为愚儒骂端,若罗氏者,可鉴也。”他们都看出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基调和叙事倾向,从理论上阐释了小说创作可以寄托、表达作者的志向、情趣乃至忧愤、讥讽,尽管故事历代积累,有着总体倾向,但在细微处作者的感慨、描写和点题,仍带有鲜明的个性意识。
在元明的文学观念中,笔记、小说只属于历史的附庸,是出于好奇或者存资料以为借鉴的动机而创作的。受制于史学的征实传统,以传奇、见闻、游记或者道听途说为特征的小说,习惯要求叙述尽量客观化,作者往往潜藏起来,用纪传体写传奇事,不露声色地叙述故事。即便是说书体中,作者或说书人的主观倾向也要蕴涵在“第三人称”的评述之中,做到文本表层一定要尽量客观。虽然可以用“有诗为证”之类的评述,但小说叙述本身并不过多涉及著作者的自我情绪,小说还是受“微言大义”、“寓褒贬于叙事”的史学笔法影响。但在明清之际的小说评价中,这一点得到迅速的突破,小说不仅限于叙述故事,而且常被视为作者情志的显性表达。如金圣叹讲自己“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他不仅借助腰斩《水浒传》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且认为这样最能体现施耐庵隐含在著作中的志向和忧虑,其述己之作意可谓明矣。
受此影响,陈忱作《水浒后传》,其《论略》直言此书为“愤书”,并序言:
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嫚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
在他看来,宋江等人遭逢奸佞、身处乱世,无法报国,历尽艰险平息叛乱,却被诛灭杀戮而离散,令豪杰心痛,英雄胆寒。故而让残余诸人再聚忠义,成就功业,可以“使读是书者,无不欢欣鼓舞,赞颂称扬有廉顽立懦之风,足以开愚蒙而醒流俗,则作者立言之本趣,庶几乎有当于圣贤彰瘅劝惩之言也夫”。受这种风气影响的《西游补》,“书中之事,皆作者所历之境;书中之语,皆作者欲吐之言”,也深深寄托了作者的影世之意。
小说创作个性化的形成,使得小说彻底摆脱了经、史的束缚,开始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体形态,可以按照文体自身的规律去建构环境。或进行魔幻般的陌生化处理,尽情表达作者的才情忧愤,增强作者对现实的干预力度,如以小说影世、泄愤,寄寓不平。蒲松龄自言《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乎!”余集读后亦尝言:“余盖卒读之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平生奇气,无所宣渫,悉寄之于书。故所载多涉淑诡荒忽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看似玄幻的人物情节,恰是现实世界无法纾解的困顿,得以在想象的世界中找到解脱。或进行写实化的处理,在读者生活的环境中,入木三分地刻画出“熟悉”的形象,引起读者反思,作为社会的鉴照。如吴敬梓作《儒林外史》,以“富贵功名”立骨,刻画儒林群像,意在使“读之者无论是何种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这种符合真实的生活逻辑,不假想象,却足从中看到品行的高下,体现出作者冷峻的人性反思。
随着小说被普遍接受,明清小说不再单纯以敷衍故事作为立意,越来越成为作者表述人生思考、社会关注和历史理解的凭借。小说的故事表层之下,是作者的人生立意、社会情怀和历史思考,作品也因为不同作者的参与,具有了人各一面的个性,小说遂进入到独创的时代,自此小说,风貌迥异,蔚然大观。或以小说论道,如《金瓶梅》、《红楼梦》、《女仙外史》、《梼杌闲评》等,就人性立意,寄托作者的文化反思;或以小说弄才,如《史》、《燕山外史》、《野叟曝言》、《镜花缘》等,敷陈场景,蒐文化名物为小说格局,显示作者的渊博才情;或以小说狭邪,如《花月痕》、《品花宝鉴》、《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以性恶着笔,勾勒社会的沉沦。小说格调不同,情致有别,皆因作者立意取向而性格鲜明,从而使得中国小说走出了积累性小说、民间评书所习用的类型化的人物塑造、花开两朵的情节模式和对比衬托的叙述策略,进入到了文人创作的个性化时代,可以完全由着作者的才、识、胆、力进行创作,而不必担心才学会被淹没在积累性小说的传统格套之中。
注:
① [日]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
② 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识者欲呕。”冯梦龙《新列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③ 许振东、曲金《17世纪苏州地区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的文人群落》,《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④ 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起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江、王莽篡汉、光武中兴等事,无不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3页。
⑤ 张永葳《稗史文心:论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
⑥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⑦ [明]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页。
⑩ [明]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