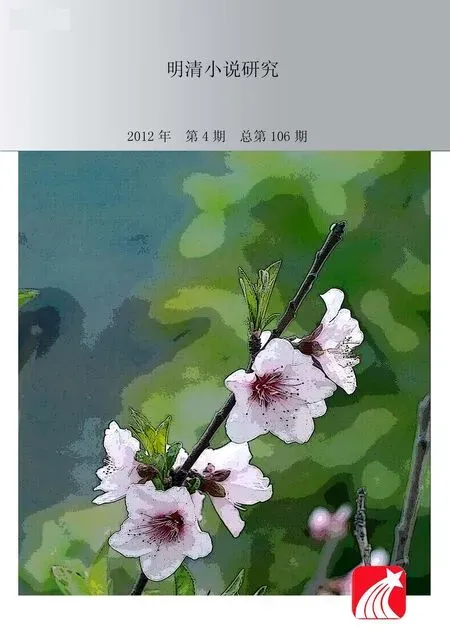“国女”当道
——论晚清新小说①中的“女性乌托邦”乱相
··
一、“慌乱病相”下的“女子救国”论
“亡国灭种”的焦虑,使晚清文人从政治实践到报刊舆论都有着明显的“慌乱病相”:其一,为了救国,时人设想出种种怪招,从“女子暗杀团”到打拳、扶乩等,不一而足;其二,忧心国事的维新派与革命家,很容易在宣扬个人主张时过甚其辞、剑走偏锋,如梁启超、邹容等人政论里排山倒海的排比语式和虚张声势的夸饰之辞,就非常典型,“不……,便不……”,“欲……,必先欲……”的句式,看似振聋发聩,实则粗疏空浮;其三,晚清政治家们多有强烈的功名之心,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秋瑾、陈天华等,都怀有百年之后“铜像巍巍”的梦想(小说《中国之女铜像》、《女子权》都有后人为前人塑铜像的情节),这种渴望流芳百世的功名之心,导致了他们不计成本、不顾策略而急于献身的浮躁心态。设想,如果在一个革命趋近成熟的年代里,是不会出现类似病态征候的。
在种种“慌乱病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极具夸饰的“女子救国论”的推出,“女国民”、“国民之母”、“国女”的说法都是其派生物。晚清文人特地创造这些词汇,就是为了凸现“女”国民的身份地位,强调其救国与“匹夫”一样“与有责焉”。但是“国女”一词,明显把“国民”和“国女”对立起来,将不含性别意识的“国民”一词等同于“国男”:“我国今日之国民,方为幼稚时代;则我国今日之国女,亦不得不为诞生时代”。(海天独啸子《〈女娲石〉序》)号称“中国女界之卢骚”的金一(即金天羽),在其1903年所著《女界钟》中,高声倡导女权,呼唤女性以“纤手”“妙舌”“慧剑”“裙衩”投入“革命风潮”,铸就“巾帼”不让“须眉”之地位,特别将“新国民”、“国民之母”等桂冠赋予他所期待的女性,并夸大女性的政治能力,推崇女性价值:“汝之价值,千金之价值也;汝之地位,国民之母之地位也。吾国民望之久矣!”②金一的言论如巨鼓铜钟,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但这种将拯救国族全寄望于女性的偏狭的思路,特别反映出晚清文人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浮躁和不切实际。动员女性群体投入民族国家建构,增大国民与“卖国贼”的对抗力量,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启蒙话语策略,但是,晚清文人在话语实践上却几近走火入魔,不啻说完全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张扬极端女权,尊女卑男,认为男子无能,救国须完全仰仗妇女,这就演绎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狂想。《女娲石》作者“海天独啸子”在性别问题上迎合当时潮流:“什么革命军,自由血,除了女子,更有何人?况且,今日时代比19世纪更不相同。君主的手段越辣,外面的风潮越紧,断非男子那副粗脑做得到的。”(《女娲石》第一回)这时已东渡日本的秋瑾,也在呼吁当代女性,要“脱范围奋然自拔,都成女杰雌英。习上舞台新世界,天教红粉定神京”③。按说,女性觉醒等于唤醒了一支潜力巨大的后备军,确实能给民族复兴带来某些希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排除男姓让“国女”独自担此重任,她们应该是与男性一起“共事铁血”④,而不是剑拔弩张视男子为“畜类”。所以,由于晚清思想界对女性救国给予过高期望,或是有意鼓风放火,随之导致了整个晚清文人阶层对女性问题的肤浅认识,呈现出舆论宣传上话语铺张,极度的情绪化和狂欢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整体浮躁的时代氛围中,晚清小说创作就集中出现了各种关于“女性乌托邦”的虚幻影像,一时构成晚清热闹非凡的文学奇观。
卑男扬女思潮影响所及,使得晚清文学到处充满了女性主导的“嘉年华”景观,不仅是攻击男性和戏弄男性无能的诗文随处可见,如秋瑾未写完的弹词《精卫石》上言言:“见那般缩头无耻诸男子,反不及昂昂女子焉。……投降献地都是男儿做,羞煞须眉作汉奸。如斯比譬男和女,无耻无羞最是男。”⑤小说里面也构筑了各种“女性乌托邦”,如《女狱花》里表现“纤手翻成新世界,香闺普种自由花”,女性们纷纷主导世界、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场景;但又设定了以男性为寇仇欲杀之而后快,所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男贼方罢手”的激进目标。《女娲石》中则出现了像凤葵、魏水母这样专杀男人的“女江湖”和给人“洗脑”手段堪称“科幻”、又特立独行立志灭“四贼”、守“三守”的女子救国组织。还有《自由结婚》中与《镜花缘》女子世界类似的“女儿国”。晚清小说虚构出这样的“女性乌托邦”盛会,主要借此鼓吹男女二元对立,颠倒传统性别秩序,设想由女性主宰世界,剥夺男性介入政治的权利,“从今以后,但愿我二万女同胞,将这国家重任一肩担起,不许半个男子前来问鼎”(《女娲石》第一回)。这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想法,在晚清文学创作中均有所反映,其背后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是晚清特殊“身体政治”的表征,值得认真解读。
二、“女性乌托邦”表现形态
纵览晚清有关女性革命的小说,其构造“女性乌托邦”突出表现有四个方面:
其一,过分夸大女性的政治能量,完全超越现实,赋予女性超常的社会活动组织能力。
小说《黄绣球》的主人公黄绣球,在丈夫影响下突然顿悟,一时就获得了锦心慧眼,其远见卓识和雄心抱负丝毫不逊色于她的丈夫黄通理。她自己率先放脚,还向众人宣扬放脚的好处,又自主创办女学,要让“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要从“一家四个人再慢慢的推到一个村上”,进而“绣成一个全地球”。尽管小说对黄绣球从家庭主妇到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转变交代得较为合乎常情,但毕竟对其政治能力作了夸大性表现,因为思想觉悟的提高绝非一日之功,不可能短期就有质的飞跃,甚至是超过男性启蒙者。《娘子军》也采用了男不如女的情节模式。主人公赵爱云要走向社会,但她丈夫李固齐开始只顾扯后腿,思想见识与赵爱云相比判若云泥。后来虽在赵爱云动员下思想有了转变,但在社会活动上却并无任何作为,反而是赵爱云发愿心要“分身无量亿数,遍劝二万万女同胞,使她们早早醒悟,各图自立”,读书、演说、办女学,把每件事情都做得红红火火。当然小说创作的主旨即是宣传女性在救国方面的作用,也有让男性相形见绌的某种故意。小说通过赵爱云的故事实际上完成了对一个品貌出众兼能力非凡的晚清新女性的塑造。赵爱云在小说中作为生活的主宰,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也不放弃在社会事务上支配男人的可能。从她不服丈夫规训,不在求学办学上向丈夫妥协方面,说明了她在个人意志和办事的毅力上都表现出男人所没有的坚忍。但在那个时代,作者对这种女性角色的把握,显得过于理想化。特别是小说后来的情节,简直天方夜谭,写爱云轻易地就去了日本考察女子教育,回来自己成功开办了一个女学堂,完成了“救济同胞唤醒女界”的宏愿,而且立志要“造出一个花团锦簇的新女界”。这明显地想象大于生活。《女子权》中一个本来很幼稚的女学生贞娘,为向父自证清白之身跳江,但却为未婚夫所搭救,自此就如变了一个人,为了争取女权,还出国游历,俨然脱胎成为一个出色的思想者和社会活动家。
这类文本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乏善可陈,其所表达的女性解放的理念在当时却有进步意义。小说固然过分夸大了女性的政治能力,使女性解放的举动带上了浪漫、虚幻和理想色彩,但从情理上基本还说得通,较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另有一些作品如《女狱花》、《女娲石》却完全走向极端,将女性对世界的改造变为女人对世界的主宰。
其二,极力宣传性别对抗,鼓动女子向男子复仇,企图建立一个彻底排“他”的“女儿国”。
小说《女狱花》⑥正是这种情绪的集中体现。主人公沙雪梅自幼习武,功夫超群,但艳若桃李,冷如冰霜。她一拳打杀酸腐丈夫,越狱之后,发誓要用“男贼”的头“堆成第二个泰山”,让“男贼”的血,“造成第二个黄河”。并认为在此“夫妇专制时代”,“做女子的,应该拼着脑血、颈血、心血,与时代大战起来”。其理想就是,“组织一党,将男贼尽行杀死。胯下求降的,叫他服事女人,做些龌龊的事业,国内种种权利,尽归我们女子掌握”。她向往女子革命的纷繁“气象”,“一声革命,恐有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罗裙儿为旗,红粉儿为城。顷刻之间,尽是漫天盖地的娘子军了”。沙雪梅与张柳娟、仇兰芷、吕中杰等六位女将致力于组织革命,后因遭遇挫折,自焚身亡。小说作者大概意识到极端性别革命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让另外一个人物许平权提倡“平和革命”,对沙的激进思想进行制衡,认为沙雪梅的思想脱离现实,“你将今日普通女子形状仔细一想,就知不施教育,决不能革命的”。但却认可,“今日时势,正宜赖他一棒一喝的手段,唤醒女子痴梦”。
《女娲石》仍然是宣扬性别对立,立志要建一个完全的女子世界。从情节的发展来看,《女娲石》可看作是《女狱花》的续篇,沙雪梅式的人物在《女娲石》中十分活跃,多个妇女政党在小说中轮番登台亮相。魏水母声称:“擒贼须擒王,杀人须杀男,入刀须没柄,抽刀须见肠。”一副要将男子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女子复仇心态。作者着意将小说人物炮制成一个理想中的女子世界,“予将欲遍搜妇女之人材,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诙谐者、文学者、教育者,撮而成之,为意泡中之一女子国”(《〈女娲石〉序》),以此表达对中国女豪杰的向往之情。其中无数女子政党,它们多以救国和建立女权社会为旨归,且各有特点。天山省的“中央妇人爱国协会”,以“专扑民贼”为宗旨,她们将培养的绝色少女嫁给政要作妾,以实施暗杀。女性身体成为暗杀的道具。“花血党”是小说描写最为详尽的政党。她们以妓院为掩护,建立了一个“女儿国”。该党以暗杀为手段,拥有百万党人,两千支部。三姊妹山精、水母和社狐,分别在山路、渡口和城市截杀被她们称为“野猪”的男人,她们的目标是“不许世界上有半个男子”。有志于描写“48位女豪杰和72位女博士”非凡业绩的《女娲石》,可惜未能卒篇,但从仅有的半部来看,它完全不失为晚清时期集科幻、哲思、文学传统于一体的“奇书”,处处充满了匪夷所思的人物想象和改良政治的激情,让人惊奇、震撼。如果说《黄绣球》是晚清女性小说在艺术上最为成熟的著作,那么《女娲石》则是这一时期最具创意、个性、“乌托邦”思想视野的作品。
其三,充分夸大女性身体功能,将其作了赤裸裸的政治的理解和运用,使一向深受传统禁锢的女性身体借助救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
《自由结婚》中关关虽然与黄祸相爱,但她却发誓,“一生不愿嫁人,只愿把此身嫁与爱国”。以身许国与其说是晚清文人对女性的政治苛求,更无如说是爱国女性的自主选择,身体成为她们投身政治的当然工具。《女娲石》开篇就写金瑶瑟自愿舍身妓院,希望靠自己的色艺,“普渡一切亡国奴才”。而“春融党”有着和她较为相似的策略,通过在全国开办妓院、勾栏,让有志救国的“国女”舍身其中,既能够传播文明,又能让那些贪婪的权贵们死在石榴裙下,达到一举诛杀的目的,这看上去确实是一石双鸟的良策。“春融党”与“花血党”的禁欲主义不同,主要是开设勾栏妓院,利用“肉身”腐蚀男学生,也“腐败官场”,通过让他们“无不消魂摄魄,乐为之死”,达成颠覆男权的目的。而“白十字社”却能对人大动手术,做法更让人瞠目结舌,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将人的脑子挖出来清洗,目的是造就一个干净的世界。
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了女性身体被政治的充分征用,在肉欲的放纵中实现政治上的变革,这到底是崇高的牺牲,还是无奈之下的堕落,是对女性的尊重还是对女性身体的羞辱,是给女性指出了一条救国的出路,还是将女性解放引入了歧途,事实上很难说清楚。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佩服作者的勇气,将崇高的救国大业与肮脏的性交易纠缠在了一起,将暴力革命的“战场”摆到了“国女”卖淫的床上,作者的本意是褒扬献身的“国女”,可无意中构成了对政治的反讽。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作者的突发奇想,也未免武断。事实上,青楼与家国兴亡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清晰。早期的《桃花扇》,后起的《孽海花》,以及辛亥革命前蔡锷与小凤仙的政治与“性”的合作,都折射出了风花雪月与家国兴亡的密切联系。由此看来,作者对女性身体的政治铺排,也是渊源有自。
与“国女”沉浮欲海、舍身救国的行为相对照,《女娲石》还通过对女性情欲的隔绝,在小说中建构起了截然相反的女性身体另一意义之维。
小说中“花血党”章程分为“灭‘四贼’”、“守‘三守’”。这一女子救国组织杜撰出一个貌似合理的“革命逻辑”,女性要实现国家、民族、家庭和性别四重革命,首要前提却是以女性自己的身体为敌,以男人世界为敌,不仅是“遏绝情欲,不近浊秽雄物”,更要革男子的命,“不许世界有半个男子”。这就将世界完全虚构成了一个女权乌托邦,女性在这个乌托邦世界里完全掌握权力,是“天然主人”与“文明先决”,这显然是非常虚妄,不合情理的,“国女”们的作为纯粹是在用一种新的不平等(女凌男)代替旧的不平等。也许意识到这一逻辑的荒悖性,文本也曾经试图弥补这一思想缝隙,幻想无性繁殖的科学把戏,要繁育后代就靠人工授精,由此保证女性身体的性的独立。“花血党”的宗旨很明确,绝不允许它的党员接近“秽男”。对男性的仇视遂导致了禁欲主义:“人生有了个生殖器,便是胶胶黏黏,处处都现出个情字,容易把个爱国身体堕落情窟,冷却为国的念头。”而为了保证“爱国的身体”就要取消“情欲的身体”,秦夫人指导凤葵将“天生的,娘养的,自己受用的”“自然身体”矫正为“政治身体”——“先前是你自己的,到了今日,便是党中的,国家的,自己没有权柄了”,看似荒唐的话却符合晚清当时女性救国的逻辑,这与为了救国舍身青楼的金瑶瑟相比不啻说构成了处理身体的两个极端,让我们由此洞悉晚清时期在女性身体与救国之间的复杂、暧昧关系。小说是政治科幻小说,完全虚构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作者扬女抑男的倾向很是明显,但作者却为何将国女的身体处理成一个完全与己敌对的客体,却特别值得认真的解读。这是对晚清社会传统性别秩序的质疑?还是想进行一番性别秩序重整?难道扩张了女性力量,就可振救国族?这无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源自于《西游记》“女儿国”而来的一种文学传统而已,这一理想在李汝珍的《镜花缘》中也曾得到重现,以武则天君临天下的盛唐来对既定的性别秩序予以颠覆,在“女儿国”中林之洋出尽洋相,裹足、穿耳等,让长期被男尊女卑压迫的女子长抒了一口气。《女娲石》里的故事虽失之极端,不妨看作戏说,但实可看出当救国乏术时,男性文人把女性作为最后利器的奇思妙想。
其四,大扮女性易身游戏,让蒙昧的传统女性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成为革命“女杰”。
女性的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晚清小说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都不约而同走了捷径:让女性似乎一夜之间就获得她们所需要的一切思想和智慧,达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效果。所谓“捷径”就是让她们在梦中接受“神”的指点,当然这“神”不再是指点宋江的“九天玄女”,也不是隐藏在深山老林里的“世外高人”,而是法国大革命时的罗兰夫人、卢梭等西方先哲。被晚清文人誉为“近世第一女杰”的罗兰夫人,经过大量诗文小说的颂扬和传播,成为“中西合璧的启蒙角色”⑦,担当起了在小说中启蒙中国女性走向政治舞台的导师。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先驱,也引起了国人的神往,因而也获得了为小说里女性指点迷津的资格。如黄绣球,本是一极为普通的妇女,她与“女杰”之间的距离判若天壤。但作者为了让她迅速地变为“女杰”,就模仿中国古代小说如《水浒传》中宋江梦遇九天玄女,《红楼梦》宝玉梦入“太虚幻境”的故事套路,让黄绣球先是得了一场奇怪的病,“浑身发热,如火炉一般,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进而梦遇一白衣女子,即罗兰夫人。罗氏给她讲解《英雄传》,启发她男女平权的道理,使黄绣球开窍顿悟,“神魂忽然一躁,形体也就忽然一热”,打那以后,就“开了思路,得着头绪,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豁然贯通”。从此胸怀“自由村”,放眼全世界,发誓绣出个崭新的地球。
《浙江潮》第四期上刊载的《血痕花》(作者署“蕊卿”),虽以叙法国革命史实为主,也有类似情节。第一回楔子中,在法国大革命庆典之日,正是留法女学生回首祖国被人瓜分之时,心绪缭乱之际,却有卢梭入其梦境,与其畅谈男女平权。卢梭对于她打破专制的志向,颇为称许。梦醒后,由女伴赠一书。而《女娲石》中也有“生前被奸,死后被裂”的“大明国女”托梦陈说亡国之痛,点化翠黛,使其“一笑而后七窍开”,所谓“道家静悟佛家顿,尽从莞尔一笑来”。如果不能遭遇“神人”“导师”,那么便有非常手段让其“易身”,如《女娲石》中的“洗脑院”,点石成金,能洗人脑筋,“再造国民”。金瑶瑟就曾身历其境,作为当然的“国女”,“那脑筋洁白无垢,不似乱臣贼子”。《女狱花》也是先让沙雪梅做梦至“十九殿”,用“男尊女卑人权缺”的现实来教育激发之,然后让她读斯宾塞《女权篇》,从而突然洗心革面再也不愿做夫权的奴隶。这当然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为何晚清小说中写女性要用上这类幻想中的情节,原因无他,自是要对传统女性进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不然因袭着传统重负的女性又如何一跃登上20世纪历史大舞台。
小说以这种瞒天过海、荒诞不稽的笔法写女性从蒙昧到开窍的过程,就有意回避了女性觉醒的艰难历程,显示了不着边际的浪漫空想色彩,但另一方面,借助梦中的权威人物亲口讲授女子解放的道理,与其是为了点化主人公,其实也是为了点化读者,以起到开通风气的作用。
三、“女性乌托邦”与晚清“身体政治”
晚清小说中,“国女”当道,演绎了轰轰烈烈女子救国的热闹场景,这无疑是一种“女性乌托邦”文学叙事。中国传统女性易身革命,脱胎换骨,体现了政治运动对女性身体的强行征用,其实并不指向女性解放的真谛,只有到五四时期,在先进思想文化洗礼下,女性被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所召唤,中国才有了真正走向精神的独立和个体自觉的女性解放运动。两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晚清国族主义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阐释和隐喻性挪用,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这样界定“身体政治”,指出:“所谓‘身体政治学’(bodypolitics),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在这种‘身体政治学’的论述中,‘身体’常常不仅是政治思想家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而且更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借以作为‘符号’的身体而注入大量的意义与价值。”⑧在“女性乌托邦”小说中,女性身体只有一个,却有时被净化,有时被舍身取“义”,背后则有着相似的“病源”,这显然是将女性身体强行纳入新的政治框架之后带来的乖谬结果。因此,仅从思想层面讨论女性解放,衡定女性的地位,不过抓住了问题之一端,而只有认识女性身体的复杂形态,才能真正理解晚清女性的真实处境,毕竟“身体”才是一切政治隐喻的物质基础。
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虽率先由男性倡导,但一些先进女性也能及时跟进,并在社会天地中演出波澜壮阔的生动剧目,如鉴湖女侠秋瑾的传奇一生足以撼天动地。但毕竟女性解放没有如五四那般生发成为一个实际运演的全社会运动,大多数女性依然被封锁在重重闺门之内,难以逾越传统规范对其身体的约束,也无法享受沐浴自由的阳光与空气。因而新小说中对于晚清女性社会生活的表现只能依据想像和虚构。正如有人指出,“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进程,又注定了这类作品不可能如写西方女豪杰那样可以据实敷陈,作品中的中国女豪杰,则更多地来源于作家的想望与艺术虚构”⑨。因此,晚清文人在写这类小说时,就倾向于将古典小说传统进行改写,把女性强行从闺阁绣楼里“解放”出来,让女性和男性一样置身于尖锐的国族危机下,极力夸大女性“姿色”在救国方面的政治功用,而无视女性真正的现实处境。然而,晚清小说很多作者的女性观念并未真正达到现代思想层次,骨子里仍然坚持男权中心的传统观念,所以在对女性身体资源进行开发想象的同时,对女性革命的颠覆性力量却充满着恐惧,因此这类小说尽管放大了女性身体的政治功用,却在身体叙述上处处彰显着伦理选择上的矛盾。
《女娲石》第七回回末如此评说“国女”为救国施出的戒情绝欲的非常手段:“天下最利害者莫如娘子军。而娘子军之别名,曰附骨疽。真个防之难防,治之难治。不独野蛮政府为之寒心,即我亦当为之丧胆。可知我国之弱之腐败,特无十万胭脂虎耳。”“胭脂虎”一说显然表明作者对女性革命并非真心推崇,一方面为之欢呼庆幸,一方面又十分恐惧女性对男权传统的破坏性力量。如果说在写到金瑶瑟、秦爱浓等有知识的“国女”时,作者笔法尚中性,但具体到草莽女英雄凤葵、魏水母的故事,就完全采用漫画笔法,直如状写母夜叉,将其完全妖魔化,即便是写人的真性情,也是“女张飞”“女李逵”那般粗莽之态,无法让人认同。设想如果真到作者描绘的这等女子乌托邦世界里,那不仅仅是进入鬼蜮的男人的梦魇,恐怕也是全社会的恶梦吧。因此很难搞清作者对于女性革命的主观态度究竟如何,赞成乎?反对乎?作者在说教上与主流舆论形成共谋,提倡男女平权,女子革命,但骨子里却不曾摆脱男子中心思维,高扬的只是女性身体“价值”,中心在于利用,潜话语层面依然是男尊女卑视女子为低等玩物。《女娲石》第六回中瑶瑟主仆二人逃出京城来到仙媛县,因凤葵在饭店里生事,被五六十乡人捉住,发现是女人,便卖到妓院里。“话说众人把瑶瑟主仆二人捉住,往身上一搜,现出一双雪白白娇嫩嫩的香乳来。又将手往下一摩,乃是个没鸡巴的雌货。”从这种叙事口吻看起来,作者虚构出一个理想的花花女子世界,但在想象的世界里却又将目的与手段胡乱搭配,其创作的性别态度大可怀疑,莫不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心理在作怪,将女性身体视为玩物工具的传统男权心态又何曾有真正改变?所以王德威也对此提出疑问,他认为《女娲石》中天香院一节“例示了海天独啸子最无羁无绊的想象;但它仍流露出晚清男性对女子理性与激进意识的几许焦灼和顾虑”⑩。
文学的“乌托邦”,建构的应是一种现实难以实现的愿望,它代表了建立完全自由而平等生活世界的人类梦想。但在晚清新小说中,构造“女性乌托邦”之所以成为很多小说的一种叙事模式,其实彰显的更多是一种时代通病。首先,“病相”的根源在于这种想像性的文学书写,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集体迷狂。王德威先生在解析《孽海花》时指出这种对女性的易身游戏,虽然“抬举妇女作为历史意识转变的象征,但也不免暴露出中国男性在政治上一筹莫展时,对中国女性的狂想”,并进一步揭示,“这与其说反映了女权意识的浮现,不如说折射出男性自恋的最后怪招”。其次,这种“病相”正是晚清社会国族危机急剧演化孕育的一个结果,在公共话语领域难以自由释放的政治激情,在文学领域却引发了文人对颠覆性的女子理想世界的创造,这不啻说寄寓了文人对女性与革命的无边狂想。他们想像出“女子救国”这种在现实中不能说是子虚乌有却更多为“传说”的事情,采用了虚幻“乌托邦”的视野及写作路数加以文学再现,将女性救国的能量夸大到极致,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其三,晚清小说家虽然让笔下“国女”可以尽情陈辞救国方略,但国女们也实现不了向“主体”身份的转移,最终也不过是为了实现对其身体的有效征用,作为对象化的客体成为文本游戏的材料,这充分证明了民族国家叙事的男权话语归属和晚清中国女性有“国民”身份命名却无“国民”精神实质的尴尬。因此,晚清新小说中的“女性乌托邦”叙事,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文本,仍然是难脱旧窠臼的“怪力乱神”的“小说家言”,以游戏的笔墨、概念化的方式来想像女性、想像中国的一种方法。当然也许对晚清那些还处于思想混沌中的闺阁女性来说,这些小说无疑是一种生动的“寓言”式启示,可促使她们尽快“舍身”、“洗身”、“脱胎”,加入到救国的行列中,以壮大“女国民”的队伍,成为国人所愿望及需要的革命“国女”。
注:
① 版本说明:本文所论小说《娘子军》,依据《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卷一,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其他小说则引自《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女娲石》及其序言出自《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负曝闲谈/黄绣球》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孽海花/附鲁男子》(上、下)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所引作品原文恕不一一注出。
② 金一《女界钟》,大同书局1903年版,第94页。
③⑤ 郭延礼选注《秋瑾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210页。
④ “愿我姊妹,扫除脂粉,共事铁血。兴亡之责,昔已签遗巾帼;光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女子军事团传单》,《民主报》1911年11月19日。
⑥ 《女狱花》一名《红闺泪》,又名《闺阁豪杰谈》)共12回,署王妙如著。
⑦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⑧ 黄俊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涵义》,《国际汉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⑨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