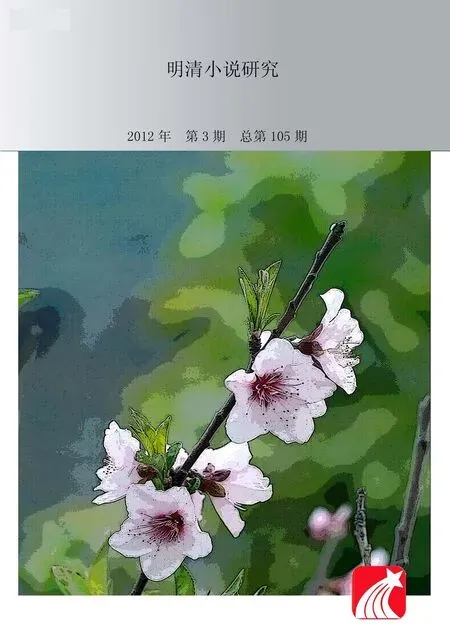论清代文人对青楼名妓的文化书写及演变
——以狭邪笔记为例
··
自清初余怀《板桥杂记》开始,出现了大量记录青楼名妓事迹的狭邪笔记,这些笔记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处境和寄寓,直至清末,社会巨变,以王韬为代表的作家一改传统狭邪笔记抒情写意的经典写法,模仿传奇志怪笔法记人写事,虚拟行文,文人对青楼女性的书写一变再变,其中蕴含着社会变迁下士人古典文化心理的形成、演变和失落。
一、《板桥杂记》的兴亡之感与名妓“神女”世界的建构
当明亡之际,在家国与种族面临双重危难的时刻,名妓与名士相辅相成,用惊艳、才华和真情谱写了荡气回肠的兴亡之歌,气骨凛然,虽然于世无补,但就文化史而言,却殊为奇特。在中国古代社会,所谓封建的宗法社会秩序、伦理纲常是由男性建立的,而历史亦由男性书写,男主外、女主内,作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始终被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参与社会政治了,自夏代妹喜、周代妲己、商代褒姒开其先河,女性甚至仅仅因其对男性特出的异性魅力往往招致红颜祸水的评价。而在晚明商业发达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名妓在普遍与东林等士人的接触中耳濡目染,已然士人化,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前代妓女群面对国家兴亡、政治动荡的疏离感相比,晚明的名妓群体在危难时刻所体现的气节以及果敢的行动力甚至让她们的名士伴侣亦望洋兴叹、相形见绌,如柳如是、李香君等。在家国无可挽回之时,这些无论生活亦或情感都与当时东林名士及尘世兴亡休戚相关的名妓,遂成为对往昔士人个体、故国以及文化沉痛回忆的表象符号,回忆者将深沉的哀痛和失落隐寄在这些本就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意味的美丽形象背后。余怀的《板桥杂记》即是这样一部以明末清初名妓为传述对象的狭邪笔记,文人对名妓的书写情怀自此成定基之势,后人踵武其流风余韵,绵延不绝,直至清末。
《板桥杂记》体例上分雅游、丽品、轶事三部分。雅游概述南朝古都金陵风流胜景,丽品写秦淮名妓事迹芳泽,轶事则写男性士人在风月场所之奇行逸事。前两部以名妓为主,事涉院家名妓种种风韵气度、举止行事以至临危大节等,写境描人如梦如幻,似入仙界,如《雅游》开篇即云: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①
再如,记秦淮灯船盛景天下无双,余怀作《秦淮灯船曲》云:“遥指钟山树色开,六朝芳草向琼台。一围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梦里春红十丈长,隔帘偷袭海南香。西霞飞出铜龙馆,几队娥眉一样妆。”“神弦仙管玻璃杯,火龙蜿蜒波崔嵬。云连金阙天门迥,星舞银城雪窖开。”②这一组诗中诸如六朝、天、海、梦、神、仙、天门等意象都与梦幻和仙境有关,所写岂非名妓云集的俗世,竟恍然如在梦中、身处太虚神界。《丽品》中具体写到李十娘居室:“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主其家。”③名妓居处已然成为文人雅集之所。
《丽品》写李香云:“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宛转,调笑无双……余有诗赠之云:‘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以巫山神女影射,此虽为李香而设,从上述一系列作者以仙境喻示记忆中的秦淮情境来看,巫山神女不妨可以作为《板桥杂记》中余怀回忆曲院名姝的总体印象。六朝、仙境、神女都是颇具历史文化蕴含的意象,巫山神女的故事源于战国后期辞赋家宋玉的《高唐赋》,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中又塑造了洛水女神的形象,这两篇赋俱用幻梦形式表达与神女欢会这一主题,叶舒宪并称宋玉的赋“造就了以幻梦形式叙写非婚性爱的创作模式”,巫山神女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填补了爱与美之神的空缺”④,后世文人做不完的非婚性爱的白日梦即源于此。在“无性”或性被隐蔽起来的家庭伦理之外,名妓的世界充满了男女性爱的魅惑,与神女原型颇为相似,后世文学亦有仙妓合一、以神女指代名妓,余怀戏称当时被推为南曲第一的顾媚的居室“眉楼”为“迷楼”,即蕴含着神秘而魅惑的情爱色彩,名妓居室、服饰及神情举止的媚人力量令士人迷醉。同时,侠义精神和民族大节在名姝身上亦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当京师沦陷之时,从良为保国公之妾的寇白门“以千金予保国赎身,匹马短衣,从一婢南归”⑤,其决绝与英豪令人折服,近于女侠。敌军主将欲犯葛嫩,“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⑥,抗节之举使人荡气回肠。“神女”不仅是情爱的化身,亦是美的化身,侠气及民族大节强化了名姝身上这种爱与美的意蕴,这即形成了余怀所建构的文化意义上的晚明秦淮名姝群像。
《板桥杂记》轶事部分大体描述了与名姝交往的狎客群体,似可与名姝群像形成反衬,亦即名姝世界似性爱与美交集的幻境、神界,狎客的世界则回归到世俗及现世,如余怀所云:
一声《河满》,人何以堪?归见梨涡,谁能遣此!然而流连忘返,醉饱无时,卿卿虽爱卿卿,一误岂容再误。遂尔丧失平生之守,见斥礼法之士,岂非黑风之飘堕、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缀葺斯编,虽以传芳,实为垂戒。⑦
余怀描述或者说建构了一个有如神境的名姝世界,读者无不动容与沉迷,在此突然棒喝一声,以垂戒之意示人,读者已然在幻梦中沉醉,故此间之意总如汉大赋的讽喻尾巴一样难以让人信服,很多学者亦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个说辞,不可尽信。但垂戒之心贯穿于轶事部分的始终,作者由此从另一具法眼揭示狎客所处的南部烟花世界是物质的、世俗的,甚至充满了铜臭味,“曲中狎客……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⑧。此处一语道破世情,在文士风流、名姝雅艳的南部烟花背后,始终统罩着一个由众多狎客织就的巨大的金钱的网,而这正是由名士和名姝共同生成的“神仙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此番俗眼观世之心于“雅游”概述中即亦埋下伏笔:“若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尽,遂欢寡而愁殷。虽设阱者之恒情,实冶游者所深戒也,青楼薄幸,彼何人哉!”无论从名妓或从狎客的角度,作者在以“轶事”为主的叙述中部分消解了由其一手建构的软玉温香、雅致风流的神仙境界。
余怀《板桥杂记》作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⑨,三藩之乱已平,清代统一形势已定,作者年近八十,以此暮年之际回忆年少时于前朝平康巷中的浪游生活,虽为名妓做传,亦有自传的意味,他在篇中明白点明与所记名妓的关系,称:
据余所见而编次之,或品藻其色艺,或仅记其姓名,亦足以征江左之风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国城,犹为李师师立传,盖恐佳人之湮灭不传,作此情痴狡狯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⑩
余怀此人,卓尔堪《遗民诗》云:“字澹心,一字广霞,号曼翁,福建莆田人,江宁籍布衣。读书破万卷,倜傥风流,交多贤豪,隐居吴门,徜徉支硎、灵岩间,著《味外轩稿》。”易代鼎革之际,正当青年,入清未仕,遗民身份使其在回忆前朝南部烟花的故人与往事时,流露出深沉的家国之悲,如其在《板桥杂记》序中所云:“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感叹:“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主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因这些名妓的命运与当时东林名士及家国的命运异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名士与名妓“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并共同经历黍离易代之悲,感慨俱通,作为“吴越党社胜流”之一的余怀,以雅眼观花,把文人与名妓的世界写得风流自然、如梦如幻,伴随时代兴亡的那一种若隐若现的文化和文人梦想的失落,令人怦然心动,同时,他亦不忘以俗眼观照旧院及尘世,警戒后人,但这警戒意味的实际功效实在有限,其一手建构的含有性爱、美、气节、侠义等文化内含的名妓形象尤如神祇一样无形中影响着后来文人在狭邪笔记创作中对名妓的态度。
二、名妓“神女”与个体身世之感的寄寓:清代中期狭邪笔记对《板桥杂记》文化意蕴的继承与新变
至清代中期,文人仿《板桥杂记》而作狭邪笔记,一时风起云涌,乾隆晚期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雪鸿小记》,嘉庆时期捧花生《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谈》及《三十六春小谱》,嘉道之际雪樵居士《清溪风雨录》、《秦淮闻见录》,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个中生《吴门画舫续录》等,蔚为大观。作者大都隐去真名,下笔行文间对《板桥杂记》的追仿非常自觉,余怀《板桥杂记》所建构的爱与美之化身的名姝群像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为清代中期的文士所普遍接受并付诸于创作实践。
乾隆中晚期以前《板桥杂记》作为“经典”为什么历史性的处于沉寂状态?何以从乾隆中晚期开始追仿《板桥杂记》的狭邪笔记大规模出现,甚至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从宏观的层面讲,脱离不了社会思潮、士风的因素制约,雍乾时期严厉的文字狱使士气消馁,文人士子“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另一方面,康熙吸取晚明纵欲亡国的教训,崇尚并推广宋明理学,理学大行其道,禁欲主义的理念深入人心,基于此,康熙和雍正都宣布取缔官妓。这一情况到了乾隆中晚期特别是嘉庆时期发生转变,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使学界跨越宋明理学直接深入汉魏六朝,如戴震、钱大昕、汪中等当时一流的学者对妇女缠足、再嫁等均持开明态度,加之以扬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使清初的禁欲主义被打破,这一时期,朝廷的政治思路亦开始转变,对明清之际的士人重新评价,其中《贰臣传》、《逆臣传》的历史编写即是这种转变的标志。随着以扬州、南京、苏州为代表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政治和理学的种种禁忌被打破之后,晚明社会的历史重新纳入文人的视野,被反复提起,其中晚明社会所独有的名士和名妓的文化传统格外受到士人的瞩目,狭邪笔记蜂拥而起。
对《板桥杂记》的大规模的模仿令人不得不细思其中基于作者群体的创作初衷。时过境迁,继明清之际的余怀之后,他们书写的深意是什么?首要的就是要确认这一批作者的身份。虽隐去真名,但却可以对他们的大致身份作初步界定,《续板桥杂记》、《雪鸿小记》的作者珠泉居士“长期在南京扬州一带过着幕游生涯”,《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谈》及《三十六春小谱》的作者捧花生实名车持谦,“家贫,以书记幕游,博洽耆古,尤长史学”,陈文述曾题《吴门画舫录》云:“鉴湖才子西溪客,骚坛旗鼓推诗伯。十年流浪老江湖,倚醉狂歌拓金戟。”“嗟我囊琴意可哀,频年落拓住燕台。青衫憔悴无人问,只有娥眉肯爱才。”由此透露作者西溪山人大概也是一位以游幕为生的下层文人。《吴门画舫续录》的作者个中生为程开泰,曾为县令,“多缘情绮靡之作”,为悼亡妾作《续锦瑟诗》五十首,并于道光八年请序于包世臣,包氏遂作《续锦瑟诗题辞》。《清溪风雨录》、《秦淮闻见录》的作者雪樵居士难以确认其人,但他在《清溪风雨录》自题中称“不豪不富不公卿,非贾非儒亦非墨,骥子鸿妻并远离,派作江南老孤客”,不难看出也是一位以游幕为生的下层士子。这些作者虽未署名,但可知大都是浪迹江南的下层游幕文士,偶或有人为官,但不过县令之职,大都功名难就、抛家别子,四处辗转、依人为生的游幕生涯使他们普遍对人生充满了飘浮和幻梦感。清代中期的人口剧增、科举以及官僚制度,致使士子求取功名要比前代更加艰难,绝大部分普通士子都被隔绝于功名之外,文人游幕在清代中期遂达到高潮,狭邪笔记的作者大都来源于这些四处飘泊、依人为活的游幕文人群体,他们比一般士人群体有着更强烈的身世之感。珠泉居士在《续板桥杂记缘起》中记述:
余曩时读曼翁《板桥杂记》,留连神往,惜不获睹前辈风流。迨闻丙申以来,繁华似昔,则梦想白门柳色,又历有年所矣。庚子夏五,从阳观察招赴金陵,曾于公余遍览秦淮之胜。旋以居停罢官,束装归里,计为平安杜书记者,无多日也。辛丑春,重来白下,闲居三月,时与二三知己,选胜征歌,兴复不浅。嗣余就聘崇川,三年羁迹,青溪一曲,邈若山河。今秋于役省垣,侨居王氏水阁者十日,赤栏桥畔,回首旧欢,无复存者,惟云阳校书,犹共晨夕。因思当日,不乏素心,曾几何时,风流云散。安知目前之依依聚首者,不一二年间,行又蓬飘梗泛乎?
珠泉居士的朋友在《续板桥杂记序》中称:“吾友珠泉先生,鹏未抟云,豹还隐雾。王仲宣才华第一,依人在红莲绿水之间;景行品概无双,寄兴于檀板金樽之侧……卿同断梗,侬是飘蓬。江淹之别恨依依,卫玠之愁肠脉脉。”沈廷炤序《吴门画舫录》云:“仆则絮已沾泥,花从著袂,眉参深浅,泪渍衫青。蓬感飘摇,酒惊鬓绿,闲情偶作,性用持孤。”《吴门画舫录》记苏州第一名妓杜凝馥:“工词曲,善琵琶,正如《羽衣》一曲,只宜天上,难得人间。岁甲子,秋风报罢,毷氉筵开,愿一聆雅奏,强而后可。宫移羽换,慨当以慷,儿女英雄,一齐俯首。昔江州司马,泪湿青衫,遂使商妇一篇,盛传千古。而声音之妙,沦落之感,古人未尝不同也。”《吴门画舫录》记名妓李响云时借吴俗插菊暗喻游幕文人的处境,所谓“昔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岂知千百年来,犹使凌霜傲骨,随人俯仰,以取悦一时乎?”捧花生《秦淮画舫录》有“名士美人,沦落同慨”之感,宋翔凤《吴门画舫续录·序》云:“夫水上有靡靡之音,则听之者不去;胸中有郁郁之意,则遣之者良难。个中生迹半天下,抑塞已久,以为中吴之游,足以荡魂销志,遁穷忘老……烟花之记,胜事所为流极;琵琶之篇,沦落因而生感。繄余与子,同为羁人,转徒异地,非无华月之夕,歌舞之欢,至于酒半,犹且悲吟心动,太息坐叹,况复览此,尤系乡国。掩卷不能以遽终,而旨趣已通乎作者;言有所不能已,遂揽笔以叙之矣。”自乾隆中晚期开始,怀才不遇、寄人篱下、飘泊无依、心灵不得自主的处境在乾隆中晚期随着游幕的普及已然成为文人的普遍生存状态,与名妓的身世相通之感渐成为中下层士人的普遍心理,在文人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着空前强烈的表现,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珍珠娘,姓朱氏。年十二工歌,继为乐工吴泗英女。染肺疾,每一椫杓,落发如风前秋柳。揽镜意慵,辄低亚自怜。阳湖黄仲则见余每述此境,声泪齐下。美人色衰,名士穷途,煮字绣文,同声一哭。”黄景仁为乾隆六十年间第一诗人,青楼才女珍珠娘的遭遇激发了诗人强烈的身世之感,与此同时,汪中在名篇《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序》中借哀悼明末名妓马湘兰寄寓身世之慨,感叹道:“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篑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汪中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兼文人,此文乃为“发愤之极作”,以失意才人比之年老色衰的女子,自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开始已渐成为文人的一个传统,但历代文人恐怕没有如乾嘉时期游幕士人这样感同身受、刻骨铭心。超人的禀赋与心灵备受凌辱、饱受挫折的严酷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游幕文人自觉地将自己的处境与名妓相沟通,而于名妓身上寄寓士人的身世之感遂成为清代中期文坛的普遍现象,为名妓列传的狭邪笔记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就直接与这种士人心态和文学寄寓密切相关。《板桥杂记》在对名姝的美化书写过程中主要寄寓了一代文人的兴亡之感,个体的不幸在易代鼎革之际与国家兴亡相比显得并不突出,清代中期为兴盛时期,易代鼎革即使作为一种记忆离这一时期的文人也已经非常遥远了,他们在狭邪笔记中通过对名妓的书写更多地寄寓了深刻的个体的身世之感,文人慨叹自己身世的寄寓成为清代中期狭邪笔记在《板桥杂记》书写基础上的一个新变。
与《板桥杂记》相承继,清代中期这些狭邪笔记的作者依然热衷于对名妓的美化书写,他们与余怀一样,也会从世俗的、现实的角度认识到妓女与嫖客之间交换关系的本质,纵然这个嫖客群体是才华出众的士人,但性感、美丽、超俗等“神女”化、士人化的名妓形象仍在这一时期文人狭邪笔记的书写中占主流,李汇群《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说,此不赘述。
三、“神女”文化意象的解构:晚清狭邪笔记中文人古典情怀的失落
道咸以降,清代国力日衰、世风日下,历经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江南烟花旧都如南京、苏州、扬州等地民生萧条、满目疮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上海建立租界,上海以其殖民地的特性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国际化大都市,士子、商人、妓女纷纷在战乱中辗转云集到上海,狭邪笔记小说表现的地域重心亦随之转移。这一时期的狭邪笔记有许豫《白门新柳记》、《白门衰柳记》,周伯义《扬州梦》,王韬《海诹冶游录》、《花国剧谈》等。
晚清狭邪笔记集中体现了士人群体由近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对古典的彷徨、怀念和失落的文化心理,较之晚明的鼎革易代、清中叶士人对个体身世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所谓名士群体面临着更加复杂而深刻的危机,即上海现代商业世界及意识对他们内心的古典文化情怀的振荡与洗礼,同时,社会结构重新洗牌,最具古典意味的士大夫阶层面临衰落并异化,商人不仅在财力上而且在社会地位上成为真正的中坚阶层。
名妓配名士的南部烟花传统渐被世俗社会的商业化吞噬,名妓的士人品格渐渐消逝,跨越中西、深谙新旧烟花之道的晚清名士王韬在为他的狭邪笔记自序时称:
顾或谓昔赵秋谷《海鸥小谱》,余曼翁《板桥杂记》,西溪山人之《吴门画舫录》,皆地当通都,时逢饶乐,其事可传,其人足重。
王韬认为,以《板桥杂记》为中心的名妓现实生活中在人格和事迹方面俱有可圏可点、令人折服之处,这是传统的古典名妓在士人心目中的普遍印象,甚至做为一种文化积淀沉入一代一代文人的心里,这与以《板桥杂记》为经典的清初以及清中叶的狭邪笔记普遍将名妓神女化或士人化的书写轨迹密切相关。进而纵观当下上海的烟花世界,王韬慨叹道:
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既无赵李名倡,又少崔张侠客……未闻金屋之丽人,能擅玉台之新咏。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杀贼,取谥贞姬;着黄而参禅,证名仙籍。绮罗因之减色,脂粉于焉为妖。是人肉班,是野狐窟焉尔。
晚清的大上海,名妓群体已然全无雅致可言,更无节气可取,她们显然蜕变了,纯粹卖身,传统的才艺荡然无存。面对这一现实,王韬在为名妓写生的过程中自觉采取“与其高谈耸听,毋宁降格求真”的书写态度,甚至对以往文人美化的烟花世界产生质疑,如其所说:“况乎奇节仅矣,冶容暂耳,必貌皆苏小,诗比薛涛,媲卞玉京之慧心,配段东美之雅操,则香国中竟无下乘,章台内悉属才人。青泥世界,尽放莲花;碧柳楼台,遍镌珉玉。是情之所必无,亦事之所罕有也。”基于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世情,王韬认为历来狭邪笔记作者在为名妓列传时普遍采取了想象虚构的小说笔法,即“余观古来文人失职,荡子无家,偶托楮毫,遂传风雅。晓风残月,不尽低徊;淡粉轻烟,岂无点缀?本非实录,有似外篇。”名妓神女化或士人化的群体形象多半来源于文人自身精神世界的投射与寄寓。王韬在序言中以对现实和人情极为清醒的认识非常自然又自觉地将以往文人所书写的名妓“神女”群像进行解构和分析,并明白地告诉读者,其笔下的名妓世界“逞妍抽秘,尽许荒唐;水月镜花,无嫌空彻”,虚拟之意和盘托出,如“人肉班”“野狐窟”的现实中的上海名妓世界在王韬《海诹冶游录》中却是另一番半真半幻的虚构景象。一方面,他比以往任何狭邪笔记作者都意识到狎妓的消费性质,更从狎客的角度对不同层次妓女的狎资作了清楚的交待,如“虽春风一度,各自东西,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遣羁旅也。其夜合之资,及他事率递减于堂名一等。故冶游而惜费者,往往舍彼取此。”“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馆,调食者,率以女子。客入以百钱赠,若留宿亦须一饼金,较之吴市看西施,稍觉便宜耳。”这哪里是传统文士狎妓的笔墨?这么直接而自然的交待狎资,直如一个商人在言说,而非来自一个向来羞言阿堵物的名士之笔。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狎妓时逢场作戏的心态,如其写明珠:
谓余曰:“儿得千金,构屋城外。曲房小室,幽轩短槛。环植花卉,若得此与君偕老于中。何如?”余笑而允之,嗟夫天涯杜牧,沦落甚矣。安有十斛明珠,买此娉婷贮之金屋耶?
而开篇对海上名妓“工词曲娴翰墨者,未之见也”的交待,则彻底颠覆了传统狭邪笔记中所建构的士子化、神女化的名妓世界,“稍识之无”的绿筠,“不识字”的巧福等没有文化或文化浅薄的妓女形象在《海诹冶游录》中成为主流。娼妓无情的论调被作者反复强调,如“甘为野鹜,耻作家鸡。烟花本质,往往然矣。其能谢客杜门,镇日不下楼者,吾闻亦罕”。的服饰以奢华巧丽为尚,“淡妆素抹”的“神韵独绝者”,“当别具只眼物色之”。对于有情于自己或自己钟情的烟花女子,作者在对他们的书写中常怀同情爱怜之心,如在《丽品》一卷专设“廖宝儿小记”,记录与宝儿相识相处的点点滴滴,当然,在写到这些女子的时候,作者总是难以抑制自恋或炫耀的心理,实际上,在与宝儿相处的过程中,金钱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使“一往情深”,作者于此上亦十分清醒,宝儿对作者提出的金钱要求都不是直接的,每次都找些理由较“自然”地向他索钱,如果能接受,作者并不吝惜,但一超过底线,就马上就警觉起来,如:“宝儿所居小桥半圯,艰于出入。意将为迁乔之莺,苦乏钱刀。余以二万缗为助,然宝儿幽悒愈深,黛影凝愁,眼波盈泪,若有不可告人之隐。余抚慰再三,移时而出。红红尾谓余曰:‘闻其夫将谋不利,欲胁君出百金,以快一掷。’噫!余笔耕墨耨,安有盈余赀,以供博徒挥霍耶?自是之后,不往者数月。”并不讳言金钱为两人继续相处的最大障碍,作者悉心建构的温柔乡遂难免染上金钱的味道,两人的“一往情深”更似作者本人对两人关系的美好想象,而非实际情况。文人赋予传统名妓的温柔、清雅、神秘的女神意蕴被消解殆尽。实际上,狎客群体亦发生了根本改变,如作者所言:
海滨纷丽之乡,习尚侈肆,以财为雄。豪横公子,游侠贾人,惟知挥金,不解文字……妖姬名倡,狎客冶优,争奇献巧,工颦善谑,以冀一当,能于酒肉围中、笙箫队里,静好自娱,别出一片清凉界,可为雅流韵事者,未之有也。
从唐代白居易对“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同情,可见传统士人群体以及名妓群体对商人的排斥,传统农耕文明下重农抑商的意识在近代的上海被彻底打破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囊中羞涩的文人亦争先恐后将自己的作品送入商品流通领域,处于由近代向现代过渡阶段的士阶层,难以逃脱时运的制约,他们一只脚站在富有古典意味的六朝烟水的传统中,一只脚茫然地踏入俗氛冲天的商品大潮的洪流中,那种阶层的没落感、文化的失落感如影随形,这一点在对名妓的书写中表现的格外突出,名妓群体、文人狎妓的心理与态度均发生了异化。
在海诹冶游系列之后,至《花国剧谈》,王韬完全以小说传奇笔法为名妓列传,一改往日狭邪笔记给人的实录印象和自传特色,他在自序中称:
芳踪胜概,足以佐谈屑,述遗闻,为南部侈繁华,为北里表侠烈,其事则可惊可愕,其遇则可泣可歌,宜汇一编,以传于世。《花国剧谈》,即以此作。大抵采辑所及,剿撮居多,孟坚纪史,半袭子长,扬云作文,多同司马,斯固不足为病也。盖此不过为文章之外篇,游戏之极作,无关著述,何害钞胥。以渠笔底之波澜,供我行间之点缀,不亦快欤?
以游戏娱乐之意为女妓列传,传奇与志怪笔法并行,其所建构的女妓世界恍然有如《聊斋志异》的女性神异世界,如写妓女大姑与谭生私奔之后:
女每夜辄梦媪呼与俱返,醒而述之,谭以噩梦无凭,一笑置之。女素有饮癖,一夕倩邻妪购得佳酿,藏于几畔,漏三下,谭入市未返,女忽跣足披发,自帐中跃出,颜色惨沮,腹如辘轳声,女伴诘之,始自言饮阿芙蓉膏。谭归视,则纤纤十指甲尽作紫黑色,急投以药,而瓠犀变箝,涓滴不能下咽,憔悴花容,香销艳萎,闻者伤之。噫!鸳鸯野合,鸾凤齐飞,遂令孤愤老鸨,游魂相逐,化作一缕怨丝,萦绕不脱,卒至俱殉。悲夫!
至此,以《板桥杂记》为经典的传统狭邪笔记抒情写意的色彩被抹去了,寄托世运及个人身世之慨的名妓形象的古典意蕴被消解,对清初以来这一狎妓书写传统的颠覆意味着古典文士阶层在晚清的整体没落和古典文化的整体失落。之后在新旧文化之间的徘徊、挣扎成为一代文人的梦魇,一切夹在近代与现代的过渡之中,旧得不得彻底抛弃,新的又不可欣然全盘接受,他们成了内心最自苦的一代文人。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士人处境和心理的变化,清代文人狭邪笔记对名妓的书写历经清初、清中叶至清晚期,以《板桥杂记》为核心,清初及清中叶的文人创建了用来抒情写意、有所寄寓的艺术的名妓世界,至清末,文人又一手解构了这一蕴含古典文人文化的经典名妓印象,预示了文人心目中古典文化的失落,昭示着一代文人处于新旧文化过渡期间的矛盾与挣扎。
注:
①② 余怀《板桥杂记》上卷,朱剑芒编《章台纪胜名著丛刊》本,世界书局1936年版。
③⑤⑥ 余怀《板桥杂记》中卷。
④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
⑦⑧ 余怀《板桥杂记》下卷。
⑨ 参范志新《余怀生卒年考辩》,《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