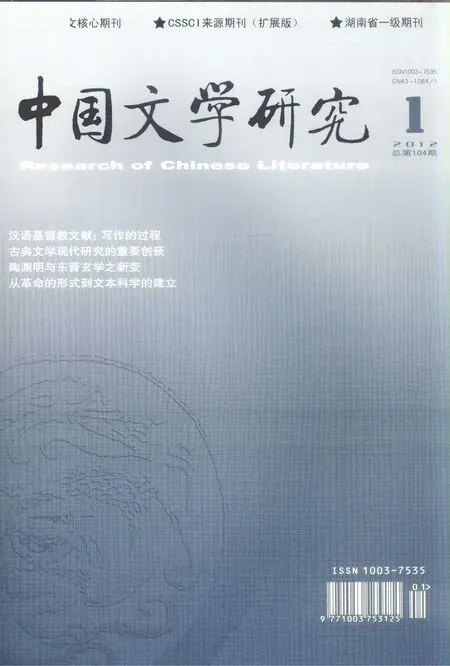皎然《诗式》“作用”与唐五代诗格的“磨炼”理论
李江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作为文学批评术语,“作用”是皎然《诗式》中最先使用的,也是《诗式》中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虽有郭绍虞、徐复观、李壮鹰、周维德、张伯伟、王守雪、张晶诸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有益探讨,然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①。笔者通过阅读发现,如果把“作用”这一概念放在皎然诗论的整体理论体系中考察,又把皎然《诗式》放在唐五代诗格的范围中进行整体考察,分析唐五代诗学相关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就会发现,皎然诗论中所言“作用”这一概念,其意义主要指向诗歌之“意”,指诗歌创作过程中对诗意的琢磨与锤炼,是唐五代诗格“磨炼”理论的一部分。
一
唐五代诗格的发展,初盛唐、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分别是两个高潮,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讨论问题也比较集中,承接这两个时代并促成其理论主题转变的,是皎然《诗式》。与律诗格律的初步形成与最后定型相联系,初盛唐诗格主要讨论声律、对偶、病犯等方面的问题;晚唐五代包括宋初的诗格讨论热点则转到体势、风格、句法等方面。而关于体势、风格、句法的讨论,皎然又是开风气之先的。王梦鸥说:“文镜秘府论西卷,罗列自初唐至皎然时代诸说诗者发见诗文语病二十八种,凡属声调之病,皎然皆无所说,故其措意者唯在意格二端,是又为其论诗之一特色,亦因此一变初唐诗论之面目,而开创中唐迄于晚唐五季诗格说之风气。”〔1〕(P303)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皎然诗论在唐五代诗格中转变风气的作用;其二,皎然诗论的讨论重心和特色在“意格”二端。皎然诗论以“格”为讨论重心,这一点已多为人所注意。《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以“十九字”概括诗之风格,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王玄《诗中旨格》即有“拟皎然十九字体”;而《诗式》的“跌宕格二品”、“淈没格一品”、“调笑格一品”、“品藻”诸条内容也属于这一类。相对于“格”,皎然诗论的另一重心——“意”则关注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皎然诗论重点和诗论特色的总体把握不准,从而使其诗论作品中的部分概念和范畴的特定内涵也因此变得难以索解。学术界对“作用”的理解与阐释也大致存在这样的情况。
皎然《诗式》以“作用”论诗,主要是从“意”方面着眼的,都是关于诗意的表达,这从《诗式》中“作用”的用例不难看出。
皎然《诗式》以“作用”论诗主要有以下几处:
1序
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2〕(P222)
这里首先是对诗地位与价值的总体认识,接下来就讲的是如何用“象”来表达“意”的问题。皎然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为诗人所用,正可谓“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然这运用世间万象表达诗人情志的过程却是值得诗人去苦心经营的。文贵创新,故陆机在《文赋》中说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3〕(P36),皎然则从“意”、“句”两个方面申说,要求诗人避免平易和凡俗。这里的“作用”,大致是指诗歌创作中诗意的提炼与表达(句的内容与形式的锤炼本身就是锤炼并完整表达诗意的一部分)。
2明作用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可企及矣。〔2〕(P223)
依照兴膳宏的分析,《诗式》“明势”、“明作用”“明四声”诸条是对势、作用、四声等基本概念的解释②。然从原文内容来看,似乎更多表达的是律诗中“作用”的必要性和“作用”之法。当然从其叙述可以看出,皎然所说“作用”,同样处理的是诗人“措意”的问题,是诗人在声律等外在形制限制下如何锤炼诗意、完美的表达内在情志的过程。诚如李壮鹰所说:“诗歌贵精炼,且有声律的限制,故叙述不可平直,须有跳跃性。但高明的诗人,于跳跃之中仍能做到词意连属,正如女工缝纫,针脚虽时隐时现,而一线相承不断。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4〕(P14)
3诗有四深
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2〕(P224)
关于“意度盘礴”,皎然在《诗式》“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条还有论述,恰可互为注脚:
4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势有通塞者,谓一篇之中,后势特起,前势似断,如惊鸿背飞,却顾俦侣。即曹植诗云:‘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因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也。意有盘礴者,谓一篇之中,虽词归一旨,而兴乃多端,用识与才,蹂践理窟。如卞子采玉,徘徊荆岑。恐有遗璞。其有二义:一情一事。事者如刘越石诗曰:‘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辕留侯。重耳用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是也。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2〕(P261)
“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一句,诗人“作用”的是什么呢?是“势”和“意”。“势”是古代文学理论中一个基本的诗学范畴,《文心雕龙·定势》是一篇专门讨论文“势”的专论。唐五代诗格中关于“势”的讨论较多,从王昌龄、皎然,到晚唐五代则成为主要话题之一。传统文论中的“势”主要指向作家、作品和文体,论述特定作家、作品及文体的风格形成及其特征。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则向更深更细处开掘,因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势”论的特定内涵。由于诗格中这些“势”论的意义所指较难索解,所以学界的意见也颇有分歧。③从皎然诗论中论“势”的用例来看,“势”大致是指诗中上下联之间在意义表达上形成的一种特别的联系,是诗意流转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曲折回环的张力。王夫之《薑斋诗话》云:“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5〕(P48)王夫之的这段论述似乎恰当的揭示了皎然势论的内在蕴含。皎然这里所言之“意”,显然是指诗意,即诗中所表达的情志。肠有百转,诗意的表达亦应曲折回环,摇曳生姿。
从上引两处的论述和举例看,皎然这里所说的“作用”,也就是对诗中“势”和“意”结构的锻炼,和前两处“作用”用例的意义相同。在《诗式》“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条,皎然以是否“作用”为标准品论前代诗作,他说:
5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者,以师道相高,故有齐、鲁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为汉明矣。〔2〕(P227-228)
皎然认为,李陵、苏武的诗歌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无须刻意营构而天籁自成,故未有作用之功;而“古诗十九首”则“辞精义炳,婉而成章”,故“始见作用之功。”这里需要澄清一点:虽然皎然《诗议》言魏晋以前“古诗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2〕(P203),但此自然正合皎然的“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2〕(P232)之理想境界,并不是说汉以前的诗歌都是不假思索、率意而为的即兴之作,它和皎然此处的议论并不矛盾。故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古诗十九首》在古人中实为特出而能发此蕴者,他说:
……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使人足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弃予矣,必曰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6〕(P642)
细味陈氏此言,对《古诗十九首》“磨炼”之功的揭示颇为精深,正可谓知皎然之心者。
6文章宗旨
评曰: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2〕(P229)
谢灵运诗,人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然此“自然”却不是皎然所言苏武李陵诗“未见作用”的自然,而是“尚于作用”之后的自然,这一点,前人言之者多矣:
王世贞:“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岐级可寻,无色声可指。三谢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极,妙亦自然。”〔7〕(P960)
沈德潜:“前人评康乐诗谓‘东海扬帆,风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约匠心独造,少规往则,钩深极微,而渐近自然,流览闲适中,时时浃洽理趣。”〔8〕(P153)又:“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於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8〕(P156)
方东树:“谢公造语极巧,而出之不觉,但见其混成,巧之至也,以人巧造天工。”〔9〕(P133)
皎然论诗欣赏妙造自然的磨炼之功,这一点他在《诗议》中说得很清楚:
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夫希世之珠,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含变之文哉?但贵成章以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2〕(P208)
皎然推崇谢灵运诗,正在谢诗“琢磨之极,妙亦自然”的特点,此处的“作用”,亦即对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经营锤炼。
另外,皎然在《诗式》分五格评诗,其“诗有五格”条云:
7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2〕(P227)
皎然以诗中是否用事和诗作“情”、“格”的高下将诗歌分为五格,以不用事为最上,“作用事”次之。何谓“作用事”?李壮鹰说:“诗中虽涉及事典,但并不直用其原意,而是经过构思,或引古事作比,或褒贬古事,以申自己的命意,皆属于作用事一类。”〔4〕(P31)此言极是。换句话说,皎然所谓的“作用事”就是:诗中虽有用事,但所用之事是诗人根据诗意表达和诗歌形制要求精心处理加工过的,因而区别于未经处理而直接引入作品之中的“直用事”或王安石所谓的“编事”④。这里的“作用”,就是从表达的角度,根据需要对诗中将用事典的处理和锤炼。
总之,通过分析皎然诗论的理论重心和皎然《诗式》中以作用论诗的用例,我们可以看出,皎然所谓“作用”主要指向诗歌创作中诗人“至难至险”的“立意取境”过程,是诗人对诗意及诗意表达的锤炼琢磨。就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诗有四炼”的理论来比附的话,皎然所言“作用”则大致相当于“炼意”。
二
“尚于作用”是皎然诗学理论的核心。这不但表现在皎然的诗歌创作理论中,而且表现在他的诗歌品评和诗歌发展史的建构中。
皎然以“作用”作为诗歌创作的法则。
皎然主张妙造天功的自然,这就要求创作时有“作用”之功但成诗后却无“作用”之迹,这一思想首先明确表现在上文分析的《诗式》“文章宗旨”、“序”、“明作用”等条中,而“取境”条又云:
评曰: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2〕(P232)
这里,皎然明确表示了对“不加修饰”、纯任天然的创作思想的反对,主张创作时应该“苦思”;并指出,只有通过“至难至险”的“作用”之功,而诗成之后又能泯灭斤斧之痕,才能写出好的诗句。这一思想,在上引皎然《诗议》“论文意”中也有相似表述。具体到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对偶和前人作品的化用,也渗透了皎然“尚于作用”的思想:
评曰:上句偶然孤发,其意未全,更资下句引之方了。其对语一句便显,不假下句,此□□□少相敌,功夫稍殊。请试论之: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又诗家对语,二句相须,如鸟有翅,若惟擅工一句,虽奇且丽,何异乎鸳鸯五色,只翼而飞者哉?〔2〕(P238)
皎然以为,对偶乃“天地自然之数”,诗歌创作自然少不了对偶,不但需要诗人琢磨锤炼,而且要不露“斤斧”,合于“自然”才好。而在化用前人作品这一问题上,《诗式》“三不同:语、意、势”云:
评曰:不同可知矣,此则有三同。三同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如汉定律令,厥罪不书。应为酂侯务在匡佐,不暇采诗,致使弱手芜才,公行劫掠。若许贫道片言可折,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阃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2〕(P238)
对前人诗句的化用,皎然分为“偷语”、“偷意”、“偷势”三种,并在下文分别举例予以说明。结合诗例来看,“偷语”就是直接袭用前人诗句中的文字,同时两句的诗意也基本相似,是为“钝贼”,罪不可赎;“偷意”则是完全化用前人诗句之意而文字不同,这也是皎然所否定的;偷势应该是说承袭了前人诗句的气韵情态但文字则完全不同,这是皎然所赞成的。诗歌创作总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对前人诗句的化用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才能做到以故为新,做到化腐朽为神奇,这就需要“作用”,需要对前人诗句的锤炼吸收,做到为我所用,如己自出。对前人诗句的文字或诗意的直接套用明显失去了作品赖以生存的品质:创新,所以皎然并不提倡;对前人诗句表现出的气韵情态的汲取首先是建立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的,其次,要将这一成果浑成的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需要极大的“作用”之功,是一种相对更难的创造活动,正体现出皎然追求自然而又“尚于作用”的诗学思想。
皎然强调“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的创作方法,遵循这样的方法创作则能达到皎然所期冀的“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2〕(P226)的有作用之功却不见作用之迹的创作效果。
皎然拈出“作用”一语,不但将其作为诗歌创作中 的方法或法则,而且作为回顾诗歌发展史的坐标和评论他人诗歌作品的标准。这在《诗式》“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条、“文章宗旨”及“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等条都明显的表现出来。这些内容本文前面部分皆有引用并做过初步分析,此不赘言。
三
如果把《诗式》放在唐五代诗格的整体环境中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皎然的“作用”理论实际就是唐五代诗格“磨炼”理论的一部分,它上承王昌龄,又下开《金针诗格》及徐寅《雅道机要》等晚唐五代诗格,是唐五代诗格核心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磨炼”一词是对徐夤《雅道机要》的直接借用。《雅道机要》“叙磨炼”云:
凡为诗须积磨炼。一曰炼句。二曰炼意。三曰炼字。意有暗钝、粗落,句有死机、沉静、琐涩,字有解句、义同、紧慢。以上三格,皆须微意细心,不须容易。一字若闲,一联句失,故古诗云:“一个字未稳,数宵心不闲。”〔2〕(P446)
这里的“磨炼”也就是“锻炼”、“锤炼”,指对文辞文意的锤炼琢磨。柳宗元《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一文云:“为文无谬悠迂诬之谈,锻炼翦截,动可观采。”〔2〕(P623)徐夤这里的“磨炼”则意同柳宗元“锻炼”,即是指对诗文字、句、意的反复琢磨。诗歌“磨炼”理论的系统提出则是在旧题白居易的《金针诗格》,其“诗有四炼”条云:
一曰炼句。二曰炼字。三曰炼意。四曰炼格。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2〕(P353)
这里提出诗歌创作中对“字”、“句”、“意”、“格”的全方位的锤炼要求,并称之为“四炼”,是诗歌“磨炼”理论的系统性表现,反映出唐人对于诗歌创作理论总结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唐五代诗格中,做诗需要“磨炼”的思想,王昌龄《诗格》即有相应表述: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2〕(P162)
凡文章皆不难,又不辛苦。如《文选》诗云:“朝入谯郡界”,“左右望我军”。皆如此例,不难、不辛苦也。〔2〕(P161)
“左穿右穴”是王昌龄《诗格》经常用到的词语,同卷“论文意”云:
诗有杰起险作,左穿右穴。如“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泉”,又“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此为例也。〔2〕(P167)
从所举诗例看,所谓“左穿右穴”就是多方面多角度表达诗意。王昌龄首先指出做诗时锤炼诗意的重要和艰难,然后又说做诗“不难”、“不辛苦”,这似乎有些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王昌龄《诗格》卷下“诗有六式”条云:
一曰渊雅。二曰不难。三曰不辛苦。……不难二。王仲宣诗:“朝入谯郡界,旷然销人忧。”此谓绝斤斧之痕也。不辛苦三。王仲宣诗:“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此谓宛而成章也。〔2〕(P186)
可以看出,所谓的“不难”、“不辛苦”就是指虽然做诗需要锤炼,但成诗之后不能留有锤炼的痕迹,不能有迫促之气。
结合王昌龄做诗要求“多立意”,“左穿右穴,苦心竭智”的表述,我们也不难明白,皎然要求“作用”、要求做诗“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理论的直接渊源。
皎然的“作用”论正是王昌龄“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却又“不难”、“不辛苦”的重“磨炼”的诗歌创作思想的发展。皎然继承了王昌龄做诗重“炼意”的思想,将此作为自己诗论的重心,并在多处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
皎然之后,“磨炼”理论在旧题白居易的《金针诗格》⑤中以更系统、更成熟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一理论以“诗有四炼”为代表,以创作法则的形式出现,不仅仅关注创作过程中诗意的形成与锤炼,而且注意到字、句、意、格在创作中的地位、关系及作用,因而提出一整套的“磨炼”主张,并成为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核心。晚唐五代诗格讨论的内容虽然比较广阔,但基本上是以“磨炼”为中心⑥,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上的直接阐述,分别从对字、句、意、格四个方面的磨炼展开。如讨论“炼字”的,就有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诗有四得”、“诗有五忌”,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诗忌俗字”,旧题白居易《文苑诗格》“雕藻文字”,徐夤《雅道机要》“叙磨炼”,宋僧保暹《处囊诀》“诗有眼”,旧题梅尧臣《续金针诗格》“诗有三炼”等。讨论“炼句”是晚唐五代诗格中最多的内容,有句式讨论、律诗各联做法讨论、句病讨论等多个方面,相关材料则有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诗有四格”、“诗有四得”、“诗有五忌”、“诗有三般句”,贾岛《二南密旨》“论南北二宗例古今正体”,王叡《炙毂子诗格》“论章句所起”“两句一意体”、“句病体”、“句内叠韵体”,桂林僧景淳《诗评》的“十字句格”、“十字对格”,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六断”,僧神彧《诗格》“论破题”、“论颔联”、“论诗腹”、“论诗尾”、徐夤《雅道机要》“明联句深浅”、“叙句度”、“叙体格”、“明势含升降”等。“炼意”也是晚唐五代诗格讨论较多的,有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诗有义例七”,僧神彧《诗格》“论诗病”、旧题白居易《文苑诗格》“杼柝入境意”、“语穷意远”、“叙旧意”,贾岛《二南密旨》“论总显大意”,旧题梅尧臣《续金针诗格》“诗有三炼”,等等。讨论“炼格”的,有《金针诗格》“诗有四得”,贾岛《二南密旨》“论立格渊奥”,齐己《风骚旨格》“诗有三格”,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诗有三格”,王玄《诗中旨格》“拟皎然十九字体”等。
其次,晚唐五代诗格的著作群体中,苦吟诗人居多;诗格中所举的诗例也以苦吟诗人诗句为主,这一情形也能说明其讨论的内容是以“磨炼”为中心的事实。
再放大一点说,诗歌发展到唐代,律诗的体格以及声律的限制使得诗歌的创作成为一种技术含量颇高的事情,要在有限的字数中涵咏丰富的情志,则必须经过反复的“磨炼”,这应该是包括皎然“作用”在内的“磨炼”理论产生的大背景。
〔注释〕
①以上诸家对“作用”的解释,可参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徐复观《皎然<诗式>“明作用”试释》(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第271-27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李壮鹰《诗式校注》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又,该书最早于198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该条注释未变)、周维德《诗式校注》第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张伯伟《诗格论》第34-37页(该文为作者《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代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王守雪《皎然<诗式>“作用”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期,420-424页)、张晶《论皎然的“作用”说》(《学术研究》2006年8期,141-144页)等成果。
②参兴膳宏《皎然<诗式>的结构和理论》,收《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79页。
③这一论题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王增斌(《唐末宋初诗格书综论》,《文史知识》1993年2期,113-116页)、张伯伟(《诗格论》,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前言部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见《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巩本栋(《环绕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的诸问题》,《文史哲》2007年1期,95-102页)等都有相关论述,笔者这里对“势”的论述也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④《蔡宽夫诗话》“荆公言使事法”条引王安石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19 页)
⑤《金针诗格》的作者问题向有争议,这里不拟论述。本文从其和晚唐五代诗格理论主题相似性的角度考虑,将其和晚唐五代诗格一并讨论。
⑥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磨炼: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3期)及《晚唐五代诗格的著作群体》(《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4期),本文限于篇幅,不做详细论证。
〔1〕王梦鸥.试论皎然诗式〔A〕.古典文学论探索〔M〕.台北:正中书局,1984.
〔2〕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李壮鹰.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戴鸿森.薑斋诗话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续修四库全书(总第159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王世贞.艺苑卮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苏文擢.说诗晬语诠评〔M〕.香港:志豪印刷公司,1978.
〔9〕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