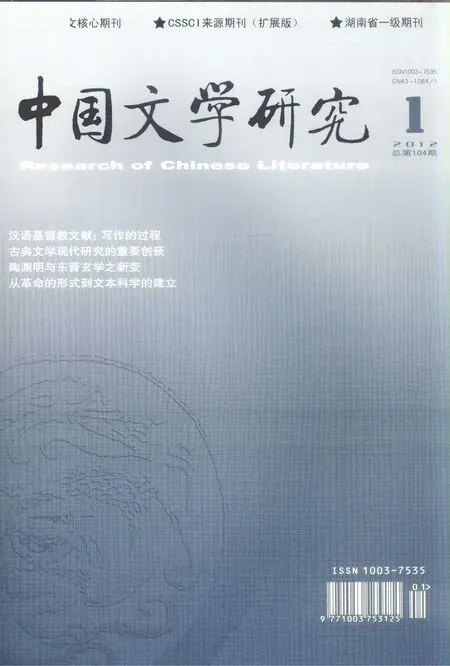陶渊明与东晋玄学之新变
曹胜高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当前玄学史,言及东晋玄学,多以玄佛合流概之,视其所论,实重阐释佛家之演生而遮蔽玄老庄之发展,合玄学而入佛学,而忽略东晋玄学的主体性。〔1〕一种思潮之消弭,虽草蛇灰线,然必有端绪。东晋玄谈之风浓厚,其论未能如西晋玄学家著述精深,可资玄学史讨论,而散入文章著述,见于立身处世,一改西晋“谈玄”为“体玄”,遂使得玄风内敛于心而不悬于口,外化于行而不彰于论。恰此时,谈佛判教之风新起,藉玄言而畅佛理,今所存佛经注赞,多援玄论,实以佛论为主体。此虽可析东晋思想之特征,然不足以辨明东晋玄学之特质,即东晋玄学在佛学之外,有无主体性的演生,其命题、观点为何?本文试杂撮史料,离析出与佛合流的玄论,并以陶渊明哲学思考的思想背景作为个案分析之。
一、抱朴守真与守拙意识
西晋太康间兴起的反玄虚思潮,削弱了坐谈玄论的空诞之风,使得省净清虚成为东晋新的政风和文风。〔2〕这种政风和士风,得益于玄学的新发展。
正始玄学的形成,出于自然和名教的辨析,这种辨析在魏晋易代之际,夹杂了深厚政治背景和惨痛的人生经历,名教和自然冲突与其说来自学理上的矛盾,不如说来自政治生活的冲突和抗争。太康玄学的讨论,集中在有无、言意、本末诸论,却少何晏、嵇康激切之风,亦乏王弼、阮籍等苦闷之气,其中虽有二十四友等浮华交游之徒,经历杨、贾党争之祸,然其论玄,多能词尚平达,语重泰夷,渐成为玄论的新风尚。待至阮瞻,“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神气冲和,……由是识者叹其恬澹”。〔3〕(P1363)以省净清虚作为太康玄家的态度。何劭《赠张华诗》云:“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树塞焉足摹。……奚用遗形骸,忘筌在得鱼。”期望琴书自娱,抛却尘嚣。张华《赠挚仲治诗》也提到:“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恬淡养玄虚,沈精研圣猷。”主张将退隐、守拙、恬淡作为理想。即便如石崇者,亦常有玄远之思,其《答曹嘉诗》:“孔不陋九夷,老氏适西戎。逍遥沧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渴望冲和玄寂的人生。这些赠答诗中屡次提及恬淡冲和的期待,足以看作西晋时期士人深沉的心理期待。
这种共识在党争不断、变乱不止的环境中,难以实现。阮裕曾有远遁之意,终应诏入仕,或问其故,答曰:“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耳。”〔3〕(P1368-1369)或出于对世事浮沉的担忧,或出于对外在事功的惆怅,西晋士人普遍有一种躬耕守拙的向往,陆云《逸民箴》:“无念尔本,聿修厥谆。执盈如虚,乃反天真。”肯定逸民的纯朴。《荣启期赞》:“居真思乐之林,利涉忘忧之沼,以卒其天年。荣华溢世,不足以盈其心;万物兼陈,不足以易其乐。绝景云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岂非天真至素,体正含和者哉!”认为天真至素、不计荣华乃人生之和。潘岳《闲居赋》亦歌自己守拙之思:“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而奚拟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很难想象躁进轻浮的潘岳有如此神驰的精神家园。由此观之,这种守拙、缄默、素朴的人生情怀,绝非书于纸面的敷衍之语、标榜之词,而是当时士人普遍的精神向往。
西晋士人重视的素朴、天真意识,源自老庄。《老子》第十九章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渔父》:“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按照陈鼓应的理解,这种抱朴守真,是守中、养中的表现,〔4〕(P91-92)汉晋间人以抱朴守真为安贫乐道、超脱穷达的旨归。《后汉书·申屠蟠传》言:“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王琨在《荐范乔》中称赞:“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箪瓢咏业,长而弥坚。诚当今之寒素,著厉俗之清彦。”不因为外在的穷达和富足而改变自己的志趣。渡江之后,偏安一隅的行政格局,使得西晋激烈的内斗暂时平息;王导、谢安等人倡导的简约政风,使得躁急功利的士人有所收敛,西晋玄谈所辨析的自然名教合一,不仅成为一种内在的修养,而且也成为一种精神的安慰。葛洪在《抱朴子·道意》中便说:“患乎凡夫不能守真,无杜遏之检括,爱嗜好之摇夺,驰骋流遁,有迷无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诱于可欲,而天理灭矣,惑乎见闻,而纯一迁矣。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而徒烹宰肥,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讴歌踊跃,拜伏稽颡,守请虚坐,求乞福愿,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把嗜好、物欲、迷情作为修身之大敌,主张守虚冲和以守中,气定神闲以养中,又如《抱朴子·养生论》所言:“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抱朴守真的意识,促进了东晋士人检束自约、拙朴自娱的新风尚。
西晋士人的放旷,从理论上得到了纠正,使得东晋清虚淡约的士风更加自觉。戴逵的《放达为非道论》论述了个性和礼度的统一,批评了竹林、元康玄学的放旷,认为士人应该“栖情古烈”、“拟规前修”,不能“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3〕(P2458)在这种认识中,质性自然和礼乐教化得到了有机的融合,都内化为个人修养。戴逵在《闲游赞》中,称赞能够以纯静之思、素朴之心俯仰宇宙、练达世事的“神人”:“使夫淳朴之心,静一之性,咸得就山泽,乐闲旷,自此而箕岭之下,始有闲游之人焉。降及黄绮,逮于台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由此提倡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晋的新玄风:“冥外旁通,潜感莫滞。总顺巢离,兼应夷惠。缅矣遐风,超哉绝步。顾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嚣务。详观群品,驰神万虑。”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天性、真情,而且能够治国理政、得心应手。这种自然与名教的圆融合一,渐成为东晋士人的人格理想。张天赐《遗郭瑀书》中说:“先生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赞赏能够在自然之中保持真性情者。支遁《八关斋会诗序》:“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遂便独住,于是乃挥手送归,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以山水娱情,以自足保真。这种尚真、乐寂、抱朴的作风,不仅是儒道思想的高度融合,而且是玄学内化为个性修养的基本特征。
东晋抱朴守真思想的形成,是西晋玄学的新发展,也是佛教思想浸润的结果。佛教中求真、率真的意识,与玄学中正在生成冲淡、清虚、天真等观念合拍,使得老庄的守中、养中观念更加明晰。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中说:“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将寂静、无执著、玄默作为法之根本。他的《比丘大戒序》又说“乃知淡乎无味,乃真道味也”,将淡漠作为佛修之要旨。僧睿在《大十二门经序》认为只有不滞于外形、不固于声色者,才能悟到佛理之“真”:“不滞者,虽游空无识,泊然永寿,莫足碍之,之谓真也。”佛教对于真的体悟,在于透过殊相看到空寂,其所谓的“真”,在于看透看穿;玄学所理解的“真”,在于回归天性,追求抛弃后天私欲污染而形成虚伪、矫饰和束缚,回归到自然而然的状态。
我们知道,庄子所提出的真,立足于其全天性之说,是要人抛却礼法,由着真性情去面对自然,不免失之于执拗。经过了魏晋儒学的浸润和调和,东晋玄论中的“真”,不再以反外在礼法、反后天修养为目标,而以反对人性之中的虚伪、自私和矫饰立意。在陶渊明看来,在当时的尘俗中,很难做到“抱朴守真”,他在《感士不遇赋》序中说自己读董仲舒《士不遇赋》“慨然惆怅”,在他看来,“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但在当时,“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自己不愿意违背真性情,去适应时俗,便下决心“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在充满机巧、聪明的社会中,渴望抱朴守真的人,只能自嘲自己的拙朴。陶渊明把自己不合于世事、不能尘俗浮沉的性情称之为“拙”,认为这是“非矫励可得”的“质性自然”。他说自己归隐,正是不能应付外在的机巧的“守拙”:“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5〕(P76)他甚至还津津乐道于这种苦拙。他在《乞食》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言自己不善言辞;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说自己“邈与世相绝”“荆扉昼常闭”,正得益于自己“深得固穷节”、“栖迟讵为拙”。他在《咏贫士》其六中赞美仲蔚:“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他不断自嘲的这种“守拙”,正反映了他抱朴自乐的安然。
陶渊明认为“守拙”正是保真,他在《劝农》中称赞上古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期望自己如同后稷那样,能够勤于垄亩,“矧伊众庶”。他在《饮酒》其二十中又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言上古之后,真淳之风不断衰落,孔子曾试图弥补,但无济于事。言外之意,增了几多遗憾。陶渊明所体悟的“真”,更多秉持了老庄的看法,即认为至世存于尧舜之前。要想保持真性,那就要远离尘嚣,回归自然,这与儒家强调的至世存在于尧舜时期不同。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中说:“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认为只有隐居,才能养真。在《连雨独饮》中,他认为“运生会归尽”,“任真无所先”,没有机心的“任真”,正是顺应大化。陶渊明的“含真”、“养真”、“任真”,是用心去体认,用行为去践行,而不是理论的总结和语言的表述,他的《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如果说葛洪、戴逵、道安等人对真的辨析,是哲学或者思想上的讨论,那么陶渊明对真的体认,则是一种生活化的践行,这种真意入之于诗,实现了“抱朴守真”观念的诗意化。
养真守拙,是晋宋之际文人乐道的一种风气。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不仅认为执政应该守拙,“长守朴以终稔,亦拙者之政焉。”而且认为自己畅游山川,颐养性情,也是守拙:“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他在《初去郡诗》中也说:“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径以拙讷自许。陶渊明和谢灵运气质不同,却都在诗中津津乐道于自己“守拙”,把守拙看成精神上的自我体认,体现出晋宋思想的延续脉络。
由此可见,东晋士人谈玄,更多是将注意力从社会移向个人,不再关注于外在的事功,而是审视内在的玄默,把礼乐修养和自然性情结合起来,通过自我体验,使得玄意内敛,不再注重理论的辨析,而重视玄意的实践。内化了的玄意,蕴涵于山川田园,随着作者的游目经历,使得外在景物与心相通,与情相契,田园诗、山水诗能够替代玄言诗、游仙诗,体玄之风当是其转型的主要思想动力。
二、应物顺化与自然态度
魏晋玄学对中国思想史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自然提升到一个与名教相并立的高度,使得人不再完全着眼于社会秩序的经营和人际关系的调整,而是在最广阔的视角下讨论作为一个自然的人的合法性,也肯定人的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这完全可以看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突破:第一,在先秦,天与人常常被理解为是并立的,人更多是顺服于天命、天德、天道、天志,在这种背景下,“天”是作为一个“异己”的力量而存在的,人必须服从天意,汉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把这种思路发展到了极致。第二,即便在《周易》经传中存在天人合一的讨论,也更多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的产物,是人试图“弥纶天地之道”的一种尝试,其立意在于“通天下之志”,也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在这种学术背景中,人的社会属性被放大,自然属性被忽略。第三,先秦诸子所论中,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是对立的。受制于时代背景和学说局限,或者过分强调人应该服从于社会秩序,如儒家、法家、墨家等,或者刻意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如杨朱、列子等,或者感慨人的被扭曲被异化而无法保持天性,如老子、庄子等。当王弼、何晏以名教本于自然立论时,已把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分别关注,把个体自我的需求和社会群体的要求并立起来辨析,作为个体的人开始自我觉醒。阮籍、嵇康所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解开了束缚在人性上的外在绳索,把作为一个自然的人的情感、向往、自由释放出来,人的自我性情得以畅达,尽管这种观念难免矫枉过正,但其所释放出的那种渴望,颠覆了此前儒道学说期望表达而无法言尽的压抑,明确承认人主体自我需求的合法性,甚至认为这种合法性可以压倒社会群体要求的合理性。元康玄学所提倡的名教即自然,则更为理性地折中了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肯定了自然的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元康玄学在此理论前提下,继续探寻人的自然性,即作为一个主体自觉的人,应该如何生活,才能达到“自然”。元康玄学从理论上作了辨析,江东士人从行为上作了实践。
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所提倡的“无待而独化”说,把人的发展、人的完善作为个案来审视,瓦解了儒家面向群体进行社会意义上的教化说,促成了人的个体独立和个性发展。那么,如何独化呢?《庄子注》发挥了庄子“虚己顺化”的人生态度,把“冥然自合”、“足性而止”、“无为逍遥”作为人保持自然的法则,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玄冥深远所致,人应该悉心体察宇宙的开合张弛,效法自然,安内游外,淡然自若,做到无心而顺有,无为而自然,逍遥而从俗。这一理论,促使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息息相通,将汉魏时期所形成的物感论,提升到一个更自觉的境地。
物感论是天人感应学说的进一步深化,其不再以“天德”和“天志”的眼光来审视天与人的关系,而是把“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是与“人”并立的外在世界,在这样的视域中,“天”和“人”都是“道”的体现,天与人同构,而且相参相应,每一个生活在自然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自然的一张一弛,一枯一荣。阮籍的《咏怀诗》,常常以“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的物我相感发端,〔6〕(P92)把自己无边的苦闷排遣到自然之中,着力抒写物我之间的细微而深切的情绪体验,把自然作为心灵的寄托和思想的载体。而嵇康则更多将山水之游作为摆脱尘俗、修身养性的方式,他在《赠兄秀才入军诗》其十七中说:“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在《幽愤诗》中所言:“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皆将自然作为人生的参照,期望从自然之中获得更多的人生慰藉。阮籍的“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6〕(P89)更多倾向于应物而感,嵇康的“至人远鉴,归之自然”,〔6〕(P19-20)则强调要顺应大化。可以说,阮籍的物感论,代表了魏晋诗歌发展的新动向,嵇康的自然顺化,则引导着两晋士人体玄的新方式。
皇甫谧在《释劝论》中说“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把天地万物视为自然运化的结果。杜预为河南尹时论政:“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3〕(P1026)主张治理国家应该顺应大道,要用心体悟天地至理,无为而自然地行政。张华《鹪鹩赋》言人生:“静守性而不矜,动因循而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杜预、张华所言的自然,既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风物,更指代应物顺化的自然态度,即挚虞所谓的“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的人生认识,〔3〕(P1419)把“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作为行为方式。〔7〕(P805)
东晋玄论、佛论、政论,皆以应物顺应、无所强求为自然.这种因循自化的理论和态度,一改西晋士人外在的躁进和功利,使得冲淡自足、娱情山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其一,重视万物独化、自化,视生死为自然循环。张湛继续发挥《庄子注》,认为天地万物自有自生,“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尔,固无所因假也。”〔8〕(P56)不受外在的拘束,而且万物变化循环往复,生死亦如此:“俱涉变化之途,则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极之域,则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8〕(P3)他主张“以形骸为真宅”,把死亡“归之于无物”。〔8〕(P31)僧佑在《重与慧远书》中说:“知以方外遗形,故不贵为生之益,求宗不由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所言,自然界中的人,要能够观化、顺化、入化,才能够离世而超脱。郗鉴病重,上疏逊位言:“自忖气力,差理难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视生死为自然规律,遥应王祥临终之超脱态度。这种超脱豁达,是对“大块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3〕(P1913)的深沉理解,是对东晋士人注重养生、渴望成仙的“惜生”的否定。
其二,执政理民,也要顺应时事,因世而变。东晋政论,顺应人情世故为自然。孔衍《乖离论》、范汪《祭典》、殷融《上言奔赴山陵不须限制》论礼,以求合于人情。《释驳论》:“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无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当矣。”慧远在《求宗不顺化》中说:“天地以得一为大,王侯以体顺为尊。得一,故为万化之本;体顺,故有运通之功。”王坦之主张名教并用,其《废庄论》言:“使夫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东晋士人眼中的自然,乃合人情物理、名教自然于一体,如《食举东西厢乐诗》所言:“广大配天地,顺动若陶钧。玄化参自然,至德通神明。”追求顺化天地与注重德行的有机统一。
其三,自然与人同构,以齐物意识体认自然,才能做到应物顺化。张湛所说的“应理处顺”,〔8〕(P13)是人与自然均应合于大道,与外物一起消长,体味自然之化迁,感悟山川之生机,反观人世之际遇,不执著,不强求,自然而然。僧肇在《般若无知论》也说:“假致疑智虽事外,未始无事。神虽世表,终日域中,所以俯仰顺化,应接无穷,无幽不察而无照功,斯则无知之所知,圣神之所会也。”人与自然万物息息相通,彼此感应,弃尘俗之杂而务心绪之宁。《阿毗昙心序》中言:“发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谓显法相以明本,二谓定已性于自然,三谓心法之生,必俱游而同感。”即要明乎本心、顺应自然、物我相感。《不真空论》:“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无滞而不通,故能混杂致淳;所遇而顺适,故能触物而一。……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夫以物物于物,则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虽物而非物。”只有放下心中非分之念,顺应物化,才能不被万物所役使,才能遗貌取神,洞悉天地运行之大道。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王羲之去官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3〕(P2101),并言于谢安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9〕(P121)把山水之游作为自然。隐士董京《诗》言:“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将清虚自然作为人生乐地。王该《日烛》中说:“无事为以干性,常从容于自然。”以清淡简约作为生活方式。
东晋士人的应物顺化,影响到陶渊明的生活态度。陶渊明所期待的自然,体现了一定的哲学思考,究其内涵有三:
一是不受拘束的自由精神。他三十八岁时所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言:“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认为人如果能够抛弃外在的凭借,才能不被奴役达,到庄子所言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无所待”状态,获得身心的彻底解脱,回归到人的本性。
二是不被异化的自在天性。《庶人孝传赞》:“父母终,思慕委毁,推财与兄弟,隐于草泽,君子以为难,况童龀孝于自然,可谓天性也。”他承认孝顺为人之天性,必须顺应这种天性。《归去来兮辞》中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种天性是不能被扭曲、不被异化的,当官场充满矫饰之风,自己不能适应时,宁肯保持自己的天性也不能委曲求全。
三是安之若命的自然态度。这种自然心性,是精神自由、生活自在的升华,摆脱了自身的喜怒哀乐和生死忧患的委运乘化。他在《形影神诗序》中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东晋葛洪、陶弘景修道以养生,王羲之、王恭、谢安等服药以惜生,以及郭璞、庾阐等求仙以延生的做法,在陶渊明看来不过是渴望摆脱生死的归宿,但无论如何用心经营,都不能超越天地运化。他期望这些“惜生”的君子不要忧虑形神的问题,应该抱着顺化自然的态度来对待生死。《庄子·人间世》曰:“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认为要保持自己精神逍遥,与其外修,不如内修,只要不迷失心性,不迷失自我,就能够用真心体悟天地大道。陶渊明所言的“共取其心”,正是追求一种喜怒哀乐不扰于胸、安之若命的自然态度。其《神释》言:“老少同一死,贤遇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的应物顺化,是超越了生死的应物顺化,是摆脱了名利观念的超凡脱俗,是放弃了世事尘嚣的哲学感悟。
陶渊明的自由精神、自在天性、自然态度,是魏晋玄学万物独化、自化、顺化理论浸润的结果。陶渊明思想中期待的不物于物的自由,使得他能够摆脱外在功业的诱惑;不被异化的自在,使得他安于农村朴素的生活;安之若命的自然,使得他能够心平气和地居于园田,把自己的感悟诗意化。
三、心性逍遥与逸民情结
陶渊明以“自事其心”、“安之若命”的态度来审视自然和人生,使他能够超越东晋多数“好事君子”的困惑和痛苦,以己心审视人情、物理、风光,把心性逍遥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应物顺化的自然态度,使得他能够敞开心扉,把不违背自己心志视为快乐。与朋友交往,他把心心相通的默契作为快乐,《赠长沙公族祖》说:“何以写心,贻此话言。”用心规勉陶延寿。《酬丁柴桑》言:“放欢一遇,既醉还休。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与丁县令欢心醉饮。《答庞参军》也说:“我求良友,实覯怀人。欢心孔洽,栋宇惟邻。”他与朋友相处的和睦,在于自己没有矫饰的真心。他在《移居二首》其一中说,“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以自己的素心来面对自然、面对友情,说明了陶渊明的心性澄澈。
一个人心性如何,既取决于他对待自然的平和,对待朋友的和善,更取决于他对待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在孤独时,他如何审视自我,如何面对自己。他在《时运》中说:“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以称心如意、自娱自乐来保持精神的自由。在自然界中,他能够与景物相欣赏,即便“偶影独游”,也能“欣慨交心”〔5〕(P8),在于自己天性的保全和精神的畅快。他在自然中寻求能够与自在之心相应的景物:“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5〕(P53)正是由于他能够顺应大化,便能放下自我:“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5〕(P125)平和地对待自然迁化。他期望在宁静的田园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快乐。“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5〕(P261)这种称心自乐,是看淡生死、看破功名、安之若命的超脱。
陶渊明的平和,不是佛教的空寂所然,也不全是道家的超脱所致,而是儒家“纵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体现。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焦虑,更有伤感,还有叹惋。他在《悲士不遇赋》中,表达了自己的诚挚和追求:“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在《闲情赋》中,他说书写自己的执着之情,意在“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表面的疏离绝情,恰是为了心性的安适。他在《赠羊长史》中,更是感慨自己的孤独:“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不是自绝于世,而是自觉对乱世的疏远。在《悲从弟仲德》中睹物思人:“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面对年岁荏苒,他依然感慨:“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5〕(P223)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杂诗十二首》其九中,写羁旅行役,充满了对家的思念和牵挂。
正因为世事与自己的心志多暌违,陶渊明才弃官归隐,以求天性的保全、精神的自由。他在《归去来兮辞》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他在作品中反复陈述自己不愿违心:“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把回到家园之中的怡然自乐,作为自己的理想:“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既然现实生活与自己本性不合,人生苦短,何不称己心而归于本真、顺大化而归于自然。他更加珍惜田园生活给予自己心灵的安慰,使得自己能够得到与心性相应的快乐和欣喜。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说:“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乡村的自在,使他体会到了长沮、桀溺等隐士的情趣。《拟古九首》其一:“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平淡无痕,欣喜由心。《咏二疏》:“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与乡邻对酒,无需言语辩白。《咏贫士七首》其三:“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只求欣然忘怀。
陶渊明的真诚而又逍遥、深挚而又闲适的自然态度,从表面看,是他的修养和性情所致,若从深层看,则是两晋的逍遥观念和逸民情结的延展。
自汉魏之际隐逸意识形成之后,便一直成为两晋文人期望摆脱现实痛苦的精神途径,尤其是在世事困顿之时,逍遥便成为保持精神自由的期待,而隐逸也成为保持不被异化的向往。陆机、石崇等躁进竞利之人,偶尔尚有澄心逍遥之念、遁世安闲之思。陆机在《演连珠》中说:“遇过而悔,当不自得。垂钓一壑,所乐一国。被发行歌,和气四塞。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渴望有朝一日能远遁尘俗。石崇在《思归叹》:“释冕投绂兮希聃,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祸不来。”认为超绝尘俗才能达到福祸不至的逍遥。潘尼《怀退赋》:“岂遁世之独立兮,庶北门之在兹。归幽岩之潜穴兮,托峻岳之崇基。”以退隐山林作为保持个性独立的方式。更不用说清淡缄默的陆云,更是以遁世立德作为理想的人格,他在《与陆典书书》中称赞“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在《南衡诗序》说“南衡,美君子也。言君子遁世不闷,以德存身”;在《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投弁释》钦羡陆绂“遁世无闷,清源是濯。馥风弥馨,明徽载铄”。把遁世归隐和心性逍遥联系起来,正是西晋隐逸的基本旨归。
这种隐逸意识,促成了西晋士人对隐逸的褒扬。皇甫谧在《高士传序》中称赞许由、善卷等“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列举九十余人,大加褒扬遁世隐逸之人。由此开端,西晋文人大量创作褒扬逸民的诗赋,赞美那些“遗情市朝,永志丘园。静犹幽谷,动若挥兰”的隐遁之人。〔10〕(P677)西晋士人对这些隐士逸民气质的描述中,充满了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想象。陆云《逸民赋》想象他们生活的自在:“寻峻路兮峥嵘,临芳水兮悠裔。盘丘园兮暇豫,翳翠叶兮重盖。瞻洪崖兮清辉,纷容与兮云际。”其《逸民箴》又称赞他们高贵的情怀:“无念尔本,聿修厥谆。执盈如虚,乃反天真。”江逌的《逸民箴》描述他们的悠闲冲和:“解发灵崖,被褐弦丝,飘飘台上,轻举高之,穆穆二仲,携策相期,盘幽隐寂,与物无治。”束皙的《近游赋》更以躬耕田园为世外逸民:“世有逸民,在乎田畴。宅弥五亩,志狭九州。安穷贱于下里,寞玄澹而无求。乘筚辂之偃蹇,驾兰单之疲牛。……及至三农间隙,遘结婚姻。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西晋士人对隐逸生活的想象,从理论层面为遁世意识提供了精神支撑,促成了东晋遁世行为的普及。
逮至东晋,士风夷泰,逍遥于世外、寄情于山水成为士人生活方式。王羲之《兰亭诗》言:“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以逍遥顺化、良辰游赏作为人生向往。谢安《与王胡之诗》也说:“触地儛雩,遇流濠梁。投纶同咏,褰褐俱翔。”以旷达自如、随遇而安为处世情怀。在这种风气下,谢玄在始宁占山封水,傍山带水修建别墅,修建北山二园、南山三园。孙绰“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倚茂林,带长阜”。〔7〕(P636)王羲之时“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名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3〕(P2098-2099)孙绰在《答许询诗》中说描述了归隐田园的乐趣:“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匈怀,神栖浩然。”栖神存默,游怀山水,与自然交流,独享闲寂的意趣:“寂寂委巷,寥寥闲扉。凄风夜激,皓雪晨霏。隐机独咏,赏音者谁。”这种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晋渴望逸民之思逐渐转化为体会退隐之乐。
这种逍遥遁世的时代风气,是道家游仙远遁观念的促成,也与东晋佛教思想合拍。在佛教看来,出家也是一种远遁:“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11〕(P220)他们认为以隐逸为旨趣的遁世,道、佛、俗皆同,都是保持心性逍遥、忘怀尘俗的修养方式,道家的含真保和与佛家的幽怀抱素相通。僧肇在《鸠摩罗什法师诔》中也说:“大人远觉,幽怀独悟。恬冲静默,抱此玄素。”东晋所推崇的遁世,意在逍遥心性、不役于俗。支遁在《逍遥论》还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把蜕于尘世之外,不役于外物视为逍遥之本,而要保持自己的真性,就要能脱离尘俗,《涅盘无名论·妙存》:“夫至人虚心冥照,理无不统,怀六合于胸中,而灵鉴有余;镜万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虚,至能拔玄根于未始,即群动以静心,恬淡渊默,妙契自然,所以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虚心应物,恬淡退隐,参悟大化,静悟自然,不违心,不屈己。
庄子的心性逍遥之论,经过两晋玄学的滤汰,以隐逸遁世、保真养性作为生活方式,使得东晋隐遁之风大兴。《晋书·隐逸传》列孙登、董京、陶潜等三十八人,《宋书·隐逸传》列戴颙、宗炳等十五人,皆由晋入宋者,除陶渊明两出外,共有五十二人,足见两晋隐逸风气之盛和遁世情怀之深。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的归隐,正是这种超然世外、不染尘俗的逸民情结的展现。他在《读史述九章》中感慨夷齐之懦、箕子之凄、管鲍之交、程杵之德、七十二弟子之贤、屈贾之感、韩非之患、鲁二儒之贞、张长公之志等在人生起伏、世事变易之际的遭遇,足见其逸民情结之深。又在《扇上画赞》中赞美荷蓧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等,称赞他们能够忘却尘俗,“寄心清尚,悠然自娱”,自由自在,做到“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不仅寄托了他对待世事变迁中人情世故的感叹,也寄托了他对逸民们高尚人格的仰慕。
从这个角度来讲,陶渊明的归隐,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时世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两晋兴起的逍遥自足的思想意识和遁世隐逸的文化风尚。陶渊明能够成为晋宋隐逸的代表,除了恬淡闲和足以楷模外,更在于其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抒写隐逸情趣,从而使之成为隐逸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曹胜高.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J〕.浙江师范学大学报,2010(1).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李志军.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张湛.列子·汤问注〔M〕.上海:上海书店,1986.
〔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