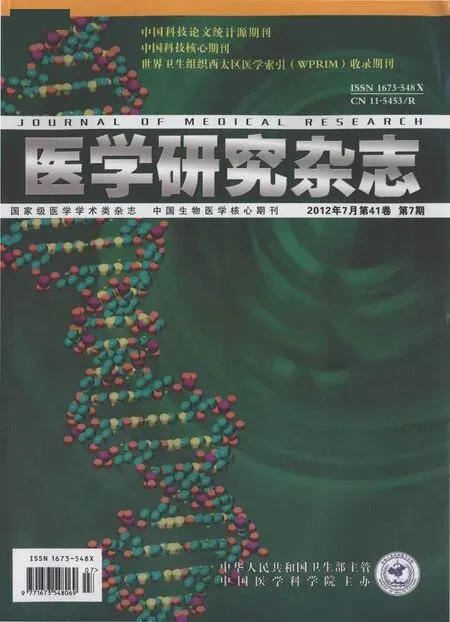难治性癫痫多药耐药基因学说研究进展
潘楠楠 郑乃智
癫痫是一类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据统计全球癫痫患者占世界人口的1%左右[1]。在我国,癫痫的发病率约为0.5%~0.6%。癫痫发病可见于任何年龄,但以青少年多见。大多数癫痫患者在接受了正规的抗癫痫药物(antiepileptic drugs,AEDs)治疗后,其病情可以得到控制。约有30%的癫痫患者仍有癫痫发作,称之为难治性癫痫(refractory epilepsy,RE)。目前国际国内对RE的定义尚无统一规定,美国国立癫痫协会提出:在癫痫中心接受2个月的抗癫痫治疗之后,仍有癫痫发作,则定义为RE。国内吴逊等提出RE诊断需具备以下3个条件 :①癫痫发作比较频繁,每月达4次以上;②应用适量的AEDs正规治疗且血药浓度保持在有效浓度范围内,至少2年仍不能控制癫痫发作且影响日常生活;③排除其他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颅内占位性病变[2]。
RE不受药物控制,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如:非预期死亡增加,骨折等身体外伤,精神和心理创伤以及社交障碍等[3]。因此研究RE发病机制,寻找治疗RE的方法,帮助患者达到无发作,具有重要意义[4]。尽管有大量关于RE耐药机制的研究,但其机制仍不明确。目前关于RE耐药机制主要形成3个学说:①多药耐药基因学说;②靶点学说;③神经网络学说。这3个学说目前均有大量的实验证据支持,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多药耐药基因学说。
药物在脑组织的分布受到严格的控制,必须穿过血脑屏障和血脑脊液屏障才能达到要作用的部位。血脑屏障由内皮细胞,胶质细胞足突,基质和周细胞构成,其内皮细胞之间存在紧密连接,因此药物要透过血脑屏障具有一定选择性。在血脑屏障内皮细胞上表达依赖ATP的转运蛋白,他们可以把进入脑组织的药物逆浓度梯度排出细胞外,在大脑中起了“第二屏障”的作用。多药耐药基因学说认为RE耐药的主要原因是进入脑内的AEDs被这些转运蛋白泵出,从而使脑内药物的浓度下降,达不到抑制癫痫发作的作用。目前研究最多的多药转运蛋白有: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MRP)和乳腺癌耐药蛋白(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BCRP)。
一、多药耐药基因(multidrug resistant gene,MDR)及P-gp
MDR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基因家族,位于人类7号染色体的长臂7q21-21.1。人类MDR基因家族有MDR1和MDR2两个成员,MDR1是可调控基因,是编码P-gp的主要基因,与多药耐药相关。啮齿类动物的MDR有3种基因型:MDR1、MDR2、MDR3,与多药耐药相关的是MDR1a/MDR1b。
P-gp由1280个氨基酸残基构成,其相对分子质量为170kDa,由两个相同的亚基组成,每个亚基均含有一个6次跨膜区和细胞内核苷酸的结合区,其N端高度糖基化。P-gp为转运蛋白ATP结合物超家族的成员之一,属于ABCB亚家族,是一种位于细胞膜上的依赖ATP的糖蛋白,可以利用水解ATP释放的能量将细胞内的药物、毒物排出细胞外。生理情况下,哺乳动物体内均有P-gp表达,主要分布在一些具有排泄和分泌功能的器官,如肠上皮细胞。在脑神经元及神经胶质细胞中没有表达。
在对RE耐药机制研究中发现,如果患者对一种AED耐药,则对其他AEDs也不敏感,尽管这些AEDs的化学结构与作用方式各不相同。存在于RE中的这种多药耐药现象与肿瘤化疗中的耐药机制相似,因此研究人员推测两者应该存在相似的作用机制。在肿瘤领域,肿瘤细胞存在多药耐药现象是由Keld Dano在1973年提出的,他发现如果肿瘤细胞对柔红霉素耐药,则会对其他多种结构功能不同的化疗药物也产生耐药性,如长春花生物碱类。此后,Victor Ling与他的同事发现一种减少肿瘤细胞内药物浓度并参与肿瘤细胞多药耐药的蛋白:P-gp。
1.MDR1及P-gp与 RE的关系:第1次指出MDR1和P-gp与RE有关的是1995年Tishler,他通过研究RE患者外科手术切除的脑组织,发现癫痫灶内血脑屏障内皮细胞有显著增加的MDR1和P-gp表达。此后大量关于MDR1和P-gp在RE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出现,并形成了多药转运蛋白学说。该学说认为RE患者血脑屏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内P-gp的过度表达,是RE耐药的基础[5]。(1)体外细胞培养观察MDR1及P-gp与RE的关系:1995年Tishler等通过研究MDR1过度表达的细胞株和正常的细胞株发现,在MDR1过度表达的细胞株内苯妥英的浓度仅是正常细胞株的1/4。2001年Edwards等通过对大量耐药细胞株研究发现,在耐药的细胞株上有大量的P-gp的表达,且表达量越高,其对AEDS的抗药性就越大,而对照组则不会对AEDs耐药。2004年Lu等对Wistar大鼠大脑星形胶质细胞在用苯妥英钠和苯巴比妥分别处理后,与对照组相比,处理组P-gp表达显著增加。Yang等用AEDs处理大鼠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后发现其表面P-gp的表达和活性大大增加[6]。(2)动物模型研究MDR1及P-gp与RE的关系:动物模型可以模拟癫痫发作,而且方便对照研究,大量的关于P-gp与RE关系的数据来自于动物模型。Rizzi等采用红藻氨酸诱导小鼠颞叶癫痫发作,结果发现在癫痫发作3~24h后,小鼠海马区的MDR1表达增加约85%,而且这些小鼠海马区脑组织内苯妥英的浓度显著下降。表明MDR1的过度表达与脑内AEDs的浓度下降两者相关。Potschka等通过建立颞叶癫痫大鼠模型,对苯妥英耐药的大鼠和不耐药的大鼠进行比较,发现耐药大鼠病灶处血脑屏障内皮细胞存在P-gp的高度表达,而在靠近其周围的正常脑组织却没有。Brandt等[7]使用颞叶癫痫大鼠模型进行研究,同样发现在耐药大鼠的病灶内存在显著增加的P-gp的表达。国内肖争等用电刺激杏仁核底外侧制做大鼠颞叶癫痫模型,6周后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P-gp的表达,发现与药物治疗有效组相比,耐药组病灶内脑组织的P-gp表达显著增加。(3)RE患者手术切除的脑组织中MDR1及P-gp与RE的关系:2001年,Dombrowski等分离出RE患者手术切除的颞叶组织中的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采用MDR1cDNA探针检测,发现与其他非癫痫切除的颞叶血管内皮细胞相比,RE患者内皮细胞MDR1基因表达增加。2002年Sidodiya对RE手术切除的脑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发现病灶内脑星形胶质细胞比周围正常脑组织中表达更多的P-gp,MDR1也呈现蛋白水平的高度表达。2005年Marchi等[8]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观察RE患者手术切除的脑标本,发现其MDR1 mRNA和P-gp表达都显著升高。国内丁成云对1例症状性癫痫伴脑灰质异位患者行手术切除病灶治疗,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发现病灶中星形胶质细胞和异型的神经元内均存在MDR1和P-gp阳性标记。这一结果与国外的研究相符,均证明RE致痫灶内存在MDR1和P-gp的表达增加。王学峰等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34例癫痫患者,发现22例MDRl表达呈阳性患者中仅有2例用AEDs治疗有效,而在12例MDR表达阴性的患者中7例有效。张伯民等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方法检测RE患者血清与脑脊液,发现其P-gp在RE组比药物控制组和正常对照组显著增加。这些对RE脑标本和外周血及脑脊液的研究说明,在RE患者的致痫灶中存在MDR1及P-gp的表达增加。AEDs是亲脂性的,可以顺浓度梯度自由穿过细胞膜。Loscher等发现苯妥英钠、苯巴比妥、卡马西平等是P-gp的底物,可以被P-gp泵出细胞,因此P-gp的表达增加可能导致脑组织内AEDs的浓度降低。
大量的实验证明P-gp与RE相关,但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P-gp在脑组织内表达的部位到底是位于血脑屏障内皮细胞还是在星形胶质细胞?另外P-gp表达增加的具体机制也不清楚。有些学者提出P-gp的高度表达可能是因为癫痫反复发作引起的[9]。Seeger等用AEDs处理大鼠11天后没有检测到大鼠脑内P-gp的表达增加,而在癫痫发作24h后即可发现海马区 P-gp呈现出过度表达。Yang等认为Seeger等用药物处理的时间仅为11天,与RE患者长期用药不相符。他们采用大鼠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培养,并与AEDs接触60天后发现,其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表面P-gp表达显著增加[6]。这些试验结果备受争议,究竟是癫痫发作还是AEDs导致的P-gp表达增加?这些只能依靠改进实验方法,找出P-gp过度表达的真正原因。
2.MDR1基因多态性与RE的关系的研究:2000年,Hoffimeyor等第1次报道了MDR1基因多态性可以影响P-gp的表达及减少药物的浓度。到目前为止,研究发现的MDR1基因编码区有50多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可导致MDR1基因多态性。SNP是指单个核苷酸的变异而致整个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呈多态性,且其分布频率不低于1%。SNP是人类遗传变异的较常见类型,根据它位于基因的位置可分为:非编码区、编码区、启动子区、内含子区SNP。目前关于MDR1多态性研究最多的位点是:C1236T、G2677T/A、C3435T。其中C3435T位于第26外显子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关于MDR1多态性的SNP位点。2003年Siddiqui对200例高加索族RE患者进行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RE患者中,3435CC基因型的频率显著增加。由此他第1次提出3435CC基因型与P-gp在血脑屏障内皮细胞的表达增加有关。随后关于C3435T基因多态性的研究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展开,但结果却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
2004年Soranzo等对高加索族中RE患者展开研究,他扩大了RE和对照组的样本含量,得出的结果与Siddiqui相同,3435CC基因型在RE患者出现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Kwan等[10]于2007年对香港地区RE患者的C3435T基因多态性进行研究,发现3435TT基因型在RE患者出现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他们2009年同样对香港地区 RE患者的C3435T基因多态性进行研究,结果却是3435CC基因型在 RE患者出现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Tan等对澳大利亚208例RE患者与401例药物敏感的癫痫患者进行研究,没有发现C3435T SNP与RE存在任何关联性。Lakhan等[12]对印度RE患者进行研究,也没有发现 C3435T SNP与 RE的关系。Sanchez等对RE患者以年龄和病因学做了不同的分类,发现在成人3435CC基因型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在儿童则没有发现C3435T SNP与RE存在关联。造成这些结果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复杂的。可能与不同种族存在基因上的差异有关。岑宇翔等发现汉族人中MDR1C3435T中,T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非洲人,而低于欧洲人[13]。造成这些差异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对RE的诊断标准不一致。目前国际上对RE定义尚无统一的规定,因此不同研究入组的RE患者病情,发病时间,服药情况等存在差异。既往研究表明联合用药,不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可以影响实验结果[14]。
P-gp抑制剂与RE的关系的研究:MDR1是可调控基因,其表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希望应用在肿瘤治疗学中的P-gp表达抑制剂能在RE中发挥相同的作用,因此开展了大量关于RE中P-gp抑制剂的研究。P-gp抑制剂可以抑制P-gp的外排功能,提高细胞内的药物浓度。如今发现的P-gp的抑制剂有数百种,可以分为7大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钙通道阻滞剂(如维拉帕米等)和环孢霉素类药物[15]。目前在肿瘤的治疗中,一些抑制剂已经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它们可以抑制P-gp的功能,减少其对化疗药物的外排从而逆转肿瘤患者的耐药。随着新一代P-gp的抑制剂的研制,如tariquidai,P-gp抑制剂表现出更高的特异性和效能。2006年Van等用电刺激制作颞叶癫痫大鼠模型,给予大鼠苯妥英和tariquidai联合治疗,发现与没有给予tariquidai组相比,联合用药组苯妥英的抗癫痫作用得到显著的改善[16]。Brandt在同样的大鼠模型中发现同时给予tariquidai可以显著减少RE大鼠癫痫发作次数[7]。国内吕洋等通过培养MDR1高表达的星形胶质细胞,发现西比灵可以逆转MDR1的表达。关于P-gp抑制剂应用于临床治疗RE的报道很少,Summers给一位严重的RE患者添加维拉帕米治疗时,其全面性发作的次数显著减少,程度也减轻。是迄今为止,P-gp抑制剂添加治疗人类RE成功的案例之一。
二、其他相关的多药转运蛋白与RE的关系的研究
人MRP基因定位于16号染色体上,其编码的mRNA长约7.8~8.2kbp,编码的MRP由1531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190kDa。MRP跟P-gp一样,都属于ABC转运体超家族的成员,属于ABCC亚家族。MRP是1992年Cole等在人小细胞肺癌细胞耐药株中发现的一种耐药相关蛋白。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MRP家族成员有9个:MRP1~9。其成员的蛋白质结构相似,基本结构是2个ABC位点和12个跨膜区。MRP功能与 P-gp相似。MRP可以表达在多种正常的组织器官中,如肺、脾、肾上腺等,在肝和脑组织中仅有低表达。MRP成员分别表达在细胞膜的不同部位,其作用也不同。如MRP2定位于细胞顶端细胞膜,MRP1、MRP3、MRP5分布在细胞膜基底外侧。MRP也具有将药物、毒素和代谢产物排出细胞,保护机体的作用。
近十年来人们对MRP在脑内的表达及定位、作用底物和抑制剂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2001年Domkrowski采用“small-number”cDNA 分析技术,发现RE患者手术切除的病灶内MRP2和MRP5基因表达增加,而作为对照组因动静脉瘤和动静脉畸形而切除的脑组织中却没有发现任何MRP基因的表达。2002年Sisodiya研究常见的因发育畸形致RE病例,如皮质发育不良、胚胎不良性神经上皮瘤、海马硬化,发现这些病例手术切除的脑组织内可见MRP1表达的增加,尤其见于病变的细胞,如发育不良的神经元、活性增加的星形胶质细胞和气球样变的细胞(病灶皮质的变性神经胶质细胞)。这些说明MRP参与RE的形成,与RE耐药相关。
丙磺舒是一种阴离子阻滞剂,目前研究认为丙磺舒是MRP的抑制剂。国外许多学者采用微透析的方法观察鼠和兔子的大脑,发现应用丙磺舒可以显著提高AEDs如卡马西平、苯妥英和丙戊酸的浓度,而且至少有一种MRP的亚型参与了这些药物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分配,可能是MRP1和(或)MRP2。用先天缺乏MRP2表达的小鼠做相同的试验,没有发现这些药物细胞外的浓度改变[17]。这些试验都支持MRP在RE耐药机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BCRP并不被人们所熟知,但它也属于ABC转运体超家族ABCG亚家族的一员。正常情况下BCRP可以表达在小肠上皮细胞和脑组织的内皮细胞,也有外排泵的作用,可以保护机体不受代谢产物和毒物的伤害。在耐药的肿瘤细胞中可以检测到BCRP的高表达,与肿瘤细胞抗化疗相关。因此研究者设想BCRP在RE中也发挥外排AEDs的作用,参与RE耐药。Aronica等[18]对55例外科手术切除的RE患者脑标本进行研究,发现BCRP定位在血脑屏障内皮细胞表面。同时也发现BCRP主要在肿瘤相关的RE患者脑组织内呈高度表达,而非肿瘤如海马硬化的RE患者脑组织内未发现BCRP有高表达。
三、对多药耐药基因学说的评价
多药转运蛋白是目前研究最多的与RE相关的蛋白。多药转运蛋白学说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基于以下几项证据的支持:①在RE患者和模拟RE的大鼠模型的脑组织内,可以发现致痫灶内有P-gp和MRP的过度表达;②在动物模型中,癫痫发作可以使P-gp水平上升,而同时脑组织内苯妥英的浓度下降。P-gp高表达和AEDs浓度下降同时出现的现象在RE患者也有报道;③在动物模型中发现,一些常用的AEDs药物可以被P-gp和MRP转运;④P-gp的抑制剂已经在动物模型中应用,并且可以部分逆转RE模型对苯巴比妥和苯妥英的耐药性[7,12]。由此看来,多药转运蛋白似乎确实在RE耐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些研究只局限在大鼠模型和体外实验。虽然有添加尼莫地平(具有P-gp抑制功能)可以恢复小鼠海马区对苯妥英钠敏感度的报道。但是没有对照实验,也不能证明尼莫地平是抑制了P-gp的功能而使敏感度恢复。
目前关于多药转运蛋白是不是参与RE耐药争论最多的是AEDs是否是P-gp的底物。早期有实验证明一些AEDs可以作为P-gp的底物。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动物模型或体外实验得出来的,在人体内P-gp是不是能干扰AEDs代谢尚不清楚。Baltes等发现不同动物之间,P-gp的底物存在种族差异,小鼠动物模型证明AEDs是P-gp的底物,在人体内可能不是或者只是很弱的底物。Sill等对敲除Mdr1a的小鼠和普通的小鼠进行比较,发现苯妥英钠等可能不是P-gp的作用底物。而体外实验,由于人体内药物穿过细胞不只是受到药物浓度的影响,还受血管内压力等的影响,其准确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综上所述,RE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一的机制不足以解释。多药耐药基因表达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长期使用某些AEDs时会诱导多药耐药基因高表达,从而产生耐药性,少数RE患者在改用或联合使用某种新药时,其发作可以被控制。这就提示我们在 RE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晰之前,合理选择AEDs,以减少或延缓RE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新的作用机制药物的研究是另一重点,尤其是关于P-gp抑制剂的研究。随着对RE耐药相关机制的了解,新的AEDs包括非多药转运蛋白底物和不良反应较小的P-gp抑制剂等,为治疗RE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也是我们今后研究工作重点所在。
1 Udani V.Pediatric epilepsy-an Indian perspective[J].Pediatr,2005,72(4):309-313
2 吴逊,沈鼎烈.难治性癫痫[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8,31(1):4-5
3 Sperling MR.The consequences of uncontrolled epilepsy[J].CNS SPE,2004,9(2):98-99
4 Löscher W,Potschka H.Drug resistance in brain diseases and the role of drug efflux transporters[J].Nat Rev Neurosci,2005,6(8):591-602
5 Kageyama M,Namiki M,Fukushima H,et al.Effect of chronic administration of ritonavir on function of cytochrome P450 3A and P-glycoprotein in rats[J].Pharm Bull,2005,28(1):130-137
6 Yang H W,Liu H Y,Liu X,et al.Increased P-glycoprotein function and level after long-term exposure of four antiepileptic drugs to rat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Vitro[J].Neuroscience Letters,2008,434(3):299-303
7 Brandt C,Bethmann K,Gastens AM,et al.The multidrug transporter hypothesis of drug resistance in epilepsy:proof-of-principle in a rat model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J].Neurobiology of Disease,2006,24(1):202-211
8 Marchi N,Guiso G,Rizzi M,et al.A pilot study on brain-to-plasma partition of 10,11-dyhydro-10-hydroxy-5H-dibeno(b,f)azepine-5-carboxamide and MDR1 brain expression In epilepsy patients not responding to oxcarbazepine[J].Epilepsia,2005,46(10):1614-1619
9 Liu XD,Yang ZH,Yang JS,et al.Increased P-glycoprotein expression and decreased phenobarbital distribution in the brain of pentylenetetrazole-kindled rats[J].Neuropharm,2007,53(5):657-663
10 Kwan P,Baum L,Wong V,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ABCB1 C3435T polymorphism and drug-resistanceepilepsy in Han Chinese[J].Epilepsy Behav,2007,11(1):112-117
11 Kwan P,Wong V,Ng PW,et al.Gene-wide tagging study of association between ABCB1 polymorphisms and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epilepsy in Han Chinese[J].Pharmacogenomics,2009,10(5):723-732
12 Lakhan R,Misra UK,Kalita J,et al.No association of ABCB1 polymorphisms with drug-refractory epilepsy in a north Indian population[J].Epilepsy Behav,2009,14(1):78-82
13 Patsalos PN,Froscher W,Pisani F,et al.The importance of drug interactions in epilepsy therapy[J].Epilepsia,2002,43(4):365-385
14 岑宇翔,陆志诚,王华侨,等.汉族人MDR1 C3435T基因的多态性[J].解剖学研究,2004,26(1):11-13
15 蒋传路,赵哲峰,李永利.P糖蛋白与难治性癫痫多药耐药[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7,3(3):237-238
16 van Vliet A,van Schaik R,Edelbroek M,et al.Inhibition of the multidrug transporter P-glycoprotein improves seizure control in phenytoin-treated chronic epileptic rats[J].Epilepsia,2006,47(4):672-680
17 Potschka H,Fedrowitz M,Loscher W.Brain access and anticonvulsant efficacy of carbamazepine,lamotrigine and felbamate in ABCC2/MRP2-deficient TR-rats[J].Epilepsia,2003,44(12):1479-1486
18 Aronica E,Gorter JA,Redeker S,et al.Localization of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BCRP)in microvessel endothelium of human control and epileptic brain[J].Epilepsia,2005,46(6):849-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