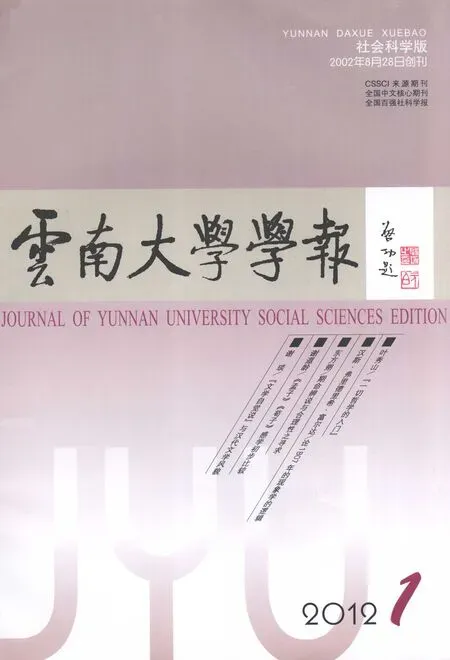“一切哲学的入门”
——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叶秀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一切哲学的入门”
——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叶秀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判断力;合目的性;立法;自由-自然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有各自独立的立法领域,这就是“自然”与“自由(意志)”,相对而言,判断力则没有自己独立于这两个领域的第三个立法领域,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判断力不“立法”。虽然判断力没有自己独立的立法领域,但是,它却通过“合目的性”原则把“自然”与“自由”这两个分裂的领域协调、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使对这个整体领域里的事物的(审美)判断具有先天的根据-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判断力也具有立法的功能——使对这个整体世界里的特殊事物作出审美判断具有合法性。
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地位在康德“批判哲学”系统中是明确的,它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所涉两个独立“领域”的“桥梁”,是“沟通”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立法”“王国”的一个特殊的环节,它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王国”,而是“依附”着“理论”和“实践”两边,时有偏重,所以似乎是一个没有“领土-领地”的“漂浮”“部分”,只是一个“活动场所”,“活”的“部分”;而这个“场所”却是我们“人”作为“有理性者-自由者”的真实的“生活场所”,是我们的“家(园)”——康德叫“居住地-domicilium”。
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涉及的是“科学”的“世界”,《实践理性批判》涉及的是“道德”的“世界”,那么,《判断力批判》也许涉及的就是我们后来叫做“生活”的“世界”。
这条思路,在后来欧洲哲学的发展中似乎已有例证,在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工作中似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迹象;这里所要做的,是追问这种理解就康德“批判哲学”本身有没有道理上的根据。
一、寻求“经验”中的“先天性”
我们一切的“知-有知”都来源于感觉经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感觉经验之所以可以提升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无论是“理论”的,还是“道德实践”的,其原因不完全在于我们的“感官-感觉器官”的生理结构大同小异,而是这种“必然性”来自于“理性”。这层意思是康德在他的第一个《批判》的一开始就指出了的。
按照康德的观点,“理性”原则上不依靠“感觉经验”,而是自成一套“必然”的系统,有自身的必然法则,譬如“逻辑”的一套规则,原则上不是从“感觉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但它却能(有能力)使“感觉经验”所“提供-给予”的“材料”“有序”。
“理性”虽然并不依靠“感觉经验”,但是康德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理性”仍是跟“感觉经验”有关的,分析、离析它们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正是“批判哲学”的工作。康德甚至还有一层意思:“理性”是在“感觉经验”的“刺激”下“明晰”出来的,但这个“出来”的“理性”并不受“感觉”的“规定”,“理性”自身是“独立”的,也就是说,这个“不依赖于感觉经验”的“理性”原本是“潜在”的,是“感觉经验”“激活”了它;而这个被“激活-揭示”出来的“理性”却具有“不依赖感觉经验”的“先天性”。
这样,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工作最基本的任务似乎就是要在“综合”的“感觉经验”中寻求它的“先天必然”的“理性”的作用。
“经验”是通过我们人的“心智能力”形成的,既然“先天性”是“理性”的,因而,寻求“经验”的“先天性”也就跟我们的“内在”的“心智能力”有关。
通常人们把我们人的“心智能力”分成“知识-情感-欲求”三个部分,康德的工作也就集中在这三个部分中寻求其中“先天性”的理性因素,也就是说,要在“经验”中离析出这种不依赖“经验”的“理性”的独立自主性来。
我们知道,单纯揭示“理性”不依赖“经验”的独立自主的“先天性”还是很不够的,因为“理性思维”自身的“逻辑形式”从亚里士多德起已经基本定型。现在的问题是:理性独立自主的“先天性”和“感觉经验”之间是什么“关系”?没有这层“关系”,我们的“理性”,或者说,我们的“心智能力”只是空洞的“形式”,是没有“内容”的,甚至永远只是“潜在”的(谢林),只有“关涉”到“经验”,这些“心智能力”才是有内容的。并且,按照康德的意思,这些“心智能力”只有在“感觉-经验”的“刺激”下才“活动”起来,发挥自身的独立自主的“能动”作用,这时我们的“意识”才是“自觉”的,而不是“潜在”的。
这样,康德的“批判哲学”在揭示“理性”的“心智能力”的“先天性”的同时,更在这个原则下,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先天性”是如何跟“经验”相“关联”的,阐释了“理性”独立自主地与“感觉经验”“相交”的这种“可能性”,康德叫做“理性心智能力——在理论知识方面是‘知性’”的“先验演绎”,因为“理性-知性”既然独立于“经验”,因而“经验”的“存在物”无权做这些“先天性”“心智能力”的“证明-证据”,而只能从“道理”上加以“演绎”,而这些能力又是“关涉”“经验”的,因而是“经验”中而又“先在于”“经验”的因素,对于它们的“证明”,康德就叫做“先验演绎”,而不仅仅是“逻辑形式-形式逻辑”的。这层层的意思,我们应该仔细地分析清楚。
那么,首先的问题是:我们人的“经验”中的“知识-情感-欲求”这些方面,其中是否蕴含了“心智能力”的“先天”的因素?康德的回答是:它们全都是有的——因而顺便说起,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情”,中文似乎还是用宗白华译的“情绪”为好,“绪”者“头绪-秩序”也——而它们跟“经验”的“关系”又是不相同的。
康德对于“知识”方面的问题下了很大的力气,《纯粹理性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批判哲学”的奠基之作,不仅事实上是如此,理论上也是如此,因为康德在写《纯粹理性批判》时,他的全部“批判哲学”,甚至全部“形而上学”哲学思想已经成熟;这部著作之所以称得上“博大精深”,值得反复研读推敲,是因为它的论述已经照顾到今后著作的主要思路,后面的《批判》读不懂的时候,往往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可以得到启发,而读后面的《批判》往往也会使《纯粹理性批判》的有些问题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三个《批判》,甚至其他著作,包括他的一些短文,都可以当成一部(大)著作——“一部”大书来读。
当然,所涉问题还是有区别的。
谈到“知识”问题,康德的工作在于揭示:由“感觉经验”作为“材料”提供的“经验”不仅蕴含了“先天性”,而且这个“先天性”的“心智能力”在“知识王国”里还是起到“立法”作用的;“感觉经验”固然“激发”了“知性”的活动,使这部分“心智能力”活跃起来,但并不能够给“事物”以“规定”,也就是说,并不能够使“事物”成为具有“必然规律”的“现象”,因而不能“确立-建立”起一个“合规律-必然性”的“知识王国”,唯有“不依赖感觉经验”的“知性”的“纯粹概念”-“范畴”才具有给“自然”作为“经验对象的综合”来“立法”的能力。
这就是说,在“自然王国-经验王国-知识王国”,“知性”这个独立的“心智能力”才拥有“立法权”。“知性”这种“先天”的“心智能力”与“感觉经验”的“关系”是“立法者”与“守法者”的“关系”。“感觉经验材料”“服从”“知性”的“法律-法则”,这样“建立”的“知识王国”是一个“必然王国”。“知性”的“法律-法则”对于“感觉经验”具有“强制性”。
然而,“知性”的这个“立法权”是一个“权限”,不能是一个“暴君-僭主”,这份“立法权”本身也是“合法”具有的,它有自己的“合法”行使权力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知性”行使它的“立法权”是“合法”的,“超出”这个“范围”就是一种“越权-僭越”,这个“范围”是“感觉经验”为“知性”“划定”的,即凡“可以感觉经验”的“事物”皆可以-有可能遵守“知性”所“立”之“法”,超出这个范围,“知性”“无权”过问,即“知性”没有“立法”的可能性。
“可以感觉经验”之“事物”皆“在”“时空”之中,于是,“凡在时空”中之“事物”,则皆“有可能”“进入”由“知性”“立法”的“必然王国-知识王国”。
这就是“知性”“先天”地为“自然王国-必然王国-知识王国”“立法”。
“不依赖感觉经验”的独立自主的“先天性”,原本也是“理性”的“自由”的表现,即不由“感觉经验”来“规定”,而是“自己”“规定”“自己”,并且通过“知性”来“规定”“感觉经验”;那么,这种“理性”本身的“自由”又复何如?
“自由”既然完全“摆脱了”“感觉经验”的“规定”,“在”“时空”之“外”,它的“规定性”只能由“理性”自身来赋予。这种由“理性”自身“规定”的“自由”,当然也是“先天的”。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揭示出,在我们的“欲求”的“经验”中,更有一个“先天”的“规定-决定”因素,“自由”乃是我们“欲求-意志”的一个“规定性”的“先天”“根据”。
这就是说,不仅“知识”是有“先天性”的,“意志-欲求”也是有“先天性”的;“知识”的“先天性”“建立-建构”了一个“必然王国-知识王国”,“意志-欲求”的“先天性”“建立-建构”了一个“自由王国-道德王国”。
这个“道德王国”由“理性”“先天”地为“自由者”“立法”,亦即“理性”为“自身”“立法”,“理性”为“不在时空”中的“事物本身(物自身)”“立法”。这样,原本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悬搁”、被“否定-消极”了的“自由-本体-思想体”,在《实践理性批判》则被“积极-肯定”了起来。
“知性”为“在时空”中的“事物”“立法”,于是“在我外部”的“空间”中“并列”之“诸事物”得到了“综合”;而“在我之内”的“时间”也“先后”被“综合”,被“知性”“规定”为“因果”的“必然关系”;而在“自由-道德王国”,因为“在”“时空”之外,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则有一个不受“时间”“先-后”、“空间”“并列”条件限制、没有“前因”的“自由”作为“原因”,故“自由因”是为“第一因”。
也许,“第一因”是“原因性”的本意。在古代希腊,“原因”这个词原本含有“可以问责”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把它纳入“真知识”的范畴,认为把握了事物的原因,也就是把握了该事物,就是“知道”了该事物,这样,“原因性”成为经验事物的把握-认知方式,由此组成为一个“因果系列”,而使“第一因”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
“第一因”为“责任者”,就“原因性”的“因果系列”“知识”问题来看,是“超越者”,“知识”的“因果系列”被(理性)“超越-提升”为“道德”问题。
“道德”原也可以理解为“经验”的问题。人类集团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利益互相“协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契约”,设定一些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因“时空”条件而“不同”和“变化”;然则,在这些由“时空”条件“限制”的“道德规范”中,有没有“超出”“时空”条件的“先天性”的因素存在?也就是说,林林总总的“道德规范”之中,有没有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必然”的“基础”?
康德认为这个“先天”的普遍必然的“道德”“根据”是有的,“道德规范”不仅仅有一个随“时空”条件“变化”的“现象”,而且也有一个“超出”“时空”、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根据”,这就是“意志自由”。
“自由”是“道德”的“先天”的“根基”,因为唯有“自由者”才是“责任者”,否则,一切的行动,皆有“推诿”到“时空”条件限制的可能性,“人”作为“自由者”“否定-堵绝”了这样一种“归于”“因果系列”“必然性”而加以“推诿”的可能性。作为“自由者”的“行动者”“责无旁贷”,而每一个“有理性者”又“必定-注定”是“自由者”,因为“(实践)理性”即“自由”。
与我们这里相关的是:“意志-意欲-欲求”在它的“经验”性的“需要-目的”之外,尚蕴涵着一个“先天性”的“规定”因素,即“规定”着“意志-意欲-欲求”在“道德”上的“性质”(德性)-“善-恶”。犹如“先天性”的“直观”和“知性”“规定”着“经验对象”的“性质”和“知识”的“真假-对错”一样。
犹如“感觉”“激活”“知性”那样,“意欲”也受“内外需求”的“刺激”,就“意志”而言,也有一个具体的“目的”,这个“目的”要由实际的“行动”在“现实”中“实现”,实现了的“目的”也可以看作“目的”作为“原因”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当适用于“因果范畴”“规定”下的“因果律”。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受“时空”条件的限制,“目的”的“实现”要“依靠”“主观努力”和“客观的条件”;只有“道德”无关“成败利钝”,只问“行动”符合不符合“道德律”,而“道德律”是“自由律”,是“自由者”之间的“法律-法则”,问“行为”所“根据”的“原则”是不是具有人人都“遵守”的可能性,因为这个“道德律-自由律”“应该”是“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普遍必然”的。
于是,康德说,“知性”在“知识王国”拥有“立法权”,而“理性”在“道德王国-自由王国”拥有“立法权”。“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由者”“立法”。
在某种意义上,“普遍必然”的“法”只是“形式”的,“立法权”并不“代替”“行政权”,“行政实施”有自己的“规则”,“知识”有“先天综合”的,也有或更多地有“经验综合”的,“意志自由”也必须通过“具体的-经验的”“目的”之“实现”才能“完成”。就这层意思来说,“理性”为“意志”的“立法”是无关乎经验的“目的”的,因此这条“法律”也不受“经验目的”的“限制”,而是“自由”的;不受“感性欲求”的“驱使”,当然也并不在实际上“压制-抑制”这种“欲求”,要做到所谓“清心寡欲”,只是在说“意志自由”是“悬搁”起(胡塞尔)诸种“经验欲望”,“意志”自有“规则-准则”,这条“自由-自有”的“准则”“规定”着“行为”(包括其原因和结果)在“道德”上的“品质”,“规定”着“行为者”“人格”的“品质”,即“规定”着“德性”。
然而,“意志”原蕴涵着一个“实践”的能力,它是“趋向”于“实现-现实”的,“理性”原本就有“实践”的能力,“自由”意味着“创造-开创”,而“现实性”又是“经验性”的,一切“现实”的事物都“应该”是“在”“经验”中的,于是,“目的”作为“自由”的“理念”来说,它的“现实性”是“在”“时间”的“持久绵延”中,“在时间中”“接近”这个“理念”的“目的”和“目的”的“理念”,“有目的”的“理念”是“具体的理念”,乃是“理想”。
“理性”为“自由者”所立之“法”,使“意志”“有权”先天地“追求-欲求-意欲”一个在时间无限绵延中才能“实现”的“目的”,从而“理性”通过“实践-道德”“立法”赋予了自身“建立-建构”“终极目的”的合法“权利”,“确定”一个“超越”“时间绵延”因而“超越时空”的“终极目的”的“理想”。
二、“判断力”与“合目的性原理”
“(实践)理性”“阐明-演绎-证明”了“终极目的”是允许合法地“建立-建构”起来的,尽管理性在“理论知识”上的“运用”(知性)范围内不允许建构这样一个“终极目的”“现实性”的“合法性”,因为“目的”在“时间”中是“无限绵延”的,这个“终极性”的“目的”只是一个“理念”,只能被“悬搁”起来成为一个没有“感觉经验”可以验证的“思想体-思想物”。
理性在“实践”领域里的运用,确切无疑地告诉我们:我们“有权”设定一个“终极性”“目的”,这个“终极目的”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上其“现实性”被“设定”是“合法”的,因为“理性”在“意志-意欲-欲求”上有一种“(先天)立法”的“权利”,这种“立法权”是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因而它与“理性”在“理论”领域的“(先天)立法权”并不发生冲突,因为它们各自是为两个原则上不同的“领域”“立法”,遵循着不同的“原理”。“理性”为“意志-意欲-欲求”“立法”,因“意志”本身具有的“能动性”,即“意志”以“目的”为“原因”“必有”一个“相应”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作为“概念”本就有“现实性”,因而“意志”的“目的”就是一个“现实”的“目的”,也是“目的”的“现实-实现”。“理性”的“实践”功能——“理性”为“意志自由-道德王国”先天地立的“法”,赋予人们(理性者)有一种“权利”去“设定-建构-建立”一个“终极目的”的“理想”。就建立这个“法律”的“实践理性”来说,这个“道德-自由”的“理性”是“有权”“企盼”其“现实性”的,而不是一个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
这就是说,人作为“有理性者-自由者”“有权”“拥有”这个“终极目的”的“理想”,人所建立起来的“经验科学”的“理论知识”“无权”“否定-阻止”“理性”给予“意志”的“自由”“权利”——“超出”“时空”条件的限制来“确立-建立”一个“终极目的”之“理想”。
“自由者”“有权”“拥有”“理想”。
不仅如此,“理论理性”不仅“无权”“阻止”这个“理想”,而且反倒要受这个“理性”的“影响”和“协助”。
“(实践)理性”固然“无权”为“经验”的“自然”“立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建构性-规定性”的“原理”,“自然”有自己的“法则”;但是“理性”通过“实践”却“引导-范导”着“经验”的“自然”,“理性”的这种“范导”功能促使“自然”与“自由”有了“和谐”的可能性,保障了“时间”朝着“终极目的”的“方向”“无限绵延”的可能性。“实践理性”给予“理论理性”一个“超越”的“方向”,对“理论理性”的“僭越-超越”“趋向”,不仅在“批判精神”下得到“遏制”,而且也得到“合理”的“疏导-引导”。
在这个基础上,原本两个各不相同的“领域”不仅有了“关系”,而且在“目的”这个“关键-环节”中也找到了“沟通”的“渠道”。
这个“关键”和“渠道”是以“判断力”为“主体”,各“心智功能”“先天立法”下的“愉快-不愉快”的“情感-情绪”。
“情感”通常被理解为“感觉”,是一些“感官”的“快感”,当然是“经验性”的。“快感”或许也会是“通感”,是一般人类所“共同”具有的,它或因感官结构相同,或因习惯相近,但也可能每个人各有差异,美味佳肴固然人人喜爱,但也会出现众口难调的情形,因为它们都是“在”“时空”中由一些不同条件和因素所“规定”的。
现在要问,在这些明显受“时空”条件“规定”的“经验性”“情感-感觉”中,有没有“理性”的“先天因素”?如果没有,“情感”问题人言人殊,谈到趣味无争论;如果有,那么这种“先天性”与“理论知识”和“实践自由”中的“先天性”有无自己的特点?
康德认为,在“愉快-不愉快”的“经验性”“情感”中仍然存在着“先天”的因素,“理性”仍然可以起着“立法”的作用,在这种基础上,“理性”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提供了使“情感”的“愉快-不愉快”这种“描述”成为“普遍必然性”的“判断”的可能性。
我们说“这朵花让我愉快”和“这朵花是美的”在哲学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前者“描述”个人的“感觉”,后者则是一个要求认同的“普遍命题”,而二者却通过“目的”这一共同的“环节”,因为“愉快”在康德就意味着“合目的性”。
涉及到理性对“合目的性-即愉快-情感”的先天性功能,对其“权限”作出“审批-划定”,乃是《判断力批判》的工作。
《判断力批判》从“合目的性”问题切入,因为“目的”概念兼跨“知识”与“道德”两个领域,而意义则不相同。
在“知识”领域,“目的”从属于“感性经验知识”,受“知性”为“自然”颁布的“自然律”“规定-支配”,单纯“感觉”的“需求-欲求”必须从属于“自然律”之下,“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目的”却受到了为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自然知识”的支配-决定,“目的”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时空”中“因果系列”的一个环节,一切所谓的“技术性的实践”其实都在“理论理性”的“领域”之内,接受“知性”为“在时空中”的“自然”所“立”之“先天法则-法律”支配。
“道德的实践-行为之动机”是“自由”的,不受“时空中自然”之限制,“知性”无权为这个“领域”“立法”,它的现实性并没有“现象界”的“结果-目的之完成”来保证,因而也没有任何“事实”作为“实例”来“证实”;但在“不计”“时空条件”——按照“理性”为“道德实践”所立之“先天法则-自由律”,这个“自由”的“终极目的”的“理想”,因其“符合”“道德律-自由律”而无需“时空”条件,就有“能力-实践能力”“扩展”为“现实性”。这样,在经验的现象界,虽然找不出一个“自由-道德”“目的”的现实的“例证”,但我们还是“有理由”亦即“有权利”“信任-相信”这个“理性”自身的“目的”是具有“现实性”的,亦即“理性”“有能力”“实现”“自己”,“自由”是“有能力”“实现”的。这样,我们“相信-信任”“自由”,“信任”“自由-道德”的“目的”具有“现实性”,这种“相信-信任”和这种“信仰”不是“盲目”的,不是“迷信”,而是理性的。“理性”的“法律-法则”“赋予”了我们“有理性者”相信“自由”,“信仰”“德性”的“合法权利”。
然而,这种“相信”和“信任”在“知性”为之“立法”的“知识王国”看来则是“空洞”的、“不可靠”的,因为在它“立法”的领域,一切都受“时空”条件的制约,“自由”之“结果”,“自由”之“实现”,被“推延”到了“无限长河”的“未来”,只是一个被“悬搁”了的“理念”。
在这里,“自然”和“自由”似乎是两个“极端”,康德《判断力批判》以“目的”的概念,把这两个具有不同性质“立法权”的“领域”“沟通”起来,通过“目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到,“自然”具有自身意义上的“自由性”,“自由”也具有自身意义上的“必然性”。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首先提出的“合目的性”概念正是“描述”“自然”的,这就是说,“自然界”——我们作为只是对象总和的“自然界”是“有权-合法地”从“合目的性”方面去“理解-阐释”它的。这就是说,这种“阐释”方式也是有“先天立法”的“根据”的。
这个“先天立法”的“根据”何在?
“知性”“无权”给出这种“法则”,因为“目的”概念并不是“自然-经验对象”的一个“属性”,“知性”“先天概念-范畴”“无法”“归摄”在一个“普遍规律”之下;“目的”概念本身也不“在”“时空”中,“时空”作为“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也“归摄”不了它;当然“自然合目的性”更不属于“自由”,因为“自然”绝没有“意志”。
这样,“自然合目的性”这个“概念”的“先天”“合法”“根据”何在?
康德说,其“合法性”的“根据”在“判断力”这样一个“心智功能”。如同“目的”概念一样,“判断力”是一种“兼跨”“知识”和“道德”-“自然”和“自由”两个“领域”的“心智功能”。
“判断”在思维的逻辑机能里是“概念-判断-推理”的一个环节,在欧洲哲学的传统中,只有运用概念才有可能进行“逻辑思维”,而“知识”的问题,则又是和“感觉经验”密切相关。在“经验知识”中,“判断”将“经验事物”的概念“归摄”在一个普遍规律之下;而在“道德-实践”中,“判断”则根据“自由律”从“本体事物”“推论”出这个事物的“实在性”来,于是人们有权对这种事物作出“合理-先天”的“判断”来。
在这两个领域(自然和自由),“判断”“按照-遵从-听命”各自所立的不同“法律”来执行自己的职能任务,在这两个领域,“判断”并没有自己的“立法权”,“立法权”在“知性”和“理性”手里。
然而,既然叫做“法”,则其所要强调的重点就在于一个“普遍性”,天下万事万物概莫能外,而事物之“具体性-个别性”则被“悬搁”起来。知性为“自然”-理性为“自由”所立之“法”,乃是一些“普遍法则”,对于“具体事物”还得“具体分析”。
不错,“具体事物”在“知性立法”下经过“判断”已经有了一个“归宿”,但这个“归宿”是“理论”的,这个事物“属于-是”哪一“类”的,“归属”于那个“普遍”的“类”“概念”之下,因而这个“事物”也只是该事物的“概念”。一个“小概念”“属于”一个“大概念”,至于那个“个体”的“事物”则尚未得到“分析”和“规定”。
然而,在一个“有序”的世界,不仅要有“普遍法则”,使这个世界成为我们有权认知的“对象”,“在理论上-在道理上”我们有权把握它的“必然性”,而且还要求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也处于“有序”之中,因而是我们“可以-有能力”“理解-解释”的世界,世界不仅在“理论”上是“合规律”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有序”的,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种“理解”也具有“必然性”的“根据”。
既然康德的“批判哲学”揭示了“理性”在各“领域”的“先天立法”职能使这些“领域”具有“必然性”而可以-允许“理解-把握”,那么,在具体特殊的世界,“理性”同样也有一种“先天立法”作用,以使这个特殊-个别的世界也有“可以理解”的基础和根据。康德认为,在“心智能力”中,除“理性”和“知性”之外,尚有一种“判断力”,它正是使这个具体特殊的世界成为“可以理解为具有必然性”的根据。
而“具体特殊”的“个体”世界也是“有序的-合规律”的,则也是“有理性的人”在“感官快乐-快感”之上有一种“愉快”的根据,犹如“德性”提供“有理性的人”以“敬重”的“感情”那样。
在这个意义上,“判断”不仅是一个“逻辑”的“环节”,而且也是一种“心智能力”,可以与“知性”和“理性”并列。因此,中文将其译为“判断力”是很好的,它也是一种相对(于“知性”和“理性”)“独立”的“(心智)能力”。
“知性”“先天”地给出“普遍法则”,当然也承认在“特殊物”的世界中也有“合规则”的“时候”,但在“知性”的“立法”原理中,这种情形只是“偶然”的“有时候”,并无“先天必然性”,如同“幸福”在“实践理性”的视野里一样,“德性”和“幸福”没有“必然”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判断力”的“先天立法”“职能”就在于使我们由于“特殊事物”世界之“秩序”而产生的“愉快”的“情感”有了一个“合法”的“先天”根据,使我们“合法”地作出“这个事物是美的”这个与“知性”“判断”“相同”的“形式”的“判断”,而“要求”“普遍”的“认同”。
然而,这个“形式”“相同”的“判断”,在“实质-实际”上与“知识性-知性”“判断”又是不同的,即它们的意义是不相同的。
康德说,“知性”“判断”是一种“规定性”的,而上述“审美-感性”“判断”则是“反思性”的。“规定性”的“判断力”是将一个经验事物的“概念”“归摄”于“普遍性”“规律”之下的“能力”,而反思性判断力则是对于“特殊的事物”进行“反思”,来“寻求”一个在“知性”是“不确定”的“普遍规律”,“知性”不能“规定”它“是什么”。“反思性判断力”与“规定性判断力”运行的路线正好相反:前者由“特殊”到“一般”,后者则由“一般”到“特殊”;后者使“事物”在“理论”上有一个“秩序”,前者则使“千差万别”的“无限复杂”的“特殊”的世界,也有一个“可以理解”的“秩序”。
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分析”下,这两种(知性和判断力)“建立秩序”的“先天立法”的性质和意义是不同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使之成为“可知”的“对象”,“判断力”的“合目的性”的“先天立法”不能“借用-借过来”“知性”所立之“法”,因而“反思性判断力”所立之“法”是为“判断力”“自己”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判断力”并不为“自然”“立法”。“自然”并无“合目的性”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自然”的是“盲目”的“必然性”。
所谓“判断力”为“自己”先天立法,也就意味着,“判断力”是为了各种“心智能力”的“协调-有序”而建立的一个“法则”,亦即,为协调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先天地“立法”。
也就是说,“知性”和“理性”都为“客体-对象(自然和自由)”“立法”,而“判断力”却为“主体”“立法”。这样,按照康德,“知性”和“理性”为“客体”“立法”,亦即“建立-建构”各自的“普遍对象”-“自然”和“自由”;而为“主体-主观”“立法”的“判断力”,则“建立-建构”不起一个“普遍对象”,它的“对象”仍然是“知性”通过“知觉”“给与”的,它的作用只是使这些“知觉表象”在“主体-主观”内部协调各种“心智能力”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一致”,因而其作用-功能也是“范导性”的,不是“建构性”的。
“知性”只能为“知识”给出一个“普遍-一般”的“经验对象”,而“反思判断力”从“知性”建立的“对象”中并不离开“知觉”的个别性,对这种特殊的个别事物按照“判断力”为自己“建立”的“先天法则”,“寻求”一个适合该事物的“规律”,从而将该事物“判断”为“类似”为“规定性判断”“归摄”下的“属性”,这个“归摄”,不是对这个事物在“客观-客体”上有所“断定-规定”,而是表现“主体-人”对该事物进行“反思”的一条“合理”的思路。
“知性”的“先天立法”只告诉我们,“自然”作为“经验对象”,必定遵守“因果律”,因为“时间”的“先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感性形式”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在“时间”中的事物,必有“因果关系”,“原因性”作为“先天概念-纯粹概念-范畴”是“知性”为“经验”确立了的。
然而,“普遍原则”确立以后,尚有特殊事物之间的具体的“因果性”原理有待“确立”,这样,这个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不仅在“理论”上必定具有“因果性”,因而是“必然”的,但就具体到“每一个”“特殊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知性”只能“断定”它们之间的“合规律性-有序”只是“偶然”的。
“知性”在“偶然性”面前之所以并没有“却步”,是因为“知性”为“判断力”对“特殊事物”的“反思”留下了余地,“知性”的“普遍立法”“等待着”“反思判断力”的“深入现实”,并将这些“特殊事物”的“现实性”“提高”到“合规律”性。不仅“普遍经验对象”因“知性”而“建立”,从而是“合规律”的,就是那在“知性”看来具有“偶然性”的“特殊事物”之间的关系中,经过“反思判断力”的“先天立法”作用,也“应该”被看作是“有规律”的,尽管“知性”对此不能提供确切的“知识”。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判断力”所做的事情,也是“知性”“想”做但因自己的“立法”“权限”而未能做的事。这样“反思判断力”对“知性”来说,就是一个“继续”和“补充”。“反思判断力”“完成”着“知性”的“未竟事业”。
不仅如此,“知性”还要在“反思判断力”的“引导-范导”下,因不在“特殊事物”面前“却步”而“不断”“扩展”自己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反思判断力”“推动-扩展”着“知性”的工作。
“趣味-鉴赏力”的提高,有助于“科学”的不停顿的“发展”。
三、“合目的性”与“趣味-鉴赏力”
“合目的性”是“理性-知性”“委托”给“反思判断力”的一种“权利”,它的“权限”是“调节性-范导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它无权给知性建立的对象立法,而只是给在这个“对象”中的“特殊事物”提供一个具有先天性的“理解方式”,“相信”这些“无穷尽”的个别事物,同样也是“有序”的,而由这种“特殊事物”之间的这种“有序性”产生的“愉快”的“情感-情绪”,也是有“先天立法”根据予以保证的。“合目的性”乃是“反思判断力”为自己调节诸心智能力所具有的“立法”权力。
“合目的性”原则所涉及的是一个“自然”的“特殊事物”的世界,是“自然”在“特殊事物”之间的“合规律性”的“先天条件”,因而都离不开“个体”事物的“知觉表象”,但又不是单纯“感觉”的,不是单纯由“感觉器官”提供的“感觉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实质”的,而是“形式”的,是一种“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
这样,康德引用了鲍姆加登的“审美的”一词。我们知道,在鲍姆加登那里,“审美的”是“理性知识”的一个低级形态,也不仅仅是“感觉材料”的。这一点,康德是考虑到了的,尽管他的“批判哲学精神”与沃尔夫-鲍姆加登不同,但“审美-趣味”是在“理性”“引导”之下这一点却是相通的。
“审美的”是离不开“感性的”,但又不单纯是“感觉的”,在康德看来,乃是由于“判断力”在“反思”“感官”提供的“特殊事物”时有一个“先天”的“根据”,尽管这个根据仅仅是“内在”的,即为“诸(内在)心智能力”的“协调”而立的“法”。
什么叫做“仅仅是内在的”?既然康德把时间设定为内在的“先天直观形式”,而空间为外在的“先天直观形式”,那么,在这里,所谓“仅仅是内在的”就可以指“仅仅是时间的”,这就是说,“审美的”并不“涉及”到“外在”的“实物”,而是将这个“特殊”的“实物”表象“吸收”到“内在-时间”中来,并加以“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外在空间”中的“实物”,“审美-鉴赏-趣味”并不“涉及”它的“实质-感官材料”,而只涉及“形式”。
于是,“审美的-鉴赏-趣味”的“愉快”并无“功利性”,就不是康德的“独断”,而是经过“批判-分析”的。
“审美判断”作为“审美”当然是“感性”的,离不开个别事物的“形象”,但是这个个别事物的形象作为“审美的对象”,即使是“实物-实在的”,却也是“虚拟”的,是通过“想象力”将其与“实在的”“时空条件”“剥离”出来,这个“对象”有自己的“虚拟”的“时空”,也就是说,有一个“内在化”了的“时空”条件,所以也是可以“直观”的,只是这种“直观”又是“内在”的,即“空间”也是“时间”的。将空间的“实物”“吸收”到内在的时间中来,以便“判断力”对这个“内在”的“对象”进行“反思-思维”,即由这个“内在”的“直观”作为“知性”“范畴-(纯粹)概念”的“条件”,而并不是就以这种“内在直观”“直接”用来“反思-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并不是说,“审美判断”是“形象思维”,按照康德,“思维”是必定要用“概念”的,“反思”也不例外;“审美”的问题不在于用了一种“不同于”“逻辑(概念)思维”的“另一种”“独立-独特”的“思维”,而是因“直观”与“概念”的“关系”的特殊性遂使“审美”这样一种“思维”有了自己的特殊“意义”。
这样,“审美判断”作为“判断”仍然必须向“知性”“借用”“(经验)概念”以及“(先验)范畴”(不是“借用”“知性”所立之“法”,“判断力”有自己的“法”)才能作为“判断”表述出来;只是这种与“知识判断”在“形式”上相同的“审美判断”在“意义”上却是不同的。“审美判断”并不是将两个“概念(不论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先天-必然”地“连接”起来,譬如“水”在“通常”环境中,加温至100摄氏度必将成为“气”,表达的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水”这个“自然对象”的“自然律”,这和一个对“水”的“审美判断”所要表达的“情绪”有不同的“意义”。“水”作为“概念”当然是“经验”的,不是“先天”的,但它是“经验”的“抽象”和“概括”,而不是一个“直观”,这样“知性”才有可能为之“立法”,按照“自然律”来找出“水”的“客观属性”,掌握其“规律”;相反,作为“审美判断”的“水”——如果这个判断中有“水”的话,则总是“具体”有所“指”的一条河、一滴水等等,而不是抽象的“经验概念”,“小桥流水人家”中的“小桥-流水-人家”尽管未曾“确定-规定”“什么桥-哪条河-哪一家”,却有一幅“直观”的“内在”的、“虚拟”的“画面”,对于这个“内在虚拟直观”的“画面”作出的“判断”-“美”,并不属于“客体”,甚至不属于这个“虚拟”的“客体”,而是“主观”“(对它们)反思-思维”的“评判-鉴赏”,用“诗”的形式表达出这个“鉴赏”的“情绪”,则有那首“小令”的传世,而它之所以有权“传世”,乃是这个“评判-鉴赏-情绪”同样有“反思判断力”为“自己”“立法”的“先天性”作为“根据”,未能“欣赏-鉴赏”的“人”“须得学习”,提高自身的“鉴赏力”,如同在“科学知识”上“须得学习”一样。
于是,康德有理由指出,“审美判断”的“主语”总是一个“特称概念”,“指”一个“具体事物”,而不是一个经验的“种-类”“概念”,因此,严格说来,“审美判断”只是说“这朵花是美的”,而说“花是美的”也意味着“大多数”而言,犹如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花是红的”一样;这就是说,不仅仅“在时空中”“可以直观”的“经验概念”,而且“就是”“直观本身”,就是“时空本身”,而按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划定的“界限”,这些“本身-自身”对“知性”来说,是“不可知”的,是“事物自身”,是“思想体”,因而是“内在”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的”所涉问题恰恰不是“现象”的问题,而是“本体”的问题。
当然,“知性”不可能通过“反思判断力”的“先天原理”“认识”“事物自身-本体”,但通过这个为包括“知性”在内的“诸心智能力”之间的“合目的性”的和谐一致,对于“知性”的那种超越“现象”“认识”“本体”的“僭越”趋向和意图,就有了一层“引导-疏导”的方式和途径,即通过“合目的性”的“先天原理”,人们被允许在自己的“内在”的“判断力”的功能中,“反思”出一种对于“事物本身-本体”的“体验-经历-经验”。“美”虽然并不是“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自然”的“客观属性”,但人们却“有权”“类比”于这种“合目的性”的“美”也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样。同样地,单靠“知性”的工作,只能揭示“本体”的“存在”,对于这个“本体”却不能进一步加以“规定”,“知性”也不能对“美”通过“判断力”加以进一步“规定”,而只能“托付”给“判断力”对其进行“反思”,亦即“托付”给“情感-情绪”,使其成为具有在“主体”上有“普遍性”的“审美-鉴赏-趣味判断”,使原本具有“偶然性”的“感情(千变万化-喜怒无常的好恶)”在“反思判断力”的“内向-内在”的“先天性”“原则”的“指引”下,也有一层“必然性”的意义。“美”作为“反思”的“概念”,对于“知性”来说,犹如对“本体”的“概念”一样,是“不可知”而只能被“思维”的,这个“可思维性”由“判断力”的“反思”,在“诸心智能力”的相互“协调一致”的“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必然性”,有权借助“知性”“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提请“普遍”的“认同”。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审美判断”是按照“合目的性原则”对于“本体”的一个“反思性判断”,而并不是“规定性判断”。
然而,既然“反思性判断”已经涉及到一个“本体”“概念”,则也就把自己的“判断”“伸向-扩展”到了由“理性”“立法”的“自由”领域,因为“自由”正是“在”“知性”为之“立法”的“自然-必然”之“外”的“意志-道德”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审美-鉴赏-趣味”的并不受“知性立法”的“限制”行使着“判断力”的“反思”职能,并使“有序”的“情感”-“情绪”与“道德”的“敬重”之“情绪”相互沟通。“敬重”是“自由律-道德律”对“情感”的“反作用”,而“(审美)愉快”是“自然律-必然律”对“情感”的“反作用”。
于是“审美判断”就有了沟通“自然”和“道德”两个领域的可能性,即“知识”向“道德”“过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判断力”的“反思”职能所“提供”和“保障”,而“反思”则是“知性”只能为之“思维”的“本体”的“再思”。“再思-反思”使“知性”“上升”地“进入”到“理性-自由-道德”领域;而反过来说,也使“理性”“下降”地“进入”“知性”的领域,虽然它们各自的“立法权”不能“转让-让渡”。“知性”不为“道德”“立法”,“理性”也不为“知识”“立法”,但是通过“判断力”根据“自己”为“自己”“立法”的“(反思性)原理”,使人们可以“理解”到“理性”与“知性”作为不同的“心智功能”之间的“合目的性”的协调关系。
按照“理性”在“实践”上为“道德”所立之“法”,“自由”作为“第一因”也就意味着“终止”了“以前”的“原因”系列,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既是“始”也是“终”,而“目的”就其概念来说,是“始”也是“终”,于是,“自由的目的”,不仅意味着“初始原因”,而且同时也意味着“最后结果”,即“终极目的”。“理性”在“实践-道德”上的“法则”,提供了“终始之道”的“先天可能性”,并且只有在这层“合目的性”意义上,即康德“实践理性-道德”的意义上,我们才看到了“原始反(返)终”所蕴含的道理:“原始”也就是“终结”,“终结”是“反(返)(回)”到“原始”。
然而,“知性立法”的“经验世界”不提供“初始原因”和“最后结果”这样一个“可能性”,“空间”在“无限”“扩展”,“时间”也“无限”“绵延”,这样,如果“理性”执意要按自己所立之“法”来办事,则必须发出一道“指令-命令”,“令”“万物终结”。只有在“万物”“终结-完成”之后,“理性”才能作出“道德”的“最终”的“判断-判决-审判”,否则就只能像尼采所指出的,“善-恶”只是随“时间-空间”“变化”的“相对”的价值标准,人们无权作出“终审”——世间并无“末日审判”,而只有到了海德格尔,指出“死”使“时间”成为“有限”的,而“死”就是“大全-终结-完成”,从而使“死”重新成为一个现代的哲学问题。
康德哲学并未“推广-延伸”到这个程度,但他的“批判哲学”在精神上为以后的哲学创造留下了余地。不管后来的哲学家如何“评价”(尼采的猛烈批评和海德格尔的审慎的尊重),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理路上的可沟通之处。在“审美判断”“形式合目的性原理”中,“内在虚拟时空”使“实际的时空”“定格”,“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康德来说,知性虽然在“法则”上即在“一般-普遍”的意义上“否定”了“事物”之“终结”,但对于“个别-特殊”的“事物”的“规律”性,“允许”“反思判断力”按照自己的“先天法则”(而不是“非法”借用“知性”所立之“法则”)来把那些在“知性”看来是“偶然”的“规律”也看成在“诸心智能力”的协调关系中有“先天必然”的根据。
这就是说,“知性”固然不允许“事物”在“客观”上“终结”,亦即不允许将“目的”和“合目的性”赋予“自然”,但却允许“判断力”在“反思-再思”的意义上来“理解”特殊、个别的事物之间有一种“合目的性”的关系,从而“使-令”它们“完成-终结-定格”,允许“设定”有一个“初始目的”成为其“完成-完善-终结”的“自由-第一”“原因”。
这个“自由因”的“引入”“经验”领域,不但“自然”的“普遍规律”由“知性”的“立法”在“理论上”具有“必然性”,而且“自然”的“特殊规律”由“反思判断力”提供了一个“主观上-情绪上”的“必然性”,从而并不像“知性”那样把“特殊规律”看成是“偶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知性”借助“判断力”有可能“看”得更“深远”,不仅“看”到了“理论上”的“必然性”,而且“看”到了“实际上”的“必然性”,只是“知性”“止于”这种“看”是“主观-内在”的,并不给“自然”“颁布”什么“客观”的“法则-法律”,因而只是对“自然”的一个“反思-再思”,对“知性”的一个“协助”和“补充”。
但是,“判断力”通过“反思-再思”对于“知性”的这一“协助-补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甚至是基础性的,因为通过这一功能,“判断力”把“理性”的“自由”“带进-邀请”到“经验世界”中来,使这个世界“添增”了一层只有对“有理性者-自由者”才“开显”的“意义”。“美”成为“善”的“象征”,“审美的”“眼光”使“有理性的人”在内在的“时空定格”中,看到了“至善”的“象征”。
具有这种“反思判断力”的人,就是具有“鉴赏力”的人,按中国的习惯也许可以叫做“有情趣”的人。
这种人虽然不是“科学家”,也不一定是“艺术家”,但有“艺术”的眼光,即有“判断力”的“反思-再思”能力,能够在“自然”的“特殊性”中“看”出“合目的性”的“规则-规律”,亦即原本“自在-自由”的品类万殊的大千世界,通过自己的“愉快”“发现”一种“合目的性”的“美”的“情绪-情趣”;此时的“自然对象”,已不是在“知性”“建构”起来的一个“必然”网络中的一个“环节”,而是一个“自由”的“产物”,“脱离-摆脱”了“一时-一地”的“时空”条件的“限制”(虚拟时空使之定格)——尽管如叔本华说的只是“暂时”的。“大自然”“鬼斧神工”,“似乎”“超越”了“知性”的“领域”,或者就在这个“领域”内“显现”出另一番“意义”。这种“自由”的意义,“似乎”有“另一个”“知性”为它的“产生”提供了保障,而这“另一个知性”当然实际上并不存在,“判断力”通过“反思-再思”,使“知性”“承认”但并不能够认识它是“什么”:“人”作为“有理性者-自由者”,“有权”在自己的“主观-内在”的“诸-各心智能力协调”中“设定”一种“超越”“知性”的“能力”“在”,通常人们也把这种能力叫做“智慧”。
“鉴赏-情趣”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智慧”,这种“智慧”当然“不能-无权”“代替”“知性”,但却“有助-协助”“知性”,“引导-范导”“知性”,使之“深入”到“事物”之“内在”之“协调”,从而“扩展”自己的“领域”。
“人”作为“自由者”不仅是“有知识-知性者”,而且是“有智慧者”,似乎就是叔本华说的,“人”“天生”就是“形而上学”的,我们“天生”“生活”“在”“意义”的世界,这是一个“基础”的世界,“知性”建构的“科学”的世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构”的“科学王国”。
■责任编辑/卢云昆
B516.31
A
1671-7511(2012)01-0003-12
2011-11-02
叶秀山,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