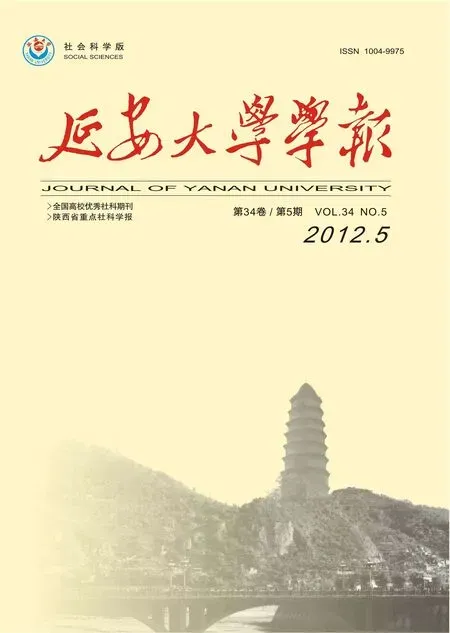批判中的同情——浅析叶广芩京味小说中的传统女性形象
申朝晖,辛东孝
(1.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2.延川县教研室,陕西 延川 717200)
叶广芩的京味小说以家族故事为蓝本,将百年的政治风云浓缩在一个家族的盛衰史中,既写出了钟鸣鼎食的满族世家在时代暴风雨中衰微没落的经历,又刻画了家道中落后贵族子弟们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在她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写得最为生动传神的就是大宅门里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与叶广芩现实家族中的人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叶广芩在作品中诉说这些传统女性的悲剧人生时,怀有比较深沉而复杂的情感体验,既对她们的缺失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同时又对她们的遭际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一、独断专权的女性家长
叶广芩的京味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封建大家长的形象,比起小说中处于时代变革期较为开明的男性统治者,身处闺房中的她们,缺乏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现代启蒙思想的熏陶,因而其身上具有更为冷酷、专权的特征,体现了传统封建文化的深深烙印。
在《瘦尽灯花又一宵》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位独断专权的封建女性形象——舅太太。出身于显赫世家的舅太太,在舅爷英年早逝后,操持家中大小事宜。虽然大清国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在舅太太统治下的王府依然看不到时代前行的脚步。风烛残年的老太太们,依然坚持着内外有别、男女之大防的陈规陋俗,因此,车夫老王只能将我及礼物送到内庭门口,丝毫不敢逾矩。虽然清王朝的统治早已终结了,但代表身份和地位的舅爷的封册仍由舅太太宝贝一样收着,因为封册是朝廷对“扎萨克多罗家几代人勇猛、忠诚的印证,但这一切却在舅爷的身后画了句号,这是舅太太最不能认可、最不能甘心的”[1]120,所以,舅太太把希望寄托在从封地选来的“儿子”宝力格身上。舅太太教育下一辈以传统的“严”为本,宝力格吃饭时“在饭桌上吧唧嘴”[1]114,就挨了舅太太狠狠的一巴掌,“嘴磕在大理石面的饭桌上,磕掉了一颗门牙。”[1]114因此,宝力格决绝地离开了王府。他走后,痛苦又延续到了命里有三个阳的“我”的身上,从三岁开始,“每年过年都不得不到老王府中去为那座阴气沉沉的老宅冲晦气”。在没落而依然威严的王府,我恪守礼节、恭恭敬敬,并在除夕之前要独自在偌大的王府中拔草清路,以迎接舅爷的魂灵回家过年。北方的严冬寒风呼号,滴水成冰,对一个小女孩近乎非人的折磨,不过出自于舅太太对传统儒家文化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文化观念的执着坚守。舅太太将自己的一生封印在封建礼教中,通过大量的陈规陋俗、繁文缛节来维护并享受着传统观念,殊不知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王府威仪严整的家法族规使桀骜不驯的宝力格如同掉了魂,离家出走后不知所终。王府的阴冷和精神上的恐惧也令年幼的“我”身心俱疲,每年回到家总要大病一场。但事实上,舅太太并非铁石心肠的人,她将传世珍宝避火珠送给我,让见惯大世面的父亲都大吃一惊。舅太太对宝力格和“我”近乎缺乏人情的严厉,其实出自于深层的器重和关爱,因而,那位真假莫辨的宝力格拒绝“认祖归根”的行为,彻底摧毁了舅太太的生存意志。舅太太终其一生都以其特有的威严和专横维护着封建制度,而她所秉持的传统观念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其实也使自己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殉葬品。
与顽固守旧的舅太太相比,《谁翻乐府凄凉曲》中的瓜尔佳氏是一位身处转型期的封建家长形象。瓜尔佳母亲家世显赫,父亲作为朝廷内阁的要员,“‘掌参与密务,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是炙手可热的人物”[1]4,这样的权势也延续到女儿的身上。“瓜尔佳母亲在金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不苟言笑,派头很大,就是跟我父亲说话,她也有一副降贵纡尊的劲头”[1]4。就是这样一位看重门第和血统的女人,当她意识到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时,也开始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观念,但维护传统与趋向进步的矛盾导致了她在子女教育和婚姻上的失败。与舅太太对“儿子”宝力格的严格管制不同,瓜尔佳母亲对小儿子金舜锫偏爱有加。金舜锫爱唱戏,但在满族文化中,戏子是下九流的职业,“谁家有唱戏的,往下数三代都不许进考场,下贱极了”[1]10。因此,瓜尔佳母亲规定只能玩票不能下海唱戏,她宁愿老五去当叫花子也不让他去当戏子,而偏偏就喜欢唱戏的老五只好伙同一群贵族子弟扮乞丐胡闹,瓜尔佳母亲也只是听之任之。对大格格金舜锦的婚姻上,瓜尔佳母亲认为“祖上是东北完达山里的胡子”[1]14的伪警察署长的儿子是无论如何都配不上大宅门里的格格,她自己也不愿意与亲家平起平坐。但时代的巨变使她意识到:门第和血统之说已经过时了,而拥有一门技术永远都吃香,署长儿子留过洋,又是德国医院院长,完全可以让大格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正是这门婚姻将大格格推向了悲剧的深渊。瓜尔佳母亲在清朝统治终结以后,已经开始懂得向时代妥协、让步,因此,她不刻意禁锢小儿子的爱好,也结了汉人警察为亲家,但在她的思想深处,大宅门的礼数、传统的文化仍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导致了子女们的悲剧。
封建统治早已湮没于历史的滚滚烟尘中,但传统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仍然在我们的头脑中萦绕不止。叶广芩在《黄连厚朴》中,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身处新时代,却固守着封建思想的老太太——惠生。惠生老太太的丈夫龚矩臣的祖上“世代为朝廷御医”[2]222,龚矩臣也是德高望重的名医,他一心钻研医术,家中大小事宜皆由妻子做主。于是惠生老太太在龚家具有了《红楼梦》中贾母一般的权利与威严,她想把家中的所有人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下,动辄就以家规压人,更无法容忍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老太太的冷酷尤其表现在对前儿媳于莲舫的态度上,在老太太看来,于莲舫主动提出离婚是对她作为大家长家庭权威的挑战,因为在旧制度里,只有丈夫休妻,没有妻子休夫的道理。所以惠生老太太表面上好意将离婚后无处可去的于莲舫收留在外院的南屋,博得了世家大度容人的好名声,其实是为了给于莲舫施加“精神”上的折磨。比起于莲舫对儿子的“背叛”来说,女儿龚小初在她的反对之下仍嫁给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任大伟,更是对权威家规的挑战,虽然老太太最终接受了任大伟这个女婿,但在心底里却只把他看作是一头为龚家工作的“草驴”[2]228。无论是于莲舫还是任大伟,他们与惠生老太太的矛盾冲突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圈内,而龚小默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珍妮与惠生老太太之间的隔阂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老太太受不了美国媳妇不懂“规矩”,而珍妮则觉得,“自从迈进龚家大门这一刻起,她觉得她是掉进一个博大精深的洞里了。无依无靠、无抓挠,松软的低使她越陷越深,这种感觉在美国是从未有过的”[3]。古老的中医能够治疗国人肉体的疾病,却医不了心灵上的痼疾,祛不了文化上的毒根。叶广芩借珍妮之口,对以惠生老太太为代表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给予了犀利的批判。
封建统治结束了,但浓厚的封建意识依然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禁锢和摧残着中国人的身心,也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阻滞的作用,作家在其中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陋习的隐忧不得不让我们警醒。
二、封建制度的“守护者”
叶广芩在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也刻画了许多在传统礼教的束缚下被牺牲的贵族女性和底层女性形象,她们在不自觉中充当了封建思想的守护者。
《瘦尽灯花又一宵》中身为侧福晋的舅姨太太狼伊雁虽然不需要像舅太太一样背负着无法承受的家族重任,但同时,“不是郡王的格格,也没有煊赫显贵的娘家,没有使用不尽的珠宝,我是罪臣的女儿”[1]119的真实境遇,使得舅姨太太成为王府中边缘化的悲剧人物。与舅太太的冷酷、严厉相比,舅姨太太是温柔而体贴的。她从未打骂过宝力格,而是从生活上悉心教导,在学问上全力栽培,因此,出走前的那个晚上,宝力格在舅姨太太的窗户外站了很久。“我”在王府过年时,舅姨太太总是笑着夸我有规矩,并耐心向我传授满族的语言文化,表现了封建大家庭中长者身上少见的亲和力。进入新社会以后,满腹经纶的舅姨太太在舅太太、田姑娘离世后完全可以凭借深厚的学识走出禁锢自己的王府,但“出嫁从夫”的思想让她始终独自守护着从未属于自己的王府,守护着封建的礼教制度。舅姨太太对宝力格的牵挂除了作为母亲对儿子的亲情外,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夫死从子”的思想桎梏。作家在对舅姨太太的描写中,虽然批判了她对封建礼教的愚忠,但更多的是对善良而多才的舅姨太太的怜惜与同情。舅姨太太由切身体验出发,对封建文化的弊端具有极为清醒的认知,但家庭出身、生存环境注定她迈向新生的步履是那样的艰难,她想自新,却又在不自觉中成为封建制度的守护者。
《雨也萧萧》中的二格格金舜镅也是个塑造得极为出色的守护者形象。二格格与丈夫沈瑞方是自由恋爱的,遭到父亲的毒打后,二格格非但没有悔改,反而义无反顾地投奔沈家。而富有品味、极重情意的沈瑞方受到金家歧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商人身份。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重农轻商”,金家人认为商人重利轻义,只要沾个“商”字就没什么好人。所以,曾视其为掌上明珠的父亲与二格格断绝了父女关系,出身于桐城世家的母亲即使到了弥留之际,也断然不肯原谅她的行为。高贵的门楣已经成为过去,显赫的家世已化为历史的云烟,但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却不会那么容易消逝,因此,经过自由恋爱嫁给商人的二格格,就被彻底地排除在金家的大宅门外,至死都无法得到谅解。然而,当年作为叛逆者走出家门的二格格,在成为人母之后又变成了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她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恪守金家祖训,不许同“商”字沾边。虽然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其子女们的精神境界受到了作家的肯定。但二格格的行为也证明,在她的潜意识里,还是认同了传统文化中对商家的否定性看法。作为封建思想观念的受害者,二格格其实终其一生都未能逃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反而是在不自觉中成为封建思想最忠实的维护者,历史的反讽莫过于此。
叶广芩的作品中还有受封建思想迫害最深的底层女性形象,《豆汁记》中的莫姜就是典型代表。莫姜原为寿康宫敬懿太妃身边的宫女,太妃出宫前将莫姜许给了宫廷御厨刘成贵,并将自己的翠绿扁方送给了莫姜。谁知刘成贵吃喝嫖赌,还因索要扁方不成划伤莫姜的脸,后来又和相好的妓女一起销声匿迹了。无所依存的莫姜被收留到“我”家做厨师,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刘成贵又出现了,还带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儿子”卫东彪。莫姜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她卖掉扁方安顿好刘成贵父子,并在刘成贵瘫痪后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莫姜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在刘成贵多年杳无音信却又再次出现后,莫姜只是“含着眼泪对我说,您说我能怎么着呢,摊上这么一个男人”[2]21。莫姜的心里立着一座贞洁牌坊,在她看来出嫁从夫、从一而终,这是无可更改的道德准则。莫姜还受到传统尊卑观念的深刻影响,只因当初落魄时,被我父亲带回家并接受了我母亲施舍的一碗吃剩的豆汁,莫姜始终以金家的“忠仆”自居,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回报了二十年。最后还因养子卫东彪对金家的迫害,觉得“对不住四爷”,在追悔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4]在莫姜看来,金家的老老小小,包括年幼的我,都是她的“主子”,因而,她对所有人都是颔首敛眉、毕恭毕敬的态度。莫姜这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她的人生就是一幕悠长的悲剧,但她却从未埋怨过、抗争过,反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忠实地捍卫着封建思想,莫姜的悲剧在一代又一代的底层女性身上重复上演着。
贵族文化的熏陶、市井生活的磨练、域外游学的参照,促使叶广芩对于滋养自己的家族文化和贵族气质既怀有深深的眷恋,又能挣破心网的束缚,以睿智清醒的目光看待没落的贵族家庭中的传统女性形象[5]。对以冥顽不化的舅太太,刚愎自用的瓜尔佳母亲,自私冷酷的惠生老太太为代表的女性大家长,虽然立足其家庭出身、社会时代的因素,叶广芩给予了一定的理解与同情,但作者主要是针对她们身上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痼弊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与鞭挞。而对于以善良而多才的舅姨太太、美丽而刚毅的二格格、逆来顺受的莫姜为代表的弱势女性群体,作家在批判她们于不自觉中沦落为封建思想的守护者的同时,对于她们惨淡、隐忍的一生,流露出深切的同情,甚至对她们身上体现出的善良与坚韧的美德发出了由衷的敬意。同情理解却审视批判,依恋感伤又清醒达观的双重叙述视角,体现了叶广芩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切而独特的反思。
[1]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2]叶广芩.豆汁记[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9:1.
[3]曲圣琪.根植于传统文化沃土的精神家园——叶广芩小说创作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1:24.
[4]宋国静.有一种佳人难再得——对《豆汁记》人物“莫姜”的解析[J].文学界,2010(11):71.
[5]吴建玲.眷恋中的突围——评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6):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