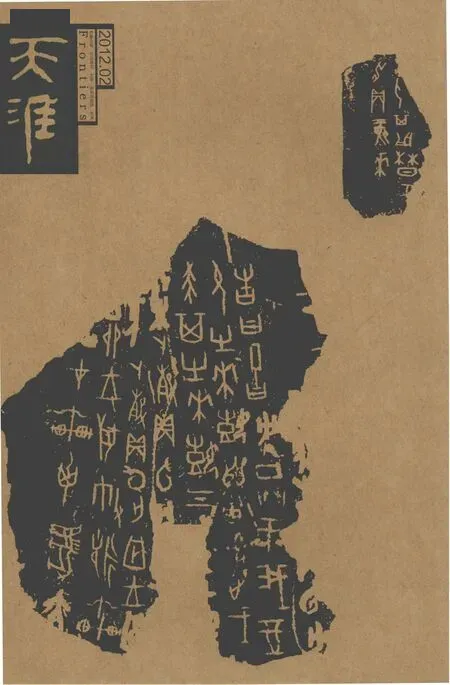站在意识形态的缝合点上
刘昕亭
2010年7月2日,贾樟柯的纪录片《海上传奇》公映,这一天仅上海一地就有十五家影院慷慨地排出了三十多场次。恰逢暑期档,对于票房至上、纪录片尚难以登陆大银幕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如此的院线礼遇,首先就堪称传奇。同时对于贾樟柯,这个2004年才以《世界》一片艰难“浮出市场地表”的体制外独立制作导演,执导上海世博会驻会影片且进入院线公映,此间的身份转化与文化资本积累,也可谓一个成功者的传奇故事了。
《海上传奇》与赵涛的“三无”出演
影片《海上传奇》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联合摄制,被列为世博会“驻会电影”,在世博会场馆中循环放映。在贾樟柯的电影创作里,这不是第一次尝试纪录片,此前《有一天,在北京》(1994)、《狗的状况》(2001)、《公共场所》(2001)、《东》(2006)、《无用》(2007)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纪录电影创作序列。作为这一序列中的最新章节,本片也确乎延续着鲜明的贾氏纪录电影烙印——缓缓的长镜头、叙事的自反,对普通人群的瞩目、对公共空间的偏爱以及对一座城市抒情挽歌式的再现。但是与贾樟柯既往电影创作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梦幻阵营”,勾连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跨度,显示着前所未有的表征野心。恰如媒体评论所言——“《海上传奇》,看得见的传奇,看不见的野心”。
《24城记》(2007)使用明星扮演与普通人讲述,招致了“伪纪录片”的质疑,到了《海上传奇》,贾樟柯精心选择了十八位受访者的“口述历史”,以标准记录访谈的形式完成全片。但是诸种叙事的断裂并未在历史当事者的现身说法中弥合,重新结构历史、讲述历史的困境也并未在贾樟柯“用影像对抗历史书写遮蔽”的宣言中消弭。这颇富症候性地体现在赵涛在本部纪录片中的“三无”出演——无姓名、无对白、无故事。
几乎无一例外的,在学术讨论、网络影评、记者访谈中,观众们都对这位御用女主角在影片中“打酱油”表示了困惑不解。影评人毛尖更是不无调侃地感叹:“(在《站台》中)贾樟柯对她的影像处理却很日常,不特写,不加强,饱含了一种对于纯洁的眷恋,所以他的摄影机像处男一样有诗意有诚意……一直到《海上传奇》,赵涛虽然在银幕上没出现几分钟,却分分秒秒是类特写的表达。”在“《海上传奇》会色情吗”的疑问里,毛尖得出结论,“赵涛的表达就是装神弄鬼,说得好听点,是文艺腔,说得难听点,是准色情。”对比贾樟柯在各式访谈中,将赵涛形容为影片“精灵”的倚重,究竟哪出了问题?这个一脸痛苦表情,在上海阴晴不定的天空下,狼奔豕突走来走去的赵涛,是别具匠心式的微言大义还是贾郎才尽下的“装神弄鬼”?
本文将赵涛在这部纪录片的出演,视作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一个“症候”——那些表述中的沉默、空白、置换与脱节,正是现实复杂性凸显的一个瞬间,是历史创伤经验归来的一个裂口。借由对赵涛在影片中五次穿梭往来的分析,本文读解贾樟柯如何在此部纪录片中,借上海一地,缝合诸种意识形态话语的错位,完成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种去革命化、去阶级化的“大和解”讲述。在这个意义上,贾樟柯的电影,确如他自己所说的“越来越走向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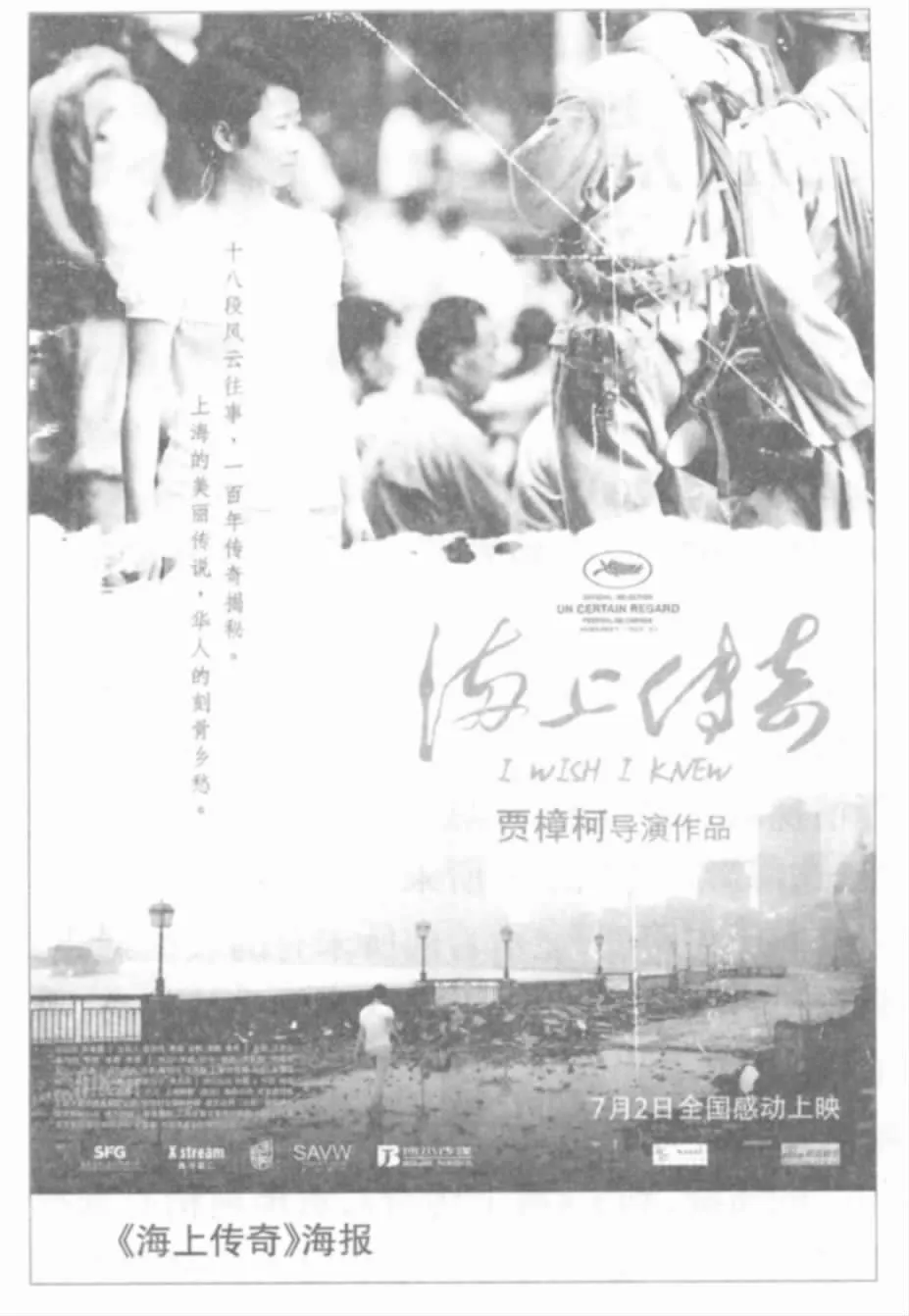
缝合:从电影理论到意识形态批评
“缝合”本是一个医学术语,指外科手术中的缝合伤口。这个词在拉康及其后继者雅克-阿兰·米勒那里被发展成为一个精神分析的理论概念,“它唤起主体和主体论述之间的关系,以及唤起想象和象征之间缺口的缩小”。
欧达尔将这个概念第一次运用于电影分析,后经丹尼尔·达扬、威廉·罗斯曼等人的批判性发展,电影“缝合理论”为观众的主体位置建构打开了一个理论探讨的空间。在对话场景中,观众既能从对话者A的位置来看,也能从对话者B的位置观看,这样一种经过剪辑建构出的完整时空关系,使得观众在视点镜头之间交互摆动,获得一种在失去和补偿之间来回往复的主体体验。无论是欧达尔分析的正/反打镜头,还是罗斯曼修正的含有三个镜头的连续镜头,电影符码的被操纵性,以及电影叙事对于这种操纵的掩饰和伪装,都使得对于电影意识形态效果的讨论成为可能。
齐泽克沿着后期拉康思想继续前进,在不同于电影“缝合理论”的另一个向度上,通过与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话,激进化了拉康精神分析的“缝合”概念,号称马克思主义对拉康的全面接管。1969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的发表,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的”论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意识形态”由是成为“个人与其所处社会的一种想象性关系”。自1989年出版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以来,齐泽克的一系列理论著作乃至电影批评,则再度反转了阿尔都塞的命题——意识形态不单是一种想象性关系,它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为我们构造了有效的、真实的社会关系,从而逃避某些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就“缝合理论”而言,吸收拉克劳、墨菲等人的研究成果,齐泽克指出,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论述远非清晰明确、严丝合缝,意识形态靠着缝合术而把众多漂浮的能指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叙述,将意义固定下来,给出同一性,维护稳定性。齐泽克理论论述的启发之处在于,就意识形态分析来说,重要的并非是一个形象或一部电影蕴含了何种意识形态内容,而是将影片视为一个意义扭结点。因为各种错综复杂常常是南辕北辙的意义和内容都会汇聚在这个缝合点上,并且都要通过这一点来形成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叙述。于是意识形态批评就不再单纯是揭示一种想象性关系,而是寻找缝合点的斗争,通过对于意识形态缝合术的揭示,拆解能指链条,让主体嬉戏沉迷于漂浮的能指中,至此才有“穿越意识形态幻象”的可能。
在《海上传奇》中,赵涛的出演正是作为缝合点,在历史鲜血漓淋的伤口处,结构起了全片——贾樟柯所言“十九世纪的殖民、1949年的解放、1966年的‘文革’、1978年的改革、1990年的浦东开放”。赵涛在片中的出现,或是作为讲述—抒情交叉结构的节拍器,或是作为场景转换的剪辑点,连贯起了一个充满了“大和解”意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一个信誓旦旦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意识形态讲述。

作为缝合点的赵涛
缝合Ⅰ:谁的传奇?
影片以交通银行前工人擦拭石狮的镜头开场(在贾樟柯的阐释里,选择在银行门口开始第一个镜头,是与上海曾经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呼应),在雄狮低声嘶吼的画外音中,维修中的道路、中景里来来往往的汽车、拆迁改造的楼房一一入画,似乎是当代中国城市中的惯常一景。银幕短暂的切黑之后,配乐转为《茉莉花》的婉转悠扬,《海上传奇》黑底红字的片名出现。场景转换到黄浦江中的渡轮,镜头从左向右缓缓横移,前景中是虚焦的围栏,中远景是江中渐次划过的轮船,一个形成于河流、繁华于河流的城市,在这个优雅如卷轴般拉开的长镜头中渐渐切题。直到嘈杂沸腾起来的人声把视野拉回船上,镜头框住了一张张普通而形态各异的面庞。在贾樟柯风格化的电影语言中,类似的开场镜头已经不陌生了,《三峡好人》、《东》和《无用》,都是以一个缓慢的抒情长镜头开场,在对各色人等特写镜头处理之后停留在主人公身上。在一个眺望浦东的全景镜头之后,赵涛“啪”地撑开一把折扇,身着白色V领T恤、卡其裤亮相了。她拿起扇子挡雨,又放下扇子带点困惑表情地左顾右盼,然后从右侧出画,右底字幕渐渐显影“上海2009”。紧接着固定镜头里,赵涛依旧是沉默不语,在一条正在修整的水泥路面上,向画面纵深处缓缓走去,镜头始终保持不动,目送着赵涛走远。接下来本片中第一个访谈者陈丹青登场。
或许可以对这组镜头做这样一种理解:赵涛就是这部电影的讲述者,像一个传统的说书人,扇子打开的一瞬间,讲述开始了。而她在影片中莫名其妙地走来走去,其实是在寻找、修复这些散落在城市废墟上的个人记忆。只可惜“那些被政治打扰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专属于过去时代的大人物们。
在这个访谈段落里,有陈丹青讲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文革”、抄家、流氓打架……有八十一岁高龄的杨小佛(杨杏佛之子)回忆十五岁时亲眼目睹父亲被暗杀;“味精大王”张逸云之孙张原孙侃侃而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奢华生活;还有杜月笙女儿杜美如对于昔日上海大亨拉家常式的讲述。这个段落涉及的历史跨度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开埠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在这些前尘旧事里,上海的确堪称传奇,这里有政治角逐的血雨腥风,有巨额资本支撑的纸醉金迷,有帮会林立的江湖社会——这是上海的传奇。但是上海还有另一面——在张原孙的采访段落结束之后,场景从西装革履的豪华舞厅转到苏州河上,搬演了十六铺码头工人负重劳作的现场,这也是影片唯一一组采用搬演手法拍摄的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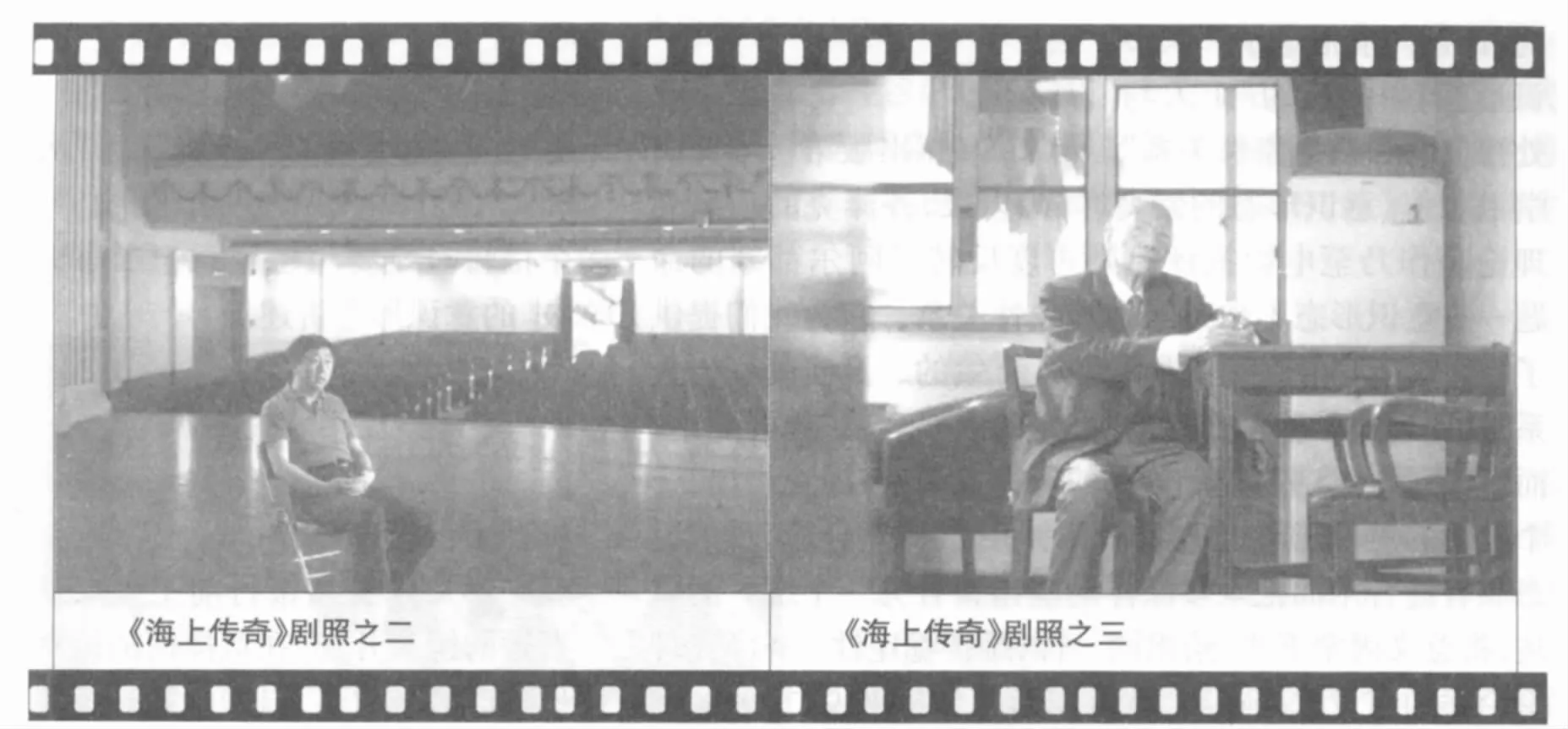
新世纪以来文化界掀起的“上海热”,在现代性、全球化的知识资源中建构起了一个“摩登上海”,这个“东方巴黎”的上海形象,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话语错位:上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辉煌、海派文化的崛起,是与被迫开埠以及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繁华与屈辱共存的“殖民地现代性”?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以钦羡的眼光打量那个曾经的“十里洋场”时,忘记这里同时也是异国官绅、海盗、人口贩子的乐园?在此贾樟柯选择的意识形态缝合术,是以风云人物的自述凸显“传奇”,以底层劳工的搬演象征半殖民地社会的苦难。于是画面上这些码头工人们不能开口,只能沉默,只能以劳动的画面在历史的喘息处现身。这一组搬演的劳动镜头连同字幕交代,将底层劳工与上海被迫开埠、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并置在一起。如果说贾樟柯在寻常里弄孩子们追逐打斗里,寻找着上海失落的英雄梦;在张原孙花园洋房、中央空调、捐战斗机的讲述中,修复着民族资本家曾经的辉煌与奢华,那么底层劳工作为视觉表征,却只能与上海屈辱的另一面共存,历史主体的叙述要留给那些大风大浪、生离死别的“传奇”。
在多少带些辩白意味的自述里,贾樟柯说,“上海是一座风云际会、精英荟萃的城市。这些所谓的精英人物基本囊括了这座城市曾经历过的所有记忆……我觉得他们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就像是全景式的长篇小说,叙述了上海五十年以来,甚至百年的历史过程,以及这种变革为普通百姓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影片的主要焦点还是放在这些风云人物身上。”在贾樟柯的阐释里,赵涛就成为“那些没有办法去讲自己传奇的人”的代表,在那些传奇故事的娓娓道来之外,茫然不知所措地困惑着迷失着。此间的尴尬与悖论在于,一面是贾樟柯声称“我对上海感兴趣,是它的传奇,而非日常”;另一面他镜头里的传奇人物却大多讲述着家长里短的普通生活,因为贾樟柯又说“我想回到一个日常的、过去的空间”。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传奇还是日常,而是贾樟柯关注的,究竟是谁的传奇?当赵涛成为一个缝合传奇人物与普罗大众的意义扭结点时,贾樟柯近年的创作困境再度彰显:在一个大踏步朝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导演那里,对于普通人的关注究竟是一种切肤的情感认同还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市场策略?如同《24城记》显影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却再度埋葬他们一样,旧上海的底层劳工也在随后的影像中被改造为长兴造船厂一身整齐行头的现代工人,一个视觉上与前述搬演场景形成呼应对照的“大国崛起”姿态。

历史,尤其是历史的创伤确实需要被记忆,但是我们也要小心被弗洛伊德称为“虚假记忆综合症”的诡计。在弗洛伊德看来,那些童年创伤性的记忆未必确实发生过,相反可能是在当下的焦虑困窘中被反身重构。伴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曾经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历史讲述正在失效,而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去革命、去阶级化的讲述策略正在变得越来越需要被“记忆”。这就是赵涛的出演作为缝合点的意识形态意义——在1949年前的上海传奇中,半殖民地的屈辱记忆被留给了底层劳工,普通人的平淡生活被赵涛代表,而历史主体性的讲述姿态则属于成功艺术家、政商名流之后们。半殖民地、冒险家乐园、资本传奇、劳工抗争诸多漂浮能指在此一一缝合起来,在齐泽克的意义上,获得了同一性。
缝合Ⅱ:大和解——城与人
赵涛的第二次出现,是拿着扇子从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缓缓走向摄影机。画面被车流和逆行的赵涛一分为二,这种视觉语言上的切割、分离对应着接下来讲述的离别故事。在赵涛外滩倚栏而立吸烟的夜景镜头之后,画外音《东方红》报时钟声切入,将影片的叙事进程推进到内战离乱、决胜1949的高潮。
当王佩民作为烈士遗腹子声泪俱下地讲述着父亲的牺牲时,当《战上海》(王冰,1959)的电影片段把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定格为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时,导演王童的回忆连同他的影片《红柿子》(1996)则展示了另一番苦涩柔情的离开与远走他乡的踌躇。影片接下来转入台湾外景地的拍摄,分别采访了李家同、张心漪和侯孝贤。这些一律操一口标准国语的讲述者们,所谓的台湾外省人,当年随着国民党战败离开大陆移居台湾,他们的上海(或大陆)记忆,是离开的仓皇、是战争的阴影、是爱情片段、是电影构筑起的男欢女爱。
以电影片段作为剪辑点,在采访了朱黔生、黄宝妹之后,赵涛第三次出场。场景再度回到影院,呼应着上文在影院空间中对台湾导演王童的采访。荧屏上播放着谢晋1964年的电影作品《舞台姐妹》,镜头反打,赵涛惊惧地坐立起身,在惊雷声中,浑身湿透地在工地上疾行。画外音是上官云珠之子韦然讲述母亲的“文革”遭遇。当他回忆“文革”中姐姐偷渡香港未果后,赵涛再度出场,缓缓步下台阶,在这个视觉上的下降情势连同左顾右盼的犹豫片刻之后,赵涛怅然回眸一眼离开,留下一个旧上海小开装扮的男士倚门吸烟。许冠杰经典粤语老歌《浪子心声》响起,场景缓缓滑落到“香港2009”。在香港段落里,韦伟、费明仪、潘迪华依次登场。如果说在上一个段落里,台湾政治人物的出走是不得不走的无奈,夹带着战场失利的逃亡意味,那么这批携家带口南下的文化人,则像银幕上赵涛的扮演一样,大多是在几番犹豫之后的怅然不舍,对于1949年后的上海,他们怀有太多的不确定,但也有太多的割舍不下。
至此,所谓贾樟柯的“野心”已经不言而喻,《海上传奇》不仅是传奇,也绝不仅是上海。通过赵涛的穿梭往来建构起一个统一的时空关系,在历史的又一个创伤口,贾樟柯触及了被冷战结构残酷撕开的上海(大陆)——台湾——香港阻隔,加入到了后冷战的“大和解”中。正如陈光兴所言,在这个时代,“和解这个字眼的出现不仅为台湾或大陆所独有,同时也是各国内部及国与国之间,处理冷战期间所造成的长期对立与伤害的策略”。在曾经的冷战年代,在酷烈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角逐里,社会主义的大陆、资本主义的台湾、意识形态“飞地”的香港,互相指认对方为他者乃至敌人。而在后冷战的时代里,“大和解”则成为以资本流动为先锋的全球化时代的主流叙事。但是如何和解?贾樟柯选择的叙事策略,是以人与城的分离为契机,表面上是“我带着摄影机来到了上海,并随着上海人离散的轨迹去了台湾和香港”;实则是“把不同年代、不同立场、不同阵营、不同经历的上海人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时间内集中呈现在一起”;而最终的野心,则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度讲述一个“大和解”的历史——“超越党派去回溯历史。过去的所谓正义,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一党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在这场大的变革里承受了什么,承担了什么”。
当“正义”、“党派”都已不重要之后,什么又被影像放大,变得分外重要了呢?1949年不再被视为有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不同政治道路之选择,而只是一些人牺牲了,另一些人必须离开的悲情讲述。对于共产党的烈士之女,那是永远失去父亲的切肤之痛;对于国民党军官之子,那是半生离别的哀歌柔板。在双方如此凄凄苦苦地互诉衷肠、互露伤疤之后,跨越冷战情感结构的“大和解”在贾樟柯处变得顺理成章。此段落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在烟雨迷蒙中俯瞰香港尖沙咀天星码头。旧的天星码头,那个“集殖民地美学与维多利亚政治于一身”的香港地标性建筑,已经在2006年末被特区政府拆除。在去殖民、去冷战的“大和解”进程中,贾樟柯选择的姿态,是挥挥手告别历史向前看,过去的故事属于老人们,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需承担历史的负债,所以赵涛再度归来。
缝合Ⅲ:告别历史,走向未来
告别了烟雨凄迷的香港维多利亚港,赵涛倚栏而立出现在游轮上,字幕显影为“上海2010”,天气也开始变得晴空万里起来。从“上海2009”中出发,历经一年,辗转台湾、香港,遭遇各种恶劣天气,赵涛终于带领观众回到了上海。在雄壮昂扬的交响乐声中,影片第一次出现了赵涛的视点镜头。这个幽灵一样的人物终于可以“看”到了,而非沉默地倾听过去,赵涛的反打镜头里是一艘上海海事局世博专用执法轮艇驶过的近景。伴随着“世博会迎来国家馆日”的广播声,影片进入当下叙述。第一个代表今日上海登场的,就是中国最早投身股海的股票大亨杨怀定。在一段世博园年轻打工者大秀街舞之后,韩寒作为压轴人物大谈自己的购车奇遇记。贾樟柯对于这一个段落的定位是上海的“财富梦”与“自由梦”,是以世博会为契机,在回顾历史之后的展望未来。一个俯瞰的大全景之后,赵涛最后一次出场。她在夜色中拾阶而上,站立桥边,一袭白衣确乎犹如鬼魅游魂,那把开场撑起的折扇已经收好放在口袋里,镜头从仰拍开始缓缓摇起,画面充满了坠楼而下的恐惧感。最后一组终场镜头,是轻轨里一群普通的上海市民。

从结构看,影片以赵涛打开折扇为开始,以收拢扇子结束;以赵涛出走寻找历史开始,以返回当下现场结束。从镜头语言看,影片以黄浦江中的渡轮开始,在现代化的轻轨中结束,都是普通人的面容百态,但是走向未来的人们,却是满脸的疲倦与焦虑。影片这个暧昧不明的尾声,或许也泄露了导演本人对整部影片叙事的一丝犹疑,一点不太甘心的迟疑。而这已经透露在赵涛第一个出场镜头里,如前文分析,选择固定机位以一个注目礼的姿态目送赵涛离去,而非移动镜头的跟随,在视觉语言上已然意味着,摄影机背后的导演并未充分认同这个镜头前的出演人物。
通过对本片的文本细读,不难看出,赵涛在影片中的出演绝非随意的“打酱油”,她在影片中的每一次出现,显然是经过精心结构的。贾樟柯借赵涛在历史创伤段落上的出现,将殖民历史、国共叙述、历史与现实的裂隙一一填满。
作为缝合点的贾樟柯
在贾樟柯纪录电影的创作序列中,《海上传奇》无疑是一个更为主流化商业化的转变。影片仍然保留了相当个性化的影像语言,但是在贾樟柯“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地缝合意识形态话语裂隙之后,这部百年中国历史的纪录影像,已然只剩下一个“苍凉而华丽的手势”了。
对于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创作来说,《海上传奇》亦是站在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缝合点上。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脉络里谈及“纪录片”,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参考背景即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崛起。在1980年代末期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纪录片”成为一个不同于简单电影类型分类的“超级能指”,它指称着与“专题片”的二元对立,同时意味着一种更为个人化、带有强烈新启蒙色彩的文化态度。而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急遽的政治动荡与社会转型之后,中国新纪录片又以其他艺术无可替代的媒介优势,置身并目击着这一“转折年代”的现场。这批当年身处国营电视制作体制的突围者,逐渐汇聚起了一个朝向海外电影节、独立的体制外纪录片创作空间,电影学者戴锦华名之为“吴文光模式”。不同于“张元模式”与中国社会主流的悬浮、游移状态,“此间优秀的纪录片作品(以《铁西区》、《淹没》为代表),直指为主流屏幕所略去的酷烈画面,直面中国社会变迁中被抛弃、牺牲的底层多数”。在《大国崛起》、《话说长江》等央视大手笔投资、国家主义姿态的专题片之外,保持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贾樟柯之前的纪录片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传统——独立制作、靠海外艺术电影市场赢利、以个人的悲欢离合触摸时代变局。但是《海上传奇》无论就其资金来源、叙事视角、历史态度来说,都已经显示出了向《大国崛起》等专题片靠拢的倾向。
如果回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诞生,一个“历史的诡计”再度浮现。这场以体制外制作开花结果的“新纪录运动”,在其发生发展之初,其实是吊诡地获得了体制力量的支持。最早一批投身新纪录片拍摄的导演们,大多隶属于各电视台的海外制作部,在以国外观众为目标受众的影片制作中,文字解说配万能镜头的拍摄方式显然不合时宜。也正是借助这股体制内变革需要的物质力量,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才能异军突起。
今天当《海上传奇》作为一部获得体制力量支持的纪录片,借重着贾樟柯对于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参展戛纳,宣传世博,展示一个愈加开放的“大国崛起”姿态,此间体制/体制外、个人视角的批判/国家宣传的讲述,巨大裂隙正在被悄悄缝合。历史的第二次发生,或许真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