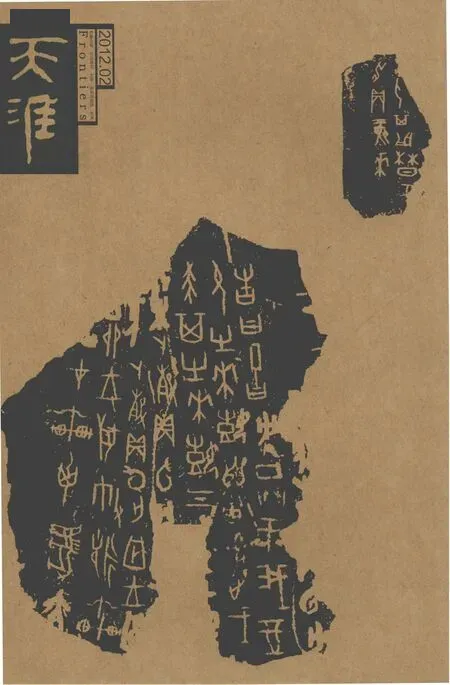《醉花窗医案》选
[清]王堉 著
石舒清 译
李香泉
我在城东三道河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叫李香泉的朋友,四十多岁了,还没有一次考中过秀才。他素来喜欢喝茶,从早到晚,每天能喝茶几十碗。只要见到炉火旺烈,鼎水沸腾,他就喜形于色。时间长了,他的脸上就少有血色,饭量也减少了。每每到了初秋时候,常常彻夜难眠。天快亮的时候就觉得渴得厉害。他从家里去私塾时,常常带着药丸,早晚不忘服用。随身还携带熟枣一袋,不时就往嘴里丢上一枚。我问这是什么缘故,他说这是从医书上看来的,医书上讲,大枣能安神,他苦于睡不着觉,因此常常不忘食用。我就问他服什么药?他说他请教了一个信天主教的医士,名叫王凝泰,王让他服用“人参归脾丸”。王医士的道理是,香泉的病是由于读书劳心、心血亏损所致。我说,服后有效吗?答说并不见效,但是也没有什么害处。我说那么让我给你看看。我给他诊脉,脉多弦急。我对香泉说,这是水停不寐的原因,不是血虚的原因。你的头一挨枕头,就会觉得心头颤动不已,而且两胁有闷胀感,小便也不利,时时觉得口渴难忍,因此才睡不好,如果把水的问题解决了,你就能睡得香了。你服用归脾丸其实是不对的,时间长了,水气上腾,就会头昏呕吐。年纪再大些,恐怕会得水肿病。香泉说,你说得对极了,赶紧给我治一下吧。我就让他服用“茯苓导水汤”。当天晚上约二更左右,香泉就起来小便了五六次,再入睡时就安稳了许多,在睡梦中还说梦话:“好爽快。”一觉竟睡到大天亮,起来发现被褥都被尿湿透了。从此就不再多喝茶,饭量也加了不少。我让他继续服食六君丸,用来强健脾胃。
香君碰到人就说我的好处。
张兄清之妹
老乡张兄清的妹妹,回娘家好几天了,忽然觉得胸口胀满,茶饭不思,还呕吐咳嗽个不停。她的妈妈怀疑是有身孕了,请我去看,我号脉时,发现六脉平顺,左关带滑象。我就告诉病家说:这个病的起因是肝气不顺,郁闷生火,肝又影响到胃,因此不想吃饭。我于是开了“逍遥散”的方子,加上“丹皮”、“山栀”,用来清火解郁。只服用两副药就好了。
王维藩
记得邻村有个叫王维藩的郎中,以给人医病为生,家里也有个药铺。村里一妇人,胃痛,找上门来让王看。王维藩采用了“失笑散”的方子,这个方子出自《海上方》一书。一吃竟很快好了。从此以后,凡是有心口痛者或胃不舒服者,王维藩都用“失笑散”来治,有时有效,有时无效,说来各占一半吧。王维藩喜欢吸大烟,一天忽然觉得胃痛,他给自己也开了“失笑散”的方子,结果痛得更厉害了,半夜里实在痛得受不了,又是撕枕头又是捶床,天还没亮就死掉了。
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失笑散”是解瘀的药,那个服之立效的妇人,一定是血瘀凝滞,因此吃了管用,若不加分析明辨,什么病都用“失笑散”来施治,不免要误人性命了。
王维藩不知用“失笑散”医死了多少病人,他最终自己死在这个方子上,说来未尝不是报应。学医的人,一定要谨慎啊。
李喜阳之女
我的邻居李喜阳,和我往来很是密切。庚申年秋天,生下了一个女儿。李的女人奶水丰足,因此他们的子女小的时候,无不肥健喜人。一天我到他家闲逛,看到他的小女儿昏睡不醒,喉咙里发出锯东西一样的声音。我问这是怎么了。李说他也不知道,今天早上忽然就成了这样,喂她奶不吃,二便闭塞不通,肚子也膨胀得鼓一样,是不是受了惊吓,恐怕没有救了,一家人正着急着要去找我呢。我说,不要担心,哪里有你说的严重。我摸了摸,觉得病人身体滚烫灼人,肚子胀起老高。我说,这是积乳作祟,积乳一通,自然就好了。李喜阳的表兄,在不远处开着一片小药铺,我就让李赶紧拿出纸笔,写好“白玉饼方”,等李喜阳拿药回来,即刻捣药成末,给病人强灌下去,只两刻许,就听到病者胸间辘辘有声,排出秽物好几次,汗也没了,热也退了,睁开眼睛哭起来。给她喂奶时,她好像饿得厉害,边哭边吃。
我就告诫李喜阳的女人说,你以后喂孩子奶,切记要从容,不得慌急,而且喂奶的时候,一定要坐着,千万不要睡卧着奶孩子,如此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那女人一听就笑起来,原来头天晚上,她正是侧睡着喂奶的。李喜阳就把女人痛骂了一顿。
赵楚仁之女
邻居赵楚仁,在天津做典当生意,家境不错,他的妻子性格比较霸悍,生了几个女儿一个儿子,两口子很疼爱子女。戊午年夏季的一天,赵的五女儿,年纪约六七岁,开始出天花。派人把我请去看看,我看到孩子身上的天花像蚕豆一样密集,平板细碎,几乎周身都出遍了。尤其嘴唇四围,密密麻麻的,一点空隙都没有。而且手脚发硬,饮食不进。我问出花几天了?答说两天。问发热不?说倒不是太热。我又问了两便情况,大便有些稀,小便有些多。我说,出花发热,三天之内,从头到脚,渐次出现花点,如果天花颗粒分明,形色红润,而且饮食如常,两便也没有什么异样,就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你女儿的天花,不到两天时间,就已出齐,形色、两便、饮食又是这样的情况,尤其嘴唇周围,天花密锁,不是好迹象,恐怕已是不治之症。赵的女人对我的话十分反感,几乎要骂我了,赵楚仁给她频频使眼色,女人才好不容易忍住怒火。我说,我是来看病的,不是来给你们惹烦恼的,十天之内,如果有谁能治好这个病,我愿意拜他为师,说完我就要走,那女人的霸悍样子我受不了。但是赵楚仁拉住我不放手,让我无论如何开一个方子留下。我就开了“升麻葛根汤”,又加了“参芪”给赵楚仁。我给赵楚仁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不一定有效。第二天赵却急急跑来,说服药后有效果了,请我务必再去看看。我坚辞不去,知道去也白去。赵楚仁气呼呼地走了,请了别的医生去。还不到十天,当天花微涡下去时,这个小女孩就死掉了。我听了觉得难过。
赵楚仁一家因此很信任我。后来在街上碰到赵楚仁,他施以长揖,向我道谢。我说病没治好,道什么谢。赵说,要是早早听了你的话,就可以少花钱了。只有商人才这样说话。我说,说来也有定数,要是不花后来那些钱,说不定你的女儿也许不死呢。赵楚仁擦着眼泪走了。
孟嘻之妻
我的朋友孟嘻,妻子四十多岁,刚刚生过孩子时间不长,肚子里疼痛难忍。请我去看。按她的两脉,实大而坚,我知道这不是好的征兆,担心朋友接受不了,我没有明言。虽然开了“人参泽兰汤”让病人服用,但是没有疗效。又来请我。我说,如果疼痛不减,就说明我的方子无用,请找别的大夫吧。孟嘻不愿意。多次登门请我再去看看。没有办法,我只好实话实说,一般来讲,产后的脉象,宜缓宜小,现在病人的脉却坚大不弱,恐怕是难治好的病。孟嘻说,麻烦你再开一方子,若万一无效,我也不埋怨你。我说,这不是埋怨不埋怨的事,只怕我白费气力不说,也让你白白花钱。孟嘻有些疑惑的离去了。
后来接连请了十来个大夫,都毫无效验,五十多天后,病人就不治而亡。
张文泉
同乡张文泉任司马一职,是我的学弟。丙辰年春,他先后入秦赴任,公务之暇,张文泉喜欢设宴招待亲朋。他的亲戚乔某也是介休人,在湖北郧阳府供职,为提饷事来到秦地,就住在张文泉家里。张文泉原本就是一个大方人,对自己远道而来的亲戚更是不在话下。然而这个乔某,却有些贪得无厌,不知好歹。好吃好喝之余,他还要洋烟抽。洋烟而外又要衣服。衣服而外再要钱财。文泉稍有不乐意,乔某就吹胡子瞪眼,好像文泉倒欠了他的。时间长了,文泉终于有些不堪其扰,想寻个法子打发他走。但是军饷一时筹措不齐。如此又延耽了两个月左右,乔某终于要走了,临走之时,乔某又百般辱骂文泉,挽袖捋拳,几乎是要打他一顿才能罢休。文泉这个人,虽然个性豪爽,却拙于言辞。积郁在心,不能发泄,心里的憋屈真是无法言喻。一天他从咸宁到我这里来,和我晚餐时,说到这个事,这个好客的人几乎要落下泪来。我劝他说,像这样的不仁之徒,不必与他计较。现在他已经远去了,那么就忘了这段不愉快吧。文泉离去不久,忽然派车来接我,我到时见他呕吐满地,汗下如雨,面色很是难看。他到底想不通,气不过。我给他号脉,六脉都伏而不强。我知道这是气郁而逆,再严重些患者会昏厥过去。忙忙捣了半碗生姜汁,给他灌下去,过了一会儿他不吐了,然而胸闷气促,转侧难宁。就给他服用了“越鞠丸合顺气汤”。天亮的时候,他的肚子里安静了,让他继续服用这个药,又过了三天,他就完全好起来。
曹某

商人曹某,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这个人酒量很大,饭量也不小。盛夏时候,他经营生意,往来奔波,一旦口渴,常常食饮生冷之物,于是导致消化不良,头痛发热,腹胀神昏。别的大夫以为是感冒,从驱风的角度来治疗,无效验。就请我去看。我号脉时,发现右关坚大,右尺弦缓,也没有浮象。我的结论是:这是不注意饮食,伤了胃,不见食物便罢,只要见到,就想呕吐,属于伤寒病中的五症之一,当作感冒伤风来治,可谓南辕北辙。我采用“金饮子方”再配以“大黄”、“槟榔”等,吃了两副药,热就退了,肚子也不胀了。五天后曹某亲自来道谢,又说到一个情况,曹说他没病之前,常常有呕吐手颤的毛病,不知是什么缘故。
我认为别无原因,是他喝酒太没有节制了,我让他服用“葛花解酲丸”,一定会好起来。曹某听了我的话,服用“葛花解酲丸”到半斤左右时,就把这个老毛病彻底治好了。
伶人某
有一个唱戏的,忘了她的姓名,是四喜部有名的旦角。六月初,出演《泗州城》,引起轰动。某官员痴迷她的演技精湛,花钱请她演一折《卖武》。她收拾齐整,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耍了个遍,在台上折腾了足足有两个时辰,这才到后台卸妆。妆还没有卸下,她就呕吐不停,好像把五脏六腑都要呕吐出来。忙忙把她送回家里,这时候不呕吐了,然而却昏不知事,在一边推也推不醒来。她的师傅很愤怒,派人去找那个官员。官员早就听说我是个看病的,托人请我去看看。我到时见病人汗出如油,一脸的残脂剩粉,不成样子,而且呼吸迫促,呼而无应。提起她的腕子诊脉,觉得六脉浮濡,按重些时脉却消失不见了。我让守她的妇人用热鞋底温暖她的肚脐处,过了一会儿,她缓缓睁开了眼睛。接下来我让病人服用了大剂量的“香薷饮”。此后两天,她一直显得较为平静。又过了三天,有人送来名片,姓名是陌生的,门人说就是那个唱戏的,她是来道谢的。我躲起来没有见她。
田大授
同村的田大授,家境还行。年老无子,他的老婆性格凶悍,因此田大授也不敢娶小老婆。后来因为变故,田的家业损失不少,田大授因此郁闷得病。城里有一个老大夫,叫荣同,田大授素来信任他,就去找他看病。荣同先是认为受了风寒,治疗无效;又作年老气虚来治,也不见好转,反而越治越重。荣同就让田大授来找我。我号脉时见田肝脉滑数,脾部见弦急,而且三至一息,我就说,你的这个病啊,说来还是肝气郁结,我给你用心看,只怕医病不医命。田听到这话变了脸色。他恳请一个方子。我让他把“逍遥散”和“左金丸”配合着服用。吃过几副,病势就缓和下来,他也能吃一点东西了。他很高兴,又来请我把脉。我觉得他的肝脉有改善,脾脉却依旧。知道这样的病终将不治,但还是开了“逍遥散”给他。田大授坚持服药,情况看起来大有改观,他显得精神旺健,还很有兴味的到一些地方游逛。有一次村里来了戏班子,在庙庑里上演,田大授也来看戏,喜不自禁地告诉我,他的病完全好了,再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心里说“脉至不息才好啊”。
后半年,我因事去京都,返回来时已是阳春三月。问到田大授的近况,说他已去世好几个月了。
寺僧昌裕
丁未年,我在老家的一个寺庙里隐居读书。这一年,按中医讲,属太阴司天。自五月后,阴雨连绵,地上湿滑泥泞。而农家忙于农事,有时不得不露宿于野。外感风寒,很容易得疟疾。我就预先准备了一坛常山药酒。六月下旬,果然疟疾大作。十个人里,五六个人都难得幸免。前来我这里索要药酒者络绎不绝。因此使不少人死里逃生。到七月中旬,疟疾势头渐弱下去,药酒也没有了。
我寄居的寺里,有一个僧人,叫昌裕。虽说是出家人,却无赖难缠。因我在寺里的缘故,他还稍知收敛。不久也得了疟疾,向我讨求药酒,我说酒没有了,再酿制也需一段时日,短期内肯定是没有酒的。昌裕好像认为我太吝啬了。我就把他叫来,对他讲,你错怪我了,我施药大众,岂会在你一人上吝啬。不过同患疟疾,但各人虚实禀赋不一样,即使从我这里得到药酒的人,也未必人人有效,也未必人人同效,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再看看如何?昌裕转怒为喜。我就给他诊脉,觉得弦而迟。我推断他患的是寒疟,发作起来,必然多寒少热,先寒后热,而且身体疼痛,少有汗出。昌裕说正是这样。我就用“越婢汤”给他驱寒,两天后他的疟疾明显转轻。总共吃了五副药,他的病就全好了。
黑六
黑六应该是绰号吧,忘了他的真实姓名。一天黑六突然腹痛难忍。强撑着来到我家里,跪下来求我救救他。我问他是怎么得上这个病的。黑六痛得流着眼泪,说昨天他吃了半大碗莜面条,然后去瓜地里劳动,渴得厉害,就喝了两碗凉水,回到家里,肚子就痛起来,胸口感到憋闷,手按一下有刺痛感。我说,这是食积不化。但你的胸中像石头塞洞那样,没有空隙,用药来治,恐怕药弱而病强,药对病无可奈何。黑六说,那先生你说咋办好,难道让我就这样痛死吗?我说你想让你的病好,必须找一个力壮的人扶了你,在开阔的田畴间多走上几个来回。黑六以为我在开他的玩笑。见我一脸严肃,就说他实在走不了。我说不这样就治不好。黑六让我再想想法子。我就用大剂量的“承气汤”配上“麦芽”、“槟榔”让他服用。我让他服用三副即可,若无效,不必再服。黑六这才回去了。吃第一副药后,黑六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胸口那里坠落下去了;吃到第二副药,突然下气暴作,忙忙提了裤子往厕所里跑,像脱底的水桶那样不可收拾,这样肚子里就空了。
病好了,黑六就肩了犁去耕地。
强学潮之妻
强学潮是个大夫。他的老婆生得蜂目豺身,不是个好东西。强学潮去世后,这个女人更加地没有忌惮,虐待儿媳,只对自己的女儿好,在家里动不动就打骂儿媳。她的女儿正好嫁给我们村里的王姓人家,粗悍不讲理,正和她的母亲一样。强学潮老婆已年过花甲,但是每天都会来我们村子几趟看女儿,走起路来年轻人都赶不上她。壬戍年春,她因为生气,食而难化,心口和胃都痛起来。刚开始她还忍耐,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去找一个姓任的大夫看病,任是一个江湖郎中,说她是年老气虚,需吃补药。吃上后痛得更厉害了。再去找任大夫时,任拒绝给她治了,说你这个病治不好了。她的女儿知道我会看病,就请我给她母亲看看。我本来是不愿给这样霸悍的女人治病的,但禁不住她的女儿女婿的一再恳请,就答应看看。号脉时我发现她的右关实大而滑数,兼肝气郁结。一定是生气后又进食,食为气雍,因此郁而生痛。她的女儿一边夸我脉号得准,一边就指责起她的母亲来,说我常劝你不要生闲气,你不听,现在病得上了,你怨谁呢?我让她们母女不要当着我的面相互攻讦。就开了“越鞠平胃散”,配以“枳实”,又大剂量的加用了“香附”。我说,开上两副药就行了。
过了四五天,在街上碰到强学潮的女儿,说她母亲的病已好了,一再给我道谢。
乔某
介休县田村,有个姓乔的人,没记住他的姓名,年老之际得了痹症,手足疼痛,痛点游走无定,难以捉摸。不少大夫都当作瘫痪病来治,药吃了不知多少,一点效果也没有。就这样委顿不振地活着,家里已给他准备好了丧具。好在痛则痛矣,饮食两便都无大碍。田村有一个经商的人,知道我,就让他家请我去给老人看看。我到他家,在见到病人之前,先向病人的儿子了解情况,我问尊大人得的是什么病?乔某的儿子说是瘫痪病。我说,老年人得这种病,十有七八治不好,恐怕治也无益。但是既然来了,就看看吧。老人住里屋,看见我即拱手致意。问答之间,感觉他口舌便利,神清气爽,没有我想象的口眼歪斜的样子。我问他手足麻木否?答说,并不麻木,只是时感疼痛,痛不可忍。号脉时,发现他六部都显得缓而且沉,兼带弱象。我说,老人家你害的既非瘫痪,也不是痿症,而是痹症。常感四肢滞拙,重不可举,举手投足,都需人帮忙才行。乔某说正是如此,问他的病还能否治好。我说治是能治好的,但是不能心急。十天半月内,要立见功效,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谨遵医嘱,大量吃药,早则三个月左右,多则半年,一定能做到扶杖而行。乔某高兴极了,说只求病好,不求速效。我先给他配了“理中汤”,另加“附子”、“苍术”;吃过五副,痛势减缓,食量也有增加。换了“姜活胜湿汤”,另加“牛夕”、“肉桂”等,让他多多服用,半月过去,不再感觉疼痛。只是举动迟缓,行步还难,针对这个情况,我开了“白术附子汤”,另加“松节”、“萆节”等。叮嘱服过十副之后,把它做成药丸来服用。同时让人早晚扶掖病人,勉强行走。如果能走出几十步,就是好的征兆。乔某很谨重地记下了我的话。
过了三个多月,病人穿戴齐整,坐着车子来看我,还带着礼物。这时他已能行走如常,只是上台阶的时候,迈过门槛的时候,能看出不便来。这时节还不能过于劳顿,我就让他尽快返回以利调养。
这一年冬日,我在酒肆里碰到了乔某,已好如常人。
又过了十多年,乔某的儿子来我这里看眼病,说到这个事,我才记起来,就记录了下来。
乔夏清
乔某的小儿子叫乔夏清,辛酉年,忽然出现在我的门口。他没有唐突进来,先递入一封函件,写得文雅歉抑,很得我心。就把他请进来。原来他已入过县庠。据夏清讲,一别十多年来,他的家道已不同往昔,早显零落。嫂嫂又很妒悍,为了不生闲气,免受虐待,他就到祁县授徒舌耕为生。开春时候,忽然得了眼病,两个眼珠痛不胜痛,晚上尤其痛得紧。找过几个大夫,都没有治好。忽然想起少年时候,我为他老父亲治病的情景,认为我是有确见的,就远道来找我求医。我拨开他的眼眶看,只见眼球周围已经起了白膜,还杂有红血点。号脉时,左关弦滑,尺微细。我说,你这个病,起于阴虚肝郁,好在病时不长,若再延宕数月,就会出现翳膜,遮住眼球,那时候就不好治了。我开了“疏肝散”和“杞菊地黄汤”,嘱他先服“疏肝散”三四剂,可止痛;再服“地黄汤”近十剂,谅必好起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火酒洗眼,注意避风寒辛热,如果做到这些,就不必再跑这么远的路来求医了。
夏清就带着药辞谢去了。
半月之后,夏清又远道而来,一为眼病痊愈道谢,同时他还带着一个姓郭的人来看病。恰逢我遇事外出,一时不能回来,他们就回去了。从此再没有见过夏清。
祁相国之一
寿阳祁相国,退休后没回故里,就住在京城。相国素来有头晕病,发作起来,常常觉得天旋地转,几乎要跌翻在地。请过不少医家看视,都认为是虚症,因此相国就常服用参芪一类,未曾离口。但是病却缠绵不去。天阴多雨时节,病情会愈加严重。一天,下了一阵小雨,雨后相国就把我请去,谈到他的病情,问可有法子一治?我见他左寸独虚,右三部一概滑而且缓,就说,先生您这是劳心过度,脾湿停痰,时作时止,身重力疲,要得好转,非祛痰不可。古人讲,祛痰不从脾胃着想,就不是从根本上治疗。脾健则痰消,痰消您的眩晕病自然也就好了。这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我就用“六君子汤”加了“益智”、“泽泻”等,嘱相国服用,五服之后,即不再感到眩晕。
相国就设宴招待我,席间,相国对陪坐的人讲,因痰致晕,闻所未闻,起初润园这样说时,我还心存疑惑,吃了他的药,竟把我的多年老病给治好了,如果不是深明脉理,是不会有如此的见识的。我觉得相国过奖了。
祁相国之二
仲秋时节,听说相国又得了胳膊痛的病,先是让他的一个部下给看。相国给那人说到我看病的经过,并且把我治病的法子也告诉了他。那人于是就附会说,我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相国胳膊痛,原因不在别处,也是痰在作祟。还危言耸听地说,相国此病若不早医,必致瘫痪。就给相国开了“大秦芄汤”。相国吃了药,不但无益,反而病情更重起来,四肢曲伸都不方便。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就撇开部下,让他的儿子子禾来请我。我忙忙去了。相国的脉浮而弱,脸上总是出汗。然而谈锋甚健,神气清明。我给相国说,您这是胳膊受了风寒,小病一桩,您的部下言过其实了。也许他畏惧您,不得不说得重些。风在表皮,先生放心,三剂药后,必有改观。于是开了“东垣羌活胜湿汤”,加“威灵仙”、“苍术”各两钱。只吃了一副药,痛就减轻了;三副药后,就完全好了。第二天我和相国闲聊。相国认为我的受风寒之说是不错的。相国的书法很好,常有人带着宣纸前来索书,堆积盈案,来不及写,近日正好有闲,心情不错,就打开窗户写字,窗外多竹,听得风摇竹叶,飒飒有声,顿感有寒凉之意。晚上睡觉,就觉得胳膊痛起来,让你一说,我就想起这些细节来。但是为什么都用发汗药呢?我有些不大明白。听了相国的话,我说,先生操心事多,医术是小技艺,您因此没时间钻研,“羌活”、“蒿本”,都属疏散之药,并不是用来发汗的。
我后来在陕西任职时,相国还写信来,和我讨论这方面的学问。
祁相国之媳
相国的大儿媳妇,也就是子禾的妻子,性格暴烈。但是相国家法很严,家规也多,大儿媳妇于是就郁积成病,腹胀不适。月事竟然连着两次没有来。都以为她是怀孕了,也就没有理会。子禾正好没有子嗣,因此很高兴,买来保胎药让她服用,但是肚子胀得更厉害了。一天子禾趁公务之暇,邀请我去看看。病者脉象左关弦急,应属肝热郁血。我就让把“逍遥散”和“左金丸”配合着服用。子禾依然觉得妻子是怀孕了,只要不是保胎药,就不情愿吃。我说,肯定不是怀孕啊,两个月的孩子,肚子哪里会大成这样,放心吧,我也不会让真有身孕的妇人吃这个药。就勉强吃了两副。肚里没那么胀了,但月事还是迟迟不来。又加了“味乌药汤”,月事就来了。
子禾虽然没有得到子嗣,从此对我却很是信任,家里无论谁有病,都请我去看。
王丹文之母
我的本家王丹文的母亲,夏天的时候,染上了疫症,断续几个月都不见好,前后找了不少大夫看,病是渐渐轻松了,但是苦于头痛发热,心里烦躁不宁。加上丹文的母亲性情不稳定,躁急,一时服药,一时又不情愿服了,不管亲邻怎么相劝她也不肯。一天,老人头痛难忍,丹文就特意把我接去,让我好好给看看。因是本家的原因,老人呼我侄子,我也称呼老人伯母。脾气犟得很,我开导再三,才答应服药。老伯母脉相沉数,肝部涩,左寸微。我对丹文说,这是血虚肝郁的病。若滋阴润血,可治发热,而且“乙癸同源”,血润之后,肝也必舒。就开了“归芍地黄汤”,另加“薄荷”、“山栀”用来清火解郁。二天后,丹文来我家,说老人的病情已大见改观,不发热,也不再呼痛,只是脾气依旧,又不好好服药了。我觉得老人的病已无大碍,她既不愿服药,就随她吧。
李友兰
我的同年李友兰,也颇精医道,辛亥年在会馆闲住,得了痛症。或手或脚,或头或腹,或腰或胁,发作起来没有个定时,也没有个固定的痛处。自以为是痹病,先用“续命汤”来治,无效;又以为是伤寒,换服“麻黄汤”,也没有效果。一天和我闲聊,对我说,他的病怎么如此难以捉摸。我说让我看看吧。他的脉相缓而且滞。我断言说,你这个病因在于湿痰流注。我正说着,友兰忽然打断我,不让我再说,他说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让我破题即可,下文由他来做。我们相互一笑就告别了。过了几天,友兰的病已好了许多。我问他服的什么药?友兰说,你我都属个中人,不必费神猜测,这样吧,你说说我所服何药。我说,不过是“二陈汤”加“苍术”、“姜黄”、“羌活”、“独活”罢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友兰就拿出方子给我看,上面种种,与我所述如出一辙,不差分毫,当时在座的还有几个人,对我们两个之间默契如此都甚表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