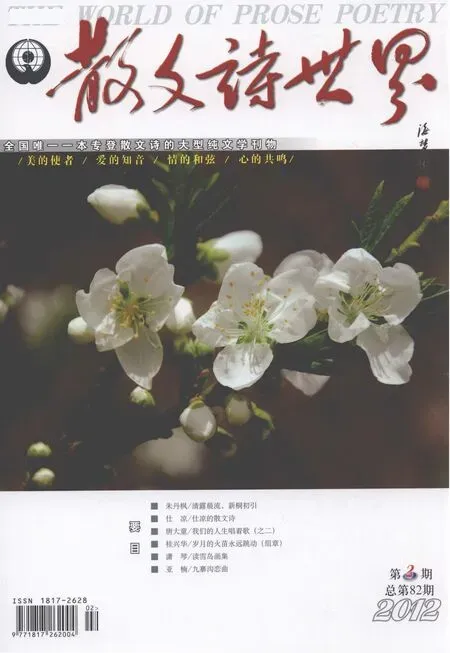牧 人 吟(节选)
安徽 许泽夫
遥远的记忆
每天晚上,我躲开尘世的喧嚣,将自己蜷缩在遥远的记忆里。
童年的足印,跟在牛蹄的后面,一天天长大。我所放牧过的耕牛,一头又一头,首尾相衔走进我的诗行。
它们是我的学生,我用手中的竹鞭,指引它们行进。
它们是我的伙伴,朝夕相处不离不弃,用一次次莽撞填实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它们更是我的父兄,木讷地干着地里最重的活,有捆草有口水就够了。
可我未曾给它们削过一支牧笛。
未曾给它们挂过一只牛铃。
甚至,未曾给它们编过一束花环套在脖子上……
那么些年,我居然想都没想过这些,真的没想过,哪怕其中一件。
突然有一天想起,就天天想了。
骑在牛背上唱歌
时起时伏时弯时直的岭脊是无与伦比的大舞台,斯斯文文的老牛是我忠实的配角。
我清清嗓子,牛儿停住了啃草,抬起硕大的脑袋,进入了角色。
晚风是优质的麦克风,将我的歌声传播到丘陵的尽头,传到密不透风的稻田的深处。
骑在牛背上,我是星光大道上走动的歌手,从童年走到中年,从山里走出山外。
一钩月亮打出了追光,广袤的蛙声鼓动着节拍,萤火虫是我的粉丝,拎着灯笼大老远赶来捧场。
骑在牛背上唱歌,歌词是我的祖父传给我父亲的,我父亲又在牛背上传给了我。
老牛听我祖父唱过听我父亲唱过,又听到我唱,它听懂了,动情之处,长哞一声。
那一声长哞,穿透了时空,今天仍然不绝于耳。
那时我们相信
那时我们相信有飞天,云彩之上就是仙女居住的天堂。
那里我们相信有织女有牛郎,仲夏的夜空,银河两岸还遗落着一担箩筐。
那时我们相信有神奇的水牛,驮着一对童男童女在天河的浅水区晃悠。
我们相信那些神话,相信神话中那些情节——
相信我们牵着的牛就是牛郎的牛。
想着想着我们会将牛绳攥得更紧,或者挽在手上,我们相信稍一松手牛就会飞到天上,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被云雾缠绕。如果那样,家里的地谁来耕啊?
待我们脱了稚气,长出喉结,有一种莫名的暗流在心中涌动,我们盼着自己是那个幸运的牛郎,每天把牛牵到小河边羞涩地等待着……
牛有个好脾气
牛有个好脾气。
赤膊的汉子用鞭子抽它,它一声不吭;调皮的孩童在它的背上肆无忌惮,它一声不吭;
渴了,一声不吭;
饿了,一声不吭;
困了,一声不吭;
它只是一声不吭,忍受着,承受着,辛劳着。
牛的祖居地在河的那边,清清的水,绿绿的草,黄黄的稻,密密的林。高尔夫球场捂住了千亩良田,断了小路毁了石桥平了田埂,沃土不种作物,偏移栽进口的洋草。
牛一声不吭,从彼岸退回此此岸。
挖掘机进逼过来,灌浆的晚稻半熟的柿树被按倒,石子扑上去水泥压上去,搅成了混凝土,蚯蚓再也拱不动,高粱再也扎不下根来。
牛一声不吭,从此岸退回村头。
一张GDP的蓝色图纸又将村庄圈住……
牛啊,这次退回哪里?我不知道,我已在一个没有星光的凌晨走出小村,挤上南下的列车。
牛啊,这时该退在哪里?我想也想不出,我想也不敢想。我在心中一隅,为它腾出一间牛舍。
诗意的夜
黑鸟的翅膀遮住了日头,天暗下去了,村庄模糊一片,小河只听其声不见其形,地垄看不清了,地沟也看不清了。
父亲歇下犁,兴犹未尽,他拍拍牛的大脑袋,牵它上了芳草萋萋的岭上。
牛埋头勤奋地吃草,囫囵吞了下去。
父亲困了,上下眼皮打架,梦乡在呼唤他,但他不敢睡着。
父亲掏出纸烟,点着一次性打火机,火光照着他满脸沧桑,牛抬起头,久别重逢似地望着他,直到火光暗去。
烟火明明灭灭,像一只伏住不动的萤火虫。引领无数只萤火虫或从山垭,或从天的尽头,一只萤火虫,接着是两只、三只、一百只、一千只……提着小灯,起起伏伏地赶来,漫山遍野地赶来,像赶超市。
父亲胸中涌动着一股激情,他想作诗,咳了口嗓子,没诵出来。
他望着家的方向,村头,那盏油灯将回家的路照彻。
六头牛
一头。两头。三头。
四头。五头。六头。
我经常这么数着,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更多是在铺开诗笺的时候。
六头牛,六个粗大的黑点,组成了一个省略号。
我的童年和少年,被六头牛填实,漫长的岁月被一个标点符号概括。
那是我牧过草饮过水的六头牛,它们排成队,从春排到冬,从我的童年排到少年。
它们不向往也不嫉妒富贵。
它们不回避也不嫌弃贫穷。
只有青草只有永无休止的耕耘。
只有缰绳只有没轻没重的鞭打。
只有沉默只有日复一日的承受。
六头牛,甩着尾巴,低垂着眼帘,渐行渐远,黑色的身影悠悠地消失于记忆深处,但那一串串牛铃,仍在叮当叮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