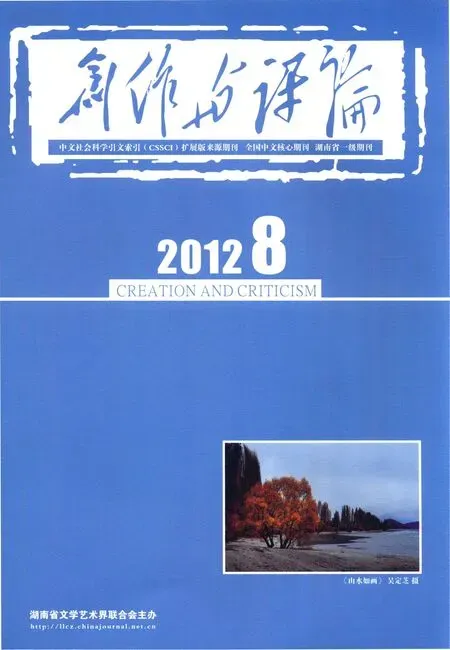轻俏时代的文学忧伤*——李佩甫小说的叙事伦理分析
■甘浩
在这个轻俏的文学时代,李佩甫显得有点“笨拙”——十余年来,他的题材选择、作品的主题意向、文学的写作技法,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只是更加精熟。这是一种值得敬重的“笨拙”。近20余年,现代汉语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文学的桎梏,步态轻盈,姿态曼妙,然而许多作家作品大多似流沙上的脚印,难以久存。李佩甫因为“笨拙”,却在现代汉语文学的大地上夯下了一柱铸石。少变的题材选择、主题意蕴取向,却使他通过小说叙事,与叙事对象建立了忠诚、悲悯、犹疑等叙事伦理关系。这三种叙事伦理关系对形成李佩甫的文学风格,使其成为当代文坛特殊的“这一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忠诚
从呼家堡(《羊的门》),到上梁村(《城的门》),再到无梁村(《生命册》),李佩甫小说的地域名称不同,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空间变化。它们作为文学转喻符号,最终都指向辽远的、一马平川的黄淮平原的一隅。这一隅在历史上战乱不断,灾难频发,是绵延了三千余年人类生命的一块“绵羊地”。就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这一隅是李佩甫在当代文学建立的只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虽然李佩甫没有用一个专有名词对之命名,但是,它已经巍然伫立在当代文学的地理图志上。
这个文学地理图标是李佩甫依靠毅力与忠诚,一笔一划,兢兢业业地营建起来的。这种忠诚首先意味着一种情感品质,它源自于对叙事对象真切、深沉的体味,然后才能够从心底对之产生珍视、尊敬的情愫。这种叙事伦理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往往是一种经验性写作。王安忆亦如是论述李佩甫的小说创作,她还说,“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宝贵的特质是生活经验,这是不可多得,不可复制,也不可传授的写作。”①而李佩甫的意义既在于此,又不是仅仅把生活经验参杂在小说叙事中那么简单。在当下文坛,李佩甫对乡土题材的痴迷度非同一般,对乡土的感情也超过了许多作家。他很少在文学技法上求奇炫新,读其故事,人物与事件历历在目,充满朴素之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故事不排斥戏剧性的虚构,可是,即使最具有传奇性征的《羊的门》,仍然无法避免读者将之与著名的许昌南街村故事联结起来的结局。《城的灯》所演绎的冯家昌及其家族故事,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生命册》比上两部作品更加靠近生活本身。主人公骆驼的传奇只是其中一个叙事线索,在他之外,李佩甫把大量笔墨皴染到老姑父、梁五方、虫嫂、老杜、春才等“绵羊地”人身上,讲述他们的生存智慧与人生悲剧。凭借对这片土地无比纯洁的忠诚,李佩甫切入到当代生活的深层结构,揭示了挣扎于其中的“绵羊地”人无法逃避的生存悲剧。
作为一种文学叙事伦理,忠诚,又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可佩的情感品质,还是一种需要非凡毅力的文学行为。它需要以近似于老牛反刍般的文学行动,不断地取材相近题材,选择相近主题,来夯实自己文学领地的边界。《羊的门》出版后,很多读者不约而同地从官场小说的视角剖析该小说的价值。回首看来,这种归类,严重误导了读者的阅读走向,因此也忽视了作品真正的价值。因为,这部小说表层的官场故事尽管精彩纷呈,但是,小说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却是呼家堡故事。在这个故事套层,诡谲多变的官场叙事基本上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呼家堡的人生百态,尤其是在沉重的生存压迫下的精神样态,让人瞠目结舌。到了《城的门》、《生命册》等作品,呼家堡变名为上梁村、无梁村,但都是讲述生存在“绵羊地”上的人们的故事,演绎着他们的婚姻、爱情、家庭故事以及为了卑贱的活下去而苦熬苦挨的人生。在种种故事讲述中,李佩甫明显是有意采用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时间序列中呈现小说故事。不管时态如何变化,“绵羊地”人在两个时间序列中的人生境遇没有实质性变化,他们的灵魂在这块土地上被逐渐异化的结果也没有变化。环境决定人,生他养他的土地,决定了“绵羊地”人的生存哲学、道路选择与人生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他们有相近的人生故事与生命样态。
近似的小说题材与主题,不意味着李佩甫的小说味同嚼蜡,反而因为作者忠诚于固定的叙事伦理纬度,小说因此在特定题材与特定主题上开掘更精深,给读者也更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忠诚的叙事伦理,也影响到小说的人物塑造。李佩甫小说人物千变万化,不过其中有三个人物类型让人印象深刻:村支书,老姑父,容易受伤的善良女性。在很多人看来,类型化几乎就是简单化的同义词。事实并非如此,类型化只是人物塑造方式的一种,与表意的深浅无关,类型化的人物也可以表现深刻的文本意蕴。在中国古典叙事传统中,成功的类型化人物形象比比皆是。当作家集中于一点形塑一个人物时,往往能够于雷霆一击中正中人心、人性或社会的要害,彰显出极大或极深的社会隐喻。李佩甫显然深解其中三味。在当下的文坛中,没有一位作家像李佩甫那样,如此出色地给予我们这样一些人物:他们不管是中心人物,还是边缘人物,其各自的言谈和意识都是如此绝对地前后一致,彼此却又有如此强烈地不同。在诸多小说中,李佩甫不断塑造这些类型人物,不仅描画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更重要地是让他们走上前台,带上各自的社会、文化信息,以供作家、读者做出自己的评价。
当然,忠诚是不能单纯依靠相近的文学题材、主题与相似的人物形象获取的。如果只是这样,当代文坛上很多作家都可以获得此等赞誉。而在笔者看来,真正具备“忠诚”品质的作家并不多,赵树理算一个,李佩甫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赵树理的历史价值之一,即是他通过小说叙事实践,不断地把婚姻问题、干部问题等阻碍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昭示出来,以期取得社会变革的进步与改善国民劣根性。李佩甫自然不是企望成为赵树理那样的社会改革家,他关注的是“绵羊地”人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命运与精神异化的过程。李佩甫正是在不断地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来描述“绵羊地”人特殊的生命感觉,表达他们特定境遇下的道德意志与伦理诉求,从而在现代汉语文学中建构了一个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志学小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李佩甫创作的最重要的意义。
二、悲悯
阅读李佩甫的小说,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李佩甫的影子。这个影子,被韦恩·布斯称之为“隐含作家”,是作家在创作时采取的特定立场、观点、态度在具体文本构成的“第二自我”,包含着作家的情感兴寄、价值取向和审美旨趣。②
泄漏李佩甫“隐含作家”身份的,是在他的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叙述动作“讲述”。我们很容易能够从李佩甫的小说中找到明显的“讲述”故事的痕迹。譬如其新作《生命册》,共十二章,每一章的开端句都是模拟小说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对话,如第二章开端句“该给你说一说过去的事了”,第三章“你知道什么是‘枪手’吗”,第四章“我要说,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你信吗?”……在建立虚拟的对话关系后,叙述者开始向虚拟的听众“你”“讲述”故事。作为一种叙述行为,“讲述”是对往事的回顾、咀嚼和回味,叙事对象经过了作家的心理过滤,自然就渗透了作家的主观情志。换句话说,作家的主观情志移情到叙述对象身上,就在二者之间建构了特殊的叙事伦理关系。
对于作家来说,在不同的作品中往往面对着不同的叙事对象,其主观情志因为种种姻缘汇聚,也会发生变化。李佩甫的特殊性,在于其叙事对象少变,其对“绵羊地”情感亦少变,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隐含作家与叙事对象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表现为作家呈示叙事对象故事时大都持悲悯的心态。
悲悯,是一种高贵的人类情感,它源自于人类对人间苦难感同身受的情感,因为感同身受,就会对身处苦难中的他人产生深深的同情与怜悯。同时,这里的同情与怜悯不是可怜,且并不轻视苦难承受者,它折射出一种博大的爱。李佩甫与其叙述对象之间就建立了此种性质的情感关系。
同样以《生命册》为例。李佩甫的这部新作的构思颇具新意,全书十二章,奇数章是骆驼的故事,指向现实,偶数章是无梁村故事,指向历史。两个时间维度的故事在外层上除了叙述人“我”之外,没有情节上的密切联系,这似乎不合乎长篇小说对于整体性的艺术要求。再从内部结构看,小说的主体故事主要讲述骆驼的奋斗史与毁灭史,是一个流畅完整的故事;而偶数章基本上是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分别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老姑父等多人的故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每部分都能够独立成章,且都是难得的小说精品,但是,组合在一块,似乎更加加重了这部作品缺乏完整统一性的错觉。如果仅仅从故事逻辑线索分析,这部长篇小说确实让人费解。然而,如果我们通过小说叙事,推导、建构作家在该部作品中的“第二自我”,就会发现,小说“隐含作家”的形象始终是统一的——他无时无刻不在以悲悯的目光关注着笔下的人群。不管疯狂如骆驼,还是卑贱如虫嫂,人生的轨迹与结局,都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生活如同炼狱,每个人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必然在这个炼狱中承受地火的煎熬,且无可奈何,无可逃遁,他们的悲剧不是个别人的,而是弥漫在这片大地上的生存悲剧。李佩甫关注的不是故事逻辑的统一性,而是深层结构上的小说意义的统一性。
人们一般习惯于以现实的生活法则度量虚构的小说故事与小说人物。当读者如是做的时候,就很难接受李佩甫小说中的呼天成、冯家昌等人物。李佩甫在讲述呼天成们的故事时,即遵循的是小说本身的叙事伦理。不过,任何文学创作都不是存放在象牙塔中,它最终还是要面对读者大众,要承受世俗道德的考量。李佩甫成功度过这个道德危机的依仗,就是他与叙事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悲悯叙事伦理。
佛家说,真正的仁爱不是对好众生的慈爱,而是对恶众生的悲悯。这是李佩甫能够与大众道德达成和解的根本。就大众道德来看,呼天成把一生中唯一钟爱的女人当作打击对手、战胜自身弱点的工具,是大无情;对垂死的母亲的行为,是大不孝,这都违背了人间最基本的人伦。李佩甫对类似行为浓墨渲染,为人物性格增色颇多,又从深层次上揭示出这个“东方教父”在为集体呕心沥血的同时,抛弃掉亲情、爱情,其本性已经完全被异化,这对于任何个体来说,都是十分可悲的事情。冯家昌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陈世美形象,他攀龙附凤,忘恩负义,在精神上永远都是一个侏儒,永远要承受来自灵魂的拷问,所以,不管他身居何等高位,都是一个可悲的形象。李佩甫悲悯的目光,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传奇人生,而是他们形成传奇时的付出。悲悯,加大了李佩甫小说的情感力度与浓度,透视到了故事背部隐秘的内容,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质量。
三、犹疑
若因为“悲悯”,就以为李佩甫在其叙事对象面前建立了高高在上的伦理姿态,那就误读了李佩甫。不幸的是,这种误读很容易滋生。滋生的原因,倒不是读者都能够捕捉到李佩甫在其小说文本中建构了悲悯的叙事伦理关系,而是来自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文本标记——小说题记。如:
《羊的门》题记之一:“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羔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摘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城的灯》题记之一:“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进得去。(摘自《新约·启示录》)”
对李佩甫小说的这种题记,有很多解读,一个可探寻的路径,是将其与作家的叙事姿态(即叙事伦理)联系起来。这种题记出自《圣经》,是圣言,自然是高高在上的教训语气与姿态。而且,在已有的论述中,李佩甫基本上采用了讲述的叙事方式,而“讲述”常常被看作是人类早期的叙事艺术,“讲述”故事的一般目的:一为愉悦,一为教谕。“教谕”的艺术目的,好像进一步坐实了李佩甫在其叙事对象面前建立了高高在上的叙事伦理关系。
事实上,李佩甫在其小说中叙事姿态很低。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他很少在作品中单面地批判某个人或某种行为,在表现情感兴寄、价值取向的时候,李佩甫甚至表现出犹疑不决。犹疑不决,是李佩甫在对叙事对象表达价值判断时显示的又一种叙事伦理关系。
譬如虫嫂(《生命册》),其名字就充满了悖论性。“虫嫂”不是她的真实名字,因为丈夫是残疾人,自己又近似一个侏儒,为了供养这个家庭,她常常偷集体的粮食,所以被人诬称为“虫”。在无梁村的道德体系中,“虫”意味着低贱,通常是对一些被人鄙视的人的蔑称。但是,长久以来,人们称其为“虫嫂”,“也不仅仅是蔑视,这里边还有宽容和同情。”当作品如是叙述时,就构成了对这个人物评判的第一个层面的犹疑。接着,故事继续下行,虫嫂不仅偷粮食,还偷人,因此引起众妇人的愤怒,她们把对男人的失望同时发泄到这个矮小的女人身上,使其受到残忍的处罚,其中的是非难辨,这构成了犹疑的第二个层面。最后,以泼墨的方式铺写她与三个儿女之间的关系,前述故事演示的虫嫂陋习,在众子女的恶行面前,全部得到了谅解,这构成了犹疑的第三个层面。纵观整个叙事过程,李佩甫都在以复杂的心态观察着虫嫂这一人物,有鄙薄,有钦佩;有嫌恶,亦有喜爱;有厌弃,又有同情。这种复杂的叙事伦理关系,在李佩甫笔下的许多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仅就《生命册》的人物塑造艺术看,李佩甫已经掌握了最困难的刻画人物的功夫:显露出他对所有人物,哪怕是最不敢苟同的人物有同情,同时又超然地与哪怕是他最喜爱的人物也保持距离。
需要指出的是,犹疑不会降低李佩甫的高度,也不会降低他小说的主题深度。因为李佩甫的犹疑不决源自于直接的生命体验。面对混杂多变的当代生活,任何一种道德体系都难以做出恰当的价值评判。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能直面生存实际,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取向。例如《城的灯》写道:“在平原的乡村,‘投降’几乎是一种艺术,还是一门很大的艺术。生与死是在无数次‘投降’中完成的。有时候,你不得不‘投降’,你必须‘投降’。有了这种‘投降’的形式,才会有活的内容。”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任何道德说教都是隔靴挠痒,无济于事,李佩甫面对这种现状,无能为力,只好以沉郁、忧伤的笔调,婉转吟唱这片土地上凄婉的歌谣。从艺术效果来说,不带教谕目的地讲述故事,可能意义更大。这颇符合刘小枫所说,“自由的叙事伦理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的多了。”③李佩甫就是在这个层面不断地讲述那片“绵羊地”的故事,虽然“笨拙”,却深得这片土地的生存真谛,因此,也没有被文学家虚幻的社会改革梦蒙蔽,从而能够真实准确地摹状“绵羊地”人的生存样貌,生动传神,而又意味深长。
注 释
①王安忆:《经验型写作》,《书城》2011年第7期。
②[美]韦恩·C·布斯著,付礼军译:《小说修辞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1987年版,第63-69页。
③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