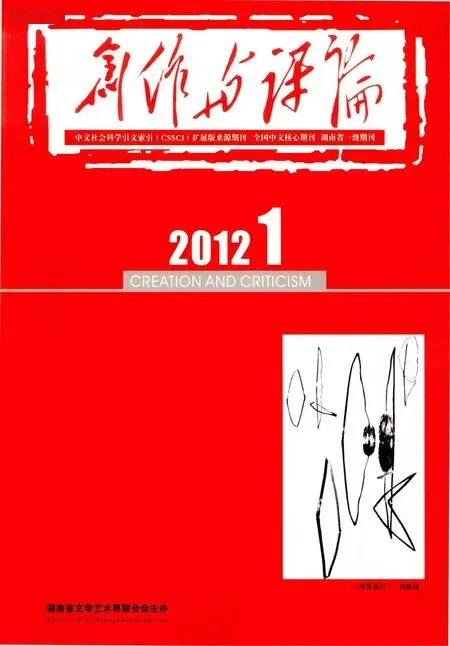悖论的力量:人生底色与理想耸拔——论小牛《割爱》的理想叙述
■ 龙扬志
情感婚恋作为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常写常新的写作题材,历来被小说家所喜爱。由于情感与人生、人性复杂纠缠,文学介入角度也千人千面。湖南作家小牛新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割爱》,以文人墨客为主角,以情感婚恋为主线,这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小说元素,探讨的却是极其严肃的理想问题。选择文人这个在当下语境中颇多丰富含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并从情感角度来切入,自然要承担一些风险,它们既有来自作家观念的,也有来自小说叙述的,但是小牛提供的这个具有底层叙述意味的文本,通过巧妙的叙事方式依次展开,借助特定历史背景与当下拉开距离,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诗性超越效果。小牛多年前就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加上他长期任职于基层文艺单位,在耳濡目染中进一步获得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积累,现在,《割爱》作为厚积薄发的一个慷慨奖赏,先后被湖南省作协、中国作协定为2011年重点扶持作品,也在所有熟悉他的读者意料之中。
小说《割爱》中,魏真这个被作家倾注了很多理想色彩的形象,一直在情感生活的道路上苦苦挣扎,在经历接连不断的旧恨新愁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与昔日梦中情人白云结成了夫妻。当然,如果仅是这样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故事本身就沦为对世俗生活的简单描摹和复写,无所谓对平常生活的超越了。并非我对小说人物命运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期待,而是主人公为了维护这份近乎神圣的感情所做出的自我牺牲击中了我,并且正是这种渗透着悖论色彩的小说逻辑,将一个简单、具体的个人性格问题上升到一个复杂、抽象的哲学问题。
和作者以前的小说一样,《割爱》书写的还是小地方和小人物,只不过他将视角调得更为深远,那个决定人物存在的模糊背景,连同存在本身,被赋予了与人物相当的重要性得到表述。这或许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所得即所见到探询生活内部奥秘,他懂得如何以文字的方式对身边这个世界提出疑问。很明显,这种疑问是以对确定性的颠覆来体现的。确定性一方面代表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在固定的逻辑中体现出来的僵化,虽然它是如此地被习惯谨小慎微的我们所珍爱,以至于付出极大的代价也要维护它,但是在艺术叙述中,它确实严重地损伤了我们对于多样性的想象能力和承受能力。从书名开始,小说就渗透了一种明显的悖论色彩,与其说它是诗意的,不如说是残酷的。“割爱”意味着对现时的无奈与失望,因此当魏真随着人生轨迹的推移向前走时,他也是一步步退回到自己的过去,其原点就是一直存留在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想象,当无处可退时,“割爱”就从象征意义退回到了物理意义。当然,也正是残酷的自我阉割促成了人物的人性和小说的诗性升华。
悖论之外,在魏真的潜意识世界里,对于情感对象的想象恰恰是一个综合体,“美丽”无比的。因为这些想象建立在人自身经验的审美极限基础之上,当它们混和而组成一个叫做理想的东西时,现实注定相形见绌。作为理想情人的最初模本,魏真是在孩童时代建立起来的,一部叫《洛神》的电影,“美丽无比的洛神在魏真幼小的心里就像太阳一样灿烂”。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洛神的形象无数次闯入魏真的梦里,“直到长大成人了才意识到,正是洛神在他幼嫩的心灵里催长了一种美丽而朦胧的早恋情结呢。虽然这种早恋情结并未导致魏真的任何早恋行为,但成年后的魏真已不知不觉将这份色彩动人的情结和满心涌动的浪漫诗绪糅合到了一起,然后渗入到自己对女性的审美目光中了。”可以说,牢固建立在魏真早期心灵中的美丽镜像,成为了他日后选择异性的一个潜意识标准,这种理想主义式的追求为他坎坷的情路历程增加了一个难以删改的注脚。
童年镜像与现实遭遇之间的反差构成了魏真精神世界中的紧张关系,阴差阳错地与王珍结婚,看起来魏真的情感状态已经获得了一种确定性。然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具备婚姻本身所需要的感情基础,是王珍处心积虑运用自己的“性感”而促成的结果,这决定了王珍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一方面缺乏自己的独立人格,她必须通过为人所不齿的方式去敲打,以此去确证婚姻的稳固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她要在魏真面前树立一种优越感,弥补自己在追求魏真时的自尊消耗。凡此种种行为,在魏真看来,都是个人“层次不高”的体现,尤其是因王珍失误而失去他们的孩子之后,那根紧绷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妥协之弦也就宣告断裂。正是这种潜藏在魏真心灵深处的动机,构成了小说的逻辑。
小说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冲突,是作为存在的复杂性而出现的。现实逻辑含混,并受外界所制约,恰如命运的轨迹一样,是综合了多重外部影响力的结果。魏真的生命中一共有6个女性在其情感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根据现实逻辑,他可以与任何一个女人白头到老,以非常现实的方式而不是小说的方式讲述完一个男人的故事。所以,小说最不符合现实的逻辑是,为了个人童年镜像的实现,在白云生理机能受损之后,魏真也主动去找鲁医生把自己剦割,彻底去掉自己作为男人的根本性欲望。在努力说服鲁医生夫妇之后,魏真因为自己完成对现实逻辑的颠覆而倍感轻松:
魏真迈着坚定雄健的步子向妇科检查台走去。他脑子里突然就冒出那位穿着火红铁靴昂首阔步的大侠形象。
手术顺利而成功。这本来就是非常容易的小手术。当魏真在鲁医生夫妇崇敬的目送下离开“新世纪医院”时,他的唯一感觉就是浑身轻松。至此,爱上洛神不再仅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他采用一种堪称悲壮的行动去实践,近乎殉道者的选择,乃是为实现个人理想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因为在白云奋不顾身地跳入湖中救他而身染疾病之后,魏真认为肉身是沉重的,由此生出的欲望也是沉重的,如果不把这些人性的沉疴抛弃,追逐飞翔的洛神注定只是一个空想。
米兰·昆德拉曾经反复阐述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在昆德拉眼里,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是由迷和悖论组成,一个有才智的小说家,正是要把一切肯定变成疑问。疑问作为存在的方式,表明了一个作家对现实的深入程度。现实对于小说家来说应该是一个不确定性丛生的世界,而依靠想象力这个得力工具,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实性的枷锁。在《割爱》这部小说中,“摆脱”是两方面的,它既可以指小说外部的结构方式,也能指代小说故事中人物的个人命运,两者统一起来,逃离了读者对于小说阅读期待的习惯性控制,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审美接受冲击。
当然,归根到底,“摆脱”的冲动来源于小说家对于理想的一种捍卫。小说世界在存在域中仅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它是否真正能够成为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总结反而并不重要。事实上,生活本身无法用二分法来进行简单概括,存在是和历史紧密关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生活既不是白,也不是黑,用小说中的一种说法,是灰色的。小说的背景集中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中,中国处在一个经济转换的时期,大多数人面临着一个心态的调整问题,铁饭碗被砸破,几乎是每个人都经历着英雄叙事向平民叙事的过渡,比如鲁医生因为医疗事故之后主动辞职办个体医院,祁红脱离文化馆自立门户开办艺术班,都可以视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典型症候。因此,灰色成为一种混和色彩,是生活的常态。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是受用的,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则很危险。写诗的邢之远给诗歌爱好者魏真送了一幅书法:“在无边的灰色中耸拔”,勉励之意,不言自明。
诗歌与诗人作为这篇小说里的一个象征代码,被嵌入了丰富的含义,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产生寻找诗意反讽的冲动,不过正好相反,小牛通过诗歌给魏真加冕一顶崇高的帽子,不难发现,所谓诗歌和诗人,在这里亦只是一个符号,它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来加以取代。然而,恰恰是诗写得比魏真好的邢之远,借助他自己的文学才能敲开了向世俗攫取个人利益的大门。与魏真不一样的是,邢之远是一个把诗歌和生活分得很清楚的“清醒者”,他以导师的身分告诫魏,生活跟诗是有区别的,“要是像写诗一样的去生活,肯定会将生活弄成一锅粥了。”在邢之远看来,诗歌只是一个用来改变生活的工具,他在北京读作家班时搭上地委组织部长之后,他向魏真表白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我不是个钻营功利的人,也不是个拒绝功利的人。”去地区卫生局当副科长的机会来临,他毫不犹豫地弃鱼而取熊掌;魏真则放弃财委的工作,即使没有职位,也以办事员的身份去了“清水衙门”文联,为的就是“自己从此算得个专业诗人了”。邢之远走上仕途之后春风得意,向魏真宣扬欲望对于人的“能动性”作用,与以前的人生哲学相比较,已经是“举着欲望出发”。最后,这个以欲望为人生第一要义的邢之远,仅仅是为了报复祁红对他的“高傲”,在祁红有求于他时以手中的权力再次无耻地兑取了祁红和魏真的尊严,魏真终于喊出了内心对于邢之远的鄙视。因此,小牛要表明的是,诗歌或其他形而上追求尽管可以作为一种爱好或者一种思想的依托,但它本身并不是保持“耸拔”的可靠支撑。
在我看来,小说的深刻正体现在这里,作者借助一个诗人在爱情与婚姻、欲望与肉体之间的悖论性纠葛,是要表达出对于人的理想与命运的一种反省。也就是说,在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中,灰色调无疑是一种最习见的生活状态,如何使浓厚的灰色调不至于完全掩盖人性中那些“正极性”的东西,并且对其保持一种朴素的敬畏之心,无疑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如果说魏真在最后那一刻完成的自我阉割是一个非凡的举措,其实在他与其他女性的交往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种对于他人幸福的考虑。比如他对小月的感情,本来有机会给小月“上保险”,但他始终没有那么做。也就是说,魏真对于小月的关爱不是以纯粹的占有为目的的,即使小月后来喜欢上了乖乖虎,愿意以自己的第一次来作为对魏真的回报,魏真仍然表现出一种宽容来拒绝这种“好处”,在关键时刻实现了对自我人性的救赎。
如果对灰色的人生进行一些额外的延伸,我们就会发现王珍其实是一个彻底被灰色所毁灭的人物,当然这个“层次不高”的女性形象值得我们同情:作为一个女人,王珍有权力追求自己喜欢的人,虽然她有着令人难以接受的缺点,但是从她的角度来说,她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对个人幸福维护的结果。假如跳出同情的维度,她的结局又是自我造成的,从这场婚姻开始那一刻起,她就不可避免地滑入了自我人格缺陷的深渊。面对危机,王珍没有从自己身上努力去寻找灰色的突破口,因此她注定要被灰色所围困,找不到出路。可以说,王珍所面临的悖谬困境超出了她个人命运的内涵,被抹上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寓言色彩。
作为一部反映存在之思的小说,小牛至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被欲望统摄的消费社会,很多人正是因为无法“割爱”而走向了沦落,我们如何去追寻一种“耸拔”的精神姿态,从而使自己免于欲望所消费,确实是摆在所有人面前一个理想与道德的难题。作者尝试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解决之道,《割爱》最终呈现出一些乌托邦色彩,仍然不失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理想主义抱负,激发人们追求理想的意愿,提升求善求美的能力,人性弱点就有克服的可能。
《割爱》以过去时光为底色,作者放弃“新奇”、“时尚”的表达手法,决绝地回到过去,回到我们曾经走过的时代内核之中,读来别有一种重温历史的温馨感觉,记忆唤醒和未来思考有时就这样奇妙地结合起来。从题材处理方法的角度说,正是弥漫于文本内外那种恰到好处的“陈旧”,体现了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悖论:存在,并不就是合理的;存在的本质,在于它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