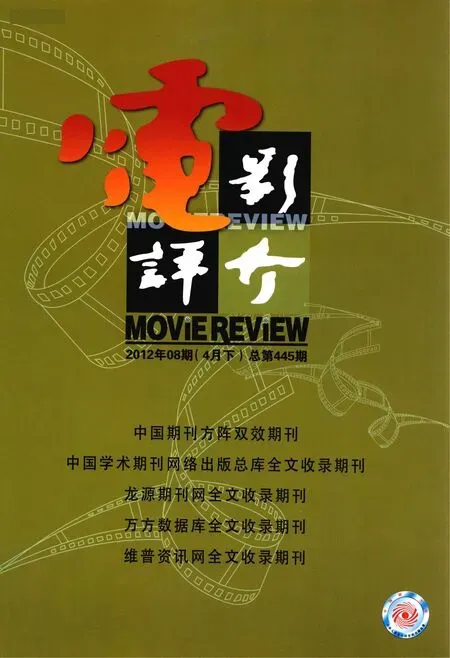对电影《白色婚礼》中“潜意识”行为的解读
(一)
法国影片《白色婚礼》是一部颇有争议的艺术片,1990年获法国凯撒奖最佳女主角。导演克劳德的镜头调和了最佳的光、影、色,以最好的角度展现了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每一个镜头都有如一幅画卷,看似随意却又是精雕细琢。
故事发生在法国一个小镇里,已经年近五旬的哲学老师弗朗索瓦和他的妻子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一个17岁少女的出现打破了他中规中矩的生活秩序,她就是弗朗索瓦班里的女学生马蒂尔。17岁的马蒂尔脸色苍白到透明,在她那洁白可人的小脸上,很难想象她有过吸毒卖淫的混乱生活。47岁的哲学老师脸色深沉,不苟言笑,你很难从他的脸上读出他是爱生活,还是恨生活。对学习的不屑一顾、对日常生活的庸碌,让马蒂尔成为学校老师的众矢之的,而只有弗朗索瓦认为她拥有非凡的天资和聪慧。他们接触的越多,他就越发现这个女孩子对人生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苍凉的理解。她总是带着轻蔑和嘲讽的眼神看他,她的灵气直逼弗朗索瓦内心深处那最脆弱的地方。
爱情总是让人向往和痴迷。当人们陶醉在美好的爱情里时,导演把镜头切换到弗朗索瓦的家。弗朗索瓦的妻子在小镇经营一间书店,每日工作繁忙,但也不乏温柔贤惠。不知从何时起,妻子总是接到不出声音的电话,有时在夜晚,有时在清晨,妻子体贴的询问,弗朗索瓦却像孩子一样在妻子面前任性的蛮横。
其实这时的弗朗索瓦也在挣扎,他究竟做什么选择才是正确的?抛弃妻子吗?这么做连他自己都会厌恶自己。远离马蒂尔吗?办不到啊。他抗拒不了马蒂尔笑容里的诱惑,抗拒不了马蒂尔独特的才思。他打开窗,伸出手,迎接马蒂尔年轻的身体,给了她美好的希望。然而他又一再对马蒂尔说,你才17,别人会怎么想?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我们靠什么生活?爱情吗?马蒂尔抬起脸说,你可以搬过来和我住,或者我们一起出去租房子。我可以扮你的女儿。我可以躲起来,谁也不会看见我,没人会知道我的存在。女孩已经近乎迷狂,只要能占有他,她可以做任何事情。
弗朗索瓦像所有被击中虚弱处的中年男人,危机和怯懦并存。他退却了。她跟同龄男生公然调情,挑衅地演给他看,她像一只妖厉的吸血鬼,吸干了他的理智和忍耐。她在他身边,她温顺得像只猫,他没想到这么纯真的身体竟可迸发出这么邪恶的力量。马蒂尔的报复行动逐渐升级:骚扰电话闹得他家无宁日,砸碎他妻子的商店,甚至想置弗朗索瓦的妻子于死地——哪怕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错。
弗朗索瓦怒火冲天的奔到了学校,他像一头野兽一样把马蒂尔拉进一个空教室,他大声的质问,而面对他的严厉粗暴,她却以拥抱软化了他貌似坚强的外壳,他们的最后一次激情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被校方调到另外一个偏远的分校区任教,弗朗索瓦的妻子无法承受这一切,两个人分手。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结束了?抑或是可以有新的生活?
一天,弗朗索瓦意外接到警方的电话,马蒂尔自杀身亡。当弗朗索瓦走进他住所的街对面的一幢出租屋,了解到了一切。马蒂尔两个月前搬进此屋,过着隐居的生活,靠房东送来的食物维持日子,她每日都坐在窗前,看着对面的一间房子,注视着房子内的一切,那里正是他上课的教室。分离不是最终结果,只有死亡才是。她追随他到了异地,并自决于此,或许他永远不会知道她坐在那张孤独的椅子上每天目睹他进出的心情,但他看到墙上的一行字“弗朗索瓦,这里就是海洋”,她该是怎样的一种解脱和狂喜。
(二)
故事刚开始不久,马蒂尔回答老师弗朗索瓦关于潜意识的问题时,她站在讲台上说:“古典学派和伯格森认为,潜意识不存在。它可能是唤醒的被压抑的记忆的总和。我个人觉得拉辛的观点很独到,他说,人一旦内心充满激情,他的身体就会着了魔似的被那激情操纵。这股力量来自上帝,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上世纪末诞生了佛洛伊德,他以医学经验为基础来定义潜意识。潜意识是唤醒的被压抑的记忆的总和,并且有时会以某种(精神病)症状出现。我们都受制于我们未意识到的压力,例如:命运神经官能症。一些人是他们命运的俘虏。他们总是重复同样的经历,就好像他们命该如此。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这些人是他们潜意识的奴隶。弗洛伊德尝试医治非肉体因素引发的疾病。这些病人是,他们未意识到的压抑的思想和欲望的奴隶。而弗洛伊德将他们唤醒,病人就会意识到这些破损的记忆,并讨论它,于是病的症状就消失了。” 这段关于潜意识的独白可以被认为是导演对弗朗索瓦和马蒂尔这两个角色所有行为的诠释。
对于弗朗索瓦哲学教师的身份,我们看到其实他并不缺乏理性,或者可以说,正是他“理性的自信”使他在迷狂中自我放逐。意向性的性爱作为一种麻醉的迷狂,对弗朗索瓦内心深处的创伤起到了暂时的治愈效果。显然,此时的理性是无能的,因为迷狂表现出的巨大敏感性产生了一种切近事物本质的真实,这也正是理性的欲求,尼采的酒神精神也是迷狂的显现。本雅明对“迷狂”有过讨论的笔记和记录。他对此的洞见即“心甘情愿地醉心于迷狂的同时,又在激情之中要极力清楚地表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并且刻意地反对它。”[1]
而17岁的马蒂尔之所以孤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地方求学,背后的原因是:马蒂尔的妈妈是个为爱而疯的女人,无数次割腕自杀,最后一次终于成功。马蒂尔的爸爸是一个精神病医生,但却放弃了自己的家人,因为他医不好自己死去的心。马蒂尔十一岁时被两个哥哥拉下水吸毒、卖淫,之后两个哥哥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逃到印度,失去了联系。马蒂尔对这个世界一直保持着警惕的清醒和压抑的愤怒,她鄙视周围的一切人。直到她遇到了大她30岁的哲学老师,她才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温存。她的爱是近乎疯狂的,她不在乎世俗的喜好,当她与世界保持着一种超越的关系时,她的迷狂是不具破坏性的,犹如大麻造成的精神恍惚的经历是一种想象升华为体验的芬芳。然而,当她纠缠在俗世的纷纷扰扰中,她的迷狂就具有毁灭的破坏性。
如果认为马蒂尔对哲学老师家庭的破坏是她迷狂的一个极端表现,那么很多观影者会认为她最后的死亡是她迷狂的另一个极端——自残。也就是说,当她得不到她欲求的对象时,她就选择自我毁灭,以此报复弗朗索瓦,所以有人也把这部影片翻译为《甜蜜的复仇》。但是笔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关于影片的结尾,马蒂尔在可以看到弗朗索瓦上课的那个小房间里安静的死去是她报复性的自残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马蒂尔当时仍有占有欲,那么她应该去找他,他们也许还会在一起生活。然而,为什么马蒂尔选择默默的注视?而她又为什么会在墙上写下“弗朗索瓦,这里是海”?为什么选择死亡?香奈儿在自传里说:“成熟地太过迅速,终要吃些苦头,或者被磨折,或者被放逐。而后若大难不死,必将怒放。”而马蒂尔虽然中途夭折,但她已然成长。
笔者把马蒂尔的死归因于爱欲。正是爱欲让她来到弗朗索瓦的身边,让她只是默默的注视着,没有再走近他的生活;也是爱欲让她在狂喜后写下“弗朗索瓦,这里是海”,让她不再成为占有欲的奴隶,让她解脱,让她永远复活在弗朗索瓦的心里。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爱欲”?
(三)
柏拉图的《会饮》对爱欲有经典的论述。苏格拉底通过对狄俄提玛的忆述,借助严密的逻辑一步步向我们展示了爱欲的含义:爱欲不是神而是介于神人之间的精灵,它是波若斯(丰盈)和珀尼阿(贫乏)之子,它既不贫也不富,总是处于智慧和不明事理之间,是神和人之间的交通,它把人的祈求和献祭传达给神,将神的旨意和酬报告诉给人们。爱欲本身不是善和美,而是爱欲欲求自己永远拥有好的东西。但是这种爱欲所求的并非美,而是欲求在美之中孕育和生产,因为惟有这样,生命才可以延续,会死的才成为不死的。[2]也就是说,爱欲就是欲求不死。可以认为柏拉图所言的爱欲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活动。
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发展了柏拉图关于爱欲的观点,他认为爱欲是一种欲求,一种对不在场者的欲求,对不可欲求者的欲求。列维纳斯恢复了爱欲自身的伦理主体性地位,认为爱欲具有绝对性,爱欲并不力求消除“欲求”与所“欲求之物”的距离,它的本质在于保持这种距离。
笔者认为马蒂尔和弗朗索瓦最初对彼此的迷狂是一种意向性爱欲的体现。马蒂尔始终没有改变对弗朗索瓦的爱,但在经历了所有的事情之后,她对爱的表达方式却变得深沉。马蒂尔的离场和缺席使爱欲成为永远不可能完结的融合,这正是列维纳斯强调的爱欲。这种爱欲关系不是占有,也不是权利;不是斗争与融合的关系,也不是认知的关系。可以说这种爱欲是一种与他性、神秘性的关系;是与未来、与永远不能在场的在者的关系。
这种爱欲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毫无原因的侵入在我们的体验之中的实在。这正是马蒂尔的体验,这种体验的独特性在于“同时达到他和超越他;同时是需要和欲望;同时是色欲和超越”[3]。马蒂尔的死亡就是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所以马蒂尔在墙上写下:“弗朗索瓦,这里是海”。
注释
[1]郭军、曹雷雨 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2005年4月第5次印刷,第245页。
[3]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by A.Lingis.The Hague: Nijhoff,1979,p255.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