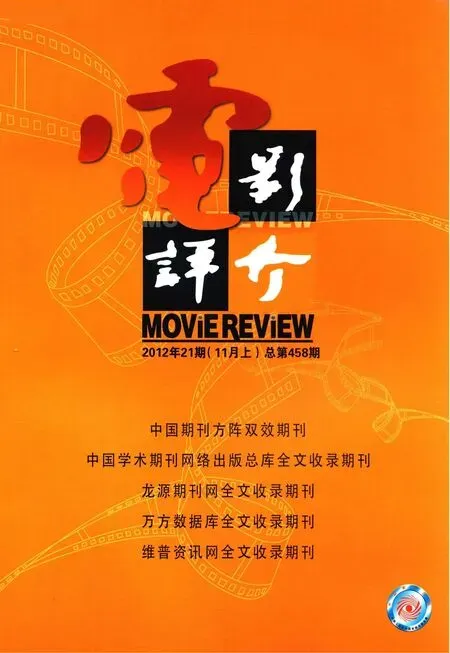古典名著电视剧改编中的情节叙事研究: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属于章回体明清小说,作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它是由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讲史”就是说书的艺人们讲述历代的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其中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往往令人印象深刻。但总体特点段落整齐,叙事清楚,仍然是以情节为叙事重心,并且由于属于世代累积性质的小说文本,所以在情节编织上注重加强史实与轶事间的联系,戏剧性地付诸于英雄人物身上,增强了叙事的连贯性和因果性,才使得整体看起来浑然一体,然而却未必无暇可挑。章回体小说前身“讲史话本”在艺人借助历史事件进行的说书演绎,因其段落式叙事客观时间限制和多英雄角色刻画,其中整体叙事的完整性也受到削弱,使得单章节情节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英雄形象的刻画凸显,人物叙事强于情节叙事。在章回体小说的成文过程中,虽然强调整体回归情节叙事,但受其基础影响,突显出现代叙事艺术问题讨论中的典型问题之争,即情节中心论与人物中心论的对立。[1]这就导致在影视改编过程中,具体影视样式的差异以及电视剧版本的不同都受此影响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侧重。
一、叙事重心的偏移
在原著母本的审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中都透露出独特并相似的时代气质和主旨志趣,这是跟作家生活的现实状况与思想环境分不开的。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为了适应作品主题对于历史原典的沿承和现实社会的观照,其叙事重心会随之发生偏移,创作手法的调整呈现出多样性,在以此为基础创作的各电视剧版本中从叙事主题到叙事风格、叙事策略和情节模式上都有所体现。
首先,文学作品的主题无非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二是作品本身所呈现出的客观意义。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有“乱世英雄颂歌说”、“道义说”、“儒家思想说”、“悲剧警示说”等,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有“游戏说”、“为英雄豪杰立传说”、“农民起义说”、“忠义说”、“悲剧警示说”、“忠奸斗争说”等,这些说法在作品中都能找到依据。但无论如何都不外乎三个层面的主题概括:一、塑造英雄;二、道德评判;三、伦理说教;四、警示千古。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都融进了对历史、政治、道德、军事、哲理等方面的思考,因此作品中呈现出的思想意蕴,即使是同一题材到了不同的创作者手中在二次创作时也会被赋予或侧重表达不同的思想主题。
从名著电视剧改编层面上看,艺术样式的改变使得电视剧明显削弱了原著主题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抹平历史跨度,更倾向于择取最具有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某一两个主题有针对性集中呈现。在靳青万《论电视剧<三国演义>对原著主题的理解与把握》文中给出过总结性评论:“作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的思想意蕴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并不否认其中包含的其他思想内容,但就起主要倾向来说,用‘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这16个字来概括《三国演义》的创作主旨,是符合这部作品的客观实际的”。[2]尽管在《水浒传》中充满强烈的侠义精神和反叛精神,但我们对于“水浒”故事的理解也一直都是“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官民二元对立模式,其中的侠义精神和反叛精神依然处于被动地位,惩恶扬善的主题思想被附着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和阶级对抗性,要既尊重原著、忠于原著又高于原著,融入二度创作的思想和智慧,即在电视剧创作中如何理解、把握并且选取舍恰当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原著以刘备集团为主干的“褒刘抑曹”的态度来断定和区分正邪,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也将有关刘备集团的战争和事迹用正面的叙事态度描写,照搬小说的笔调极力把刘备刻画成一个宽厚仁德之君,曹操集团则奸诈呈反面之貌,刻意地遵从原著的创作使得曹刘虽然对比明确但却有失客观、全面、生动。新版的《三国》中改变了这种先入为主被限定的正邪二元对立模式,叙事层面上较少地掺杂明显的历史评判,而将评判的空间留给观众,弱化了对于主题理解的政治意识导向,更利于带动观众的参与欲望。
叙事主题的转变与叙事风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维柯说过,人类有三个时期,即神话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黑格尔说,我们进入了市民社会。”[3]《三国演义》原著作为一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为人类描绘了维柯话语中的那个“英雄时期”,比较而言,1994版《三国演义》更忠实于原著宏大的史诗风格,也更好地还原了原著作者的显在创作动因——主观情绪情感的宣泄以及教化意识的宣扬,简单地从刘曹集团的褒贬倾向就一目了然,但对于史实的摹写却秉持一种较为严肃冷峻的态度,可概括为事大于人,完全正剧的风格使观众在欣赏时会产生“距离感”,不煽情也不戏说,观众无法用过于感性或游戏的心态进行观赏,这就增大了它所表现的情节、人物在时间空间上与观众的距离。新版《三国》虽然在风格定位上依旧为“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但由于很大程度上在英雄这个特殊群体保持英雄特性外更重在寻找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与生活,因此实际上英雄主义表达的比重被缩小。新版《三国》看似冷静客观地呈现历史,实则本质上照应了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喻言,冷静的表象背后是热忱的主观创作。新版的《水浒传》中更是增加了大量草莽英雄落草之前的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感纠纷,带上很多“戏说”的意味去多角度阐释草莽英雄的身世和内心世界,这种富有现代感的审美趣味消解掉了历史距离,也消解掉了英雄主义的崇高感与严肃感,叙事风格呈现出热情活泼的状态。也因此引发了“历史正剧”与“言情武打”等诸多观众点评的争议。
二、情节结构变化
任何叙事作品都必须符合一定的叙事逻辑制约。叙事主题的变化很大程度上缘自叙事序列的改变,根据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对于叙事序列的说法,基本序列互相结合产生复合序列,这些结合的实现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有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左右并连式等,[4]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三国》一书,有追本穷源之妙”,重点强调了其叙事逻辑中的因果关系,而在《水浒传》中也是如此。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第二回回前总评中说道:“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以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5]前因后果的关系是整个水浒故事的第一逻辑,其中单个英雄故事发展的逻辑仍然遵从这样的因果关系进行,但传统长篇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属于诸多有独立叙事结构的段落,通过并不十分紧凑的首尾相接组合而成,单个的英雄故事并列叠加在一起,逻辑紧密性显得松散。这种情况却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很高的自由度,自始至今影视剧中都有体现。
在以单个英雄原型或核心故事情节为基础素材进行影视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创作者根据原本存在的叙事逻辑衍生出属于自己的叙事逻辑,从而使得具体的故事内容被丰富化,情节线延长化,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扩大化等特点,这些以简化繁创作的“加法”原则,避开传统长篇小说中的横向的长度美和连续性,重新建构的故事具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短而精特点。
与篇幅较短内容含量少的电影及短篇电视剧不同的是,在创作长篇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时,则需要首先重视的就是电视剧情节的连续性。关于制约电视剧的“连续”究竟有多长的因素,首当其冲“应该是故事本体,是故事内容本身的长度。故事决定着故事叙述。这是最基本的,也是电视剧本体的一个属性,是电视剧故事叙述的一个结构问题、一个载体容纳性的问题”[6]。原著小说中充斥着林林总总的缺乏表现力的情节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背景介绍,其作用只服务于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并不需要完全照搬呈现在电视剧中,所以电视剧的改编在大的故事结构上采取的手法则是做“减法”,简化不必要的情节呈现,集中表现重点内容。如《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对于黄巾起义历史背景的具体呈现比重较大,着重刻画了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情形,还原了特殊的时代感。新版《三国》中开篇则采用直接旁白讲述的方式一笔带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在爆发后的第八个月,即告平息。”长篇电视剧在具体单个英雄故事的情节结构上也表现出明显的调整,在新版《水浒传》中多个英雄形象都增加了私人日常生活的描绘,比如林冲受难前与妻子的家居生活以及受难后对妻子日夜思念的情景,故事情节上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动,原著与1998版电视剧《水浒传》中重点展现的是林冲遭高俅陷害的始末,
新版《水浒传》在剧情比重上将林冲与妻子的日常生活的展现做了充分详致的刻画,反映出在不同版本的经典翻拍过程中创作者为求新异避免雷同有意省略掉观众熟知的情节的创作倾向。同时,情节结构上出现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依赖叙事线索的调整,如新版《三国》全剧以“董卓进京、曹操刺董”开篇,历经了“诸侯会盟伐董卓”、“貂蝉献身除国贼”、“群雄逐鹿夺徐州”、“官渡大战争北方”、“火烧赤壁定三分”、“三国鼎足各蓄力”、“夷陵之火蜀败亡”, 直至最后“诸葛司马争兵斗法”这一系列情节段落。除了将“三国”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情节主轴外,
本剧还设置了诸多精彩的副线,如在魏国内部设置了“曹氏诸子夺嫡之争”、“曹丕曹植和甄妃的爱情纠葛”、“曹氏与司马氏皇位之争”等副线;在蜀国内部设置了“关张对诸葛从不服到信任”、“荆州部将与川内旧臣从对立到同心”、“刘备与诸葛的战略分歧”等副线;在吴国内部设置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老将军对少壮派的成见”、“孙权与周瑜之间的和作与对抗”等副线。整个剧作冲突饱满,主副线索层次分明,笔力部署详略得当,体现了很高的结构技巧。如此情节结构调整,对整体叙事架构的完成提供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注释
[1]李胜利:《电视剧叙事情节》,2006年7月第1版,第60页。
[2]《 电视剧<三国演义>艺术评论集》,赵群主编,1996年7月第1版,第211页。
[3]《 电视剧<三国演义>艺术评论集》,赵群主编,1996年7月第1版,第119页。
[4]转引自《论<水浒传>的叙事逻辑》,王平,《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
[5]转引自《论<水浒传>的叙事逻辑》,王平,《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
[6]沈贻炜:《论电视剧的连续性》,《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