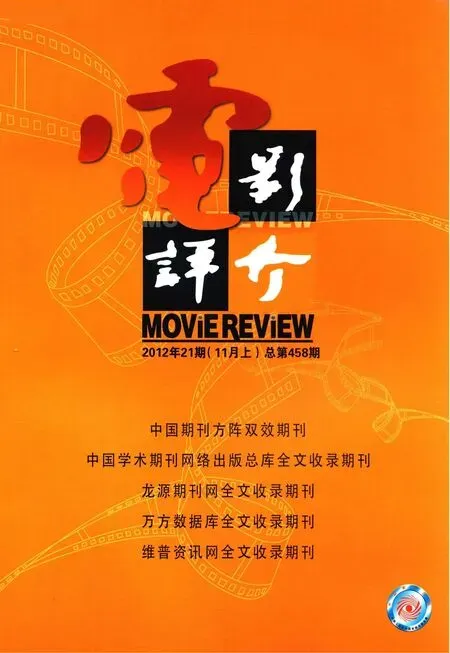浅析中国散文诗意电影的电影语言特点
“中国散文诗意电影”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诗电影,中国诗电影,散文化电影,散文诗式电影等一系列相关理论之上的。因为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对这类影片进行权威性统一性的定义,故本文将我国具有某一种美学特性的影片定义为“散文诗意电影”,即:在叙事上采用开放性姿态,摒弃传统叙事手法,不追求因果关系结构,淡化情节,弱化冲突;在结构上不以严密的时间序列为线索,多采用松散、自由的框架结构;在情绪表达上化外在的叙事张力为内在的心理张力,强调节奏感在剧情推进中的作用及情感的表意作用;在艺术风格上着重意境的渲染,多呈现出自然含蓄的诗意风格。在这一界定中,“散文”强调此类影片的叙事和结构特点,而“诗意”则旨在突出影片对意境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此类影片在美学上一个最为显著的特性即为强调情绪而非情节对影片的推动作用。
纵观我国电影史,从早期的《小城之春》、《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到八十年代的《城南旧事》、《边城》,再到九十年代的《那山 那人 那狗》、《我的父亲母亲》,直至近些年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香巴拉信使》等,都是散文诗意电影的代表之作。由此可见散文诗意电影是我国电影的一脉重要分支,其优良的传统和在当前的发展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
电影作为一种新兴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及综合艺术,拥有一套完整的符号表达系统,即电影语言。不同于诗歌、绘画、书法、音乐等传统艺术,这种语言同时诉诸于观者的视觉和听觉,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立体的观感经验。本文即从电影语言入手,探究散文诗意电影在视听语言上的风格化特点。
从某种角度来说,电影是用镜头来讲述故事的艺术。因此这里首先讨论的是散文诗意电影的画面特征。单就电影画面本身来说,它和我国传统艺术中的诗歌和绘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诗和画并不是两门孤立的艺术,相反,它们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散文诗意电影也可以说是天然的诗与画的融合。这一点直接的体现在此类电影的构图方式上。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有过这样的论述“美的形式之积极的作用是组织、集合、配置。一言蔽之,是构图。使片景孤境能织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无待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的更深一层的真实。”[1]正是以中国绘画这种独特的构图方式为美学根基,我们可以看到散文诗意电影多用镜头的摇移和长镜头来体现中国画长卷轴的构图方式,从而消解了蒙太奇式的主观切割,也使影片具有了一种气韵生动的幽远意境。
在影片《小城之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长卷式画面的灵活运用。整部影片是在一个横移镜头和俯瞰画面展现的颓废的城墙中开始的。不同于绘画,电影是由一系列画面构成的流动的整体,因此我国古典绘画中的这种散点透视和长卷式的构图方式表现在现代电影中,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摇移镜头和长镜头的运用。这样的镜头贯穿了影片的始终,甚至在人物对话中也采用了这种缓慢移动的镜头运动。如章志忱初到戴礼言家的那晚,随着镜头的摇移,我们依次看到了唱歌的戴秀,凝望周玉纹的章志忱,床上病怏怏的戴礼言,端药给戴礼言的周玉纹。这一个画面依次交待了全剧五个出场人物中主要的四个人物,并在镜头的移动中隐含了这四个人物的关系,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压抑与希望并存的复杂意境。
正是摇移镜头造成的这种类似古典长卷的绵延不绝的画面,精妙的传达出了散文诗意电影所追求的意境。一切景语皆情语。就是这种叙事上的间断成就了情绪上的连贯,从而使影片张弛有度,气韵生动。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电影画面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景别的运用上,而这自然也成为了散文诗意电影诗化表现的一种体现手段。基于电影语言理论和中国传统美学,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镜头中的全景(大全景)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山水画,而特写镜头则近似于我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画。因此,我们就以全景和特写这两种景别来论述散文诗意电影画面中的意境感。
说到全景镜头对意境的展现,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由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在这部影片中,黄土地和黄河常常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之上,充当了叙事的主角。而黄土地与黄河丰满形象的塑造则是靠全景镜头来完成的。在这种全景镜头里,黄土地的形象是荒凉而沉重的。天空仅仅占据了很小的比例,而人物则以一种更为弱小的姿态出现。这样的画面其实是有语言的,人们从这一片静态中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古老的传统,是某种不可更改的力量和庄严。和黄土地凝重的静形成对比的就是黄河水波涛汹涌的动。虽然对黄河水的表现运用的也是全景镜头,但导演却有意回避了渲染黄河水的一泻千里,而是拍这条浩瀚大河的局部,这样就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增加了一种温暖感与亲切感。于是,这片土地变得荒凉却不冷漠,沉重但不哀怨。可以说,这种静态镜头、凝固式的视觉感受成为了《黄土地》标志性的镜语方式。而从影片对黄土地和黄河的全景展现上,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气息、一种氛围,一种对古老土地、古老文化的关注与审视。
与《黄土地》中的全景镜头形成对比的是《城南旧事》中特写镜头的运用。因为这是一部以英子的视角表现童年记忆的影片,所以英子的“眼睛”成为了影片重要的表现意象。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此,在本片描写英子眼睛的特写镜头中,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双纯真的眼睛,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英子的内心,体验到的是英子真实的情感。例如英子在街上看到昔日的朋友小偷被抓走的时候,镜头里出现的始终是英子的一双眼睛。但这不是一双普通的眼睛,这其中包含了疑惑、懊悔、不舍、伤感等种种复杂的情感。这些感情是无法通过语言表达的,而这一双眼睛足以道出英子内心丰富且复杂的感情。正是这双眼睛给了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也精妙的传递出了一种画外之音,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悠远意境。
除了画面本身的构图与景别,电影中的色彩也是一种很好的表意工具。正像中国古代绘画中用墨的浓淡重浅来传达意蕴一样,电影也可以用色彩来完成对诗意的追求。任何颜色都是有着特定的表意作用的,因此,每种颜色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而一部电影颜色基调的选择也势必是导演主观思想意识的一种外化与流露。在张艺谋担任导演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色彩就成为了影片诗意的重要体现因素。本片对色彩独具匠心的应用体现在黑白与彩色画面的处理上。在这部影片中,现实生活以黑白的影调呈现在银幕上,相反,回忆却是以一种饱满的彩色展现的。于是,现实的哀伤与回忆的温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现实中,父亲的去世令母亲的生活陷入了彻底的黑暗,相伴走过大半辈子的人就这样先走了,带走了母亲生活的一切色彩,生命只剩黑白。可在回忆中,一切都是那么鲜亮。各种色彩以极高的饱和度出现在银幕上,比如母亲的红棉袄。在这里,颜色也是写意而非写实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其实更适合用灰暗的色调表现,但当时的感情确是鲜活的,是纯真的,正如这些饱和度极高的颜色。正是这种色彩的应用,使影片弥漫着一种浪漫的诗意。
以上简要分析的是散文诗意电影如何利用画面造型元素体现独特的诗意,下面来看一下声音这一元素在影片追求意境上的作用。电影是一种影像——声音的综合性媒介手段,因此声音对于影片来说是一个同画面一样极其重要的因素。电影中的声音主要包括音乐、音响和人物语言这三个方面。音乐在电影中最主要的作用即情绪的渲染,而在有些电影中,音乐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电影叙述的角色。例如电影《城南旧事》中的主题音乐《骊歌》。在二十年代时,《骊歌》就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学堂歌曲,而《城南旧事》中对此歌的重复性表现更是使这首歌再次获得了流行的生命。在影片中,这首歌以不同的变奏形式贯穿了整部影片。它是英子对于童年一份珍贵的记忆,同时也是英子内心世界的含蓄表现。在不同段落的歌声渲染下,观众的情感得到了有效的积累,从而也获得了逐次增强的情感冲击,直至与影片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成功的音乐的使用,才使得本片在视觉、听觉的双重空间中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记忆中的童年,也才使影片有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意境。
而在人物语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散文诗意电影多采用画外音的形式,如《小城之春》、《城南旧事》、《青春祭》、《那山 那人 那狗》、《我的父亲母亲》、《草房子》、《暖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画外音的形式是一种小说式的语言,而它之所以被广泛的运用于散文诗意电影中,也是由这类影片的特点所决定的。散文诗意电影表现的多是细腻的情感,是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但这类影片的主人公常常是寡言的,语言不是他们宣泄情绪的主要工具,于是画外音就成为了他们与观众沟通的一个有效手段。就像海德格尔的论断:自然语言由于与人的亲近性而具有一种对于人的心理活动和感情活动的特殊表现力。因此,这种画外音形式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影语言对于人的亲近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画外音这种形式也更利于表达影片意境。画外音带来的多是一种对于往昔岁月的回忆,而回忆本身就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过去的现实生活在人脑中的一种诗意化存在形式。因此,主人公通过画外音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夹杂着怀念和感慨的朦胧的诗意感。
综上所述,对电影语言风格化的运用形成了中国散文诗意电影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注释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