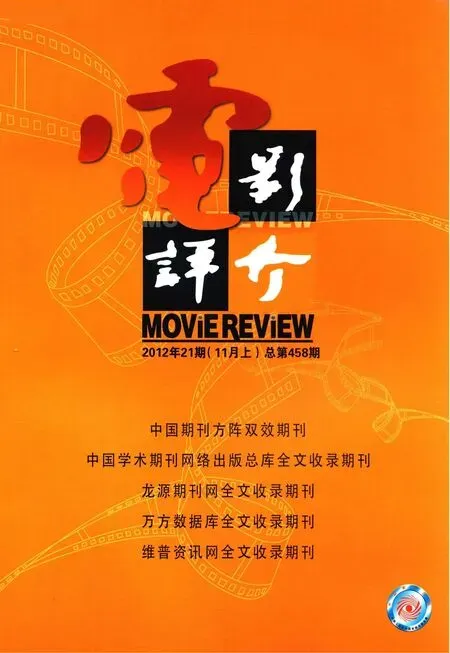纪录片对观众的时空场效应
纪录片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五个:电影院、非院线系统(如一些团体、俱乐部放映等)、电视台、碟片和网络。近年来,只有《较量》、《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圆明园》等几部屈指可数的电影纪录片进入影院,它们的出现,成了中国纪录片产业化的一个标志。2007年3月21日,由上海纪实频道和上海新天地国际影城主办的首届“真实中国影院计划”启动,打破了以往故事片垄断影院的局面。《圆明园》、《故宫》、《东》、《布达拉宫》、《龙脊》、《谁刺杀了陈果仁》、《平衡》、《幼儿园》、《房东蒋先生》、《小人国》等优秀纪录片陆续进入影院放映,但也反映了在中国纪录片通过院线放映的困难,再加上地域性的限制,它的观众更是无法与故事电影相提并论。通过非院线系统放映的纪录片大多带有明确的团体目的性和文化性趣的选择性。由于时空的客观封闭性,观众在一种强制的环境下大都接受了节目的内容。电视则介于电影院与非院线之间,它是纪录片放映的主要平台。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构建公民意识是它的责任,也是社会赋予它的任务。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的观众,总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顺从地接受电视传播的内容和文化,尤其是纪录片。
一、纪录片对公民意识的唤醒和启迪
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和教育的普及,媒体逐渐脱离精英藩篱,走向大众,人们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平等地获取各种信息,信息和反馈的双向流通也空前畅达。在传播与反馈的过程中,作为民族国家意识“传声筒”的大众媒介承担了构建公民意识的责任。公民意识在经媒介的传播后被作为受众的私人接受,转变为可以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公众意识。追求客观真实的纪录片,在对社会现实的记录过程中,自然会流露出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对大众的集体规训。强烈的公民意识就在这种关怀和规训的过程中传达并被公众接收。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清楚以下几个概念:
“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从其产生来看,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部分。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不论其年龄、性别、出身、职业、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依法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国家在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时候,必然要对其公民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其核心正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同于公民意识,公众意识相对来说主要源于公众对某一公共事务或自身问题所产生的自发意识。所以,两个概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公民意识来自于传播者,特别是主流文化纪录片中创作者所倡导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而公众意识则来自于受传者,他们在受到社会环境、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受到纪录片中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所自发产生的一些意识。如何让大众传播中的社会事务被作为受众的私人接收,进而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公众效应是大众传媒以及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舆论宣传或者舆论监督,这对于提高受众的公民意识有积极作用。纪录片,尤其是主流文化纪录片,构建公民意识是它的主要任务。无论是《话说长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还是《丝绸之路》突显国家开放、交流的重要性,还是《森林之歌》对保护自然的强调与暗示,都在潜移默化地构建公民意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振兴民族意识有关,与对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启发有关。那么纪录片是如何构建或增强公民意识的?
从“纪录片”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对真实的追求是贯穿其始终的。但是,主观性就像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诅咒命运一样,又是生而注定,挥之不去的。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如果纪录片代表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那么,构建有利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公民意识就是他们的重要任务。纪录片力图使观众忘记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即忘记他们是坐在电视前观看纪录片的,“这样有利于他们想象而进入那些展现在银幕上的事件中去,就好像有待了解的只是事件而不是电影;只需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无须知道影片本身的拍摄情况。”[1]为了让大部分观众进入创作者预先设定好的话语时空中,接受纪录片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力量,纪录片与电视企图对大众“合谋”。
纪录片制作者是对他人进行讲述。“无论是关于一个时事事件,还是一个个体,讲述都为影片感受到公众意识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氛围。”[2]无论是流露着的个人思想,还是隐藏着的国家民族意识;无论是使用“我们”还是“他们”,纪录片始终是在讲述一些东西,它的对象是站在媒体面前的受众。纪录片特别是一些专题片通过各种手法将电视机前的观众统一到自己的意识形态范畴。作为个体的受众,在没有被某一组织召唤之前他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在个体独立的空间里,他是不受约束和规范的。但是在媒体构建了一个公共领域之后,思想的碰撞让每一个个体开始思考利益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观看电视时的观众是暂时与现实社会脱离的,观众投身于电视所构建的虚拟时空中,跟随着这个虚拟时空中或直截了当或通过暗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纪录片创作者再把要解说的对象包装成一种公共利益物品,使之容易在受众的思想中产生“共识”。这种所谓的“共识”在纪录片的解说中被传达出来,在传统的或主流的价值观参照下传递新的意识形态思想或强化已存在的主流价值观。“长江”系列纪录片对祖国河山的赞美和对改革发展进程的记录极易引起民族自豪的共鸣;《大国崛起》对世界历史中大国兴衰的探讨启迪中国未来发展之路和振兴民族的意识;《舌尖上的中国》则是通过对美食的传承发展来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情感共鸣。
当对公共领域中思想产生认同的时候,公民意识开始觉醒,强烈的、高昂的情绪就会产生,极易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当电视机前的个体吸收了纪录片中构建的公民意识,将其自发地带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并影响现实生活中受众行为的时候,公民意识完成了向公众意识的转换,从而完成了对纪录片中构建公民意识的真正认同。
二、观众接受式观看的时空场效应
1、电视的“冷媒介”属性
现代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观众对它所传播内容的接收,实际上是经传媒的私人接受。信息接受的私人化和隔离状态,造成了公共生活的死亡。相对于现代的网络媒体来说,电视媒体术语“冷媒介”,受众参与的程度不高。“相对于那些为影院播放而制作的电影来说,电视纪录片的图像和声音质量粗糙,内容显得不够浓缩集中,缺少热情、节奏缓慢,而且过于随意,使得在审美和情绪上不够‘热’,是一个冷媒介。”[3]而影像播放的过程更是一个“冷传播”的过程,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影像和声音所传达的内容,即使有不同的观点,也无法即时地与之交流、讨论。
但是,随着大众传媒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为了迎合最大限度的大众需求,很多媒介不得不调整其文化商品的内容。纪录片虽然一直都在追求客观真实,保持纯净精神指引的姿态,但是,当它选择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之后,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成了它的指标之一。在这里,公众的批判意识逐渐让位了给了大众消费观念,批判意识逐渐消失,只停留在少数人身上,这股批判力量远不能抗衡人们对大众消费的狂热。于是,在有限的私人空间里,交流和批判被无形的障碍阻挡,私人接收状态下少了群体的盲从和暴力,少了反叛和抵抗式的阅读,在相对封闭的时空里顺从地接受影像中传达出来的“声音”。
2、观众的求知欲望
在信息社会,有多重因素鼓舞着人们去求得知识,获取信息。面对强烈的竞争环境,“知识就是力量”被现代人奉为真理。对未知历史的探究,对浩瀚宇宙的好奇,让一切能满足人们窥视欲的事物都备受追捧。“‘历史瞬间’的目击者是有限的,而人们对‘历史瞬间’的‘知情权’是无限的。”[4]
纪录片由于它广袤的涉足面,以及对事实真是的追寻,使得它成为现代人追捧的一部大百科全书。无论是对科学的探究,还是对历史的探索,还是对自然的发现,还是对生活的记录……任何一点都足以吸引求知者的青睐。
3、观众对纪录片的指向心理
由于摄影影像对现实世界具有强大的复制功能,所以在观众心理上极易产生 “真”的指向,加之观众自身能力的有限,大都(主要针对普通大众来说)采用接受式的观看心理。同时,纪录片由于它广袤的涉足面,以及对事实真相的追寻,为现代人构建了一个大百科全书式的时空场景。无论是对科学的探究,还是对历史的探索,对自然的发现,对生活的记录……任何一点都足以吸引求知者的青睐。真实性本身容易让其它观点和意见失语,所以电视纪录片的真实性则最容易构建相对封闭的时空场。从《望长城》开始,纪录片制作者们明显认识到,如果想让观众们真正关心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唯有让他们看到最真实的记录场景。所以在《望长城》中大量真实记录的镜头给人印象深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寻找民间歌手王向荣的过程记录,打听王向荣家在何处时碰到的牧羊人,以及找到王向荣家时焦建成与王母的一段情感交流都是自然真切的生活流程,观众无法不接受这样的情感召唤,自然地就融入到影像所设定的时空场中。
4、观众对影片背后机构性组织的信任
受众都有相信权威的心理,当人们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进行选择的时候,权威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如果纪录片是由中央电视台拍摄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对该影片的纪录片身份,以及它可能达到的客观性、可靠性、可信性的程度都会给予较多的肯定。作为观众至少会预想,这些影片具有非虚构的特性,是对我们所共享的历史世界的表达而不是影片制作者想象性的创造。
三、结语
在观看纪录片时,由于以上因素的陪伴,观众与电视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环境。在这个时空环境里,电视纪录片通过解说词展示着话语的权力,观众则像个小学生聆听着来自解说的声音,电视也通过这种话语权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思想意识形态,并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注释
[1][美]比尔·尼可尔斯著:《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2][美]比尔·尼可尔斯著:《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3]何苏六著:《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4]肖同庆著:《影像史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