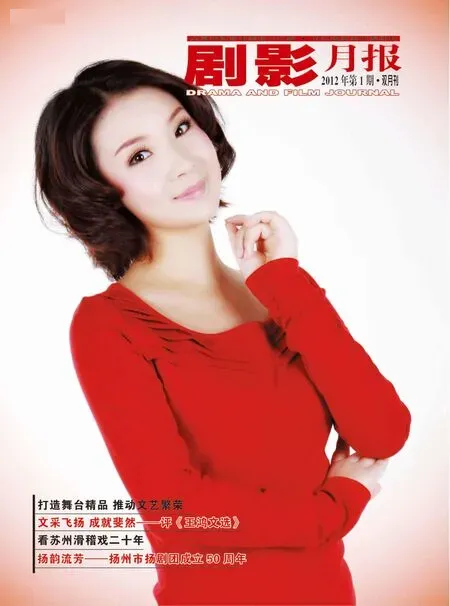扬州评话中的间离效果
——简评惠兆龙先生《武大郎娶亲》
■胡展
扬州评话中的间离效果
——简评惠兆龙先生《武大郎娶亲》
■胡展
间离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的著名学说,布莱希特1936年在《娱乐剧还是教育剧》一文中初次提出并阐述了间离(孙君华《试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间离的本质是“陌生化”,简而言之,就是让观众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扬州评话是扬州地方文艺的一朵奇葩,近年曾在扬州发现汉代的说书人俑,可见这一艺术的历史悠久,一般认为扬州评话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明末扬州著名评话艺术家柳敬亭。一般认为,扬州评话讲究说表惟妙惟肖,让听众如身临其境,“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扬州画舫录》),显明地与让观众“不融入剧情”的方法是背道而驰的。那么间离与扬州评话又有什么联系呢?近日重听著名评话大家,全国曲艺牡丹奖得主惠兆龙先生的《武大郎娶亲》,深感间离效果在扬州评话中的重要作用。
《武大郎娶亲》取材于《水浒》。潘金莲年轻貌美,因与潘太公有染,被太公夫人设计嫁给了“三分象个人,四分象个鬼,并起来七分数”的武大郎。故事很简单,既无“打虎”的紧张,也无“三盗九龙杯”的曲折,更无“王英打店”的火爆热闹。但正因为简单,反更见演员的功力。惠兆龙先生有几十年的艺术积累,在说这段书时厚积薄发,举重若轻,将一段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说的高潮迭起、妙趣横生。
扬州评话讲究说表细腻,在说这段书时,惠先生深刻揣摩不同人物的身份与心理,将梳头妈子的尖刻、媒婆的油滑、武大郎的拘谨与幼稚刻画的惟妙惟肖。但这段书里有一个主要人物,竟然一句话也没说,却依旧让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就是老安人。且听这段表“那怎么办?哎,她倒这么大了,干脆代她配人。她要配个配不得的人,把她推下火坑。”惠先生将老安人的心理活动处理成表,从旁述的角度说出。表演时语速低缓、语调阴沉,一字一句用力喷吐而出,将老安人的愤懑的心情、阴险的动机、残忍的手段刻画得入木三分。实际上老安人是一个“拙口钝腮”之人,她说话的语气、语速应当都不是这样,若是将她的心理话原样模仿地说出来,不但枯燥,而且反而影响了这个人物的塑造,说不定会使观众产生同情感。惠先生的处理使听众从这个人物的表面间离出来,深刻理解到了她的本质,使观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扬州评话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动作传神。惠先生在表演陈毅,举手投足间将陈毅的儒雅、自信、镇定与不怒而威的气势挥洒得恰倒好处,因为被誉为活陈毅。《武大郎娶亲》风格是喜剧,描写的近十个人物无一不丑,这就决定了在表演时动作尽管要传神,但不能太像,而且必须要夸张。“这个小伙上去打了一恭。‘我小人见安人请安。’接着就曲背哈腰。你哈吗,还有数些,难为他过哈很了,直接是脊背朝天。”在说表同时,惠先生做点头哈腰90度,浑身缩成一团的动作,若是严格说来,这一系列的动作无疑是过了,并不符合这个人物,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境。惠先生正是通过这一夸张的动作,将这一人物趋附权势的“丑”放大,将老安人故意刁难这一事实放大。观众看了,反而觉得更为贴切,往往发出会心一笑。扬州评话动作的传神,不是要求百分百整齐划一,而是要神似,要更好地表现人物。
扬州评话在表演时经常通过口头说表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描绘景物、抒发感情。看这段:“金莲在轿子里头跺足捶胸、放声大哭,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潘金莲在轿子里头哭,有一个人快活呢,哪一个?武大郎。武大郎跟在轿子后面,跑得爪爪的,口水洒洒的。什么道理?一钱不花,老婆到家。”在这篇书的结尾,介绍了两个当事人结婚时的表现,看似闲笔,却另有深意。这里暗含三评:一评这场婚姻:不平等、不和谐;二评潘金莲的表现:跺足捶胸,反应十分强烈;三评武大郎的表现:懵懂欢欣,举止失态。这三评为后来潘金莲叛夫杀夫留下了伏笔。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表演者无意玩深沉,无意将悲伤气息留给观众,而是将千言万语,化作观众的又一次粲然一笑,更多的回味,却在散场之后。
“间离”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把二者融合为一,实际上就是要求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以惠兆龙先生等为代表的扬州评话演员们正是这样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