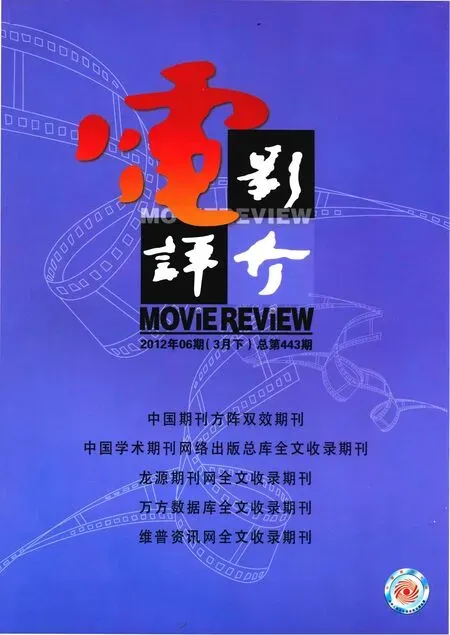谈土家服饰的研发与时尚
一
土家服饰的研发,有一问题是老生常谈:“什么是游客希望看到的土家服饰,同时又是本民族成员爱穿戴的服饰?”头一句,说的是游客希望看到的土家民族服饰承载着民族文化元素的“魂”;后一句,指的是民族成员希望自己的族饰是承载着时尚审美元素的“魄”。说白了,这就是土家服饰的研发与时尚的关系的问题。长久以来,民族服饰的研发者有一个误解,好像一讲“民族”就不能时尚;一讲时尚就不能“民族”。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谈起“土家服饰”时,有一位朋友问我,倒底什么是土家服饰?笔者不假思索地反问说,倒底什么是汉族服饰?这看似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文化困惑:谁见过一成不变的土家服饰?但谁又见过一成不变的汉族服饰?可以说,谁都见到过,又谁都沒有见到过。这回答是一个文化佯谬: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对服饰上一些民族文化符号和文化元素的记忆;谁也无法见到那款“一成不变”的民族服装,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唐装可以说是设计得最成功的中华民族服饰吧,但那是“唐”装吗?那只是一款“中华文化概念装”,被世界各国元首都穿著亮相,所谓“闪亮登场”,隆盛推介,任何广告也沒有这么强大的“元首效应”,一时间,为服装业带来财源滾滾。但是,在火了一阵之后,也从市场上逐渐淡出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许多业内人士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土家服饰问题,不是一个文化的“伪命题”。因为全世界服装在新潮流引领下的趋同,谁也无法阻挡这股时尚潮流闯过民族的风雨桥和山寨篱笆。所以,要研发出一批让游客希望看到的,而又受本民族群体喜爱,同时又愿意穿着的服饰,实在是一项艰巨的商业性文化工程。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土家服饰文化的研究,已经摆脱了曾经的天真,从而走向了认识上的成熟。它表现为——
一、“摆脱”了在那些土家“化石服饰”上无益的纠缠和心思的浪费。比如,学者们都爱说到《黄师姐》的服饰,尤其那根“丝帕子”的事,黄师姐时代,如果也有旅游业,(我是说“如果”),那么,它的确能赶上当年的服饰审美时髦。因为当年中原妇女的头饰,己经是满头皇皇:如银簪、金钗,流苏、步摇。对比下,黄师姐这位漂亮的土家女巫,〔1〕确实创造出了当年中原游客所希望看到的“菩萨蛮”形像,在山外人眼里,能产生“异域美”的冲击效果。但如果让它戴在今天土家青少年女性身上,作为窗口展示,合适吗?这套“化石服装”的文化价值,在于它锁定了“曾经”。它说明黄师姐时代,土家服饰己由蔽体遮羞、防寒保暖的服饰诉求,转而有了“行路又好看,坐到有人瞧”的服饰审美诉求。但“曾经”的东西,只适用于“曾经”,并不适用于今天。
二、研发中,学界己开始注意到,应该展开对“服饰污染”的治理,对那些“转基因”土家服饰的逐渐淘汰和摒弃。所谓“转基因”服饰,是指把任何民族的服饰,只要觉得其特色可以“为我所用”,就引进来,加长续短,综色杂佩,强加给本民族成员,这就是“转基因服饰”。转基因服饰不仅太扎眼,而且它的危害还在于:使固有的民族服装失去特色,造成服饰污染。
如,眼下那些大红大绿的腰鼓队、民族舞蹈队的服装,还有许多旅游景区经营“农家乐”的农民,他为了宣传民族文化,招徕游客,都能自觉缝制民族服装。但是,他们所穿戴的服装,只有花哨,没有土家文化符号和美感,而它们偏偏又像稗草一样,生命力极强,满街都是。这类服饰是在沒有民族文化观照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产品,从而造成对土家服饰的“污染”。这当然不能怨广场的大婶大妈们,她们穿著土家服饰的热情,是难能可贵的,这热情也正是今天旅游窗口所需要的,她们活动在城市这个最显眼的窗口:广场、大街,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知道,她们都在展演本民族文化,应该爱护和鼓励他们这种穿着民族服饰的文化热情。但是,让她们穿着这身不伦不类的服装,外地人透过“窗口”看到的是土家服饰吗?如果有关部门能为她们制作出外地游客希望看到的那种土家服饰,也为了新研发出来的那些较成功的土家服饰能够迅速普及,有关部门是否可以考虑对他们进行补贴费用的方鼓励购买,使她们成为活跃在文化窗口的漂亮的土家人形象,成为理想的土家文化风景,成为能游走在窗口的免费公益广告。
二
王平先生在谈到对今天的土家服饰的研发时提出的近似值是,“游客希望看到的”那种服饰。〔2〕
什么是游客希望看到的土家服饰,同时又是本民族成员爱穿的服饰?专家学者们在理论层面上己达成了共识:即提练、升华土家服饰的文化元素,用文化符号作为民族服装个性化标志。这是土家服饰的魂,把魂附在“时尚”这个魄上,就会设计出民族个体既爱穿又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所以服装设计不能“抛弃”时尚,如果这样,服装反而会被时尚所拋弃。时尚好像挂历,必须不断地被撕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时尚是短命的;但它又在不断更新自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永恒的。所以,“时尚”与“土家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服装,也会过时,但被抛弃的是“时所不尚”,它又会不断地跟新的时尚结合。跟时尚不弃不离的,是土家服饰的魂。魂是固有的,魄(时尚)却在不断“趋炎附势”,民族服装也不断“借尸还魂”。循着这个规律,新时尚的土家服装又会出现,形成良性跟进。如果民族服装脱离了“时尚”,那么,最后被拋弃的,将是土家民族服饰,而不是时尚。土家服饰能离开时尚吗?
时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实践层面上已收到了可喜的成效。恩施卅民委、职院主办的《土家服饰特辑》(2008年《鄂西民族》第四期)展示了许多新研发的土家服饰,尤其是该图冊36到37页所展示的服饰,符号简洁,保留了土家族服饰主要元素,又跟现代时尚隐约尾随,而不露行藏,终于找到了服装研发的感觉。这是土家服饰研发工作者前赴后继得到的成果。虽然全冊所展示的服装中,也有许多符号用得过多,有的在元素和符号的使用上欠“巧”……但“看者容易做者难”,《土家服饰特辑》中那些精美的服饰,本身就是最好的研发范示,可以试行推介穿著,并让它们永远置于市场的诉求和修正之中。
三
土家服饰要成为民族个性化的标志,研制者要想把土家服饰发展为产业,就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向民间广泛搜集传统上曾经喜闻乐见,又被丢失的文化符号,使服饰上的土家文化元素更加丰富多彩。据笔者所知,土家民间,遗存有大量尚未被发现,而又可以用于土家服饰的文化符号。其中除了被广泛使用的“白虎”符号、西兰卡普作符号外,民间还有许多可以为土家服饰所用的符号。这里列举几个土家创世文化中有关生命原型记忆的符号。一、“长春合欢藤”:是两股绞缠的青藤,是一个把“二蛇襄芜”(“交合蛇”像)图案艺术化、抽象化、最终符号化的结果。这个生命活动的符号,是土家人为了对本民族人种起源记忆精心的创作和浓缩,也是民间文化力所能及的艺术处理。它的文化隐喻,是土家始祖傩公、始祖母傩母(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创世神话)生命创造的原型。该图案原来多用于帐檐绣花,手巾绣花,由于它的改造空间大,既可用于上衣排扣的两侧作饰文,也可以用作襟袖花边,使用起来如西兰卡普花边一样方便、随意。二、土司城李超先生很喜欢一个符号性图案,这里姑且为它命名为“阳石一箭”。 “阳石一箭”是一个园形图案,不知原创者为谁。是浓缩廪君与盐水女神故事(土家经典神话)的符号化。三、“栏杆(杆栏)眺月”,又叫“眺月求子”,这是当年庄园财主嫁娘新婚期使用的头饰名。“栏杆”,是一条加了硬衬的绣花条纹头箍,如土家吊脚楼栏杆,上绣有杆拦式条纹,尾端缀有钮扣或系结带儿。“月”是缀在头箍中央的圆形绣牌,是一个直径比栏杆略长的圆牌。上面绣有一株车前草或葡萄串,这是多子的符号。这符号是1956年冬,笔者的一位亲人从芭蕉乡硃砂溪一位龙奶奶那里见到的……对这类符号,很可能由于我们不能作出准确的文化解码,而被弃之如草芥。笔者相信,文化工作者只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田野”,一定会发现许多民族服饰元素。
土家服饰有了丰富多彩的土家文化元素和符号,又能巧妙地与时尚结合,让时尚变为土家的时尚,就一定能理直气壮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个性化标志,在研发上就会更加自由,设计空间也更加广阔。因为服饰可以千变万化,而它的民族文化的内核,不会变化和丟失。由于民族凝聚力越来越高,文化振兴的热情越来越大,民族服饰的内核只会越来越彰显。
绞尽脑汁对民族服饰式样研发,不如用心地研发服装符号。这里说“研发”,是用心地把民族服装文化元素提炼成文化符号,有了个性鲜明的符号,服装就有魂。做“民族文化概念服装”,比如蔡元亨先生所列举的“虎装系列”,就像把校徽戴在学生胸前,不管它穿什么衣,都会认出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一样。何必勉强民族成员去穿那些花样翻新的对襟大褂呢?
当然,把民族文化元素提炼成文化符号,不仅属于工艺范畴,更是属于文化实用学的范畴。由于旅游业的刺激,土家民族服饰的研发,也不仅是民族文化问题,更是时尚问题、经济问题。
〔1〕蔡元亨 大魂之音:巴人精神秘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1
〔2〕王 平 论土家服饰的当代变迁〔M〕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