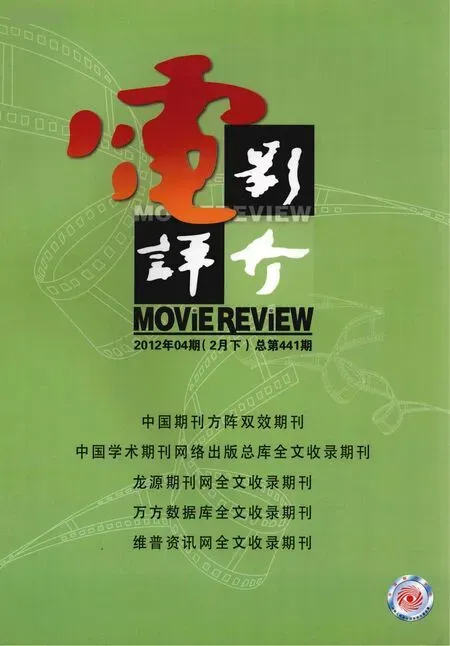电影《金陵十三钗》人物身份刍议
作为电影文本的《金陵十三钗》与原著文学文本有着直系血缘关系,但其效果呈现却有很大区别,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电影《金陵十三钗》视为独立文本存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影视改编过程中人物身份设置的创造性变迁。电影中出现的人物身份可分为:以玉墨等为代表的秦淮妓女、以李教官为代表的中国军人、以书娟为代表的教会学生以及洋人入殓师约翰。
《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并且在多部文学及影视作品中以多种形式反复出现,因此这些作品从题材上皆被视为有关大屠杀的“南京”叙事。在“南京”叙事中始终未曾脱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框架,作为救赎模式的经典故事,创作者要追求普泛化的情感表达并创造个性化的审美旨趣,其中人物身份背后的内涵延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每个表层身份背后都熔铸了对于身份类型的深层内涵,对这方面的深入探讨更是解读这部电影的重要途径。
一、妓女与侠女
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河畔妓女是故事的核心角色,妓女形象自古有之,也是艺术作品中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表现对象,但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这些女子的身份背后首先隐藏的是侠女身份。她们是救赎主题的具体实践者和殉道者,并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将自己的妓女身份淡化直至彻底置换,最后以侠女的精神本质走向传奇书写,从而在身份定位上造成巨大的审美落差,实现戏剧突转,完成英雄叙事。其实她们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具有连续性的身份结构,与尸骸遍野的悲凉景象和残暴骇人的杀戮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热出场——扭捏妖娆的身姿、纷繁魅惑的衣着、烟花教坊式的怨怜喧哗,但其中主要视角又落在对玉墨内敛、含蓄、贵气、神秘等精神气质的呈现,俨然是对于传统“侠风”的摹写,这些都表明了她们身份的特殊性,也注定了她们夺目的主体表达,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传统书写中常规的负面表达,也标志着对其身份的独特审视与肯定。十四个秦淮妓女华贵风情地大步走向教堂的镜语表达更是带着浓重的侠士情怀,与大气洒脱放荡不羁的青楼风范相结合,协调统一的情感契合把这些女子通过性和肉体去交换物质生存的现实尴尬遮蔽不见,同时隐去了对其社会身份和性别价值的公众认证,只剩下单纯美好的样貌与矛盾又神秘的欲望。
这种对于女性主体张扬的审美再现,绝不是片面的以隐去负面效应来突出正面效应。这些妓女也并非属于“恶之花”式放弃灵魂、欢纵肉欲、沉沦堕落的底层妓女,而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反而更带有“同是天涯沦落人”般强烈情怀标识的人物群像,但又区别于经典文本《桃花扇》中李香君式“抨击奸佞热爱国家的妓女形象”[1],而是将有情有义置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之下,她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与教堂里的教会学生一样。对于这些妓女的侠义书写姿态也是她们身份转变的开始,从妓女身份变为侠女身份的过程在经历了她们与教会学生的冲突之后随着日本军队的介入也变得清晰起来。教会学生在日军进入的刹那放弃钻入地窖而掩护她们的行为,让叙事关注从妓女们的外在样貌和身份转入其内心层面的深层探寻,她们被学生的义举所感染,也唤醒了外在社会身份掩盖之下的“情义”,虽然是被动改变,但无疑这种叙事逻辑是完全合理的。妓女身份也随之合理地走出传统的边缘定位,融入到主流的社会价值中,进入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直到最后选择代替女学生去赴一场生死未卜的灾难,舍身而取义。这种救赎模式,是典型报恩式的侠义表达模式。
一直被排挤在社会伦理之外的妓女形象,道德和政治责任是不必负的,她们的正常存在恰是威胁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因素,身份的重新编码是对地位和价值的置换。边缘化的有情有义的妓女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妓女,她们的身上带有了很强的奇观性,地位和价值的提升使之一跃从被救者变为拯救者,她们身上被付诸了无限的希望。在教会学生面前,她们褪去青楼妓女的外在身份后,消解了显性与隐性的双层对立和障碍,成为年长的依赖对象,被动强硬地承担起拯救的重任,扶危济困落在一群妓女身上也具有了必然性,也成了“叙事奇观”硬性的审美需要。但这仅仅是妓女“情义”建构的第一步,成为教会学生的保护者和拯救者的“侠肝义胆”侧重表现性情中的“义”,要真正呈现其真实立体“重情重义”的真性情,对于“情”的建构则更为重要。作为女性身份下的最为本真的情感欲望的表达,固然离不开与男性的依恋和纠葛,如影片中豆蔻对小伤兵王浦生既怜又爱的复杂情感表现,她为了给临终的王浦生弹奏一曲琵琶,而舍生忘死地奔回妓院寻找琴弦,却不幸遭遇日军残暴奸杀,成了典型的殉情者;美花临赴宴的前夜拿出一副玉镯,交给女学生,流着泪后悔当年因为没信送玉镯的男人、没跟他一起走,这个并未出场的男人却一直藏在她的内心,这份含蓄的爱也不言而喻;玉墨的情感相比较更加清晰,无论是她对于军人身份的李教官的因为崇拜而衍伸出的情感依赖还是对于神父替代身份出现的洋人约翰浓烈直白的爱恋,都是铺垫起她赴难豪情的情感基础。因此,边缘化的社会身份注定的“婊子无情”式薄情观念得以纠正,也为后面十三位女子慷慨赴义提供了坚实保证,她们最终彻底化身为侠女形象。
妓女形象作为影片叙事书写的核心角色,内在的身份转变决定着角色塑造的成功与否。这种转变需要形象塑造的前期身份定位必须是多层次的,侠女的内在身份才是真正表现的叙事重心,救赎的主题内涵附着于她们身上才符合逻辑。
二、军人与儒士
《论语•卫灵公》曾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爱作为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舍弃自己的生命也成了历代儒士遵从的价值信仰。
影片一开篇就是中国士兵与日本兵的惨烈对抗,中国士兵已经死伤众多,就在此时一群女学生逃了过来,为了让女学生顺利逃走,这群本可以突围出城的中国士兵选择了留下保护学生,导致众战士阵亡,只剩下李教官和年轻的重伤兵浦生侥幸存活。这种价值选择固然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然而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壮烈要求极端化——毁灭自我,成就他人,丝毫不带有自我生存的欲求和对毁灭的恐惧感,反倒更为彰显拯救过程中的成就感,这是对儒家社会伦理秩序的充分肯定。中国军人身份的理想与抱负不像西方社会价值模式下的个人主义表达,而更集中表现其内在意识下的集体价值建构,使得故事要求对世俗目标的微观刻画变为对英雄信仰赞美的宏观追求。
军人形象的刻画在儒家社会伦理秩序的大背景下展开,逐渐呈现出以尊伦理懂道义为特色的儒士身份,因此在这些军人形象背后隐藏的“二律背反”也凸现出来:第一,这些军人身份的英雄形象非常勇猛,可以杀出重围出城求生,但同时却也并不能足够勇猛杀出重围,在保护学生的过程中绝非日军对手;第二,他们本应严守部队纪律保存战斗实力不被学生所打扰,但同时军队保家卫民的使命危急之下又使得部队纪律必须舍弃。这样的矛盾悖论,也决定了这样身份的英雄群像必然走向悲剧结局。儒士身份下的末路英雄李教官,既理性又充满智慧,他料定了结局却并不冲动行事,而是暂时丢下军人的尊严忍受妓女们对他的误会将生命危在旦夕的王浦生送到了教堂的地窖,王浦生作为一个被卷入战争的无辜者,不仅是年少的弱者,在身份定位上更不算是军人。除暴安良、抑强扶弱,作为中国古典英雄豪杰最突出的精神特质,无疑在这里也成为英雄塑造的主要情感基调。但更重要的是,在儒家观念仁爱的影响下,其人性温情细腻的一面顿时显露出来,令我们看到一位有血有肉、举智慧重情义的英雄义士。李教官安顿好王浦生之后,又来到教会学生房间的门外,默默掏出女孩子跑掉的一只鞋放在门口又悄然离去,这些细节刻画对于英雄塑造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也不乏刻意之嫌。温情的表达在英雄主义呈现中属于张扬的氛围营造,而儒士身份的要求必须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强调情感的节制和谨慎,[2]当李教官遇到被他英雄气质所吸引并产生依赖的妓女玉墨时,他们彼此的情感却显得十分隐忍含蓄,勇气和毅力俱佳的英雄面对女性魅惑,克己禁欲的传统伦理规范成了他们之间情感表达的无形障碍。
儒士身份超乎常情的极端英雄主义表达,是儒家英雄共同的归宿。李教官最后在教堂对面纸店对大规模日军的伏击,带有典型的英雄传奇色彩,是个人英雄主义最极致的呈现。神勇的武艺展示、深谋的战术安排、惨烈的战争场面,都为李教官轰轰烈烈的结局选择做足了铺垫,将带有史诗风格的英雄豪气渲染到顶峰,完成了军人形象背后儒士身份“杀身成仁”的救赎使命。但遗憾的是,军人角色救赎使命的完结并不是整体叙事救赎主题的实现,身份价值在整体叙事架构中得不到具有推动力的实质性延伸,导致军人群像的塑造在极端个人英雄主义呈现中显得更加单薄。
三、入殓师与上帝
洋人约翰是一名美国入殓师,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贪利纵欲的底层混混。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因为企图得到英格曼神父的丧葬费用,来到教堂却发现并不能得到想要的利益,但仍然执拗地陷入这场灾难,却又继而完成自我内心救赎和对他人的救赎。可见,底层入殓师这样的身份动机设定是存在悖论的,冒着枪林弹雨的威胁和无情的杀戮,一个底层小人物出现在灾难现场,没有足够的诱惑动力驱使且在发现并无所获之后依然不曾离开,直到等待质变来临,这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书写中“欲扬先抑”的叙事手段。同时,底层混混贪婪世故的外表却依然掩饰不住约翰入殓师职业的特殊性,从事与生死相关的神圣性职业身份的隐喻暗示了他绝不是一位平凡英雄,但对于“上帝”式的英雄的塑造却是从底层小人物到平凡英雄再到上帝身份的转化开始,在约翰的双重救赎中完成的。
影片中约翰以先入为主的入殓师身份出场,却由于英格曼神父在轰炸中已经被炸飞无须入殓的黑色幽默导致这个显性的职业身份完全失效,这层预设的职业外衣一旦褪去,使得约翰形象塑造少了束缚变得自由起来,然而同时也造成了人物行动理由缺乏说服力的缺憾。底层小人物被动卷入灾难的叙事模式与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同车同辙,但对于约翰入殓师身份的暂时彻底割裂却导致人物形象也出现前后落差,因此在约翰开始自我内心救赎的时候仅仅依靠他穿上了英格曼神父的弥撒服就得以实现也显得非常生硬。约翰与玉墨的简单调情,很显然约翰出于肉体欲望的发泄远不及玉墨想利用洋人来求得活命更为合理充分,反倒不如着重塑造约翰对玉墨内心深处生出的一种着迷,如此设置或许可以解决前面约翰形象留下来的叙事不足。并且在中国军人李教官这个坚毅勇敢的儒式英雄面前,完全褪去职业身份的酒色约翰更加被动地被推到神圣的对立面,也使他实现“上帝”身份转换的上升空间达到最大化。约翰自我内心救赎的历程,实际上便是“上帝”身份的建构过程,他目睹了豆蔻和香兰被日军残杀后的惨状,并放弃了唯一可以逃离抽身的机会。李教官的牺牲和后路的断绝双重动力为约翰非一般救赎身份最终确立提供了充分的主客观条件,他终于扛起对他人救赎的旗帜,成为尊严和正义的最终庇护者。约翰“上帝”身份的确立对核心叙事即如何实现妓女主动替学生去赴宴提供了保障:他拥有了强有力的话语权,一跃成为所有人的精神向导,并同时入殓师职业身份的回归为其提供了重新塑造人外形与灵魂的万能本领,一切救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玉墨与约翰的情感转变以及在充满隐喻意味的交合仪式,同样也是印证“上帝”的存在和对其神圣的救赎洗礼。最后的一场戏中约翰亲手将金陵十三钗送上赴死的卡车,再开动卡车救出了困在南京城的学生,这种绝妙的灵魂置换,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
另外,影片中的乔治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角色,自始至终没有退缩。他的存在对于约翰身份的成功设定起着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乔治其实是真正的神父,他继承了英格曼神父的衣钵,是典型的布道者,并成为“上帝”约翰的助手和信徒,最终殉道完成自我救赎和整体救赎。
注释
[1]刘道生:《古代文学作品妓女形象浅析》,《钦州学院学报》,2010年4月。
[2]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28-31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