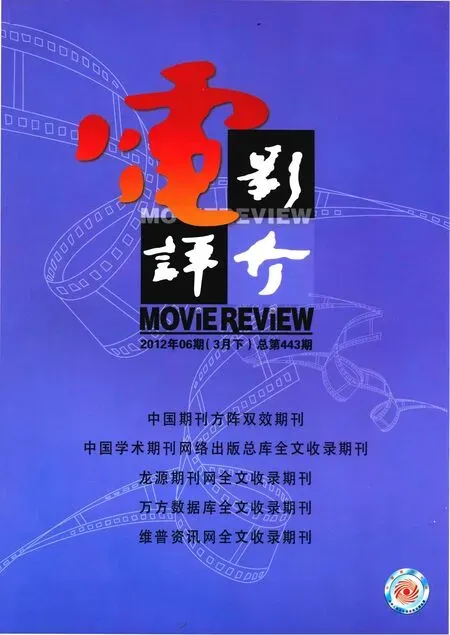从后殖民主义看《阿凡达》
1.《阿凡达》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后殖民电影
《阿凡达》是一部具有技术主义和思想性结合之完美的、典型的后殖民电影。除了故事情节让我们心潮澎湃以外,3D技术的运用给我们带来了梦幻般的奇观,我们对于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轮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影对奇观的依赖、对技术的推崇已被置于电影艺术的特性了。《阿凡达》是我近半年以来观影体验最震撼的一次,它打破了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目前是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它所传达的既有为新技术所催生的全新视觉图景所震撼的表情,又不免在初次接触3D革命的成果时,就因看到一些旧的思维在借新技术的体来还魂而感到吃惊。新技术只是为了更好的包装和倾销一种意识形态,笔者在纳美人的镜像中认出自己的时候,感到一种面对阴谋图穷匕首见时的伤感,原来我就属于第一世界所致力于规训和宰制的“他者”——纳美人。尽管《阿凡达》的背景徘徊在地球与“潘多拉”星球,但其实,讲的还是人类各种族之间的事情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卡梅隆成功的运用了新的3D电影技术,使得他自身赋予了技术主义色彩的头衔,有些评论家质疑3D的到来是电影的发展还是电影的终结?从后现代语境来看,技术的发展促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来临,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后果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这种新的语境中,我们以传统方式建构起来的认识与实践对象必将呈现出新的面貌与特征。继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存在论”角度对技术进行反现代的“叙事”之后。利奥塔把技术看作是现代性的“元叙事”之一,这种元叙事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许诺的自由与幸福,相反它却使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合法化”了。福柯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把技术看作是“知识/权力/道德”的微观实施机制,这样技术就不仅仅是一种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统治策略,同样发现了詹姆斯•卡梅隆隐藏在影片中的野心与殖民的意识形态倾向。另一方面从3D技术本身可以说和好莱坞同龄,在美国电影还在摸索着试图确立一种新的技术形态的时候,3D电影也应该说是一种备选方案,可以说电影和科技是密切不可分的,技术能推动电影的发展,电影是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作品。作为美国电影先驱的埃德温•鲍特早在1915年就进行了立体短片的放映,之后在经典好莱坞时期,3D电影的尝试也屡见不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3D电影始终没有成为主潮。《阿凡达》所掀起的浪潮似乎是要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传统电影的地盘,以宣言的姿态迎接3D电影的诞生,这在评论家和观众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共识,可见卡梅隆无论是在制作上还是在宣传上都要力求达到这种效果。
在影片中有着两种文明与文化的人,一种是地球上的人,另一种是影片中的纳美人,他们是居住在一个叫潘多拉星球上的人。地球上的人是以欲望、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向导。代表人物是军方的迈尔上校,他具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第一世界的价值观等象征符号,他在银幕上的形象给人一种傲慢冷血、不可一世的感觉,他认为只要在武器上面有先进的装备,就可以打败那些纳美人,取得他们想要取得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和纳美人一样有着本体论上的一致,那就是我们所依存的环境,万物相生相克,我们和纳美人一样都是活在自然体的生物园中,是大自然的生灵。因人类的高速发展,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外力来达到目的,而纳美人拥有着庞大的生物资源,这使得西方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人物——“帕克”这个权力者对“第三世界”产生了征服的利益心甚至据为己有的“野心”,而西方一直从远处居高临下的观察纳美人的生活环境,就像生活在潘多拉星球的纳美人不知道一直在观察生活在空间站的人类,为了剥夺他们的资源和家园,创造出和他们一样外形的变形地球人。
这部影片之所以成功,不光是这些因素,还有着将技术与艺术融合得非常完美的属性,在故事情节上有一种深刻的意义,在思想上有一种灵性的意义。卡梅隆在电影这个艺术门类乃至电影史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而技术是她用来更好的解放弱势种族以及更有策略地殖民弱势种族、倾销了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一部在我看来非常完美的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后殖民电影。
2.《阿凡达》中的后殖民元素
美国的后殖民理论家弗•杰姆逊在他近年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阐述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第三世界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正如纳美人一直赖以生存的家园之树被人类的炮弹把他们的文明连根拔起一样,家园之树在影片中象征着文明、母语、意识形态,是他们一切生存的根本。语言的习得可以说在文化习得里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人们能熟练掌握一门语言时,才有可能说皈依了这种文化,认同了这种文化所建构的身份。在《阿凡达》里,杰克的阿凡达如在成长小说里一样,为了成为一个“纳美人”而经历了种种学习和磨难的过程。尽管他学会了所有在丛林里求生的技能,但是他没有学好“纳美语”。他与“纳美人”的交流几乎都用英语,或依靠妮特丽的翻译,最后当他领导“纳美人”抗击侵略者的时候,更是激情澎湃地用英语进行指挥。杰克对英语的选择可以说是对自己西方文化身份的确认,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中指出,文化,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并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而帝国主义在今天不再以领土征服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并进行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殖民、演讲等方式征服后殖民地人民,而杰克最后所做的演讲是推翻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武装霸权,但杰克也变成了赛义德所说的“香蕉人”外黄里白,外部形象是纳美人,内部的意识形态还是第一世界的体现,这同时也反映了第三世界学者思想上的尴尬。
“阿凡达”这个词来自于印度教,意为“神的化身”,在西方语言中一般理解为“变形”,“变形”这个词往往是贬义的。在影片中,“阿凡达”不仅是指为了与纳美人沟通而创造的第一世界的人的变形,还有着詹姆斯•卡梅隆隐藏在片名中的野心与自负,成功的运用3D技术以此达到新技术革命的变形。这是他在《泰坦尼克号》之后蛰伏十余年打造的一部力作,而且这部作品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正式启动了3D电影市场,之后就会有无数的3D大片纷至沓来。迎来了3D电影时代对2D电影时代的取代。可是确切地说,所谓的取代只是技术的变形,但也看到第一世界国家巩固自我的殖民意识和行动的体现。《阿凡达》的叙事结构和人物造型我们早在西部片里就已经司空见惯了,所以该片也只是众多西部片的变形。众所周知,西部片是最彰显美国精神的电影类型。在西部片中,美国白人通过与作为“他者”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对立,从而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地位。正如片中美军将领口中不断念叨的“野蛮人”,与西部片中白人和“野蛮人”的冲突对立,最后以驱逐和屠杀“野蛮人”来实现疆域的开拓一样,《阿凡达》中也是以抢占“野蛮人”的土地和资源为叙事主线的。片中没有明确地指出进行侵略的是美军,而是以地球人自居,但是从一般美国电影中对高科技武装的美军的再现手法来看,只有美军才能担当这样的杀戮大任,该片中军队的战争思维也与美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着紧密相关,这也包括了美国向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军事政策颇为相近。无非是《阿凡达》把事件的发生地扩展到了虚构的“潘多拉”星球,而“野蛮人”也换成了虚构的“纳美人”。这重复的还是一种白人至上的帝国主义、第一世界、后殖民主义逻辑。
《阿凡达》可能会成为如电影从无声转有声时期的《爵士歌手》(和从黑白转彩色的时期的《浮华世界》这样里程碑式的影片。然而,电影还是电影吗?电脑后期对演员表演和形体的大幅度改造和特效所合成的超现实景观从根本上改写了电影的定义,纪录现实的重要性被后期特效的重要性所取代。电影这门巴赞所说的以现实为渐近线的艺术变成了以幻觉为渐近线的艺术。电影的本体被彻底倒置了。电影的幻觉被保留在恰当的距离里,产生于银幕世界与放映厅在“物质上”的隔离,依赖于观众的“灵魂出窍”对银幕内人物的认同。如今3D电影中向观众弹射一个物体而造成观众的躲避不是电影存在的逻辑,最多也只是在新浪潮时期比如说戈达尔的电影中才会出现人物直接对着观众说话的现象。对神圣的不可触碰的观众这一边的边框的冒犯可以说是对电影的冒犯。那么这种冒犯的企图来自何方呢,我敢说当今的3D电影只是玩家无法操纵的电脑游戏而已,同样是电子合成的景观和迎面袭来的物体。法国思想家吉尔•利波维茨基和让•瑟鲁瓦的《全球银幕:媒体文化与超现代时代的电影》中针对对主宰世界的大片美学已经超越了德勒兹所定义的时间-影像和运动-影像,并提出了三个概念:过度-影像、复合-影像和距离-影像。简单地说这三个概念分别是指:电影中速度、节奏、暴力程度急剧提高的现象;影片时空的调整和形式的复杂化;自动指涉性,即电影不断指涉自身。然而,这几个概念还是难以涵盖3D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们也许可以创制出如合成-影像或互动-影像之类的概念。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3D从一开始就加入了blockbuster的阵营,它不可企及的天价制作费用和强势的意识形态散布手段注定使它成为美国进一步控制和剥削世界的利器。
“纳美人”作为“他者”的代名词。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作为“野蛮人”的“纳美人”到底是些什么人的时候,就会发现更大的问题。无论是对白人杰克的“阿凡达”的脸部分析还是对“纳美人”妮特丽的分析,都可以提炼出“纳美性”的基本因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纳美人”的那条清朝式样的长辫子。长辫子可是有着很长的历史,在英文中长辫子被称为“pigtail”,即“猪尾巴”,在西方辱华的历史上pigtail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时至今日辫子仍然是西方人丑化中国人形象的素材之一,在《阿凡达》中长辫子还有着沟通动物和神灵的功能,可见卡梅隆赋予了这条清朝式的长辫子一种原始的、兽性的力量,这显然不是西方人在抬举我们,而是将“东方人”与自恃文明的西方人区隔开来,正如国外获奖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都给西方人塑造了一种民俗奇观,攫取西方的好胃口,一种从东方故事中得到满足的关于对自己的文化优越感认同以及神秘感,“潘多拉”星球正如东方的清末时期,神秘感驱使西方人不断地窥视、征服、破坏东方文明来制造出“被看”的方式,而东方主义者所处的自然环境、丰富的能源,其实已经勾起了权力者的贪欲,这无异于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帮凶,第一世界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东方主义,正如清末时期,八国联军对华的侵略与掠夺。克里斯汀• 汤普森的博客文章《Motion-capturing an Oscar》中比较了《阿凡达》中演员的前期表演与做后期特效后的结果。她的文章着力于揭示特效在赋予“纳美人”脸部以动物性,也是赋予了原始的、兽性的力量,比如说像狮子的鼻子、像猫眼一样的眼睛。然而我在第一次看到“纳美人”的时候,就认出了他们脸部的“黑人性”:眼睛圆而大、双眼之间的距离很大、鼻子上部大而平坦,还有用一个麻花小辫子扎成的发型。笔者进一步了解之后还发现,饰演纳美人的无一不是少数族裔演员:妮特丽的扮演者、母亲的扮演者和楚泰的扮演者都是黑人演员;而饰演族长的演员则是印第安人。我们还可以在“纳美人”的穿着和生活习性上认出印第安人:纹身、彩绘、羽毛、武器,在丛林中生活,以狩猎为生,信仰万物有灵……“纳美人”长有嵌着耳环的高耸的耳朵,牙齿洁白而犬齿非常突出。这让人想起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大师茂瑙的《诺斯费拉图》中的吸血鬼造型。“纳美人”在造型上是作为白人的“他者”和其它人种与各种动物的混合体,在文化上是非西方文化的大杂烩。因此,意识形态的写入也是通过对身体的塑造来实现的,操作过程是以相当隐蔽的方式来完成的,以致于可以瞒天过海,让全球观众尽情享受好莱坞带给他们的视觉盛宴时而不知道自己就是片中的“纳美人”或者是做的事情就如人类一样。
《阿凡达》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主义”文本,而处理的手法是主要是将对象阴性化。美籍华裔学者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第一章就分析了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在《末代皇帝》中对溥仪和中国的阴性化处理。《阿凡达》遵循了类似的手法,对白人的他者“纳美人”进行象征性的“阉割”。美军与纳美人的首轮交战中,奥马地卡亚族的族长很快就丧生了,他的妻子作为精神权威的时间也非常短,而楚泰的统治也是相当短暂的。楚泰屈服于杰克作为幻影骑士的威力而心悦诚服地交出了领导权。此时,纳美人是一个阴性化了的需要白种男人保护和领导的族群,而纳美女性妮特丽对杰克的爱慕和纳美人对杰克的顶礼膜拜重复了好莱坞百年不变的处理这种题材时的叙事范式。我们在美国电影的早期时期,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叙事神话:白种男人将有色人种女性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或者是有色人种女性主动爱上了白种男人,又或者更完整一点的是后者是前者的继续,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在一部2009年的美国电影中还会看到这样的故事,不得不感叹好莱坞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播种机的顽固不化和回归到最开始的中心。
如果说美军以军事手段直接进行侵略是过期的殖民伎俩,这以《阿凡达》中的美军为代表的杰克这个人物,他在感召、教化、领导“野蛮人”的新手法可以被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升级版,即后殖民主义。我不同意很多西方评论家所说的卡梅隆否定的是西方式的文明,想要创造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人。恰恰与之相反,卡梅隆所拥抱的是后殖民主义的统治策略,一种更高明、更“人性”的统治术,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帮凶的好莱坞也绝对不可能生产一部否定西方的电影。在约翰•福特的西部片《日落狂沙》中,由约翰•韦恩饰演的里森去认领被印第安人虏去多年的侄女黛比时看着两位目光呆滞的白人女孩不禁感叹道:“难以相信她们是白人。”在看《阿凡达》的过程中我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难以相信杰克是白人。”然而,他确实是白人。他是以白人的精神来感召绝望的“野蛮人”与“邪恶”的白人进行对抗的“善良”的白人。诚然这不是一部宣扬和平的电影,而是一部宣扬暴力的电影。宫崎骏的动画片《百变狸猫》触及到了类似的主题,人类对自然的摧残导致了自然的报复。而在《阿凡达》里自然的报复始终没有出现,最后竟是通过塑造一位变了形的白人英雄来完成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这才是影片立意的重点所在。
结语
影片中有着强烈的后殖民主义色彩,对于潘多拉文化来说,任何文明都是先进的文明,文明不存在优劣之分。电影是一部可以从意识形态和叙事语言方面去寻求东西方的沟通的文本。一方面是民俗的奇观性、变形性构成了西方观众对东方世界或者是边缘世界有着好奇的窥视欲,另一方面又在电影的观念、意识形态、读解传统以及技术革新发展上尽可能去迎合西方的口味和习惯,这确实是帝国主义霸权,将第一世界的优势用极多例子来强制灌输给第三世界,电影走向的趋势以及技术的发展是第一世界所运用的成功策略,也是他们对第一世界文化的全球性支配地位所表现出的有意认同,作为第三世界不管是无奈的必须,还是自觉的臣服,总之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有意识地把西方的窥视欲包括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了,这种包括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第三世界影片的发展和创作,但我们所要关注的其实是文化殖民的内蕴以及它的历史走向。
[1]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